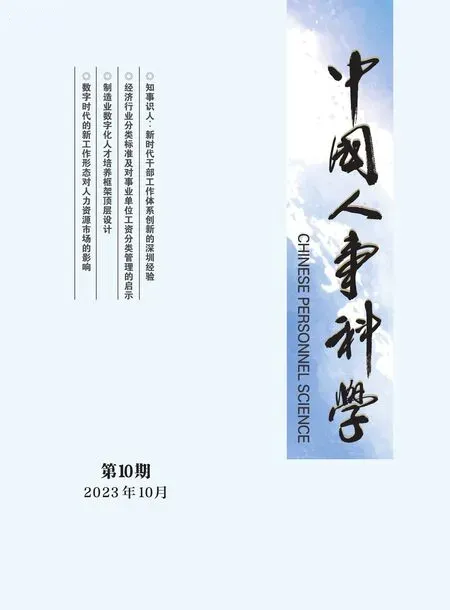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新工作形态对人力资源市场的影响
□ 吴 帅
一、引言
工作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受生产空间、生产要素及生产工具的影响较大。在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工作形态:一是原始经济形态下,人们主要的工作方式为集体狩猎;二是农业经济形态下,家庭式小生产成为主要的工作形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生产规模相当小;三是工业经济形态下,工业化大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雇佣制成为主要的工作形态。进入数字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正加速改变传统的社会分工,人类社会面临新一轮的工作形态变革。例如,平台作为新的生产组织已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在传统灵活就业形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平台网约、“微创客”等新工作形态;又如,在智能化生产工具的作用和影响下,远程办公、人机协作等正成为新的工作形态。
“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2015 年,德国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题为《重新设想工作“工作4.0”绿皮书》的报告,掀起了一场有关“工业4.0”背景下工作形态变革的讨论。2017 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全球未来工作委员会”,重点关注工作与社会的关系、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作的机会、工作和生产组织以及工作的治理等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业和人的发展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本文聚焦工作形态问题,从数字时代的工作场景与要素变革出发,基于我国实践,分析梳理新工作形态的主要类型、特点以及对人力资源市场与流动管理的影响,旨在勾勒数字时代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的未来图景。
二、数字时代的工作场景与要素变革
劳动过程理论认为,技术条件和社会关系共同塑造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过程。[1]在数字时代,通信基站、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正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的业务流程和交易方式。业务上的跨界以及产业间的融合将逐渐打破传统的业态边界,进而催生一批跨界新业态。具体来看,数字时代劳动过程的底层逻辑正发生以下变化。
(一)生产空间平台化
根据尼葛洛庞帝的预测,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平台将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的重要载体。[2]相比传统的生产空间,数字化平台的显著特点是虚拟性和中介性。它们在用户群体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将有相互需求的不同市场主体聚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技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促进各方互动和交易。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生成内容成为社交媒体平台占有和支配的使用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用户加入,用户数据则被平台出售给广告商转化为平台利润。”[3]
在传统的生产空间中,相比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消费者在信息获取方面往往处于劣势。而数字化平台中,数字化连接将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组织的生产效率和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大幅提升。各类数字化平台作为虚拟空间,可替代传统实体空间,为供求双方提供市场信息、撮合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例如,网络招聘平台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改进劳动力配置空间,提供更多和更灵活的工作岗位;物流应用平台可借助算法模型快速分析匹配供需方,并模拟出最优配送路径,从而实现精准高效的线上物流。生产空间平台化还体现为:各种互联网平台将各类生产、生活性数据导入算法系统,加工形成新的生产性数据流,以此来创造经济价值。
在生产空间平台化的影响和推动下,人力资源价值链突破时空限制,使得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在空间上呈现分布式特点。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传统组织边界,降低了人力资源要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壁垒;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有力促进了灵活就业的供需对接。受此影响,劳动力市场弹性增强,人力资源流动加快,劳动者可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受聘于多个雇主,利用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灵活用工平台切换工作。使人力资源市场化流动配置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特点。
(二)生产要素资本化
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人力资源要素深入融合,加速推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换。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体力、技术、技能的分享提供了平台支撑;另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为知识、信息等潜在的人力资本交易提供了逻辑基础,也为社会资本向人力资本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体力、技术、技能、知识、信息、社交资源等通过数据化转化为资本,参与生产活动,并成为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在生产要素资本化的推动下,人力资源加速向人力资本转换,人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体力、技术、技能、知识、信息、社交资源等要素转化为人力资本,弹性参与各类生产活动,从而创造生产价值。受此影响,一方面,影响劳动者工作选择能力的主要因素由过去的制度性要素变为工作胜任力,即技术技能水平高低与多样化程度,人力资源的价值高低将成为影响其交易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户籍、身份等制度性因素不再是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障碍,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不再限定于某一固定的组织内,而是可作为柔性资本进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从传统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跃升。
(三)生产工具智能化
生产工具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物件,介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到了传导劳动的作用。机械化革命带来第一次生产力升级,专用生产工具的发明使人类劳动效率得以大幅提升。电气化革命带来的第二次生产力升级拉开了自动化的序幕,利用化学能、电能、原子能替代人类的生物能,人类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由数字化转型引领的第三次生产力升级,本质上延续了自动化的替代过程,通过应用计算机、机器人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对脑力劳动的部分替代。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互联网、终端设备等成为新的重要生产工具。
在制造业领域,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智能制造不断深化。智慧化工厂依托传感器、数字控制器、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通过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可视化、精益化,从而提升生产和管理效率,实现安全生产。在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机器人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在全面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推动着工作场景从实体向虚拟转变。受此影响,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既不受空间限制,也不受时间限制。例如,随着虚拟现实技术近年来在教育、游戏、医疗等众多行业的广泛应用和深度拓展,远程办公正成为新的重要工作方式。
三、数字时代新工作形态的主要类型
伴随着生产空间平台化、生产要素资本化以及生产工具智能化的深化发展,数字时代的工作形态将从静态的、固化的传统形态转向动态的、变化的新形态[4]。平台网约、“微创客”、远程办公、人机协作等不断出现的新工作形态,为人力资源市场注入新动能。本文着重梳理了当前较为典型的四种新工作形态。
(一)平台网约工作形态
平台网约工作形态,是指在平台经济背景下涌现的灵活就业模式,主要形式是平台型企业通过建立在线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和交易机会,劳动者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以“抢单”的方式,承接服务业务。根据提供服务的内容以及所需的职业能力,平台网约工作形态可分为劳务型和知识型两大类,前者主要依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后者主要依托劳动者的创新、创造以及创意能力等。
1.劳务型平台网约工作形态。形象地说,它是数字时代的“马路市场”,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劳动力供需对接。当前,生活性服务行业是平台网约工作形态劳动者较为集中的领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最典型的是外卖行业的从无到有,并迅速实现爆发式增长,业务边界不断拓展,配送内容从餐饮扩展到生鲜等,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外卖骑手以相对灵活的就业形式从每一笔订单中获取报酬。
2.知识型平台网约工作形态。即掌握一定专业技术或技能的人才和有需求的个体或企业雇主,通过平台实现供需匹配,劳动者通过输出技术技能获取报酬,比如Logo 设计、程序开发、UI 设计、网站建设、装修设计、工业设计、文案策划等。这种工作形态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技术外包,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全项目技术外包,即发包方将整个项目打包,由承包方(即接单的一方)自己组建团队,完成交付;二是任务链外包,即发包方将项目拆分为不同模块,分别外包。
(二)“微创客”工作形态
“微创客”工作形态,是指劳动者通过对其知识、信息以及社交资源的价值进行开发,从而获取报酬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传统个体经营活动中以物或具体服务作交换的方式,“微创客”工作形态主要依靠网络平台的系统对接和算法结算。从主体来看,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微创客”并未成立个体经营组织或公司,更多以“独立工作者”或“兼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当前,“微创客”工作形态可分为信息型和社交型两大类。
1.信息型“微创客”工作形态。即掌握特定信息的劳动者通过分享或传播信息以获取报酬的生产活动。从价值创造角度看,信息型“微创客”直接或间接地从受众获取报酬,以微博打赏、微信付费阅读、知乎live、喜马拉雅收费音频等为代表。从劳动者的收入模式来看,用户打赏和知识付费是此类劳动者的收入来源。
2.社交型“微创客”工作形态。即劳动者凭借其社交资源,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渠道”资源,将社会资本转换为人力资本。该工作形态主要包括直播型、经验型和社区团购型。直播型模式指具有一定号召力的网络红人利用其影响力,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进行商品营销以获得利润;经验型模式主要是通过分享购物经验或体验来吸引消费者;社区团购型模式以线上线下融合为特点,以线下社区为核心,社区团购的“团长”借助熟人社交关系,整合需求并对接商家完成交易。
(三)人机协作工作形态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化设备”的人机协作模式逐渐成为新的工作形态。“人机协作”是指人和自动化机器共享工作空间并同时作业的工作场景,其本质是将机器和数字技术的刚性、智能化及机器感知与人的柔性、能动性及情感感知相结合,强调在人工智能完成简单、重复、高危工作任务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思维性、能动性,从而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优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人机协作的基础是数字时代人类劳动者与机器之间工作的再分工。
1.机器或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是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重复性、常规性的体力工作或脑力工作。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0 年调查数据,截止到2030 年中国有多达2.2 亿劳动者的就业可能受自动化技术的影响,平均到每位劳动者约有87 天的工时会被自动化生产机器取代,有3.31 亿农民工或将面临22%~40%的工作内容被机器替代的风险。[5]
2.传统的人工作用不是简单地被机器取代,而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的双重革命,其实质是对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智能机器的角色“从工具转换为劳动者”,[6]传感器、工业软件、机器人、大数据分析等提供的生产能力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它们不是对人类体力、技术能力等简单补充,而是革命和超越。另一方面,智能化的设备、流程以及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将劳动者从重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更多投入有创造性的活动,完成那些具有创新性、沟通性、学习性等特征的工作任务。
(四)远程办公工作形态
数字时代,生产空间平台化和生产工具智能化使得劳动者远程办公成为可能,Facebook、谷歌等高科技公司允许部分员工永久在家工作。相比传统的现场办公模式,远程办公工作形态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传统的工时统计方法面临挑战。远程办公使得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给工作时长的计算带来困难。2020 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对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实行居家隔离政策的16 个城市、近300 万人的电子邮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实行远程办公后工作时长多了近50 分钟。[7]
2.劳动者的工作交往环境发生变化。缺少茶水间的聊天,如何和同事维持良好的友谊?如何维系我们的社会资本?[8]有研究发现,远程办公可能会损害同事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9]而微软一项针对350 名员工的内部调研发现,转为远程办公后,员工们一对一的沟通增加了18%,还自发组织了“睡衣节”“晒宠物”等各种主题在线聚会。[10]
四、数字时代新工作形态的劳动特点
新工作形态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基于雇佣制的传统劳动关系。劳动者作为独立的生产主体与服务对象形成平等的生产合作关系,可以身兼数职、远程办公,为多个生产节点提供服务。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与组织间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劳动者与组织的空间交互减弱
现代工厂制度是机器大工业发展后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变化的结果。进入数字时代,云计算、互联网以及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生产线等智能终端共同构成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劳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实现灵活就业。在此背景下,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做什么工作、在哪工作、与谁工作、什么时候工作。由此,劳动者可以摆脱传统意义上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从事规定劳动的“到岗”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空间交互减弱,关系呈现虚拟化特点。
(二)劳动者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减弱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传统雇佣制工作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往往只提供劳动,生产资料则由雇主提供。在生产空间平台化和生产要素资本化的推动下,劳动者通过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多地将体力、技术、技能、知识、信息、社交资源等要素转化为人力资本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传统的雇佣关系被合作关系取代,生产活动执行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逐渐统一起来。受此影响,个人对组织不再是传统雇佣制下的强依附关系,劳动者的身份不再限定于某一特定组织内。他们可能不再与任何一家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作为独立的生产主体与服务对象形成平等的生产合作关系。例如,不同于传统雇佣制下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往往通过购买或租赁车辆的方式获取劳动工具。
(三)组织对劳动者的规则约束减弱
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是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一重劳动关系、八小时全日制劳动、遵守一个雇主的指挥等为特征的制度设计。[11]在此关系中,劳动者直接受雇于雇主,雇主对劳动要素进行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数字时代,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被弹性化、灵活化的劳务关系或合作关系所取代,劳动资料供给、劳动过程管理、劳动结果考核等都将发生质的变化。数字时代的各类组织不再必须是由工人、厂房、设备、资金等构成的实体,而可能是一个由各种生产要素“分布式”组成的无边界系统。劳动者可以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决定加入或退出组织,并自主开展工作。平时组织成员与组织系统可能不发生关联,只有在面对用户需求时,他们才与组织发生关联。从劳动过程监管来看,平台网约和“微创客”工作形态等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从过程导向转为结果导向,组织对劳动者的生产管控正在削弱,“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同时存在,且平台对劳动的控制变得更加碎片化”。[12]
(四)组织对劳动过程的管理趋于动态
数字时代,平台网约、人机协作等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而形成的新的工作形态具有极强的动态管理特点。一是实施过程的动态性。例如,网约车在服务过程中,大数据可以根据实时路况信息调整路线。在算法调度技术支持下,美团、滴滴等网约服务平台的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距离任务派发者的地理位置来选择是否接单。二是用工关系的动态性。随着传统雇佣制被打破,个人与用工企业的双边关系变为个人、平台、用工方(或者用工企业)等之间的多边关系。在多边关系结构中,个人与用工方之间的关系通常只是临时性的,随着任务的结束而终结。
五、新工作形态对人力资源流动与管理的影响
数字时代新工作形态的发展使得标准劳动关系日益松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认识、逻辑体系及工作架构都面临变革[13],对劳动力市场、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劳动者的工作生态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对人力资源流动配置的影响
受新工作形态的影响,劳动者在区域、行业和单位间的流动,无论是流动规模、流动频率还是流动机制,都表现出新特点。
一是区域性流动更加频繁,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加剧。一方面,在传统经济形态中,劳动者的跨区域流动体现为物理空间的变换,流动成本较高,同时,劳动者对于空间变换后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新环境的社会融入问题有较多顾虑。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远程办公、在线交付成为现实,人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不再以人的物理空间转换为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区域性流动的门槛,“高频”流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为劳动者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创造了机会,劳动者可通过虚拟的工作环境,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可能与其专业、知识、技能、兴趣、特长相匹配的组织或个人提供服务。
二是行业性流动成为“新常态”,劳动者自由切换职业的通道被打开。数字时代,跨行业流动将成为越来越多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标配”,他们不再满足“从一而终”的职业规划和“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而是崇尚变化,渴望有不同的职业体验。从行业间流动情况看,当前数字经济活跃的领域主要是与互联网相关的行业以及其他如技能服务、技术咨询、劳动生产等行业。其中,既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装修、货运、餐饮、搬家等,也有智力密集型行业,如法律咨询、科技中介、财务管理、科技研发服务等,还有技术技能密集型行业,如设计、销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家政服务等。
三是户籍和身份不再是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障碍,技术技能提升和转型成为新的“堵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被认为是阻碍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制度性障碍。而在新工作形态中,随着传统正规就业模式的雇佣关系被打破,户籍和身份不再是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障碍,劳动者可以通过“平台—个人”的交易模式自由选择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二)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传统企业在用人制度上,以签订中长期劳动合同为主,工作内容一般也较为单一,以岗定人。但对新工作形态下的劳动者而言,传统雇佣制下的工资、绩效考核、员工培训等制度难以适用。总体来看,新工作形态将给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以下风险和挑战。
一是传统的组织文化建设路径将面临失灵风险。组织文化是员工价值观和行为的总体,由此表现出的组织环境和文化网络的综合作用,[14]是组织成员贡献的黏合剂和一组给定的价值以及社会理想和信念[15]。新工作形态下,随着人力资源流动速度的增强,劳动者与组织的空间交互减弱,团队的柔性程度随之增强,这与要求较强稳定性、传承性的传统企业文化建设方向相悖。实践发现,新工作形态下的劳动者更倾向选择与自我价值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如发现某个组织的固有文化与其个人价值存在较大的冲突时,他们将选择“用脚投票”。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模式,在新工作形态下,社群化传播将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模式。
二是团队柔性化将带来员工忠诚度降低的风险。新工作形态下,由于劳动者对组织的依附性减弱和组织对劳动者的规则约束减弱的双重影响,员工忠诚度降低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风险。对于大型公司来说,其市场地位、经济规模和劳动报酬有助于增加其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新工作形态灵活性过强的特点可能导致项目进行中劳动者半途退出的风险。
三是新工作形态将倒逼组织内部结构变革。组织结构是由一个组织内各要素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构成,是一个内部制度体系协调参与者行为规范的系统[16]。随着劳动者与组织关系发生变革,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组织结构将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创客化”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过程是不同于以往面向管控的职能网络的能力协作网络。[17]这使得劳动者与组织的合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战略联盟”的形式。海尔集团员工转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员工以创业者身份在企业平台独立创业,企业作为孵化者不干涉员工创业的日常运营。[18]在此背景下,组织为了达到其生产管理的目标,就需要改变传统用工模式下的科层管理方式,以适应新工作形态下劳动者与组织关系的变化。
(三)对劳动者工作生态的影响
新工作形态下,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制被弹性工时所取代,生活与工作、创业与就业的边界逐渐消融,“斜杠青年”“U 盘化生存”“新个体户”成为劳动者的新称呼。这将对劳动者工作生态产生如下影响。
一是多重职业带来多元身份。新工作形态的发展给人们的职业选择带来无限的可能,使人们拥有更加自由和丰富的生活。人们将同时拥有多个职业身份,白天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晚上或许是直播带货的互联网营销师。
二是多重职业有助于释放劳动者的多元兴趣爱好。新工作形态的发展将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把“为兴趣而工作”的理想变为现实,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等自由选择工作内容、工作对象。
三是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日渐消融。在数字时代,对于一些人来说,工作即是生活,生活也是工作。比如,对于旅行博主而言,旅行是其生活的一部分,但用文字、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在网络上分享旅行所见所闻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四是上班通勤打卡将成为历史。随着工作时间弹性化,个体对劳动过程控制力增强,新工作形态下的劳动者将摆脱固定工作状态,根据个人需要并在合理估算成本的基础上自行决定或调整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可以预见,在新工作形态下,未来越来越多人不必在公司里朝九晚五,也不必生活在公司所在的城市。
五是职场的社交关系将日渐淡化。在传统雇佣制时代,职场人都处于由同一个单位或公司的领导、同事组成的“职场圈”之中。但是在新工作时代,由于人与组织关系趋于松散,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将弱化。居家远程办公使同事之间日常交集变少,人际关系趋于简单,“办公室政治”的困扰可能越来越少;但也会产生新的孤独感,同学圈、亲友圈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六、结语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进入数字时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发生变革,工作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基于雇佣制的传统工作形态相比,新工作形态劳动者与组织的空间交互减弱、劳动者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减弱、组织对劳动者的规则约束减弱、组织对劳动过程管理趋于动态化。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加剧,劳动者自由切换职业的通道打开,户籍、身份等不再是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主要障碍;对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企业文化建设、员工忠诚度管理以及内部组织架构等都面临新挑战;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多重职业带来多元身份有助于释放多元兴趣爱好,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日渐消融,上班通勤打卡将成为历史,职场的社交关系将日渐淡化。为适应新工作形态的发展,未来迫切需要构建新的人力资源管理逻辑体系以及组织架构,这既是理论研究的使命,更是实践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