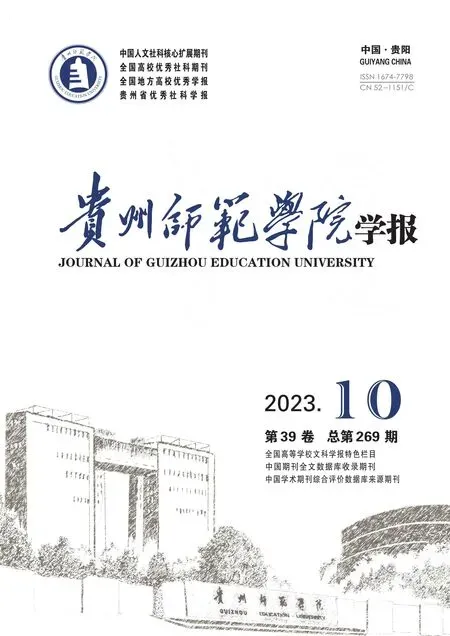王弼哲学思想中“名”与“称”的解析
张 婉,钱新瑞
(1.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2.山东现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王弼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其《老子指略》《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著作,使玄学达到鼎盛。这不仅在于重新挖掘了《周易》《老子》《论语》等经典的内在价值,更重要的是,王弼发现了解释经典内在价值的新方法。由古至今,人们习惯于用语言构成形象,以形象表达思想,也可直接理解为“言”“象”“意”。王弼认为这三者间存在递进关系,即言以构成象,象以表达意。“名”与“称”作为“言”的两种形式,各自具有局限性。所以需要忘言得象,在把握“象”最主要内涵的基础上理解“象”,进而才能做到“得意”,如此便是得意忘象。可以说,得意忘言的解释方法贯穿王弼玄学思想的始终,相比于两汉经学是一种新的经典解释方法。[1]因此,如何理解“名”与“称”以及这两者如何作为一种工具承接“象”,进而实现“得意”则是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名”与“称”:言的两种重要形式
“名”定于彼,是定义性的概念,是对外界事物的规定。这个概念是由被规定者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名”以事物为依据而产生,是客观性的。“称”从于谓,是指称性的概念,是由说话人赋予的,由说话人的意向所决定的。“称”由主观给予,是主观性的。“名”与“称”为言的两种重要形式。王弼对两者做出了深入的阐释与区分,使其作为得意的前提,并在解释《周易》《老子》《论语》等经典时发挥重要作用。
(一)名:定彼之言
王弼认为“名”是定义性的概念,“名也者,定彼者也”[2]197。“名”是指命名,它起到规范一个具体对象的作用。“名”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有确定的对象,便能够命名,而没有确定的对象,则无法命名。“名”以具体的对象为依据而产生,所以,王弼说“名号生乎形状”[2]198。具体的对象是“名”产生的根据,没有这个对象,“名”则无从产生,也没必要产生,这就指出了“名”的来源。“名”来源于被规定者本身的特征,通过事物的特征来给事物命名,是出于客观的认识。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写到:“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2]199,指出了名形之间的关系。二者存在着主从关系和先后关系。从客观实际上来讲,“名”的出现与存在必须以“形”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而“形”则直接决定“名”,并且决定着以何种语言、文字表达出一个恰当的“名”。因此,牟宗三指出:“名生乎彼,从客观”,“名号生乎形状,故名号皆定名”[3]123。他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理解“名”,认为“名”(名号)是由客观所产生,而“形”只是对象事物的某些特征,不是事物的全体。因此,王弼在对“名”作界定时,就暗示“名”作为“言”,具有一种潜在的局限性。
王弼提出的“名号生乎形状”这一论断,以及有关名号与客观对象之间关系的思考,都受到名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的是受到汉末魏初社会上流行的形名思想的影响。汤用彤曾说:“至若辅嗣著书,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之玄学家。然其论君道,辨形名,则并为名家之说。《老子注》自未受《人物志》之影响,然其所采名家理论,颇见于刘邵之书也。”[4]18王弼虽然是较为纯粹的玄学家,但是他也吸收名家思想,尤其是形与名的关系,并把这一思想用于注解《老子》。汉末魏晋时期的形名家的中心理论是检形定名:“如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4]10王弼在《老子指略》中也提到:“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2]196法家尚同用形法检查约束一切,名家崇尚“定真”即名实相符。名家与法家关系紧密均言循名责实,名家更推崇检形定名,王弼吸收名家形名理论用于规定“名”,认为名号是根据事物的形状所确定的。
在王弼看来:“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仁不得谓之圣,智不得谓之仁,则各有其实矣。”[2]199所以“名”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辩名言理,二是定名论实。
第一,关于辩名言理,即通过论辩“名”与“形”的关系来言说事理。王弼首先明确“形”与“名”的生成关系,“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2]199,名由形生成,而不是形由名生成,两者是单向的生成关系。王弼吸收汉末魏初名家的思想来论证“名”与“形”的关系。“名家原理,在乎辨名形。然形名之检,以形为本,名由于形,而形不待名,言起于理,而理不俟言。然则识鉴人物,圣人自以意会,而无需于言。”[4]25名家以形为本,形名关系在识鉴人物方面表现为:有文武智勇才性的人,即是有名,可以作为人臣,圣君符合中和之道,超乎一切才性之上,因此无名。名家由识鉴人物,检形定名,引出言不尽意,最后归为无形无名。王弼作为玄学大家,深知体用本末之辨,把名家的思想加以变通,主张言不尽意。所以形名关系也不再拘泥于识鉴人物,而用于解释“道”,“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2]195在这里“形”与“无形”不再只是指事物的特征,而是分别成为“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化身,通过辨析这对概念,抽绎出“无”这个在其思想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概念。而所谓言理,主要是对“道”的言说,无形无名是指“道”的“无”性,有形有名是指“道”的“有”性。
第二,关于定名论实,它注重对“有”的规定,是承接辩名言理的。有形有名者才能定名论实,无形无名者则不可以定名论实,即定名论实是相较于“道”的“有”性而言的,它是辩名言理中理的一部分,而定名论实的“实”是指万物。《老子》第一章中写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2,“有”成就万物。而理与实的关系和有与万物的关系一样,“理”成就“实”,所以要在辩名言理的基础上定名论实。“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2]196,“形”是有确定性的,必然有所分别,而其中的分别便是“实”的表现,因此说“各有其实”。相较于“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2]196来说,名家只是单纯强调名与实的关系,缺少实与理的关系,而王弼通过“名”把实与理联系起来,赋予“理”本体论意义,使实以理为依据,因此仁、圣、智各有其实。
(二)称:从谓之言
“称”从于谓,是指称性的概念,“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2]197,这是“称”的性质,是对客观对象的指称,而非直接定义,更多的是意会的方式。在王弼看来,“名”与“称”的根本区别在于来源不同,“名”来源于“形”,而“称”来源于“我”的“涉求”,即“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2]198“我”是指人的主观意愿,“涉求”是指寻找,人出于主观的寻找而赋予事物指称性的称谓。“称”虽然不够严谨,但是却能够表现出说话者的意愿。所以,牟宗三指出:“‘称出乎我’,从主观。”[5]123
王弼强调,“称”主要用来言道,“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2]197。“道”不能通过客观对象来把握,只能通过人的主观认识来寻找,“道”“玄”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对“无物而不由”“无妙而不出”的万物本原的一种指称。但是,“称必有所由”“有由则有不尽”[2]196,“道”“玄”本身有自己的含义,被用来描述万物本原,就更难表达万物本原所包含的所有含义和特征,即“称谓则未尽其极。”
(三)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与“称”的区别
虽“名”与“称”均属于“言”的范畴,但王弼认为两者均存在局限性,他说:“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2]196,“当”即适合、恰当,“既”指尽。换言之,“名”与“称”在描述事物时均有局限性。命名存在不恰当的地方,指称不能包含对象所有的特征,明确指出语言词汇的局限性,以确认本体的不可指称性。
王弼又进一步指出“名”与“称”两者的区别。“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尽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2]196命名必然出现分别,“名”具有区别它物的特点,它是由事物的特征决定的,一旦给事物命名后,再通过名来认识事物,便会出现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有分则有不兼”,即由事物的某一特征命名,必然不能兼顾事物的其他特征。称谓必然有所凭借,所凭借的本身就是一种指代,更不能穷尽事物所有,与事物的真实面貌不同,因此“不尽则不可以名”。所以“称”不能作为“名”,这二者是不同的,且不能互相替换。这就需要注意“不兼”和“不尽”的区别。“兼”同“并”,“不兼”即是“不并”。就某一特征而言,“大”和“微”是不兼的,比如“大”是可以包括所有拥有“大”特征的事物,即是“尽”,但是却不能包含“微”这一特征所代表的事物。也就是说,某一特征和另一特征不兼,但是却能包含拥有此特征的所有事物,因此“不兼”和“不尽”不同。然而,“称必有所由”“有由则有不尽”,“称”是有所凭借,是根据事物的原由赋予的,并不是事物的特征,是由称谓者主观赋予的。由此观之,“名”和“称”两者是不同的。
二、“名”与“称”:作“言”明“象”以观“意”
王弼在“言不尽意”的基础上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并强调“尽意莫若象”。换言之,“言”与“象”在获得“意”之前就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但“象”所包含的含义大于“言”所代表的概念词汇,“言”只能把握“象”的关键内涵,这就导致“象”很难直接呈现出“意”。因此,“得意而忘象”是对“象”的再一次抽象化,使其不再拘泥于“言”的层面,也就是经验层面,而是对超越性本体的把握。如果不能明确这一点,便无法实现“象以言著”。
(一)尽“象”之“言”:“言”对“象”的呈现
王弼在《周易指略·名象》写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2]609这里虽然说的是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但是王弼在这段话的后边却援引庄子的观点,对三者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言”和“象”作为得意的手段,关键在于得“意”。在得“意”之后,“言”和“象”可以忘掉,不是说“言”和“象”不重要,而是需要减少“言”和“象”对“意”的影响,不执着于“言”与“象”而妨碍对“意”的把握。
尽象之言,是对“象”描述指称修饰之“言”,通过“名”和“称”突出“象”的关键内涵,从而把感性“象”抽象成理性的“言”。“尽意之象”便不能是存象之“象”,因为存象仍然是感性的,而意比言更加抽象,此时的尽意之象只能为“忘象”,通过否定来把握本意,其表征为“忘象之象”[9]。
郭齐勇认为:“王弼取庄子的观点重新解释《周易》关于‘意’‘象’‘言’三者的关系,把三者关系拓展为一个认识论问题。”[6]277这个认识论问题就是“象”作为经验对象所包含的含义大于“言”所代表的概念词汇。“言”只能把握“象”的关键内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和“称”,这两者正是通过把握“象”的关键内涵给予“象”命名和指称的。而“意”所内涵的内在本意是超越“象”所代表的经验对象。这就导致“象”很难直接呈现出“意”,那就需要“得意而忘象”。本质是王弼用《老子》中本体论思想来解释《周易》中“意”“象”“言”三者的关系。
(二)得“意”忘“象”:“象”对“意”的实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2]608象能尽意,言能尽象,“象”作为经验对象所包含的含义大于“言”所代表的概念词汇,“言”只能把握“象”的关键内涵,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象能尽意,言能尽象?这就需要继续理解王弼的这段话:“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2]609王弼把“言”比作捉兔子的蹄,把“象”比作捕鱼的筌,在这里“象”“言”都是得“意”的工具,真正得“意”的是用“象”和“言”的人,言不尽意却能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这是对“象”再一次的抽象化,是在对“象”通过“言”的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次升华,是对“意”和本体的把握。
比如概念词谓虽然不能包容经验对象,但是人却能通过概念词谓把握经验对象。在经验对象意识内或层面上不能给出本意(本体),人却能感受到经验对象之上的本体,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虽然不能明确地言说道,却发现道的存在。这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有关,天人合一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之中,人的作用是一直体现在其中的,人作为体道者,需要借助“有”。所以王弼在答裴徽的论难时说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7]175借助经验事物来体“无”,而不拘泥于“有”,最终要舍弃“有”来把握“无”。
“名”与“称”两者作为“言”均具有局限性,这与其所处的具体语境和特定对象有关。[8]在具体的语境下,“名”与“称”能够说明特定对象,一旦离开具体语境容易产生歧义,比如指代词“他”“这”。所以,人在认识对象时只能把“名”与“称”所代表的“言”看作工具而不能看作是目的。“象”也是如此,只是用于得意,而不是得意本身,如果拘泥于言象本身则反而失去本意。王弼所言的“象以言著”,即“象”通过“言”来凸显把握其中的内涵,其形式就是通过“名”与“称”,呈现出“象”的内涵与外延。这个过程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但抽象化的过程必然会损失一部分“象”的原意,因为“言”自有其局限性。所以需要忘言得象,在把握“象”最主要内涵的基础上,理解“象”,进而得意。
三、“名”与“称”作为“得意”工具的运用
王弼辨析“名”与“称”是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刘笑敢将王弼的《老子注》称为顺向的诠释,即文义引申式诠释。[5]136王弼对“名”与“称”的诠释,虽然吸收名家思想并进行创造性发挥,但其基本思想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引申式发挥,与《老子》原文中的基本思想方向大体一致。“名”与“称”作为得意的工具,在诠释“道”“玄”“志于道”等关键概念时发挥重要作用。王弼正是通过二者才完美的传达出他对“道”“玄”“志于道”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从而构建出他的玄学思想。
(一)对“道”的“得意”
王弼明确“名”与“称”的区别,目的是用来解释“道”。在他看来,道是不能“名”的,道只是“称”。“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赜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弥纶而不可极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则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为之者败其性,执之者失其原矣。”[7]196
“道”是万物所通向的终极,“道”本身是一种指称性的代词。“道”有“玄、深、大、微、远”多种特征,但是,当用其中某一特征来命名“道”时,便存在矛盾,“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2]196。因为“名之不能当”,“名”是有局限性的,“名必有所分”“分则有不兼”,“大”和“微”两者不能兼,不能用其中一个给“道”命名。因此,《老子》书中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只能称为“道”,不能命名“道”。“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2]195这里的“由乎无名”就是指万物之所由的道,道不能被命名,所以称“道”为无名。
王弼注解《老子》第一章第一句“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2]1“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是指可识可见有形象之具体事物,具体的“有”才能通过“名”来定义,而“常道”和“常名”是不可道,不可名的。“道”有生之,畜之的功能,所以王弼在《老子指略》开篇写到,“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2]196“道”无形无相因此不可名,但是出于寻找“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的涉求要给予“道”一个指称,或者是形容。“道”本是万物之所由,一旦赋予名,便是确定性的,所以不可以命名,只能用“道”作为指称,“道”本来指道路,用来指称“道”也只是源于有道路通达的含义。因此,想要对“道”得意,必然先要舍弃道路这层含义,只得万物之所由这层含义,从道不可被命名这一点,体悟道的“无”的特点。
(二)对“玄”的“得意”
王弼区分“名”与“称”的区别,才能更容易理解《老子》中的语言,才能更好地把握“玄”的深刻意涵。更能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王弼关于“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4]25的注解:“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同谓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2]2
王弼从区分“名”与“称”的角度注解这一句,始与母同出于玄但是名号不同,是因为两者的作用不同,在首有“生”的作用则谓之始,在终有“畜”的作用则谓之母。道无不通也,无不由也,道有多种特征,老子看到道“生之”“畜之”两大特征分别命名为“始”和“母”,因为名号生乎形状,“始”和“母”也只是表示“道”其中的某一特征,因此不能同时定义为“玄”。“道”是不能被定义的,只能“谓之玄”,“玄”是幽暗静默无形无象的一种状态,是不可称谓之称谓。“玄”不同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名称,而只是对“无”与“道”的一种形容。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然弥纶无极,不可名细;微妙无形,不可名大。是以篇云‘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2]196又说:“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是以谓‘玄’则‘玄之又玄’,称‘道’则‘域中有四大’也。”[2]198“玄”只是权宜性的,指称性的称谓,甚至也不能定于“一玄”,因为“玄”只是形容一种冥默无有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定义性的“名”,是出于人的涉求,寻找这样一种状态的“道”,如果把“玄”作为这种状态的定义性的名,那这个名就“失之远矣”。这种状态来源于人的理解,而不来源于“道”本身,人需要寻找这种状态的道,因此称之为“玄”。人对终极的寻找是不能停止的,因为一旦找到终极便不是终极,故曰“玄之又玄”。
在《老子》中“常道”不可以用来命名,只有“非常道”才可以命名,因为名号来源于有形的对象,而“常道”作为“无形无象”的恒常不变的万物本原是没有确定的对象的,因此不可以命名。王弼通过辨析名的内涵,更清晰的揭示出“道”不可言的特征,体现出“道”的“无”性。“道”“玄”则是作为称谓出现的,虽然这两者作为称谓并不能完全表达出万物本原的全部特征,但是比把这两者作为名号来看,更加易于理解,更加灵活,所以“谓玄则‘玄之又玄’称道则‘域中有四大’”[2]198,“道”“玄”作为指称性的“言”,不像名号具有定义性。因此可以不只定于一玄,“道”也可以称域中有四大。
(三)对“志于道”的“得意”
道是“无”的称谓,没有道不通达的,没有不以道为凭借的,所以王弼在《论语释疑》中注解“子曰:志于道。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2]624这段话王弼把“道”解释为“无之称”,认为道“无不通”“无不由”,这明显是老子所说的“道”,是用老子之“道”释孔子之“道”。为何被“况之曰道”时,便“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因为“况之曰道”。况,古同“贶”,赐予,出于人的主观意愿赋予“道”的称谓。这与王弼所说“称谓出乎涉求”契合,人由“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意识到事物背后存在的本体,出于人的寻找,却发现任何有形有象的事物都不足以成为这种存在,只有“无”符合这种特点,但是当无被命名为“无”时,便有规定性,便不是无,所以用“道”来指称它。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道没有象,也就不能用言来准确的表达。
“无”不是“道”的名号,而是对“道”无形无名的一种形容。“无”不能被命名,只能用“道”来权宜性的称谓。王弼辨析“名”与“称”是在《老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结合玄学的方法来解释《论语》中的“道”。在《论语》原文中把“志于道”与“德”“仁”“艺”并列而谈,本身是教导弟子进德修业的秩序和方法,层次分明,像一个教学大纲,侧重于实践,具有明确的方向。既然以“道”为志向,“道”就应该是明确的,应该是“有”,何谈“无”?所以王弼把儒家的“道”玄学化,按照自己的意思改造孔子之“道”,把儒家所言的“志于道”,改造为本体上的“道”。这个“道”不是由人所决定的,也不是人为设立的,是本就存在的,贯穿始终。人志于对道的追求,就是追求最根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根本性规定,人志于道便是必然的。这就使儒家的“道”也有了本体论意义,体现王弼调和儒道的态度,也体现出他以道解儒的诠释方向[10]。
王弼对“志于道”的解释,可以看出“名”与“称”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反过来借用对“名”与“称”的辨析能更好理解“志于道”由儒家之“道”向道家之“道”的转变。“言”是用来描述“象”的,既然“志于道”之“道”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即为忘象。忘象之“象”,仍然可以用“言”来描述,即是通过“无”来称之,通过否定来得意。
四、结语
王弼对“名”与“称”的辨析是在老子“名”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又吸收魏初形名家的思想,丰富“名”的内涵,进一步指出“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2]198。“名”与“称”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二者有所同,又有所异。相同之处在于“名”与“称”均属于“言”的范畴,且二者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包含事物的所有特征。不同之处在于“名”与“称”在明确事物的方式与角度上,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去明确“象”,从而形成互补。王弼对于“名”“称”之辩的分析,其目的是为了使“言”作为“得意”的工具重新重视起来,由“言不尽意”发展为“忘象忘言”,进而实现“得意忘言”。可以说,“名”“称”之辩在王弼哲学中属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这二者作为“得意”的工具贯穿王弼玄学思想的始终,为经典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方法。通过对“名”与“称”二者的解读,有助于理清王弼对老子“名”的思想和魏初形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王弼玄学的思想本质与内核。因此,尽管“名”与“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老问题”,但依旧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