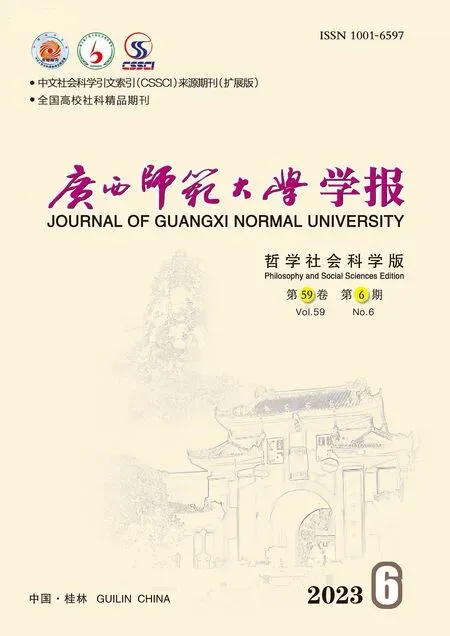移民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余淼杰,吴 双
(1.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2.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如何影响商品的流动?根据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商品自由流动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因此会削弱让要素发生流动的动机;而要素能自由流动,两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将会接近,进而会导致产品价格趋同并减少贸易[1]。所以,如果一种要素的流动越自由,商品的流动似乎会减少,二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然而,这与我们在经验世界的直观感受并不相符:自上世纪80年代末冷战趋于结束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和国际贸易的交易量都大幅上升,外国出生人口比和贸易产出比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图1所示。人、资本、货物都在大规模地跨国境流动,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也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作为劳动力——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然而从数据上看,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保持着同步的高速增长。

图1 1960—2005年世界贸易产出比和OECD国家外国出生人口比的变化[3]
人确实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但又不只具备生产要素一种属性——人同时还是交易的执行者以及消费者。在赫克歇尔与俄林之后,廷伯根(Tinbergen)将著名的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领域来解释贸易流[2]。从引力方程的视角,我们能得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反的结论:由于贸易成本会阻碍国际贸易,而移民的增多恰恰会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贸易成本、促成贸易,因此人的流动会促进商品的流动。此外,随着微观基础越来越受到重视,消费者需求端的偏好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考虑。由于移民对原籍国的食材、服装等商品普遍存在偏好,甚至带动周边的本地人产生类似偏好,移民增多会增加其所在国对原籍国的产品需求,进而增加进口。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能推导出移民与国际贸易互补的结论,这不仅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符,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印证。
另一方面,克鲁格曼(Krugman)提出了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学,也给我们理解移民规模扩大的影响提供了另一种视角[4]。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移民的到来会使得所在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促进所在国产品的出口。但移民带来的规模效应对于进口的影响并不直观,既有可能因为生产规模扩大而进口更多中间品,也可能由于存在规模经济而选择自己生产以替代进口。这两方面效应的存在也使得文献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移民与进口之间是互补关系。
本文全面回顾了关于移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大量相关研究普遍证明了移民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但少数研究在一些子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了移民与进口之间的替代关系。我们首先分国家(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分析维度介绍了文献中的理论解释与实证结果,然后也介绍了发现移民减少进口的少数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阐述了引力模型的理论解释并介绍了移民促进贸易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实证证据;第二部分分析了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移民影响需求、降低企业进入成本的作用,并介绍了移民促进出口在企业层面的实证证据;第三部分介绍了移民可能的进口替代作用,包括对最终品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引力模型与国家(地区)层面的促进效应
最早对移民和贸易的关系展开详细讨论和检验的是古尔德(Gould),他提出移民通过帮助外语沟通、提供市场信息、建立互信三种渠道影响贸易成本[5]。由于移民会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进入引力模型,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拟合引力模型、估计贸易对于移民的弹性是引力模型自然而然的一个实证应用。首先,我们以黑德和雷伊斯(Head and Ries)所提出的简单的分析框架为例,阐述传统引力模型对贸易成本渠道的理论解释,以及如何得到用于实证检验的回归方程[6]。之后我们介绍引力模型的发展修正,以及无法被传统引力模型刻画的偏好渠道。说明理论解释之后,我们将分类回顾大量支持移民对贸易存在促进作用的实证文献以及相关的异质性分析。
(一)理论解释
i国从j国的进口量mij可以有如下表达形式:
(1)
其中,yj是出口国j的GDP,sij代表j国产出中被i国消费的比例;yi是进口国i的GDP,yw代表世界的GDP,τij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式(1)就是一个简单版本的引力方程,表达式简单但含义深刻,其背后的隐含假设是i国的消费能力与i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yi/yw成正比,并受到贸易成本τij的阻碍。
具体而言,贸易成本的形式被假设为τij=exp(-Xijβ),Xij代表影响贸易成本的各种变量组成的向量,可表示为
Xij≡[lnDISTijADJijlnIMMIijOPENiOPENjln(Pj/Pi)]。
(2)
其中第一个对数项纳入了影响交通成本的变量:DISTij代表两国间的地理距离,ADJij是一个代表两国是否地理上相邻的虚拟变量,如果相邻则取1。第二个对数项纳入了影响交易成本的变量:IMMIij是来自i国、居住在j国的移民数量,OPENi代表i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开放程度,可由(mwi+miw)/yi给出。而第三个对数项允许了对“一价定律”的偏离,Pj/Pi代表了j国相对于i国的价格水平,也将直接影响i国对j国产品的需求。结合以上两式,就可以得到一个用于回归的方程形式:
(3)
从式(3)中可以清楚看出,移民存量通过改变贸易成本中的交易成本来影响贸易量。同时,影响大小与地理距离、开放程度其他许多因素相关,所以在回归中这些因素都应加以控制。
那么控制这些变量是否足够?随着学者们将微观基础引入引力模型,他们发现即使控制了种种可观测的国家变量,仍有一项重要的遗漏变量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被称为多边贸易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这个变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两国贸易不仅仅受到两国经济的影响,还取决于两国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因此,要估计移民引起的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变化对贸易量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这两个国家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是否也会发生变化[7]。
此外,在计量上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如式(3)的引力方程也存在问题。席尔瓦和泰雷罗(Silva and Tenreyro)指出这种对数线性化方法在异方差下会导致不一致的估计,并且对贸易量取对数与现实世界中大量的0值贸易流不兼容[8]。因此,早期一些文章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之后,黑德和迈耶(Head and Mayer)总结了一系列方法用于对引力模型的无偏估计[9],包括处理归并数据的Tobit方法[10,11]、Heckman两步法[12]、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8]等。
以上讨论都是基于移民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进入引力模型,但移民还可能通过改变进口国偏好来影响贸易。两种渠道有不同的福利含义:当移民影响贸易成本时,移民能帮助交易双方克服信息摩擦,促成贸易,也就促成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如果移民仅仅是改变进口国偏好,则不存在这种效率提升的效果。因此,区分两种渠道的影响可以厘清移民在提升效率方面的作用。
康博斯(Combes)等学者尝试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进行结构估计来量化两种渠道的影响。他们研究法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仿照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Dixit-Stiglitz-Krugman)模型,认为移民既进入信息成本,又进入偏好[13]。具体而言,地区i从地区j进口的贸易成本τij为:
1+τij=TijIij。
(4)
其中Tij代表交通成本,Iij代表信息成本,并有如下形式:
Iij=(1+migij)-αI(1+migji)-βI(1+plantij)-γIexp(φI-ψICij)。
(5)
式中migij和plantij分别代表移民和企业网络,Cij代表这两个地区是否地理上邻接,其他希腊字母均为参数。式(5)表明移民网络和企业网络都会降低信息成本,因此他们指出,如果不控制这些网络效应,基于传统引力模型的估计会高估交通成本和地理距离对于贸易的影响。
而为了量化偏好渠道,假设i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为:
(6)
其中j代表任意一个进口的地区,h代表j地区任意一种商品,cijh代表i地区消费者对j地区h商品的消费量,σ为常替代弹性,这些设定均与标准的CES效用函数一致。他们在函数中加入了aij一项,代表i地区消费者对j地区商品的总体偏好程度。偏好与移民网络migij、代表是否地理上相邻的Cij以及随机项eij有关:
aij=(1+migij)αaexp(eij-φa+ψaCij)。
(7)
因此,移民数量越多,j地区产品能给i地区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也就使i地区有动机增加对j地区的进口。
然而,由于模型中的代表偏好渠道的参数αa和代表信息渠道的参数αI无法被分别估计出来,他们无法通过结构方程来定量地计算出两种渠道各自的影响,只能通过实证策略来证明偏好渠道的影响可能很小。后续文献大多也是通过异质性检验等实证方法来对比两种效应,但费勃玛耶和托玻尔(Felbermayr and Toubal)假设了贸易成本对称之后,用i地区从j地区的进口量除以j地区从i地区的进口量,成功地估计出了代表偏好渠道的参数[14]。他们这么做的逻辑在于偏好效应只会影响进口而不影响出口,而贸易成本渠道同时影响进出口,因此用进口比上出口就会消去贸易成本渠道的影响,剩下的部分完全被偏好效应解释。与前人结论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偏好渠道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考虑中低技能移民和差异化产品时。
即使大多数文献都强调了贸易成本渠道的作用,并且认为偏好渠道的作用相对较小,在第三部分我们仍将重新讨论偏好渠道的作用机制:其作用较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移民对原籍国产品的偏好并没有发展为进口,而是促成了在所在国的本土化生产,形成了进口替代。
(二)实证研究
实证文献中,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广泛地得到证实,估计出来的结果普遍支持移民增加10%会导致进口或出口增加1%~4%,经济意义显著。由于移民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通常支持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迁移,研究移民影响的文献也主要关注在发达国家的移民的影响。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时期都非常广泛,既有使用跨国、跨州数据集的,也有关注特定国家、民族的,表明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普遍存在。此外,在估计总体效应的同时,研究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异质性检验,为具体的机制分析提供了证据。结果基本认为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主要是通过贸易成本渠道而非偏好渠道实现的,并且这种贸易成本渠道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有关移民的异质性,很多文献关注了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或职业异质性,也有一些文献对比了不同来源国的移民。移民职业技能方面,文献中的结论不尽一致。古尔德(Gould)发现移民的技能对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技能水平有相互抵消的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技能水平越高的移民可能会有更多关于原籍国的市场信息,促进贸易;另一方面,技能越高的移民更可能自己建立企业,这对贸易有替代效应[5]。黑德和雷伊斯也发现企业家们对贸易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最小的[6]。但也有学者发现从事管理或销售等商务的移民极大地促进了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尤其刺激了对文化不同的国家的出口,原因是这些移民直接传播便于公司开展贸易的信息,并且在这些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作用是最大的[15]。
在移民的来源国方面,如果原籍国经济体量越大,且与所在国在制度、语言等方面差异越大,那么该地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古尔德估计增加一个新加坡裔美国移民会导致每年新增加3万美元的进口和4.8万美元的出口,但一个菲律宾裔美国移民能增加的贸易量不到10美元[5]。根据引力模型,原籍国的经济体量会影响贸易量的大小,因此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与原籍国经济体量正相关也十分合理。吉尔玛和余(Girma and Yu)分析了在英国的移民情况,他们发现来自英联邦的移民作用小,而其他地区的移民作用大。他们认为,由于移民的偏好效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普遍存在,因此这种异质性无法被偏好效应解释,应该归因于非英联邦的移民能带来新的关于自己原籍国的信息[16]。敦列维(Dunlevy)发现当在美移民的原籍国制度越腐败时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越大,而当移民说英语或西班牙语时作用较小[17]。有学者在对西班牙出口的研究中发现这一作用对与西班牙文化差异更大的国家影响更大[18]。布里安特(Briant)等人以在法国各省(département)的各国移民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来自制度较弱的国家的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更大;但如果是复杂商品的贸易,无论移民原籍国的制度如何,移民都会促进进口[19]。这些证据都支持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当原籍国和所在国差异越大时,移民能带来的信息增益越显著,有效减少信息摩擦、帮助建立互信,因此贸易成本降低的幅度更大。
除了移民的异质性,商品的异质性也同样值得关注。文献十分一致地支持移民促进贸易的作用在异质性、差异化的商品上更为显著[14,18,20,21]。考虑到交易异质性商品面临着更大的信息摩擦,买家卖家匹配更为困难,移民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有学者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建模,指出不完全信息造成的匹配摩擦将会干扰价格机制,影响贸易利得的充分实现,而国际化的信息共享网络则可以克服这种摩擦[22]。因此,移民促进交易实现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效率和福利意义。除了贸易成本渠道外,移民对原籍国产品的偏好通常也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费勃玛耶和托玻尔不仅发现了贸易成本渠道在差异化产品上的作用是同质性产品的三倍,而且发现偏好渠道在对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促进效应中的贡献也十分显著,达到了大约一半[14]。因此,无论是通过贸易成本渠道还是偏好渠道,移民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都主要表现在差异化产品上。
移民除了会影响原籍国与所在国之间的贸易,还可能影响所在国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尤其是当第三国有大量同族移民时。劳赫和特林达迪(Rauch and Trindade)研究了全球的华侨网络,他们发现华侨网络对双边贸易有明显促进作用,在华侨占比与东南亚相当的所有国家之间,华侨网络至少能解释60%的差异化产品双边贸易增加。机制方面,由于对差异化产品双边贸易量的作用要比同质性产品的更大,移民在帮助匹配买家和卖家中的作用得到证实;此外,族裔共同体的制裁作用会阻止投机行为,也更有利于贸易的达成[20]。他们的研究表明了移民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的突出作用,但没有考虑偏好渠道。之后,安德森和冯·万库普(Anderson and Van Wincoop)以及费勃玛耶等人都指出了他们估计的问题[7,23]。在估计结果的解释上,他们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大量华侨的国家或地区主导的,并且无法排除历史贸易联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在理论解释部分提到的,他们遗漏了多边贸易阻力,因此估计结果有偏。费勃玛耶等人进而用一个改进后的引力模型来识别贸易成本渠道的作用,他们发现朗契和特瑞戴德将华侨网络的作用高估了至少一倍。同时,他们将研究对象从华侨网络拓展到了各种族裔的移民网络,发现波兰、土耳其、墨西哥等族裔的移民网络事实上都比华侨网络的作用更大[7]。类似地,魏浩和袁然采用了最新的全球华人存量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发现华人存量每增长1%,双边出口总额增长约为0.165%[24]。
总体上,这些较为早期的文献忽略了一些识别问题,后来的文章大多用早期的移民网络做工具变量来克服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研究者们要么直接采用历史的移民存量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19],要么采取一种更为普遍的“偏离—份额”(shift-share)工具变量,即根据历史上某族移民在各国的地理分布将当期全部的该族移民在各国之间分配,从而接近当期该族移民在各国的存量。该工具变量最早由卡德(Card)提出,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方面之后的移民普遍更倾向于定居在本国移民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该工具变量与当期实际移民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使用历史的移民分布可以保证工具变量不会受到后续年份移民目的国经济、政策冲击的影响,因此更为外生[18,24,25]。然而即使采用了这样的工具变量,内生性问题并不能被完全克服。例如,可能有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响贸易和移民,因此用历史移民做工具变量也无法解决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或者一些企业会在准备开展对外贸易业务之前就雇佣移民,造成反向因果问题;另外移民还可能通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FDI)来影响贸易[1]。因此,为了使得估计结果准确一致,这一领域最近的一些研究利用了自然实验来构建更为外生的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基于自然实验的估计结果比之前文献中的促进效应略小一些,但依然显著。斯泰恩格雷斯(Steingress)利用美国难民安置计划对政治难民的随机分配作为自然实验。由于难民无权决定自己被安置到哪个州,且安置计划不大可能是基于一个州和难民原籍国之间的贸易机会来制定的,因此作者使用美国各州的难民数量作为近期外来移民人数的工具变量,发现移民人数增加10%会让美国的州增加1.0%来自移民原籍国的进口,增加0.8%的出口[26]。也有学者在研究时利用了美国对越南贸易禁运时期越南难民被疏散至美国这一历史事件。1975年的第一波13万难民是被随机安置到美国各州的,因此可以被用作后续一百多万移民的工具变量。他们发现,在1995年解除禁运后,美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在越南裔人数越多的州增长越快[27]。类似地,巴哈等人使用德国的机密行政数据,将德国遣返前南斯拉夫难民的外生分配规则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德国行业中遣返的难民增加10%,出口将增加1%~1.6%[28]。艾瑞欧则使用了另一种自然实验。在《瑞士—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协定》实施之后,瑞士各地区《协定》生效的时间有所不同,且到边境的距离也不同,因此受到的影响有差别。他因此使用这种实施时间和地理距离上的差异来识别,发现高技能欧洲工人的流入导致从其原籍国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提高;更好的中间品进而提高了产品质量,使瑞士产品对国际市场更具吸引力,从而促进了出口。因此,瑞士全球价值链的效率在上游和下游都得到了提高[29]。
此外,也有部分近期研究采取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研究角度,例如贸易的二元边际以及区域贸易协定。有学者使用西班牙的出口交易数据,发现移民促进贸易的效应几乎完全是由于在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即出口交易单数增多——上的作用[18]。范兆斌和张若晗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式,将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定义为上一年已出口产品的出口值,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上一年未出口产品的出口值。他们使用了中国 2000—2013年对 34个 OECD国家的出口及移民数据,发现移民流量与集约边际的出口显著成反向关系,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移民存量对集约边际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同样不显著[30]。铁瑛和蒙英华则关注了移民网络对于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发现移民网络可以通过促进双边贸易流来提升两国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概率,并且促进作用边际递减[31]。
二、企业异质性框架与移民对企业出口的促进
随着企业数据逐渐可得以及迈利茨(Melitz)将企业异质性模型引入国际贸易领域,近十年来研究者们纷纷将研究的尺度由国家层面推进到企业层面[32]。由于模型的预测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会出口,贸易成本或者需求因素对企业出口活动的影响自然也与企业自身的生产率等特征有关,因此仅仅使用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加总数据会掩盖这种企业异质性的影响,也遗漏了重要变量。另外如果区分开贸易的二元边际,以一国或地区出口企业的数量作为扩展边际,那么就忽略了企业自身生产率对出口参与的重要作用;如果用一国或地区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作为集约边际,那么贸易成本变动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将是不确定的:在位企业的出口量会增加,但同时也会有其他生产率更低、销量更低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以,控制企业生产率并进行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是有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引力模型能直接用于考察进出口的双边贸易关系,企业异质性框架只是对于企业出口的建模,因此相关文献基本也只关注了移民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巴斯托斯和席尔瓦(Bastos and Silva)第一次使用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这一问题。他们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基于迈利茨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加入了艾顿等人提出的中进入成本方面的市场异质性、需求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建立了理论模型来分析移民网络在促进贸易方面的具体效应及其如何与企业生产率相互作用[33,34]。模型需求端,任一国家c的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效用函数为:
(8)
其中q(j)是c国消费的j产品的数量,Ωc是c国消费的产品集,σ是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常替代弹性,ac(j)则代表了企业在需求上的异质性,在此特指企业j与c国消费者之间的网络联系。如果企业j进入了c国市场,通过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它在c国的市场份额为:
(9)
式中xc(j)和pc(j)分别代表企业j在c国的出口收入和价格,Xc和Pc分别代表c国消费者在差异化产品上的总支出、c国的市场加总价格指数。
模型供给端其他设定均与迈利茨的做法一致,除了企业出口到c国市场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有市场异质性,设定为Fc。因此,企业j在市场c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10)
可解得企业j以到岸价(CIF)计的最优定价为:
(11)

(12)
净利润为总收入减去可变成本以及固定成本:
(13)
只有当净利润非负时,企业才有动机进入c国市场,因此结合式(12)和(13),企业的进入概率可表示为:
(14)
而企业以离岸价(FOB)计的出口收入的对数为:
lnXc+(σ-1)lnPc-σlnτc。
(15)
式(14)和(15)分别代表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者均与企业生产率φ(j)正相关,体现了企业异质性的作用。在移民网络的作用方面,根据式(14),移民网络会降低进入c国市场的固定成本Fc;另外,企业如有更多移民网络带来的与特定目的地之间的联系,则会有更高的ac(j),因此二者都将提高企业参与出口活动的概率。另外, 由式(15),企业的出口强度与Fc无关,但与企业在特定目的地的需求冲击ac(j)正相关。基于这两个模型的预测,研究者设定了如下回归方程,控制企业生产率φj以及其他国家层面的变量Xc,进行实证检验:
P(Ejc=1)=P(αlnφj+βXc+γlnemigrantsc+ηjc);
(16)
(17)
他们使用了线性可能性模型(LPM)加上固定效应来估计式(16)的企业进入概率,并且使用了T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来减轻估计式(17)企业出口强度时存在的企业自选择偏误。
巴斯托斯和席尔瓦利用葡萄牙的企业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移民网络对出口的参与率和强度都有显著作用[33]。类似地,杨汝岱和李艳也用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发现移民网络能够明显降低出口目的市场的不确定性,服务于企业的出口“试错”机制,从而显著提高在位出口关系出口额的增长率(集约边际),提高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存活率(扩展边际)[35]。蒙英华等则发现移民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更多的企业从事出口发挥作用(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移民网络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概率与出口强度[36]。他们将所有企业的平均出口额作为集约边际,而杨汝岱和李艳仅将在位企业上一年已有出口某产品到某市场的交易计入集约边际。二者对于拓展边际的结论差别恰恰证明了移民提升企业出口概率和强度的作用:出口概率增大使得一些低生产率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拉低了平均出口强度,所以即使在位企业出口强度提升,所有企业的平均出口强度可能没有明显变化。
对于使用国家或地区层面数据的研究,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企业雇佣了移民所以出口扩张,还是仅仅因为企业所在地区有更多移民就会使出口扩张?有学者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探索认为应归功于前者。希勒(Hiller)利用丹麦企业—劳动力匹配的面板数据,发现移民带来的增益必须通过被企业雇佣而得以实现。另外,他在文章中强调了出口企业对外国员工的雇佣需求造成的反向因果,也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一是某一国家的外来移民在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工作的人数,二是某一国家的外来移民在同一地区其他公司工作的人数。对比OLS和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他认为OLS的结果存在低估[37]。同样地,安德鲁斯(Andrews)等人对德国企业的研究也证明了移民进入企业工作对于促进出口的重要性。他们文章中OLS的估计结果显示企业中外国工人占比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出口的概率就增加1.5个百分点;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则达到7.5个百分点。他们认为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大于OLS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是那些受到工具变量(外国工人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影响的企业的效应,如果我们认为那些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外国工人的企业正是获益最多的,那么工具变量法的结果可能有一定高估;另一方面,企业存在着对移民数量的测量偏差,因此OLS会导致衰减偏误(attenuation bias),但工具变量法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用加总数据来计算的工具变量不大可能存在类似的测量误差[38]。
随着文献中对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逐渐成熟,后续也有部分研究考虑了基于产品质量和移民技术水平的异质性作用,发现高技能或高受教育程度的移民对高质量产品的出口作用突出。杨希燕和童庆发现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高技能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作用逐渐递增;与之相反,低技能移民网络的作用则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下降[39]。蒙英华和赵倩玉发现移民网络提升了中国中高质量产品的出口,其中往北方国家的移民网络降低了中国低质量产品的出口;并且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40]。
三、另一种可能:移民的进口替代作用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移民能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促进进出口贸易,然而,在实证结果中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这一点,部分研究发现了移民对进口的替代作用,尤其是在进行一些子样本的异质性分析时。这类替代关系虽然可能存在,但并不十分明确,可能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对此,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包括规模效应引起的对最终品的进口替代,以及对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一)对最终品的进口替代
吉玛和余(Girma and Yu)在分析英国的外来移民对英国进口的影响时发现,英联邦裔移民表现出对贸易的替代作用,虽然非英联邦裔的移民依然明显地促进了贸易。他们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企业对于英联邦的市场环境等信息已经非常了解,移民并不能带来额外的信息增益;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英联邦裔移民规模较大,尽管偏好渠道存在,但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当地生产相关产品具有规模效应,所以要比从移民的母国进口更加经济[16]。因此,在这个案例中移民的贸易成本渠道很小,偏好渠道则促成了在移民所在国的本土化生产而非增加进口。
蒙英华和赵倩玉将这种规模经济作用称为进口替代机制,他们研究华裔移民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认为当华裔移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使移民所在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它们也可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而改为在所在国生产。他们进而发现这种进口替代虽然不起主导作用,但在中国对北方国家的贸易中作用突出。北方国家对中国进口的替代也减少了中国出口的低质量产品,有利于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并且高等教育华裔移民对中国出口低质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尤为明显[40]。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进行机制检验的实证文献大多认为偏好渠道的作用较小,这可能也应该部分归因于偏好渠道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并不能有效促进进口。尤其是考虑到文献中研究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普遍工业发达,生产的规模效应突出,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生产效率较低,这就更可能导致偏好渠道的作用有限。
(二)中间品的进口替代
除此之外,移民的流入还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上游的离岸生产,进而减少对中间品的进口。但前人研究中对移民与离岸生产之间的关系结论并不一致。
如果从离岸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无论是企业内部离岸生产(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建立跨国公司)还是企业外部离岸生产(外包),移民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促进相关营商信息的传播,加强契约约束,帮助克服文化、社会、制度上的距离,因此既能降低建厂或收购的成本,又有利于建立跨国的供应商联系,理应促进企业进行离岸生产,尤其是在移民母国的离岸生产。大量文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利用实证数据发现了移民对跨国直接投资(FDI)的促进作用[41,42,43]。苗翠芬等直接以离岸服务外包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移民网络与服务外包承接规模显著正相关,作用机制为降低监管政策差异引致的固定成本,同时移民会产生需求偏好,提高怀旧交易的可能性[44]。
然而,奥特塔维诺(Ottaviano)等人却从数据中发现移民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离岸生产的就业份额。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美国本地居民会承担最复杂的工作,移民会承担最不复杂的工作,而中等复杂度的工作会离岸生产,因此移民的涌入对本地居民影响有限,但却会对离岸生产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在这种替代效应之下,移民的就业将会与中间品进口负相关[45]。他们的文章侧重于对不同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分析,几年后他们另一篇研究英国服务业企业的文章则分析了移民对于企业离岸生产以及进出口的影响。奥特塔维诺等人发现,双边移民比例每增加10%,出口就会增加3%~4%,但中间服务进口会降低1%~2%。他们称之为移民的双边出口促进效应和双边进口替代效应[46]。
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的结果?艾格(Egger)等人认为应该区分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他们考虑了企业的全球采购策略,发现当移民增加时,企业虽然从每个供应商处的进口量(集约边际)会增加,但会减少在该国的供应商数量(扩展边际)。他们认为,当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经营者会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供应商以分散风险;但如果有很多移民能化解不确定性,企业就会减少供应商的数量,但从每个供应商那里购买的数量会增加[47]。奥特塔维诺等人所作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在一个地区的总进口量,因此他们无法区分移民在二元边际上的反方向作用,得到的是一个加总的效果,影响的正负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作用的相对大小[46]。
然而即使是这样,依然无法解释为何移民对进口的加总效应会是负向的。在最新的文章中,奥勒和玻佐利(Olney and Pozzoli)利用丹麦全面细致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以及移民来到该国的外生冲击,重新检验了移民与进口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多边(multilateral)移民减少了总的离岸生产份额,与奥特塔维诺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是双边移民对双边的离岸生产起到的是促进作用,与奥特塔维诺等人相反。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奥特塔维诺等人研究的是服务业企业,他们假设外包的服务只能由特定族裔完成,因此来自某国的移民和离岸生产到该国是替代关系;但是奥勒和玻佐利研究的是全体企业,他们内在地假设了更灵活的生产过程,认为外包的工作不局限于特定族裔,因此来自某国的移民会减少企业总的离岸生产需求,但会增加到移民原籍国的离岸生产[48]。
因此,从承担生产任务的角度来讨论,移民的增多确实替代了部分原本被离岸生产到国外的工作,也可能进而减少了企业从部分国家、部分供应商的中间品进口。但考虑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述移民促进贸易以及FDI的渠道依然存在,表现为企业在移民原籍国和另一部分供应商的中间品进口强度提升。
四、结语
移民对贸易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但已不是一个新颖的学术话题。大量文献已经证明移民总体上对进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很重要,但贸易成本渠道有更重要的效率提升意义。然而,近期依然不乏相关研究继续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总体而言,较新的前沿研究一方面是在因果识别上做得更为干净,使用自然实验结合“偏离—份额”方法来构建工具变量,以获得更加一致无偏的估计结果,例如利用移民接收政策的外生性,利用移民相关协定生效的时空差异等。另一方面则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其他角度,或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如区分贸易的二元边际,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研究移民对贸易协定的制定或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另外,也有学者对移民与进口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对比与前人结论的不同并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沿着这些较新的文献推进的方向继续深耕,这一领域也有一些其他的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1]。第一,关于移民与贸易的关系前人研究已经阐述得较为清楚,但移民、贸易与FDI之间会有更加复杂的相互关联[49]:移民可以认为是劳动力的流动,FDI则是资本的流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会相互促进还是替代?另一方面,FDI与出口被认为是企业进入一国市场的两种替代战略。因此,把FDI纳入移民影响贸易的框架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但也更贴近现实情况。第二,贸易会如何影响移民?这一问题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达国家选择关闭边境的今天更有现实意义,但由于移民决策的内生性更为严重等原因,这方面研究尚不充分。第三,已知移民促进贸易能提升效率,那么这种福利的提升效应具体有多大,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除了国际移民,中国等国还有规模庞大的国内移民同样值得研究。有学者发现放松户籍限制、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要比贸易自由化更大[50]。继续推进相关研究能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内循环提供进一步指导,有突出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