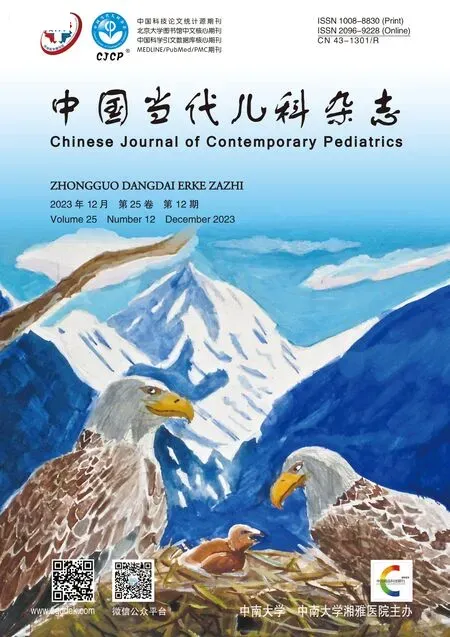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水平检测对生长激素缺乏症的诊断意义和思考
李堂
(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代谢科,山东青岛 266000)
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 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growth factor-1, IGF-1)轴在调控人体生长发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GH 可分别在GH 释放激素(growth hormone-releasing hormone,GHRH)的刺激和生长抑素抑制作用下以脉冲方式分泌,进而作用于多种细胞、组织和器官。对于生长而言,GH以长骨和脊柱骺板为靶器官,是骨骼生长的主要驱动因素[1-2]。GH 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种是通过与跨膜GH受体结合直接作用,另一种则是诱导IGF-1 分泌以发挥效用[3]。IGF-1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机体内GH 分泌状态,是GH 发挥生物学作用的主要介质。因此,GH 与IGF-1相互作用,影响骨骼生长发育。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GHD)是导致儿童身材矮小的常见原因[4],GH 激发试验和IGF-1 水平检测是目前临床诊断儿童GHD 的重要依据。
1 多种GH 激发试验联合使用帮助诊断GHD
GH 激发试验通过下丘脑或垂体水平的各种刺激试验激发GH分泌,并与正常个体在刺激下可以达到的理想GH峰值进行对比,从而判定是否存在GH缺乏。目前国内外指南中推荐用于儿童的药物GH激发试验包括胰岛素低血糖激发试验、精氨酸激发试验、可乐定激发试验、左旋多巴激发试验、胰高血糖素激发试验、GHRH 激发试验[5-6](表1)。其他新型GH激发试验药物,例如马西瑞林和生长激素释放肽-2[5],尚待评估是否可应用于儿童人群。

表1 儿童常用GH激发试验汇总
考虑到任一GH 激发试验均有一定假阳性率(国外调查数据显示身材矮小的儿童经GH 激发试验出现假阳性结果的概率高达30%[7]),故临床应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两种药物激发试验[1,8],以降低过度诊断为GHD 的风险。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矮小症临床路径(2019 年版)》,在纳入胰岛素低血糖激发试验、精氨酸激发试验、可乐定激发试验和左旋多巴激发试验4项中,明确规定必选2项,其中前2项必选1项[9]。当2项GH激发试验中GH峰值不正常时,方可作为GHD的诊断依据之一[1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H 激发试验仍存在特异性不佳的问题,即使进行两种激发试验,其特异性也仅为14.9%~49%[11]。鉴于GH激发试验存在假阳性率高和特异性不佳等局限性,许多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存在是否有必要对患儿进行复测的争议。一方面,由于GH激发试验需要采血,属于有创检查方法,且费用相对较高,重复检测往往会增加患儿痛苦以及家长的经济负担。国外学者Oron 等[12]发现精氨酸-可乐定联合激发试验(n=362)检测儿童晚期和青春期GHD可减少对第2次GH 激发试验的需求。生长激素研究学会针对GH激发试验的复测争议,也认为既往基于不同激发试验被诊断为GHD 的儿童不应被要求重新检测[13]。而另一方面,应当明确GH激发试验是目前临床确诊GHD 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标准。GHD 的诊断应结合生长速率和骨龄等综合判断,具体应满足以下7 个要点[10]:(1)身高落后于同年龄、同性别正常健康儿童身高的第3百分位数或低于2 个标准差;(2)年生长速率低于以下水平,即3 岁以下儿童<7 cm/年,3 岁至青春期前儿童<5 cm/年,青春期儿童<6 cm/年;(3)匀称性矮小、面容幼稚;(4)智力发育正常;(5)骨龄落后于实际年龄;(6)2 项GH 药物激发试验GH 峰值均<10 μg/L;(7)IGF-1水平低于正常。
2 多种因素可影响GH激发试验结果,设定个体化GH峰值切点优化判读
目前不同国家、地区采用的GH激发试验的峰值切点略有不同,国际共识和我国采用的GH激发试验峰值为10 μg/L (峰值超过此值,可排除GHD),部分国家和地区峰值为7 μg/L 或5 μg/L。笔者认为设定个体化GH峰值切点,有助于优化对GH 激发试验结果的判读。多项研究已证实GH 峰值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青春期状态、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14]。
2.1 BMI标准差评分与GH峰值成显著负相关
Abawi等[15]基于5 135例儿童58项研究数据进行了一项系统性分析和Meta 分析,探讨BMI 标准差评分(standard deviation score, SDS)对儿童GH峰值的影响,发现BMI SDS 与GH 峰值成显著负相关,即BMI SDS 每增加1 个百分点,GH 峰值降低11.6%,且这种关系也已存在于BMI SDS 正常范围的儿童,故可能导致超重和肥胖儿童GHD 的过度诊断。另一项纳入991例身材矮小儿童的大型队列研究证实GH 峰值和BMI SDS 呈显著负相关,且独立于激发试验类型[16]。因此对于不同体重儿童的医学诊断,临床医生可考虑根据儿童体重状态调整GH激发试验的临界值,如根据Abawi等[15]的经验:若将5 μg/L作为正常体重儿童的GH激发试验临界值,对于超重儿童(BMI SDS≥1)和肥胖儿童(BMI SDS≥2)临界值可考虑分别调整为4.6 μg/L、4.3 μg/L;若将10 μg/L 作为正常体重儿童的GH 激发试验临界值,对于超重儿童(BMI SDS≥1)和肥胖儿童(BMI SDS≥2)临界值可考虑分别调整为9.3 μg/L、8.6 μg/L。目前现有的研究讨论了分层BMI 指导GH 激发试验的峰值,但是由于所分析的人群包括肥胖和非肥胖但身高正常的儿童,且此类人群未进行GH激发试验,因此这些研究存在高风险偏倚。考虑到BMI 的影响不容忽视,并随着国内超重/肥胖儿童比例逐年升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明确具体数值,以更好地指导实验室诊断。
2.2 青春期前性激素“引发”对GH 激发试验结果的影响尚无定论
青春期前生理性GH分泌往往相对较低,对此类儿童行GH激发试验前,有专家建议用性激素进行“引发”以增强GH 分泌,减少假阳性结果。2016年美国儿科内分泌学指南则建议对>11岁青春期前男性和>10 岁青春期前女性进行GH 激发试验前使用性激素“引发”[17]。目前最常见的“引发”年龄,男孩为10~13 岁,女孩为8~12 岁,所用性激素制剂多为口服17β-雌二醇或己烯雌酚。然而,“引发”时,GH分泌可能会以非生理性方式增强,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从而导致患儿未能及时接受治疗[18]。因此,临床对“引发”仍存在争议,上述研究对结果的影响并不确定,是否能有效减少假阳性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在我国,临床中较少对青春期前儿童进行“引发”,且是否基于青春期调整GH峰值,目前鲜有研究结果支持。
2.3 不同年龄和性别儿童GH 峰值存在差异,新生儿GH峰值有待考证
Chen等[19]进行的回顾性研究纳入18例身材矮小的GHD患儿,结果发现GH激发试验中男性患儿的GH 峰值在>10 岁组中最高,其次是7~10 岁组,≤6 岁组最低;对于女性患儿,7~10 岁组和>10 岁组的GH峰值相比≤6岁组更高。若临床怀疑新生儿患GHD,可通过单次GH检测证实,最好在出生后1周内低血糖发生期间进行检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尚未确定诊断新生儿GHD的GH峰值。2000年儿童和青少年GHD 诊断和治疗共识指出,GH<20 μg/L 提示新生儿存在GHD[20];而2020 年,有研究分析25 例重度GHD 新生儿和281 例健康新生儿(胎龄34.0~37.9 周) 的GH 水平,认为GH<7 μg/L在足月新生儿血液筛查中确认重度GHD具有较高的准确性[21]。而在合并其他垂体激素缺乏症或存在三联征(异位垂体后叶、垂体前叶发育不全及垂体柄异常)新生儿中,2016 年美国儿科内分泌学指南建议GH峰值为5 μg/L[17]。在此问题上,我国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有说服力的见解,适合我国新生儿的GH峰值还有待考证。
2.4 影响GH峰值的其他因素
激发试验时间长短、患儿垂体磁共振成像的冠状高度和矢状面高度与GH 峰值也有一定相关性。Yau 等[22]研究纳入315 例身材矮小或生长发育不良儿童,用精氨酸和左旋多巴进行GH激发试验,发现在试验120 min时停止而不进行至180 min,并不影响GHD 诊断。Chen 等[19]通过比较不同年龄组身材矮小GHD患儿的GH激发试验结果,发现GHD 患儿垂体磁共振成像冠状高度和矢状面高度与GH 激发试验中GH 峰值呈正相关。这些研究所纳入的样本量都较少,指导作用有限。
3 IGF-1 检测也可辅助诊断GHD,并监测GH治疗依从性
IGF-1 是由GH 刺激靶细胞所产生的多肽,主要在肝脏中合成,其在外周血中与IGF 结合蛋白(IGF binding protein, IGFBP),特别是IGFBP-3结合后,输送到周围组织发挥作用。IGF-1在促进细胞生长和分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无明显脉冲分泌,并且昼夜节律变化很小,被认为是GHD 的预测生物标志物[23]。
目前IGF-1 用于GHD 的诊断已成为临床共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所编写的《基因重组人生长激素儿科临床规范应用的建议》已明确指出,IGF-1是协助诊断GHD的重要参考指标[10]。在临床上,我国所采用的IGF-1诊断参考值范围,主要是基于2009年顾学范教授团队发表的我国不同年龄(6~18岁)健康儿童IGF-1水平研究[24],以及2022年巩纯秀教授团队发表的中国1~19岁儿童和青少年IGF-1数据[25]。多数研究表明IGF-1在诊断GHD时具有良好或中等特异度,但灵敏度较低,且IGF-1水平即使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GHD[1,26]。有学者发现IGF-1 SDS 为-2.0 或更低时或可预测GHD,而IGF-1水平>0 SDS且经年龄、性别和青春期校正的数值有极大可能性排除GHD[18,26]。对于骨龄超前的患儿,IGF-1的水平需要根据骨龄校正[27]。
早期识别GHD 患儿,改善终身高,已成为临床的重点关注。IGF-1 也可用于GHD 早期筛查中,不过其准确性仍有争议。Iwayama 等[28]对纳入的298例身材矮小或身高增长速率迅速下降儿童测量IGF-1 水平,并使用可乐定、精氨酸进行GH 激发试验,结果显示IGF-1水平作为GHD筛查的准确性不高,且灵敏度(68.5%)和特异度(41.7%)较低。另一项研究对纳入的649例身材矮小儿童使用GH 激发试验评估IGF-1 水平,结果显示GHD 患儿和其他身材矮小患儿IGF-1水平无显著差异[29]。与前述持不同意见的是,Inoue-Lima 等[30]对48 例GHD患儿和175例GH正常儿童的IGF-1和IGFBP-3采用贝叶斯法分析,结果发现IGF-1 SDS 对识别GHD 的灵敏度为92%,特异度为69%,可作为筛查GHD的有效工具。而国际关于诊断矮小和/或生长迟缓的儿童指南建议将IGF-1(含/不含IGFBP-3)作为实验室检测指标之一,对潜在的临床病理原因进行GHD 筛查[31-32]。但IGF-1 用于筛查GHD的SDS临界值未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学者认为其临界值可能在0~-2 SDS之间[33]。
此外,国内外指南也指出监测GH治疗期间的IGF-1 水平可用于评估治疗依从性和安全性[10,17]。GH 治疗过程中应维持IGF-1 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在患儿依从性较好情况下,若生长情况不理想且IGF-1 水平较低,可在GH 批准剂量范围内增加剂量。若患儿IGF-1水平高于正常范围,往往建议降低GH剂量。然而,IGF-1是否可作为判定GH治疗反应的指标还未在长期研究中得到证实。并且在保证患儿接受GH 治疗获益的同时,GH 治疗剂量应增加或降低多少范围也未确定。因此,若要完整评估如何根据IGF-1 水平调整GH 治疗剂量,需要后续长期、大规模研究。
综上,GH/IGF-1 轴的实验室检测在GHD 疾病领域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考虑到不同患儿的差异性,或可根据患儿BMI、青春期、年龄、性别等因素,调整和建立适合我国儿童人群的GH峰值和IGF-1临界值。同时需要注意临床诊断GHD应结合GH激发试验、IGF-1、生长速率、骨龄等多种指标综合评估,避免单纯参考一项或两项标准。此外,更精准识别疑似GHD 患儿,探寻其他更明确诊断GHD 的新指标等方法,或可帮助改进GHD 诊断,帮助患儿及早确诊并接受治疗以改善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