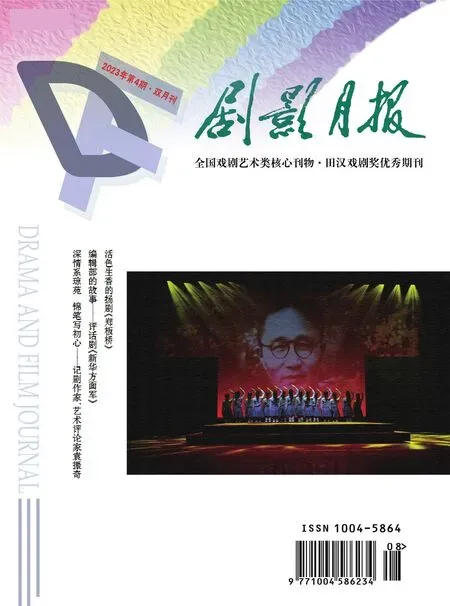浅谈戏曲的歌舞演故事
■刘觅滢
以歌舞演故事,是前人对中国戏曲的明确定义,也是人们对中国戏曲长期形成的共识。在中国戏曲的实践中,通过歌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表现神话故事、社会生活、英雄传奇,完全符合“以歌舞演故事”的美学本性。《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虾兵蟹将的总动员,忠奸邪恶的大比拼,天上人间的搏斗,让一个神话拥有震撼心灵的场面,也拥有地动山摇的力量。在这个神话故事,爱情的力量宛若梦幻,一个不太接地气的神仙故事,因此触到心灵的柔软部分。《情探》原本是一个男人荣华富贵后抛弃糟糠之妻、妻子死后复仇的故事。然而,田汉富有想象力的剧本,一旦被演员激情地载歌载舞的表演在舞台上尽情发挥,那种情感的激荡让人内心波涛汹涌。程砚秋曾说过:“演任何剧都要含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恰如《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伟大作品。作者如果仅仅写出窦娥在蒙冤丧命之际,感叹命运之悲惨,也就会缺少足够的戏剧性的情节张力。关汉卿让窦娥发出:“大旱三年,血飞白绫,六月飞雪的刑前三愿,真的是感天动地。”的呐喊当最后的三愿在呐喊中狂舞,对黑暗的控诉,便具有抗争者的行动力——而且是非凡的行动力,足以造成山崩地裂的行动力。悲剧主题,也强化了一个弱女子赴汤蹈火、不可摧毁的意志力。当然,歌舞在故事中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这种作用往往不是小家子气的润滑点缀,而多半是画龙点睛式的,烘托高潮的辉煌和绚烂。
通过歌舞塑造人物是中国戏曲的主要特色。但是服务于人物的歌舞绝不是大路货的东西,它必须是独特的人物的灵魂舞蹈,是由独特的性格产生的独特的行动。不妨看看那些优秀戏曲作品中歌舞是如何让人物神采飞扬,变成彩绘和雕塑的。脍炙人口的京剧《拾玉镯》几乎完全由真实、生动的细节编织成情节的花环,这花环上的花朵在歌舞中可谓花枝招展、摇曳多姿。它展现了少女孙玉姣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初遇异性的欣喜、娇羞、心灵悸动。她开门、关门、放鸡、数鸡、穿针纳鞋、拾镯、藏镯等一连串的细节,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孙玉姣的性格特点及感情特征。江苏省京剧院的京剧《骆驼祥子》,看文本并没有特别的引人之处。但最后产生的舞台效果却让人们兴奋不已。从京城到乡下县城,从专家到百姓人家,可谓赞不绝口。这样的轰动效应与黄孝慈、陈霖苍二位表演艺术家精彩的舞台呈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个戏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拉黄包车的身段,而且是那么富有形式美和表现力,完全刷新了中国戏曲的舞台语言。就个人条件,陈霖苍演祥子已不是最佳年龄、最佳身材,但是他把握住了人物的灵魂、体态行为,在舞台夸张和生活真实之间,找到了最接近黄包车夫生命状态的歌舞化舞台语言,从而使骆驼祥子的形象与电影、话剧迥然不同自成一格,同时以京剧艺术的鲜明特色,活泛了小说的人物风貌。古装戏里有一些剧本也许并不是最佳作品,但有一些人物却让人们印象深刻。这得力于表演艺术家们运用歌舞的语言,赋予人物的心灵以风采和神韵。如周信芳的《徐策跑城》,那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他舞蹈化的动作中,在须髯的飘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戏创作中,包括颇多争议的"样板戏",在英雄人物的表现中,对于如何以歌舞塑造人物灵魂,也还是有一些成功的探索。如杨子荣的《打虎上山》和解放军小分队的滑雪进军的场面,舞蹈很壮美。无论是人物的服饰还是身段动作,都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它们并非传统程式,是从现实生活中滑雪运动的姿态动作提炼而来,而从这种表现形式以及审美特点来看,它又与传统程式有着内在联系。在现代戏曲创作过程中,舞台时空得到了全新的开拓。有些作品对舞蹈演故事的戏曲特色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开拓,如汉剧《弹吉它的姑娘》,写一个殡葬女工的爱情遭遇,其中有一段戏,是几个男青年出于不同的心理打电话给姑娘的情节。演出中编创了一段打电话的舞蹈,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动作变得轻灵优美,并由此展开了多层次的舞台空间、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当然,在实践过程中,也有一些歌舞演故事的误区,比如,在戏剧元素稀薄、矛盾冲突缺乏、看点亮点较少的情况下,某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以歌舞穿插其中。譬如:用歌舞表现抗洪救灾,表现冲锋陷阵,表现欢天喜地。而这些歌舞既非情节发展的需要,也非人物塑造的必需手段,不是喧宾夺主,便是画蛇添足。这类歌舞往往会打乱整个演出节奏,破坏演出的整体效果。比如,有些老导演善于让满台演出都歌舞化。这一方面说明,导演因为当过演员,拿得出演员的活儿,可以示范讲解,让演员不至手足无措;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导演还是对本子缺少足够的信心,他需要用夸张的歌舞表演、繁杂的舞台场面,让自己内心的不安得到掩饰和消解。他在舞台上设计的动作,相当一部分就是为歌舞而歌舞、以套路做戏路,整个演出表面上行云流水,实际上只能浮光掠影地走过场。比如,有时为了视觉冲击力、心灵震撼力,需要把歌舞场面做得壮观宏大。但是戏曲演出中这类场面是否是越大越好?目前的市场运作水平,已经出现多至六七十人的舞蹈场面。首先,这是需要花钱去经营打造的;其次,就算在资金投入和人员组织方面没有问题,也容易破坏本身的剧场整体。宏大壮观的舞台场面固然是资源共享的优化结果,但土豪金式的摆阔却是冗杂多余的破坏因素——不可缺少的豪华歌舞确实可以支持,但鸡肋式的歌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或者有些歌舞成为大年三十晚上的兔子,“有它不多,无它不少。”
传统戏曲的创作观念,往往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规制内容,其实形式有时是可以变为内容的。在新戏《徐虎的故事》中,三个报修箱拟人化,以三个年轻女孩来表演,贯穿全剧,她们与主人公徐虎对话、碰撞、积极互动,是载歌载舞的生动与有滋有味的思考有机结合,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内容的转化和变异。从剧情设计开始,有表演发挥空间的歌舞表演,适合为表导演提供二度创作的情节和场面。在现代扬剧《皮九辣子》中,有一场墙里墙外戏,皮九和顾二嫂互相试探心意,从顾二嫂干活常用的小凳、竹竿,到皮九遗落的纽扣,环境、心境、道具都为歌舞演故事提供了足够的条件,歌舞也联络起诸多要素,形成精彩的戏剧场面。探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时代结合,让歌舞更具有穿透心灵的力量。锡剧《孔繁森》是歌颂英雄人物的一个现代戏,主要事迹当然不可能脱离新闻报道,但能否通过想象力让人物的灵魂如飞天一般,手持彩练当空舞?而这种想象的舞台体现,不是说教的、空泛的,应该是饱满的、朴实的。剧中有一个情节,孔繁森深入群众走访藏民,夜宿雪山时发生了严重的高原缺氧现象。他身心疲惫,感觉天昏地转,人几乎不行了,便写下遗嘱,准备直面死神。就在这个昏昏沉沉的时候,他产生了幻觉:年近百岁的老母亲来看他了。老母亲是自己推着轮椅来的,母亲走下轮椅,听儿子叙述,给儿子打气鼓劲。儿子说,妈,我不行了,我就要倒在这高山上了。母亲说,起来,儿子,那么多藏民同胞盼着你呐。最后是母亲把拐杖递给孔繁森,让他扶着坐到轮椅上。于是在风雪高原上,出现了这样激动人心的一幕:百岁老母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前进在茫茫雪原的长路上,一段心曲伴舞,让人心生感动。
国外的音乐剧与中国戏曲在歌舞演故事的命题上,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从当年的《猫》《悲惨世界》到如今的《人鬼情未了》,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现代舞、音乐说唱、街舞等在音乐剧中的广泛应用,同样会启迪多维的创作方式,让更多的当代歌舞与传统戏曲融汇渗透,解构和重建。更多地了解当代文学艺术在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的最新成果,尤其是跨界的创意,新鲜的手段,乃至天马行空的思维,能够让民族的创作风采更迷人,创作眼界更高远,创作情怀更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