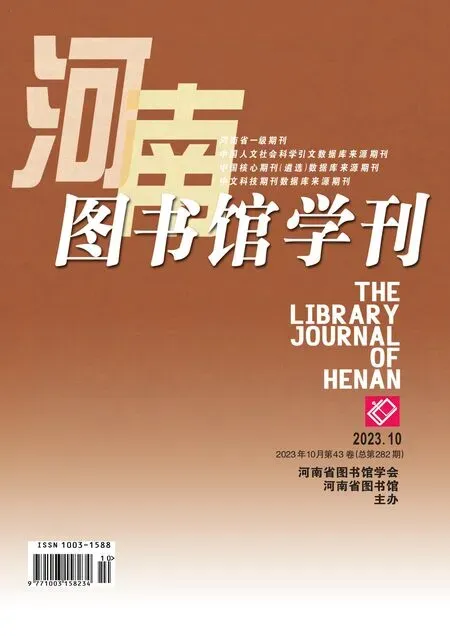刍论著作权转换性使用规则适用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
刘 微
(郑州图书馆,河南 郑州 450000)
美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规定和关于“例外权利”的条款是分别设置的,这种“因素主义+规则主义”的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非经授权使用作品的开放立法模式,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基于“规则主义”的封闭式立法[1]。美国对合理使用采取开放立法的最大优势就是使法律制度具有较大的适用弹性,在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类型案件中显示出明显的包容性,较之封闭式立法更加灵活与有效。尤其是随着以“转换性使用”为代表的著作权创新理论的出现和相应规则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丰富了美国著作权制度中以“四要素”为圭臬的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内涵,展现出新的活力与生机,在应对一系列数字图书馆著作权案件的挑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和基于数字技术的图书馆新的服务功能的开发创造了新的法律条件。目前,美国著作权转换性使用规则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其地域范围之外,我国人民法院借鉴这项规则审理的著作权案件日渐增多,我国图书馆界应积极利用转换性使用规则的理念和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提供的新的法律条件,开展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1 美国著作权制度中判断合理使用标准的发展脉络
1.1 从判例法到成文法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特别是其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结果与裁决倾向于对其他法院的司法实践具有规范和引导价值。追根溯源,美国现行《著作权法》第107条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就萌芽于其判例法,是对大量案件审理成果的总结与发展。1841年,美国法官Joseph Story在“Folsom v.Marsh案”中,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系统地阐述了合理使用理论。此后,随着司法实践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合理使用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由此推动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成文法进程,并在1909年《美国著作权法修正案》中设置了“合理节略”的规定[2]。1976年,美国颁布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这部法律对著作权制度中的诸多规范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成为美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中取消了“合理节略”的规定,而在第107条设置了“合理使用”条款——著名的“四要素”[3],即判断使用作品行为的合法性需要综合考量下列因素:使用的目的与特点;作品的类型;使用的作品中,被使用部分与整体的比例;使用作品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所造成的影响。至此,以“四要素”为核心的合理使用制度最终实现了法典化,成为美国司法实践中审理著作权案件时最核心的标准。
1.2 从“四要素”到“转换性使用”
合理使用“四要素”在美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是一种“抗辩事由”,是法院认定使用行为合法性的依据,而非使用者可以按照其《著作权法》第108条至第122条直接行使的“例外权利”。如果使用者在“例外权利”条款之外使用作品而被起诉,法院则要按照“四要素”的原则规定,判断其行为是否合法。然而,“四要素”的规定较为笼统和抽象,甚至有些简陋,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知性,以致司法实践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等问题。有学者指出,“四要素”的规定并不科学,是“一种粗糙的公正”[4]。特别是在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新型案件的挑战中,“四要素”的弊端愈发突出。1990年,美国法官Leval在梳理自己长期从事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四要素”为前提,创造性地提出了判断合理使用的“转换性使用”理论,认为如果对作品的后续使用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必须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或者根据其他目的与性质,创造出新的信息、美学、认识与理解[5]。该观点随后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案”的审理中采纳,成为著作权司法实践的重要原则。
2 转换性使用规则对合理使用“四要素”的新诠释
2.1 对商业使用行为的解释
著作权制度是一种激励工具,权利人再创作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其从事智力劳动得到的经济回报,而合理使用则限制了权利人通过自己行使权利获得报酬的机会,这构成对其经济利益的“第一次打击”,但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具有合理性。然而,如果使用者在行使例外权利的同时,利用权利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获利,则将进一步萎缩作品的市场空间,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构成“第二次打击”,则属于不合理。因此,对使用作品行为是否具有商业利益的判断被放在“四要素”的第一位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商业性使用”的重要地位在“Campbell v.Acuff-Rose Music案”之后被动摇,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更是被法院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法院指出,谷歌数字图书馆的行为是转换性使用,其商业动机不影响转换性使用,转换性使用倾向于合理使用的成立。谷歌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和权利人提供的服务具有质的不同,没有剥夺权利人未来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机会[6]。可见,在转换性使用规则框架下,对使用行为合法性的判断由是否具有商业性向是否增加了新的表达和功能转化,是否具有商业性这个原本对判断合理使用有较大影响的因素显得不再重要。
2.2 对使用作品数量的解释
“四要素”中的第二要素,即“作品的类型”,并不利于对数字图书馆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但基于转换性使用规则,这个标准的重要性逐渐式微,转而侧重于对第三要素“使用作品数量”是否合理的判断。合理使用规范要求将使用作品的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是防范将他人作品变成使用者的作品。在判断使用作品“量”的同时,法院还要考量使用作品的“质”,即便使用作品的“量”具有合理性,但假若构成对他人作品“实质部分”的利用也属于不合理。基于转换性使用规则,对使用作品“量”和“质”的判断,在美国法院对数字图书馆著作权案件的审理中都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认为谷歌数字图书馆提供的片段浏览功能具有合理性,因其将图书的每一页都分成八个部分显示,而且片段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使用者不可能通过多次搜索、浏览将不同的片段集合为一个作品整体。另外,谷歌数字图书馆将每本书20%的内容列入“黑名单”,用户始终无法浏览[7]。在“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更是认为数字图书馆提供的全文搜索功能具有合理性,因为这是实现数字化项目的目的所必需的[8]。因此,只要数字图书馆使用作品的行为具有转换性,无论是使用作品的“量”还是“质”都可以突破传统认识当中的“合理限度”。
2.3 对竞争性替代的解释
“四要素”中的第四要素,即“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造成的影响”同样是判断合理使用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例如,有学者认为对合理使用的判断最终要落脚在使用者的使用是否会对原作品市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上[9]。特别是1980年著名的“索尼案”奠定了该要素的核心地位,其适用主要是衡量使用行为是否对原作品构成竞争性替代,即所谓的“市场中心”范式。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指出数字图书馆提供片段浏览功能,不对权利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即使有时搜索者的需求通过数字图书馆得到满足并导致销售量的损失和图书馆需求的减少,但这些销售损失通常与著作权并不保护的历史性事实有关,不足以使这些复制构成有效的竞争性替代。在“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认为数字图书馆提供的证据表明,如果通过为用户提供图书检索、为视障者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方式构成对原作品市场价值的侵害,不仅需要有较高的投入,而且要面临较高的风险,因而没有实际的可行性。相反,无论是“谷歌数字图书馆案”,还是“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案”,法院在审理中都认为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不同于原作品的功能,由于增加了作品的可见度,有利于扩大作品的销售市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判断合理使用行为的“市场中心”范式向“转换性使用”范式转化的趋势。
3 转换性使用规则对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影响
3.1 对图书馆著作权立法的影响
201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包含了“四要素”的内容[10]。在此背景下,目前我国人民法院适用转换性规则审理的著作权案件已达数十起,这为我国合理使用制度有效应对新技术的冲击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要将《意见》第八条的主要精神真正变为一种规范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被人民法院普遍遵循的原则,就必须将其法定化。我国图书馆界在参与完善著作权立法的过程中除应提出补充“权利限制”条款下的合理使用“清单”的建议外,还应呼吁学习借鉴美国《著作权法》中的“四要素”与司法实践中适用转换性使用规则的经验,对合理使用采取开放式立法,主要是将现行“权利限制”条款下的开放性表述单独列为一个条款,以便能够包容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对作品进行挖掘、检索、浏览等使用目的的需求。
3.2 对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影响
数字化存储与定位提高了信息检索与使用的效率,其不仅应用于生产经营,更成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辅助手段[11]。图书馆对馆藏资源的大规模数字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保存作品、搜索和获取作品以及大数据分析[12]。美国法院对“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案”的判决结果,契合了大规模数字化存储与网络定位的要求。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对合理使用立法模式和适用标准的不同,导致我国图书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八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范畴之外对馆藏资源的非经授权的数字化保存存在较大的风险。转换性使用规则对我国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与出版社、数字资源供应商谈判授权事宜时,应基于转换性使用的理念,积极引用国外的成功案例,争取本地数字保存的权利,以防范网络故障导致的数字信息资源存取障碍。
3.3 对丰富用户服务功能的影响
无论是“谷歌数字图书馆案”,还是“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案”,美国法院都认为数字图书馆使用作品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作品的使用具有不同于原作品的新的目的或新的性质,也就是具有“新功能”,如:法院认为谷歌数字图书馆将书本内容转化成数据的目的是数据挖掘和文本服务,从而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还认为谷歌数字图书馆对图书的使用方式以前从未有过,赋予了图书新的价值,能够促进新的信息和创意的产生[13]。我国图书馆在转换性使用规则的指引下,也可以开展多样化的功能开发与服务,如在对馆藏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上向用户提供检索、片段浏览等服务,还可以利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阅读障碍者获取作品的有利规定,开展丰富的作品无障碍获取服务。在这些服务中,图书馆必须以我国法律规范为前提,事先评估著作权风险,正确把握行为边界,由于目前转换性使用规则在我国的适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律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图书馆不能完全以此规则作为免责的挡箭牌。
3.4 对数字项目开发模式的影响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是耗资巨大且具有相当风险的工程。相对于政府支持的公共图书馆,私营力量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支持数字项目计划的实施,能凭借商机接触到最新的数字技术和信息,从而成为推动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美国法院适用转换性使用规则对谷歌数字图书馆商业性质合理性的认定,呈现出支持私营力量介入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明确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14]。一方面,政府有必要从政策上对数字图书馆的商业化运作持一定的开放态度,为能够带来明显社会利益的数字化项目提供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空间;另一方面,图书馆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条件,与私营力量合作开展数字化建设,创新多元化的运作模式,同时在收费标准、利益分配、资金管理等方面接受审计、国资等部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