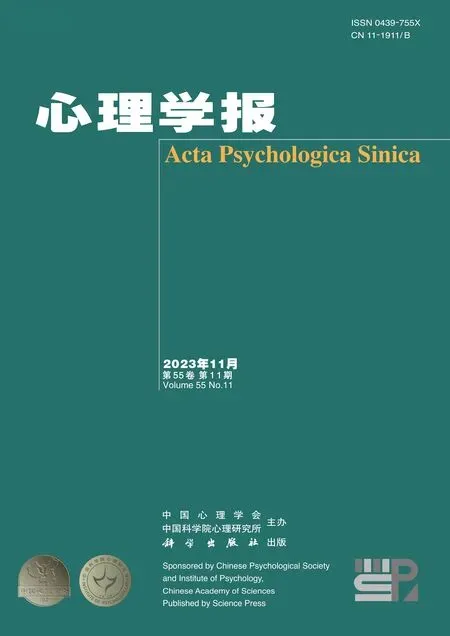延展心智:脑是实现心智的唯一基础吗?*
苏佳佳 叶浩生,2
延展心智:脑是实现心智的唯一基础吗?*
苏佳佳1叶浩生1,2
(1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金华 321004) (2广州大学具身认知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当今时代, 人类正处于科学技术试图催生新文明的前夜。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科技将人类的认知能力延伸到机器之中, 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情感和意识体验, 使得人们逐渐接受“心理生活并不局限于脑”这样一种信念。这引发了人们对“延展心智”问题的关注。延展心智曾经主张, 记忆、思维、情绪和情感等心理过程并非局限于有机体的脑或中枢神经系统。相反, 在某些条件下, 有机体非神经部分的身体、身体之外的环境和世界都是实现心智的有效成分, 发挥了构成性的功用。早期的延展心智研究集中于认知过程的探讨, 经历了三波浪潮; 后来又扩展到延展情感, 探讨了情绪和情感的延展属性。近期, 意识体验是否可延展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如果认知、情感和意识体验都可超越个体的生物疆界, 包含实现心智过程的外部资源, 那么, 心理生活可能就不再囿于头颅和皮肤, 脑也并非实现心理生活的唯一器官。实际上, 延展心智依然是建立在具身认知的理论之上, 关键是如何看待“身体”的主动作用。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心理生活的本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心理生活, 延展心智, 延展认知, 延展情感, 延展意识
“如果能出现新的轴心时期, 它必定在将来, 正像第一轴心期紧跟在一个漫长的间歇期之后, 即普罗米修斯时代, 这一时期奠定了发现的基础, 最终使人类生活脱离了动物界, 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 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 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 (雅斯贝斯, 1989, p.113)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1 延展心智
轴心时代以来, 人类一直生活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北纬30度上下、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释伽牟尼和以色列的犹太先知等先哲确立的文明范畴之中。几千年来, 并没有革命性的新文明诞生。当今时代, 人类正处于科学技术试图催生出新文明的前夜。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科技将我们的记忆储存等“认知能力”从大脑延伸到机器之中, 俨然已经成为了人类“延伸的大脑”。2022年, 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诞生, 它不仅可以像人类一样交流, 还具有写文章、编程序、改代码等思考决策能力, 甚至还有幽默等“情感表达”。未来, 在马斯克的元宇宙文明构想中, 人类的“意识”似乎也可以超越人脑, 延展到机器上。凡此种种, 机器似乎“拥有”了人类的智能, 这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心理生活并不局限于人脑”, 引发了人们对“延展心智”问题的关注。
“延展心智” (extended mind)指的是“认知并非总是和必然地限制于人脑……服务于人类认知加工的物理状态可以超越个体生物脑的疆界, 包括了个体的身体和环境的适当部分这样一种观念” (Boem et al., 2021, p.14)。近年来, 这一观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Heersmink, 2020, 2022; Overstreet, 2022; Parise et al., 2020), 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Adams, 2019; Kiverstein, 2018; Ongaro, 2022; Rupert, 2004; Smart, 2022; 刘志斌, 高申春, 2016; 朱林蕃, 赵猛, 2019)。最初, 延展心智似乎只是一种心物关系的哲学思考, 但是, 现在这一问题的探讨开始影响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经验研究领域(Armitage et al., 2022; Farina & Levin, 2021; Fivush, 2011; Froese, 2015; Redshaw et al., 2018; Sims & Kiverstein, 2022)。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证实, 儿童的确经常使用“认知卸载”等策略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Armitage & Redshaw, 2022; Bulley et al., 2020)。认知卸载实质上就是一种认知延展策略。通过身体和身体与世界的互动, 认知活动不再局限于脑的中枢神经系统, 而是与外部环境资源形成整合的系统, 从而扩展了认知范围和能力。也就是说, 儿童的问题解决策略并非总是依赖于“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 记忆并非总是储存在头脑中, “智能手机、意念控制的假肢和谷歌眼镜都提供了存储信息的新方法……记忆似乎无处不在: 从海兔的神经节到DNA, 再到硬盘” (Zlotnik & Vansintjan, 2019, pp.2−3)。正如Farina和Levin (2021)指出: 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者们在日常工作和实践中, 早已含蓄地接纳了延展认知的观念……延展心智已经成为一个稳固和成熟的研究规划, 且对经验科学有着强烈的实践意义……, 它并不是一种缺乏经验内容的哲学咒语(pp.131−134)。
早期, 延展心智研究集中于“认知”的探讨, 经历了三波浪潮, 后来又扩展到“情感”, 探讨了情绪情感的延展属性。近期, “意识”是否可延展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将首先讨论三波延展认知, 进而追溯从延展认知到延展情感的演进历程, 最后论述意识体验的可延展性。在此基础上, 思考延展心智观念给我们认识心理生活的本质所带来的启示。
2 三波延展认知及其启示
“延展认知”的基本观念最早是由认知科学哲学家Clark和Chalmers (1998)在其经典论文《延展心智》中提出的, 随后在认知科学领域激发了热烈讨论。Clark和Chalmers在论文的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问道: “心智止于哪里?世界的其他部分始于哪里?” (p.7)。表面上看, 他们所提出的是一个“位置”问题, 即心智在头脑中, 脑是心智的唯一器官?或者心智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界限, 延伸到环境和世界?但是, 深入分析揭示出, 他们关切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心智的位置, 而是在对认知、意识乃至心智的“本质”发问。心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使得它能超越头颅和身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物理环境和世界中?
Clark和Chalmers依据的是一种“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观点。功能主义主张, 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心理的, 不取决于它的内部构成, 而是依赖于它所发挥的能力, 或者它在自身所属系统中扮演的功能性角色。举例来说, 外出购物时, 我们可以在头脑中记住所要购买的物品, 也可以用手机记录一个购物清单, 方便查阅。实际上, 人脑和手机这两种信息保存方式都是为了实现同一种记忆功能, 在前一种实现方式中, 信息暂存在人脑中; 在后一种实现方式下, 信息暂存在手机中。我们没有必要因信息存储的位置不同而视前者为“心理的”, 后者为“物理的”。人脑、笔记本和手机都是实现记忆功能的有效载体。因此, 功能主义坚持“多重可实现” (multiple realisability)原则, 即同一类型的心理状态可以在不同的“基质” (substrates)上实现。
在随后的争论中, Clark等人利用了“对等原则” (Parity Principle)来为延展认知辩护。首先, 根据对等原则, 头颅和皮肤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分界, 决定某个事物是不是“心理的”, 不是取决于它的位置, 而是取决于它所发挥的功能:“如果我们面临某项任务, 世界的某个部分发挥了某种功能, 如果这个功能在头脑里,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识别它为认知过程的一个部分, 那么, 世界的那个部分(因此我们主张)就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 (Clark & Chalmers, 1998, p.8)。这就是说, 重要的不是位置, 而是为完成那项任务所作的贡献。如果贡献对等, 那么状态就应该是对等的。在这里, 关键的问题在于功能的同态(isomorphism)或对等性。如果手机具有与大脑同样的记忆功能, 那么, 我们就可以认为, 手机也具有认知能力。换言之, 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超越头颅, 而延展到手机中。因此, 手机就可以被视为人类一种技术器官, 作为人类五感的延伸, 与大脑一道共同构成人类的认知系统。进一步思考, 如果人脑之外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都是实现认知功能的有效载体, 那么, 我们完全可以说, 认知超越了人脑, 而延展到身体和环境之中, 身体和环境也是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等原则构成了早期延展认知观念的界定性特征。认知科学家John Sutton虽然赞成认知的延展性观点, 但是却反对使用对等原则对延展认知所做的解释。Sutton (2010)看来, 认知的延展性存在着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即延展认知的第二波。“第二波延展认知”强调内部生物因素与外部物理因素在认知形成中的功能差异。恰恰是这种功能上的差异, 而不是功能对等影响了认知。“从第二波延展认知的理论家来看, 其主要问题恰恰是早期延展心智主题倡导的对等原则……因此, 延展心智的第二波挑战对等原则” (Gallagher, 2018, p.430), 并在其理论建构中, 尽可能地避免对等原则的使用, 转而利用“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作为理论工具, 尝试使用互补原则来对认知的延展性进行解释和说明。
Sutton (2010)认为, 对等原则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其一, 对等原则忽略了人们在利用外部资源方面所存在的个体差异。在日常生活中, 面对复杂的活动, 根据一个人的嗜好、需要、偏向和兴趣等等, 人们在利用外部资源时, 其方式和风格存在着明显不同。同样是记忆列车时刻表, 有人喜欢记录在笔记本里, 而另外的人可能宁愿到候车室的屏幕上查阅车次信息, 还有一些人复述几遍后, 把它保存在头脑里。这启示我们, 某些人可能更善于延展认知, 因为这些人更善于利用外部资源。但是, 对等原则却忽略这种个体差异, 关注的仅仅是认知状态和认知过程的一般特点。其二, 对等原则忽略了认知所利用的外部资源的差异, 似乎所有的外部物体在改变认知状态方面发挥着千篇一律的作用。由于外部物体在性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某些外部物体比其他外部物体更易于改变认知, 导致认知状态的延展和变化。比如, 笔记本和计算器就比课桌和茶杯更容易为认知所利用, 认知更容易通过笔记本和计算器而得到延展。但是, 对等原则却忽略这种差异, “没有直接提示我们探讨特殊外部符号系统的特异和独特性质, 忽略了与这些外部资源互动的特殊方式” (p.200)。其三, 对等原则忽略了认知的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性质上的差异。脑内部的生物机制与脑外部的物理机制从性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丢失笔记本, 但是你不可能丢失头脑。二者尽管具有同样的保存信息功能, 性质却迥然相异。
有鉴于对等原则存在的上述问题, 第二波延展认知主张改造延展认知的经典主张, 以“互补性”取代“对等”。“互补性”指的是“整个(持久的或暂时的)系统的不同成分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具有不同的性质, 但是可以以集合的和互补的耦合(coupling)方式对灵活思维和行动做出贡献” (Sutton, 2010, p.194)。换句话说, 第二波延展认知的理论家认为, 手机等外部物体之所以能增强生物脑的记忆能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于生物脑的功能属性。第一波延展认知强调了“内外”功能的同态或对等, 鼓励我们关注内外成分的类似和相同处, 从而忽略了神经系统与非神经系统操作上的差异。第二波延展认知恰恰要求我们关注内外成分的“不同但互补”的属性。内部的神经过程与外部的非神经成分虽然属性不同、功能各异, 但是它们却是可以互补的。两者互助互利, 紧密结合, 从而形成了一种“混血儿”式的认知力量, 大大增强或放大了认知能力。
话剧表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话剧演员需要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的台词, 这对于普通人很困难, 但是, 有经验的演员会利用舞台的各种布景和安排来记忆台词, 在不同的时间, 利用不同的舞台设计和与之互动的方式, 巧妙地提醒自己应该表达的内容。在这里, 演员的记忆延展到舞台上的许多外部资源, 生物记忆与外部资源并非对等, 而是耦合与互补之关系。生物记忆与外部物体互动互补。因此, “第二波延展认知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对等原则的依赖, 转而强调利用环境物体和结构改变认知过程” (Loughlin, 2020, p.5)。
如果说第二波延展认知只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等原则的使用, 那么, 第三波的延展认知则尝试完全抛弃对等原则, 转而接受“非线性动力学”的概念, 对认知的延展属性作出全新的解释。Sutton主张, 除了延展认知的第二波外, 可能存在延展认知的第三波, “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第三波延展认知, 它可能是一种去除内部和外部边界的认知科学……第三波延展认知将这些内部和外部边界分析为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发展和文化成就, 这个边界总是开放的……” (2010, p.213)。
在《延展认知及其固定属性: 走向延展认知的第三波》一文中, Kirchhoff (2012)发展了Sutton的观点, 总结了“第三波延展认知”的几个特点: (1) 延展认知的内在和外在成分并无固定不变的属性。第二波延展认知曾经主张内在成分与外在成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 但是这些属性是互补的。第三波延展认知则认为, 无论是内在成分还是外在成分, 其功能属性都具有“历时性”特征, 即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形”和“重组”, 并非固定不变(Kirchhoff & Kiverstein, 2020); (2)心智的边界不是固定的, 而是开放的和灵活的。因此, 它淡化“边界” (boundary)概念。对等原则主张, 对于行动主体来说, 存在着“内在的”和“外在的”的区别, 即内部心理和外部世界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第三波的延展认知则认为这个边界是相互渗透的和开放的, 与知觉和行动的范围有关; (3)反表征主义。对等原则假定了内在和外在的区别。相应地, 行动主体需要通过内部机制“表征”外在世界。外在资源之所以能发挥认知功能, 就在于它能替代内部机制表征外部信息。在这里, “表征”功能是必须的。但是, 在第三波延展认知那里, 表征概念完全是多余的。行动主体沉浸在各种文化实践活动中, 与世界互动、耦合, 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本身就是最好的表征, 不需要再假定内部认知表征的存在。(4)最后, 取消中枢神经系统在认知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主张认知并非以有机体的脑为中心, 而是分布于脑、身体和环境之间, 是三者互动与耦合的结果。认知系统是个“混血儿”, 其中一些成分是神经的, 另外一些是非神经的身体部分, 还有一些是外在世界的。认知并不存在于头脑中, 就像“飞翔”的能力并不存在于鸟的翅膀里, 而是存在于鸟的翅膀与空气的动力学交互之中, “认知”涌现于脑、身体和环境三者的互动与耦合之中。
尽管三波延展认知的侧重点不同, 在一些问题上, 如怎样看待对等原则方面, 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主张, 但是, 它们分享着一些共同特点:“概括地说: 把各种取向整合在一起的, 是他们都主张某些认知或心理过程并不限制在心物的焦点, 而是延伸出身体的自然疆界, 包含了某些外部实体, 无论这些实体是物理器具、技术装置, 甚至是其他个体或群体。” (León et al., 2019, p.4847)
首先, 延展认知倡导者都认为认知并非发生在个体头脑中的私有事件。实现认知的物理机制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包含外部资源。认知可以超越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延伸到身体, 并通过实践活动延展到环境和文化之中。在这一点上, 它与传统认知主义大相径庭。无论是符号加工心理学, 还是联结主义心理学, 都主张认知过程发生于有机体的内部, 是内在的, 与环境和世界是隔绝的。但是, “延展认知的假设并不主张人类的认知过程时时处处都是神经生理过程与环境资源的混合物, 而是认为某些认知过程是神经的、身体的、环境因素的软集合。因此, 延展认知假设与内在主义观点是截然对立的” (Sims & Kiverstein, 2022, p.27)。
其次, 延展认知是反对“神经中心主义” (neurocentrism)的。根据神经中心主义, 脑是心理的主要器官, 中枢神经系统是认知过程的唯一机制, “无论主观经验, 还是社会经验, 都依赖于包含于头颅内的、奠基于脑内的表征过程和内容为基础” (Zaslawski & Mathieu, 2017, p.1)。但是, “Clark等人倡导了有关认知系统的一个特殊范式:根据这一范式, 认知系统由脑、身体和环境构成, 即延展心智的假设。这一假设主张, 人类认知过程是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协同作用的结果, 认知过程并非限于神经环路” (Anderson, 2015, p.1)。这就是说, 中枢神经系统并非认知过程的唯一实现基础, 认知过程动力性地分布于脑、身体和环境之中, 是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
3 从延展认知到延展情感
Sim和Kiverstein (2022)指出:“自从Clark和Chalmers (1998)首次提出延展认知以来, 延展认知已经经历了几波浪潮。但是这几波延展认知的共同点是, 都聚焦于人类的认知过程” (p.27)。换言之, 他们仅仅关注了心智的认知方面, “给予认知以中心地位” (Carter et al., 2016, p.198), 心智的情感方面却被忽视了。近年来, 人们开始“关注情感现象, 如情绪事件等是否也可以延展到外部资源” (Viola, 2021, p.229)。“延展心智的假设指出, 在认知过程中, 环境中的物体发挥着心智的部分功能。基于这样一种思路, 某些情绪的研究者主张存在着情绪的身体延展和情绪的环境延展” (Brinkmann & Kofod, 2018, p.160)。实际上, 由于心境、情绪和情操等情感(affectivity)与身体和环境的固有联系, 情感更容易超越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延伸到环境, 与外部资源形成互动耦合的整体(叶浩生等, 2021)。
传统上, 受内在主义心智观的影响, 情绪被视为发生于有机体内的生物或神经反应。在著名的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中, 情绪是“紧随令人激动事实的知觉之后的身体变化, 当这些变化发生时, 我们对同一变化的感受就是情绪” (James, 1890, p.1065)。换句话说, 詹姆斯认为情绪就是对身体变化的感受, 而这种感受发生在有机体内部, 是一个“内在”事件。当代新詹姆斯主义者、神经科学家Damasio (1999)继承并发展了詹姆斯的情绪观点, 主张情绪就是大脑内部代表身体变化的神经模式的激活。这些理论观点都是内在主义情绪观, 似乎只要关注发生于有机体内部的过程就可以理解情绪。依照这种理解, 情绪的延展是不可能的。
但是, 情绪不仅是一种内在感受, 还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动力性。情绪不仅为外物所引起,而且指向一定的对象, 会引发一定的行动。愤怒并非仅仅是具有心跳加速、面红耳赤等身体变化的内在情绪感受, 还是被某个外在事件所引起的, 更会引发我随后的行动。情绪的这种意向性和动力性把内在感受与身体、环境连接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情绪和情感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延展到了外在世界。
情感延展的最基本表现是情绪体验对身体的依赖。实际上, 具身的情绪学说早就主张, 情绪并非发生在脑中的认知评估。实际上, 悲痛、惊愕、愤怒和喜悦等情绪体验都伴有心跳加速、肌肉紧张、瞳孔放大等明显的生理现象。这些生理反应并非情绪的生理伴随物或副产品, 而是情绪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情绪体验的形成过程中, 身体的生理、生物、形态和行动细节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非神经的身体部分在情绪体验的形成中做出了重要贡献(Carr et al., 2018)。
情绪体验超越了头颅的疆界, 而延伸到非神经的身体部分, 这被称之为情绪的身体延展假设(the hypothesis of bodily extended emotions)。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支持了这一假设(Brinkmann, 2020; Gross, 2015; Jain et al., 2019)。这些研究发现, 面部表情、姿势、手势和动作都是情绪载体的有机部分。例如, 注射了肉毒素之后, 情绪体验的能力明显下降。那些患有抑郁情绪的病人注射了肉毒素以后, 由于面部肌肉的麻痹, 无法皱眉, 抑郁症状也有了明显改善(Havas et al., 2010)。再如, 莫比乌斯综合征(Moebius Syndrome), 这是一种先天性双侧面瘫, 患者缺乏面部表情的能力。病人经常报告说, 情感体验变得平淡或减弱, 而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缺乏面部表情造成的。一个患有此病的人声称她小时候没有情绪, 因为她无法用面部表情表达情绪感受。然而, 当她在西班牙度假时, 被当地人优雅的手势所打动, 回国后, 她有意识地将类似的手势融入到自己的行为中, 最终发现这种利用整个身体来表达情感的过程重新校准和强化了她的情感体验(Krueger, 2014)。这都说明了情绪和情感的身体延展, 支持了延展心智的“反神经中心主义”观点。
情绪的身体延展假设同“具身认知” (embodied cognition)的情绪学说是一致的, 两者都认为情绪的载体超越了中枢神经系统, 包含了非神经的身体成分。两者的不同在于: 具身的情绪学说认为情绪的载体是生物的、生理性质的, 存在于机体的内部, 而延展情绪则主张情绪的载体不仅存在于有机体内部, 而且超越了皮肤的界限, 包含了承载情绪的外部环境(Krueger & Szanto, 2016)。这就引申出情绪的环境延展假设(the 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emotions)。
情绪的环境延展假设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上, 即在某些条件下, 情绪和情感的载体直接超越了行动者的身体, 延展到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外部资源上。在某种意义上, 如果没有这些外部资源, 适当的情绪和情感就无法产生。在这里, 外部资源成为情绪感受的载体, 扮演着驱动、促成或导致情绪体验的角色。例如, 某种音乐会诱发乡愁, 刺眼的光照可引发愤怒, 红色的背景能激发兴奋, 而蓝色的月光则让人平静。音乐、光照、色彩和月光都是情绪和情感的载体, 没有这些外在的载体, 此类情绪和情感就无从产生。在这个意义上, 音乐、光照、色彩和月光都成为情绪和情感的适当成分。它们超越了个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环境, 成为我们实现情绪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延展认知的对等原则, 如果某种外部资源在认知产生的过程中扮演了与内部生物资源同样的角色, 那么这些外部资源就可以被认为是认知系统的适当构成成分。在经典的奥拓(Otto)思想实验中, 罹患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的奥拓把需要记忆的信息记录在笔记本里。笔记本发挥了与脑的生物记忆同样的功能。因此, 笔记本构成了奥拓记忆系统的适当成分。在这个意义上, 奥拓的认知延展到了笔记本这个外部资源, 没有这个外部资源, 奥拓的认知就无法正常进行。同样地, 对于某些情绪体验来说, 特定的环境条件是必需的。没有这些环境条件, 情绪体验就无从谈起。特定的环境状态或条件提供了培育某种情绪感受所必需的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就构成了实现某种情绪体验所必需的部分, 成为情绪系统的构成成分。
但是, 正如对等原则在解释认知的延展属性时所面临的困境那样, 对等原则在解释情绪的延展属性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尽管内部生物资源和外部物理资源发挥着同样的功能, 但它们是异质的, 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格式和动力。换言之, 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不具备功能同态性(functional isomorphism)。体内疼痛和阳光照射都可以诱发愤怒, 两者功能相似, 但是性质完全不同, 导致的行为反应也大相径庭。因此, 情绪的延展可能更适合在“互动”和“互补”的框架下进行解释。钢琴师在弹奏音乐时, 钢琴师的情绪和情感通过钢琴得以抒发。同时, 弹奏出来的乐音又改变了钢琴师的情绪体验, 影响了接下来的钢琴演奏。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和耦合的圆环, 彼此制约、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 情绪和情感超越了个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环境物体, 与外部资源形成氤氲聚合的整体。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情绪的身体延展还是情绪的环境延展, 情绪都是个体的。不管情绪载体是身体化的, 还是外在物理性质的, 情绪体验都为个体所拥有。即使情绪的生理或物理载体超越了头颅或皮肤的疆界, 情绪感受都是个体性质的。就像奥拓的记忆虽然超越了奥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笔记本, 但是奥拓的记忆仍然属于个体心理范畴。情绪的环境延展同样如此, 并没有跳出个体的圈子, 仍然从属于个体心理。但实际情况是, 在许多条件下, 情绪不是个体的, 而是通过多人实现的。在这类事例中, 情绪不是个体性质的。相反, 同一情绪为二人或更多个体同时拥有。这就是情绪的社会延展假设(the hypothesis of socially extended emotions)。
情绪的社会延展所表达的是, 某些情绪的实现不是单一个体所能完成的。相反, “两个或更多的个体是同一情绪的承载者……这种情绪是随着时间涌现出来的, 具有群体水平的特性。它超越了组成这一群体的所有个体, 不能被归结为任一个体水平, 因此是一种集体成就” (Krueger, 2014, p.536)。
情绪社会延展的典型表现是两个个体面对面的情绪互动。在母婴的事例中, “由于婴儿识别、理解和矫正自己情感状态的能力是不成熟的, 正处于发展之中, 因此, 她们的情感调节基本上是由她们所面对的那个人所控制的” (Taipale, 2016)。由于缺乏注意控制、知觉辨别或情绪调节的内在机制, 婴儿认知和情绪功能的实现几乎完全依赖母亲或其他照看者。在互动的过程中, 母亲通过欢快的语调、关注的表情和轻柔的身体接触让婴儿进入喜悦状态。婴儿的喜悦状态强化了母亲的行为, 母亲也同样体验到喜悦情感。母亲的喜悦情感又通过身体接触让婴儿产生进一步的喜悦体验。在这一过程中, 婴儿的情绪延展到母亲, 母亲的情绪延展到婴儿, 喜悦的情感体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她们分享着同一种情感体验(Samdan et al., 2020)。在这里, 喜悦不是个体内在的, 而是人际的或社会的, 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单独任何一方都无法产生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 喜悦情感超越了个体, 延展到人际, 成为群体互动的产物。
情绪的人际延展并不限于母婴互动。成人之间也经常体验到这种情绪和情感的分享与相互调节, 如交际舞中的舞伴、浪漫的情侣和聚会中的朋友经常体验到这种情绪的相互延展。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利用人际交往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感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我们总是寻求一些时间与伴侣、朋友和家庭在一起, 因为这会给我们带来轻松和喜悦的感受, 而离群独处是没有这种体验的。在这样一些情境之中, 情绪不是属于个人的, 而是群体水平上的。处于互动中的个体与他人组成了一个“情感环” (affective loops)。你的情绪不再是你个人的, 而是受到他人情感的调节。同时, 他人的情感也受到你的情感的调节。此时的情感体验不再是“我的”, 而是“我们的”。通常, 彼此之间的这种情感互动和耦合会导致一种全新的情绪感受, 如兴奋和狂喜等等。单独的个体则不可能产生这种情感体验(Gallagher, 2017; Raymond Harris, 2020)。
情感体验能不能超越个体, 延展到他人, 成为一种共享的体验?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着一些争论。反对观点认为情绪是第一人称的现象学体验, 是个人的一种内在感受, 无法超越个体延展到他人。支持的观点以集体情绪为例, 认为情绪的分享是存在的(Goldenberg et al., 2020)。在上述人际延展的事例中, 情感体验的产生并不依赖于个体的内在机制, 处于情感体验中的个体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调节。没有来自于他人的刺激, 情绪感受就不可能形成, 如政治集会上的群情激昂, 音乐晚会上的集体兴奋等等。在这些条件下, 情绪体验都不是个体的。没有他人的存在, 就不会产生如此的体验。从属于群体的情绪状态深刻改变了个体的情绪感受, 个体情绪的改变又深刻影响了群体的情绪体验, 在这种条件下, 情感体验不是私有的, 而是共享的。它超越了个体的疆界, 延展到人际、环境和文化, 成为一种“社会的”情绪感受。
4 意识可以延展吗?
延展认知到延展情绪的事实说明, 记忆、思维、情绪和情感等心智过程并非局限于有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脑也并非心智的唯一器官。相反, 在心智活动中, 有机体非神经部分的身体、身体之外的环境和世界在心智的实现中, 都扮演着“构成性” (constitutive)角色。这是一种积极外在主义观点。心智并非像传统认知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 仅仅表现为发生在头脑中复制世界的表征和表征的信息加工过程, 还包括有机体日常的所作所为。“因此, 延展心智主题背后的关键观念是, 某些认知过程可以而且的确延展到头颅之外。根据这一主题, 认知并非仅仅发生在个体的生物疆界以内, 相反, 认知产生于神经结构、身体和世界的动力互动之中” (Farina & Levin, 2021, p.131)。有机体通过身体活动作用于世界, 世界反作用于有机体。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中, 有机体的记忆、思维和情感超越了生物疆界, 延展到支持心智活动的外部资源(Risko & Gilbert, 2016)。所以, 心智与脑, 脑与身体, 身体与环境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对于心智来说, 外部资源不仅是因果性的, 而且是构成性的。“构成”意味着非神经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和世界中的某些部分, 如工具和人工制品等, 是完整心理过程的必要成分。缺少了这些成分, 心理过程就无法正常进行。基于这种思路, 我们说, 认知和情感等心智活动超越了有机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环境和世界之中(Hirst et al., 2018)。
从认知延展到情感延展所带来的最大启示是, 人的整个心智, 包括人的意识体验都可以超越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延展到环境中可利用的外部资源。这被称为“延展意识主题” (extended consciousness thesis) (Kirchhoff & Kiverstein, 2019; Vold, 2020)。
认知可以延展, 情绪和情感也可以延展, 这些延展涉及的都是亚个人水平的活动。换言之, 处于这些延展状态中的个体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体验, 那么在意识体验中呢?意识体验是否可以延展?“延展心智主题的倡导者, 包括Clark和Chalmers (1998)通常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划一条界限, 主张尽管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和过程可以超越生物脑和身体的疆界, 但是意识状态却不能。他们认为延展的意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Vold, 2020, p.244)。因为意识乃是一种神经生物现象, 完全基于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信息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高速传播, 导致意识的涌现。如果意识体验延展到身体和环境, 那么由于身体和环境是“低带宽”的, 即信息流的传播速度比较慢, 脑与身体、脑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传播无法达到脑内神经网络的传播速度, 意识无法从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Chalmers (2008)指出: “也许部分原因是意识的物理基础需要在极高的带宽上直接访问信息。具有高带宽灵敏度的未来扩展系统或许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 我们与环境的低带宽意识连接似乎只能导致错误的形式” (p.xiv−xv)。因此, 意识体验的载体不可能在非神经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中实现, 所以, 延展意识是不可能的。
但是, 从认知延展到情感延展的事实表明, 意识体验同样具有延展属性。情绪感受是一种第一人称的现象体验, 如果情绪感受的载体可以超越有机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环境资源, 那么, 意识体验的载体为什么不能超越有机体的生物疆界, 延展到支撑意识体验的外部资源呢?心理学的实验(Chambers & Reisberg, 1985)表明, 被试在观察和回忆一个两可图形(鸭/兔)后, 如果被试对图形进行了一番想象性回忆, 然后要求被试描述图形中的两可线索, 找出想象图形中相反的细节(如果想象的图形是鸭, 那么就找到兔的细节; 如果是兔, 就找到鸭的细节), 结果发现, 全部被试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被试在想象中已经把两可图形固化为图形的某一方面, 在意识中无法恢复那些相反的细节; 然而, 如果要求被试把想象中的图形画出来, 外化在画板上, 在画板上修改想象中的图形, 则所有被试都轻松完成了任务。被试无法在内部对自己想象的结果进行修改, 但是, 如果意识经验外化出来, 放到画板上, 被试就可以对自己的意识经验进行修正。这说明被试的意识经验已经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在外部画板上得以实现。
另一项研究(van Leeuwen et al., 1999)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该研究发现, 在创作抽象艺术作品时, 内部想象能力使画家可以结合不同成分, 创作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但是, 一旦想象出一个全新的形象, 内部想象能力却不能把这个想象的作品再分解为全新的成分。然而, 如果画家在素描板上画出这个形象, 即把这个形象外化出来, 在试错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意识体验不断修正, 就能创作出一个全新的艺术作品。画家在想象中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必须借助于素描板, 把自己的意识经验不断投射到素描板上, 在外部资源上完成对自己的意识经验的修正。正是通过想象过程与外部资源的互动, 意识经验才能得到修正。在这个意义上, 画家的意识经验超越了画家脑的神经生物过程, 延展到素描板这个外部资源上。素描板成为画家意识经验的载体。
感官替代(sensory substitution)研究也支持了知觉意识经验的产生并不局限于脑内的神经系统。所谓感官替代, 指的是通过技术的方式, 把通常由特定感官支持才能产生的知觉意识经验(如视觉)由另一感官进行替代(如触觉感官或听觉感官)。它可导致同样的视知觉意识经验。这项工作的开创性研究是由Bach-y-Rita (1972; 2002)完成的。Bach-y-Rita以盲人为被试, 研究怎样利用皮肤触觉来替代盲人已失去的视觉。在这项研究中, 实验者在盲人的头部或肩部配备了一个摄像头, 视频的摄像头通过计算机向被试的额头、背部或大腿上传递信息, 引发被试皮肤上的振动, 振动的模式与视频图像一致。经过一段适应性的练习以后, 那些能主动控制摄像机, 或者在运动中接近或远离目标的被试, 能够对三维空间中远端物体的数量、相对大小和位置等做出可靠的判断, 并做出伸手和抓起物体等动作, 似乎产生了目标对象的心理表征, 即产生了视觉意识经验。在另外一项听觉替代视觉的感官替代研究(Auvray et al., 2007)中, 来自摄像机的视频图像被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声音刺激。通过耳机, 被试对这些不同频率的刺激进行接收。同样经过短暂的适应性练习以后, 配备这种装置的被试能够在三维空间中定位和识别远端物体的形状。不同频率的声音刺激似乎让被试有了视觉意识经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远端物体进行识别。
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些以触觉或听觉替代视觉的感官替代研究中, 无论是用触觉替代视觉还是用听觉替代视觉, 都涉及到知觉意识经验的转换, 但是这种转换是在基础神经活动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 脑内的神经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导致转换的不是脑的神经活动, 而是外周感官。这说明意识经验的实现机制并没有局限在中枢神经系统内, 它超越了头颅的界限, 在外周感官中得以实现。正如感觉运动生成论(sensorimotor enactivism)的代表人物Noë (2009)指出的那样: “世界本身可被描述为属于我们自己意识的实现机制” (p. 65)。
这些研究有力证明了中枢神经系统并非知觉意识体验的唯一实现机制。这种外在主义的解释同感觉运动生成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感觉运动生成论主张, 视知觉意识体验并非完全产生于脑(Di Paolo et al., 2017)。实际上, 视知觉意识体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 是在脑、身体和世界的互动中形成的, 部分是由有机体感觉运动技能的运用构成的。换句话说, 知觉意识体验并非完全是由脑的神经环路产生的。至少某些知觉体验, 部分地产生于感觉运动神经和肌肉活动。有机体作用于世界的身体动作和世界对有机体的动作反馈, 都是知觉意识体验的构成成分。感觉运动神经和肌肉活动在某些适当条件下, 构成了实现知觉意识体验的有效成分。感觉运动生成论的代表人物O’Regan和Noë (2001)在《视觉和视觉意识的感觉运动学说》一文中指出: “在我们看来, ‘看’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是一种探索环境的特殊方式。内在表征的活动不会产生‘看见’的体验。外在世界就是它自己的、外部的表征。当有机体掌握了我们所说的感觉运动权变(sensorimotor contingency)的规律时, 就会产生视觉的体验” (p.939)。以先天性白内障患者为例, 经过手术, 患者具备了“看”的能力, 但是却不能形成正确的视觉意识。一位患者在拆开绷带的那一瞬间, 面对外科医生的脸, 他看到的是“一片模糊”, 中间却能“发出声音”, 因为患者不能把以往的感觉运动知识与“发出声音的这片模糊形象”联系起来, 无法形成“脸”的视觉意识体验。这说明, 视觉意识体验与身体的感觉运动技能是联系在一起的。脑的神经环路并非实现视觉意识体验的唯一机制。
如果说知觉意识体验对感觉运动技能的依赖只能说明初级意识体验的形成, 那么, 情绪和情感的延展属性则可以说明情感体验对身体和环境等外部资源的依赖。“我们人类不断地与世界互动, 以影响我们的感受(feeling)方式。我们寻求他人的陪伴来提升我们的精神, 使用高度复杂的流媒体设备来娱乐和愉悦, 不遗余力地创造艺术——只是为了获得纯粹的满足……我们的情感状态经常是由环境因素(如物理物体和其他人)所激活、支持和调节的” (Saarinen, 2020, p.820)。情绪和情感是一种独特意识体验, 人类一直在通过改变环境的身体活动来提升这种体验。然而, 情绪和情感并非完全是一种发生在头脑中的内在反应。现象学早就指出, 意识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即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 意识是某个对象的意识。情绪的意识体验同样如此, 情绪体验总是指向某个客观对象, 为那个对象所引起, 并导致作用于那个对象的行为倾向。单独一个脑并不能产生我们追求的那种体验。这意味着, 情感体验超出了头颅, 发生在脑、身体、环境和文化的更大集合中, 身体、环境、人际关系等外在资源, 在适当条件下, 都可以成为情绪体验的实现机制, 即成为情绪体验的载体。
在情感体验的探讨中, 近年来兴起了“情感龛位” (affective niche)研究热潮(Nagatsu & Salmela, 2022; Saarinen, 2020; 2021)。情感龛位指的是情绪和情感发生在一个物质和文化环境中, 被身体、环境和文化等外部资源所“架构” (scaffolded)和“铸就” (enacted)。情感龛位把人与环境耦合在一起, 使得特定的情感体验得以实现。“许多情绪研究者们建议: 情感作用(affectivity), 包括情绪、心境和动机状态等, 是被物质实体、社会风俗、物理和中介空间等环境资源铸就和支持的。这样一来, 情绪超越了有机体的身体, 在不同程度上为外部环境资源所塑造” (Hven, 2019, p.105)。这说明, 情感体验并非一个产生于内部的事件。情感体验的实现既包括神经激活、腺体分泌等内部过程, 也包括身体动作和环境对象等外部事件, 外部资源在情感体验的实现中扮演着构成性角色。在一个音乐晚会上, 我们不是在真空中欣赏音乐, 而是处在众多的听众中。我们不仅在听音乐, 同时也在听其他人听音乐, 这样一来, 我们的音乐体验就改变了。我们的音乐体验并非仅仅是中枢神经激活的产物, 而是音乐厅氛围的结果。所以我的音乐体验不是在脑中实现的, 而是“情感龛位”造就的。
5 讨论与思考
5.1 笛卡尔鸿沟的超越
从认知的延展, 到情感的延展, 再到意识的延展。依照这样一种分析, 心理生活超越了“笛卡尔鸿沟”, 横跨在大脑、身体和环境之上。自笛卡尔从认识论上确立了心物二元论以来, 思想界一直视心物、心身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同实在。依据笛卡尔的观点, “心”之特点是能思维, 存在于皮肤之内, 但并不占有物理空间, 不具备可延展性; 而包括身体在内的“物”占有空间, 但是不能思维。换言之, “心”只存在于身体之内, 与身体之外的物理空间通过皮肤相互隔绝。后来兴起的颅相学更是把心智定位于脑, 主张“脑是心智的器官”。这种内在主义(internalism)观点深刻影响了心理学, 传统认知心理学秉持的就是一种“认知是发生于脑中的信息加工”的内在主义观点。
内在主义分为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内在主义和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的内在主义。形而上学的内在主义主张某种特定心理能力的实现完全依赖于有机体内部的活动。对于生物个体来说, 产生于脑内的神经激活模式足以解释思维、记忆和情绪等心理现象, 并不需要再劳神关注有机体之外的因素。方法论的内在主义则认为心理生活的分析单位应该是个体的, 其关注的焦点在心理生活背后隐秘的内在机制。方法论的内在主义也被称之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
但是这种观点遭遇了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挑战。外在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 它主张认知、情感和动机等心理状态并非完全由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内的因素所决定, 非神经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对心理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外在主义可划分为“内容” (content)外在主义和“积极” (active)外在主义。内容外在主义主张心理生活的内容或意义构成性地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环境。积极外在主义之所以是“积极的”, 是因为它主张环境的因素在驱动认知和思维等心理过程方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主动的。内部认知与外部世界并非仅仅是因果关联的, 而且是“构成性的”, 即外在环境资源在某些条件下是心智和认知系统的构成成分。Clark和Chalmers在积极外在主义的基础上, 大胆地提出了延展心智的观念: 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在适当条件下就是完整心智不可缺少的部分, 实现心智活动的机制并不完全囿于个体神经生物系统, 在某些条件下, 心智的实现机制超越了个体的生物疆界, 包含了非生物的外在物理资源。
在捍卫积极外在主义观点的过程中, Clark和Chalmers所依据的是对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首先要做的是鉴别哪些外部因素具有认知功能; 其次, 找出与之对等的内部机制; 最后, 如果那个内部机制是认知系统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这些外部因素不能算是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呢?
对等原则依赖的是内部生物因素与外部环境资源之间的功能类似性(Milojevic, 2020)。它关注的是内外因素的功能对等。依照这一原则, 只要内外因素在驱动认知方面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那么外部的非生物资源就可以被视为认知系统的一个部分。Sutton (2010)等延展心智的拥护者一方面支持Clark等人的延展心智观念, 另一方面, 认为外在环境因素在驱动认知方面并非因为功能类似或功能对等, 而是因为功能非类似(dissimilarity)或不对等。恰恰由于这种功能属性上的不对等, 内外因素执行了不同功能, 才使得认知得到扩展和增强。内在的生物状态与外在的环境资源互动、互补, 共同铸就了整体的认知力量。
Sutton (2010)称自己这种对延展认知的互补性解读为延展认知的第二波, 并认为可能还存在延展认知的第三波。事实上, Kirchhoff和Kiverstein (2019), 甚至包括Clark本人(Constant et al., 2022)都卷入到延展认知的第三波浪潮中, 对认知的可延展性进行了重新解读。在第三波的延展认知那里, 内外因素不再具有固定的边界,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属性。相反, 完整的认知系统是个“混血儿”, 既有神经的和生理的成分, 也有身体的、环境的和文化的成分。总之, 它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疆域, 与环境资源整合在一起, 形成了强大的认知力量。
第三波延展认知的另一个特点是, 不仅认知是延展的, 情绪和情感也是延展的, 甚至意识经验也超越了个体的生物疆界, 在非神经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世界中得以实现。“延展意识主题主张, 实现意识经验的生物机制有时包含了神经的、身体的和环境因素的混合物……延展意识的捍卫者询问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皮肤和头颅的疆界在解释意识经验方面具有优先权?为什么只有发生在这一疆界内的过程才能算是意识经验的实现机制?” (Kirchhoff, & Kiverstein, 2019, p.25)。实际上, 意识经验的生物机制是环境中完整的有机体, 而不是单独一个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意识经验的实现需要脑、身体和环境的联合行动。
“延展心智”的观念一经提出, 一方面倍受推崇; 另一方面, 也颇受争议。就赞成的一方来说, 延展心智所表述的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 人类的心理生活本来就没有封闭于头颅甚至皮肤之内, 人类一直在利用语言、文字、行为动作、计算器等手段扩展认知的范围, 卸载记忆于环境, 减轻认知负担; 当今新兴的信息技术更是通过搜索引擎、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模拟、强化和扩展人类心智活动的范围, 增强和扩大人类的认知能力。但是, 批评的一方则认为, 认知主体利用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资源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时, 认知主体与外在资源是耦合(coupling)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耦合的双方是独立的, 一方并不能成为另一方的构成成分。但是, 延展心智主题却错误地把“耦合”视为“构成” (constitution), 以为耦合的一方成为了另一方的有效构成成分。通过这种方式, 认知能延展到外物。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耦合一构成谬误” (Kaplan, 2012)。有批评者指出, 如果外部资源因为参与认知活动而被视为认知过程的适当成分, 那么认知的边界就无法确定, “认知膨胀” (cognitive bloat)就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Allen-Hermanson, 2013)。
但是, 我们不是“缸中之脑” (Brain-in-a-vat), 而是有血有肉的有机体, 这个机体又处于一定的物理和文化环境中。海德格尔的“Being-in-the-world”概念是对人的生存状况最恰当的表述。按照二元论的观点, 存在着一个“主体”和与之相对的“客体”。如果接受这种主客二元认识论, 则主体与客体就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 就有一个“内部”和“外部”分界。但是, 如果我们接受人的存在是海德格尔的“Being-in-the-world”, 人与客观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整体, 则人与世界就是一个“应对” (cope with)关系, 周遭世界的一切都是“用具” (equipment), 是为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所使用的“工具” (instruments)。心理生活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 不是一个生物脑所能够完成的。正是通过有目的的身体和工具的使用, 通过身体作用于世界的活动和世界的反馈, 心理生活不再限制在中枢神经系统内部, 而是延展到环境和世界, 与身体动作和文化实践耦合为超越物质和精神鸿沟的、水乳交融的整体(Ongaro et al., 2022)。
5.2 认知、情感和意识还有没有边界?它们可以无限延展吗?
心理生活的这种“混血儿”性质引申出一个“边界”问题。依照主客二元论观点, 存在着心物、心身、主客和内外的划分, 在心理与物理、认知与身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个边界让系统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泾渭分明。边界以内是心理的、认知的、现象的, 而边界以外则是物理的、身体的或环境的。然而, 如果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海德格尔的“Being-in-the-world”, 那么, 心理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再者, 如果我们说心理生活超越了头颅和皮肤, 延展到环境和世界, 那么认知、情感和意识还有没有边界?它们可以无限延展吗?
在《具身心智: 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一书中, 瓦雷拉等(2010)强调指出: “认知不是一个既定心智对既定世界的表征, 它毋宁是在‘在世存在’所施行的多样性动作之历史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 (p.8)。这就是说, 认知并非一种对世界的静态表征。相反, 认知是一种具身的行动(embodied action)。有机体以身体的方式作用于世界, 世界以反馈的方式反作用于有机体, 心智和认知就产生于这种互动中。这意味着, 记忆、思维、情感和动机等心智能力部分地是由我们根植的环境实现的。心智并没有限制于中枢神经系统。换句话说, 人们的心理生活并不以头颅或皮肤作为边界, 而是通过身体行动延伸到环境, 与外在环境构成统一的整体。
梅洛·庞蒂早就指出: “世界与主体是不可分离的, 与之分离的, 只不过是一个作为投射世界的主体; 主体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与之分离的, 只不过是一个作为主体自身投射的世界” (Merleau- Ponty, 1962, p.430)。这就是说, 主体和世界本来就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系统。主体是在这个世界中来认识这个世界, 而不是以主客二元的方式, 凭借“客观之眼”观察和表征这个世界。当主体反思时, 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反思之前就存在于此的世界中, 与那个世界并没有分离。与之分离的, 不过是在反思过程中投射出的一个世界。人不是一个幽灵般的心智, 盘旋在客观世界之外, 观察和表征世界。人始终存在于世界之中, 是一个“在世存在”, 与世界构成统一的整体。
那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 心理生活与客观世界没有边界?心理生活可以无限蔓延, 遍布宇宙万物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说, 主体与世界是一个整体, 须臾不可分离时, 并不意味着主体与世界没有差异, 也不意味着心理生活与客观世界没有内外之别, 更不意味着心理生活没有边界。但是, 心理生活的边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这种边界类似于认知科学理论前沿“预测认知模型” (叶浩生, 苏佳佳, 2022)在“认知就是推理”意义上所使用的“马尔科夫毯”概念(Bruineberg et al, 2022)。
“马尔科夫毯是一组状态, 通过这组状态, 把内在状态与外在状态或隐蔽状态从统计上掩蔽或隔离开来……用图论的说法, 马尔科夫毯是一组节点, 它保护内在状态(或节点)不受外在状态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 内在状态只能通过毯的状态而被外在状态间接影响。因此, 在统计意义上, 内在和外在状态被马尔科夫毯区别开来” (Ramstead et al., 2021, p.45)。
van Es (2020)也认为: “马尔科夫毯是一种统计形式, 人们可以用它来标记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分离。在这个统计形式中, 我们将状态分为内部状态和外部状态, 内部状态占有马尔科夫毯内的所有状态, 外部状态占有马尔科夫毯外的所有状态。毯子本身的状态标志着双方之间唯一的接触点, 包括受内部状态影响并影响外部状态的主动状态和受外部状态影响并影响内部状态的感觉状态。重要的是, 这意味着内部状态和外部状态在统计上是条件独立的” (p.1003), 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 预测加工模型以自由能原理的“主动推理”为其理论基础, 并以“马尔科夫毯”作为其形式系统, 并不能成功为心智划界, 实际上, “‘主动推理’ (active inference)根本不是‘推理’, 而是一种行动(doing), 一种生成式的调整, 一种世界性的参与” (p.1015)。
这就是说, 作为一个整体, 系统之内的因素与系统之外的因素仍然内外有别。系统有自己的特点和属性。这些特点和属性使它区别于其他系统。但是, 这些特点和属性不是固定不变的,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边界也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而是认识的角度、统计上的推理。
系统的特点和属性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没有永恒不变的特性和特征。系统内外因素的边界是多重的、嵌套的。随中间状态的变化, 边界也发生着改变。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心理生活的边界, 则这个边界不是一种实体状态的边界。没有一个实体边界把心理生活与客观世界区别开来。我们有的是一个“马尔科夫毯”, 即某种中间状态。通过这个中间状态, 心理生活的内在因素主动地影响着客观世界的外在因素; 同时, 客观世界的外在因素也通过有机体的感觉状态而影响着心理生活的内在因素。在某种合适的条件下, 也正是通过这个中间状态, 心理生活在客观世界的外在资源中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 心理生活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生物边界, 延展到环境资源上, 放大了我们的认知和情感能力, 使得心理生活与我们生存的世界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体。
心智和认知超越了头颅和皮肤的疆界, 也就是说, 心智和认知的位置并非完全限制在头脑中, 脑并非心理生活的唯一实现机制。当然, 这并不是说, 脑不重要。而是说, 在人们的心理生活中, 身体、环境和文化等脑外因素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没有这些外部资源, 心理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可能在一些条件下, 某些心理状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依赖更大, 如选择性注意等; 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 对身体或环境等外在因素的依赖可能超过了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需求, 如动机和情感体验等等, 所以无法用均等的原则作统一的说明。心理生活不是一个纯粹的内部“精神事件”, 心理过程发生于脑、身体和环境耦合互动的关系之中。它是一个关系性存在。单单一个脑并不能产生心理生活的“鲜活体验” (lived experience)。
5.3 延展心智实际上是具身认知的延展
归根结底, 延展心智启示我们:认知、情感甚至意识可以突破大脑, 延展到身体和环境中, 并且, 心理生活的边界就像“马尔科夫毯”一样, 认识论上, 是可塑的, 完全取决于有机体如何通过“身体”来选择有意义的外部资源而与之建立耦合的认知系统。在这个意义上, 延展心智势必要建立在“具身认知”的理论之上, 即认知是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的三位一体的动态系统, 而“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了“主动”进行意义建构的角色, 基于此, 身体的边界才是活的, 心智的边界才是活的。因此, 延展心智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身体”!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曾经区分了“躯体” (Körper)和“活的身体” (leib)。“Körper”是“客观的身体”或“作为客体的身体” (body-as-object), 这是生理学和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与之相对, “Leib”是“主观的身体”或“现象的身体”, 是“作为主体的身体” (body-as-subject), 这个身体才是认识的主体。这也恰恰是具“身”认知所强调的“身体”的真义。
未来的轴心时代, “谁掌握了人类‘身体’的奥秘, 谁就拥有了打开未来元宇宙新文明大门的钥匙, 当然, 也许同时也掌握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苏佳佳, 叶浩生, 2023)。
Adams, F. (2019). The elusive extended mindIn M. Colombo, E. Irvine, & M. Stapleton (Eds.),(pp.21−31). Books.google.com
Allen-Hermanson, S. (2013). Superdupersizing the mind: Extended cogn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ognitive bloat.,(3), 791−806
Anderson, M. (2015). The extended mind. In M. Anderson (Ed.),(pp.1−40). Springer.
Armitage, K. L., & Redshaw, J. (2022). Children boost their cognitive performance with a novel offloading technique.(1), 25−38.
Armitage, K. L., Taylor, A. H., Suddendorf, T., & Redshaw, J. (2022). Young children spontaneously devise an optimal external solution to a cognitive problem.(3), e13204.
Auvray, M., Hanneton, S., & O’Regan, J. K. (2007). Learning to perceive with a visuo-auditory substitution system: Localisation and object recognition with ‘The vOICe’.(3)416−430.
Bach-y-Rita, P. (1972).. Academic Press.
Bach-y-Rita, P. (2002). Sensory substitution and qualia. In A. Noë & E. Thompson (Eds.),(pp. 497−514). The MIT Press.
Boem, F., Ferretti, G., & Zipoli Caiani, S. (2021). Out of our skull, in our skin: The microbiota-gut-brain axis and the extended cognition thesis.,(2), 1−32.
Brinkmann, S. (2020). Learning to grieve: A preliminary analysis.,(3), 469−483.
Brinkmann, S., & Kofod, E. H. (2018). Grief as an extended emotion.(2), 160−173.
Bruineberg, J., Dołęga, K., Dewhurst, J., & Baltieri, M. (2022). The emperor's new Markov blankets.,, e183.
Bulley, A., McCarthy, T., Gilbert, S. J., Suddendorf, T., & Redshaw, J. (2020). Children devise and selectively use tools to offload cognition.(17), 3457− 3464.
Carr, E. W., Kever, A., & Winkielman, P. (2018). Embodiment of emotion and its situated nature. In A. Newen, L. De Bruin, & S, Gallagher (Eds.),(pp. 529–55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ter, J. A., Gordon, E. C., & Palermos, S. O. (2016). Extended emotion.,(2), 198− 217.
Chalmers, D. (2008). Foreword. In A. Clark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D., & Reisberg, D. (1985). Can mental images be ambiguous?,(3), 317−328.
Clark, A., & Chalmers, D. (1998). The extended mind.(1), 7−19.
Constant, A., Clark, A., Kirchhoff, M., & Friston, K. J. (2022). Extended active inference: Constructing predictive cognition beyond skulls.,(3), 373− 394.
Damasio, A. (1999).London, UK: Vintage.
Di Paolo, E., Buhrmann, T., & Barandiaran, X. (20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rina, M., & Levin, S. (2021).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 Domains and application. In R. Michael & L. Thomas (Eds.),. Springer.
Fivush, R.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559−582.
Froese, T. (2015). Enactive neuroscience, the direct perception hypothesis, and the socially extended mind. B, 22−24.
Gallagher, S. (20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llagher, S. (2018). The extended mind: State of the question.,(4), 421−447.
Goldenberg, A., Garcia, D., Halperin, E., & Gross, J. J. (2020). Collective emotions.,(2), 154−160.
Gross, J. J. (2015). The extended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Elaborations,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1), 130−137.
Havas, D. A., Glenberg, A. M., Gutowski, K. A., Lucarelli, M. J., & Davidson, R. J. (2010). Cosmetic use of botulinum toxin−A affect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language.(7), 895−900.
Heersmink, R. (2022). Extended mind and artifactu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y.,(4), 659− 673.
Hirst, W., Yamashiro, J. K., & Coman, A. (2018). Collective memory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5), 438−451.
Hven, S. (2019). The affective niches of media.,(1), 105−123.
Jain, D. K., Shamsolmoali, P., & Sehdev, P. (2019). Extended deep neural network for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69−74.
James, W. (18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plan, D. M. (2012). How to demarcate the boundaries of cognition.(4), 545−570.
Kirchhoff, M. (2012). Extended cognition and fixed properties: Steps to a third-wave version of extended cognition., 287−308.
Kirchhoff, M. D., & Kiverstein, J. (2019).. Routledge.
Kirchhoff, M. D., & Kiverstein, J. (2020). Attuning to the world: The diachronic constitution of the extended conscious mind.,, 1966.
Kiverstein, J. (2018). Extended cognition. In A. Newen, L. De Bruin, & S, Gallagher (Eds.),(pp.1, 3−1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ueger, J. (2014). Varieties of extended emotions.(4), 533− 555.
Krueger, J., & Szanto, T. (2016). Extended emotions.,(12), 863−878.
León, F., Szanto, T., & Zahavi, D. (2019). Emotional sharing and the extended mind.196(12), 4847−4867.
Liu, Z. B., & Gao, S. C. (2016). Extended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ment.,(3), 218−221.
[刘志斌, 高申春. (2016). 具身视域下的延展认知及其反思.,(3), 218−221.]
Loughlin, V. (2020). Extended mind. In V. P. Glaveanu (Ed.).(pp. 1–9)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Merleau-Ponty, M. (1962).(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Milojevic, M. (2020). Extended mind, functional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5), 2143−2170.
Nagatsu, M., & Salmela, M. (2022). Interpersonal and collective affective niche construction: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edia..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07/s13164-022-00625-1
Noë, A. (2009).. Macmillan.
Ongaro, G., Hardman, D., & Deschenaux, I. (2022). Why the extended mind is nothing special but is central..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22-09827-5
O'regan, J. K., & Noë, A. (2001). A sensorimotor account of vision and visual consciousness.,(5), 939−973.
Overstreet, M. (2022). Writing as extended mind: Recentering cognition, rethinking tool use.,, 102700.
Parise, A. G., Gagliano, M., & Souza, G. M. (2020). Extended cognition in plants: Is it possible?,(2), 1710661.
Ramstead, M. J., Kirchhoff, M. D., Constant, A., & Friston, K. J. (2021). Multiscale integration: Beyond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1), 41−70.
Raymond Harris, K. (2020). Group minds as extended minds.,(3), 234−250.
Redshaw, J., Vandersee, J., Bulley, A., & Gilbert, S. J. (2018).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use of external reminders for hard-to-remember intentions.(6), 2099−2108. https://doi.org/10.1111/cdev.13040
Risko, E. F., & Gilbert, S. J. (2016). Cognitive offloading.,(9), 676−688.
Rupert, R. D. (2004). Challenges to the hypothesis of extended cognition.(8), 389−428.
Saarinen, J. A. (2020). What can the concept of affective scaffolding do for us?,(6), 820−839.
Saarinen, J. A. (2021). How museums make us feel: Affective niche construction and the museum of non-objective painting.,(4), 543−558.
Samdan, G., Kiel, N., Petermann, F., Rothenfußer, S., Zierul, C., & Reinelt, T.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behavior and infant regu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100923.
Sims, M., & Kiverstein, J. (2022). Externalized memory in slime mould and the extended (non-neuronal) mind.,, 26−35.
Smart, P. R. (2022). Toward a mechanistic account of extended cognition.,(8), 1107−1135.
Su, J. J., & Ye, H. S. (2023). Metaverse and “embodied” cognition.(1), 3−11.
[苏佳佳, 叶浩生. (2023). 元宇宙与具“身”认知.(1), 3−11.]
Sutton, J. (2010). Exograms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 extended mind,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R. Menary (Ed.),(pp. 189−22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aipale, J. (2016). Self-regulation and beyond: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infant-caregiver dyad.,, 889.
van Es, T. (2020). Minimizing prediction errors in predictive processing: From inconsistency to non-representationalism.(5), 997−1017.
van Leeuwen, C., Verstijnen, I., & Hekkert, P. (1999). Common unconscious dynamics underlie uncommon conscious effects: A case study in the iterative nature of perception and creation. In J. S. Jordan (Ed.),(pp. 179−218).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2010).(H. W. Li, Trans.).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瓦雷拉, F.-J, 汤普森, E, 罗施, E. (2010).(李恒威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Viola, M. (2021). Three varieties of affective artifacts: Feeling, evaluative and motivational artifacts., (20), 228−242.
Vold, K. (2020). Can consciousness extend?,(1), 243−264.
Ye, H. S., Su, J. J., & Su, D. Q. (2021).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Enactive approach to emotion.(12), 1393−1404.
[叶浩生, 苏佳佳, 苏得权. (2021). 身体的意义: 生成论视域下的情绪理论.(12), 1393−1404.]
Ye, H. S. & Su, J. J. (2022). The Predictive Cognitive Models: A New Unified Paradigm for Cognitive Science?., 65-78.
[叶浩生, 苏佳佳. (2022). 预测认知模型: 认知科学的新统一范式?., 65−78.]
Zaslawski, N., & Mathieu A. (2017). “Shaun Gallagher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mind: Recontextualizing ‘decentered’ cognition”.(1), 1−7.
Zhu, L. F., & Zhao, M. (2019).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extended mind.(6), 1−8.
[朱林蕃, 赵猛. (2019). 重新审视“延展心灵”概念., (6), 1−8.]
Zlotnik, G., & Vansintjan, A. (2019). Memory: An extended definition., 2523.
Extended mind: Is the brain the only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mind?
SU Jiajia1, YE Haosheng1,2
(1School of Psycholog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2Center for Embodied Cogni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Today,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a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computers, and smart phones 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changed human emotional experiences, making people gradually accept the belief that memory and thinking are not limited to the brain.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roblem of the so-called ‘extended mind’. The extended mind thesis maintains that mental processes such as memory, thinking, emotions, and affection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brain 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f an organism, nor is the brain the only organ of the mind. On the contrary, under proper conditions, the organism’s non-neural body, the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body, and objects in the environment all play a constitutive role in mental activities. The early extended mind research focused on cognitive process, and has undergone three waves of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has begun to focus on extended emotions. The most basic manifestation of extended emotion is the dependenc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on the body. It is argued that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head and extends to the non-nervous body, known as the hypothesis of bodily extended emotions. In addition, extended emotion holds that the carrier of emotion not only exists in the organism, but also transcends the boundary of skin and contains external resources carrying emotions; this is known as the hypothesis of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emotions. Emotions are individual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physically or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However, in many conditions, emotions are not individual, but achieved through multiple people. In such cases, the emotion is shared by two or more individ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alled hypothesis of socially extended emotions.
The significance from cognitive to emotional extension is that the entire mental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including human conscious experience, can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ead and skin and extend to the external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known as the extended consciousness thesis.
From cognitive, to emotional, and to consciousness extension, mental life transcends the Cartesian gap and straddles the mind, the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mind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skull and skin, that is, the place of the mind is not entirely confined to the brain, and the latter is not the only basis of the former.
Does mental life have no boundary with the objective world? Can mental life spread infinitely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universe? When we say that the subject and the world are a whole and inseparable,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r does it mean that there is no boundary in the mental life. However, the boundary of mental life is not ontological, but epistemological, similar to the Markov blanket concept that exists only statistically.
Extended mind thesis shows that cognition, emotion and even consciousness can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the brain and extend into the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ognitive boundaries, like a “Markov blanket”, are epistemologically malleable, depending entirely on how the organism chooses meaningful external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coupled cognitive system with. In this sense, the extended mind is bound to be built on the theory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at is, cognition is a trinity dynamic system in which the brain is embedded in the body and the body is embedded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body” plays an active role.
mental life, extended mind, extended cognition, extended emotion, extended consciousness
2023-02-06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身体运动与心理发展研究” (20FTYA002)。
叶浩生, E-mail: yehaosheng@gzhu.edu.cn
B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