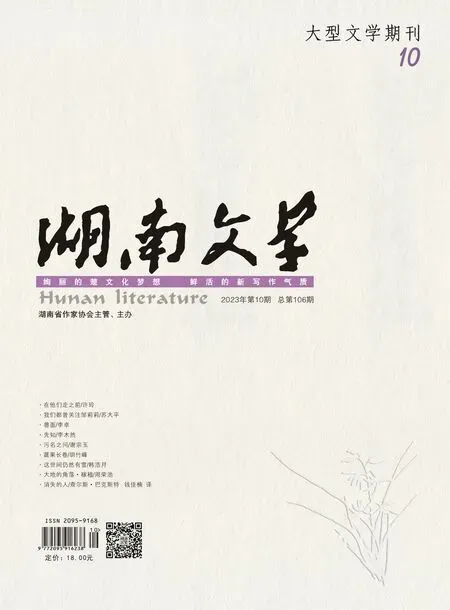新的历史书写刻度
——王跃文《家山》读记
刘启民
一直以来,乡土题材都是作家王跃文创作的重镇,小说家王跃文最近重磅推出了他的新作《家山》,以煌煌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湖南大湘西沙湾村的现代变迁历程。显然,这部厚重的大作凝聚了作家最多的心血与情感,用王跃文自己的话,说是叫“十年打磨,日日掩泣”。《家山》虽是一部虚构作品,但作家是以自己家族的命运故事为蓝本,有诸多可以查考的人物原型和历史事情,因而显得尤为动人,因而赋予了这部作品真实的力量,就像司达汤的《红与黑》、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许多划时代的杰作一样。而当王跃文用精妙的语言雕刻那些已经离去的家族叔伯们的命运时,事实上就像是在文字的世界中为先辈们立下碑冢。通过文字的运作,作者最终完成了文化和精神上的继承与皈依。尽管先辈们已经离去,尽管我们已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我们精神血脉与共。换言之,王跃文在通过写作——或者说通过回溯、追慕与构想家族先辈的历史,完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认同。
追寻民族的文化归属和认同的目的,让《家山》与过去的乡土题材书写区别开来。一百年前,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这些作家们面对现代社会时的惊惧与忧虑,由此带来的对乡土社会的回望,与王跃文创作《家山》时的心境已完全不同了。如果说鲁迅对乡土所做的是奔赴现代世界时的“回望”,那么王跃文所做的,便是在中国已经领略现代世界之后,重又对于民族先辈的“皈依”。从忧惧的“回望”,到虔诚的“皈依”,历史已经走了一百年。“皈依”式的乡土写作,亟待着同代的批评家赋予新的命名。
“文明”,或许是《家山》式乡土书写最为贴切的概念,更能承载作者写作的情境、姿态与心念。而王跃文正是以乡土题材为出发点,写就了一部阔大的民族文明史。面对中国日益的崛起,许多的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就已经开始提“文化”“文明”这样的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情,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当王跃文以一种近乎苛刻的方式,试图去还原先辈走向现代的命运、呈现他们生活的起居用度与语言遗存,当作者不断在不同场合强调“乡土里有最完整的中国”,来彰明在城市化社会中书写乡土的意义,他难道不是在呼应着费老关于“文化自觉”的倡导吗?我相信,作者正是在以一种书写文明史,思考我们从何处来的心态在写作。
一部乡土世界的百科全书
所谓“文明史”,首先意味着对于所展现的社会形态作出全面而细致的复刻式深描,意味着在描绘世界的深度与精度上着力。在人类的文学史上,能够称得上文明史的作品并不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对各自所展现社会的人情风俗、社会变迁的深描上,呈现出极深的造诣。同样,用文学描摹再造乡土生活世界上面,《家山》有着它的野心,可以说,《家山》就是一部乡土世界的百科全书。《家山》聚焦于大湘西地区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落沙湾村,呈现出其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几代人的生活变迁。作者以一种人类学家的勤恳与细腻,还原了生活于此的人们原生态的日常,展现了人们的劳作生息、风俗节庆、政教秩序,呈现出农耕文明里的自然节气、地理风物,和人们的伦理信仰、民风人情。作者几乎是在以匠人的姿态,将山地乡土文明世界一点一滴地重新雕刻在书里,稠密的乡土气息透过文字,几乎扑面而来,使得小说带有一种博物志的色彩。
对于乡土世界的丰满、精细呈现,还体现在《家山》对沙湾村不同农户鲜明的、差异性的刻画上。这个有着两姓始祖的村落,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发育衍化出不同的农民家户来。雇人种田的田家——在过往历史里被称为“地主”的佑德公、远逸公,以钱财和心力维系着沙湾的安宁与礼教秩序,而他们的下一代陈劭夫、陈扬卿,或是投身戎马远赴战场,或是扎根村中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依然成为承托乡村政教秩序的中坚力量;达公与扬高一家人丁兴盛,既有自家田地又趁着人多租种他人田地,在农会这样的新新机构中好勇逞强,试图立住脚跟;修根这样带有自耕农色彩的农户,守着自家的土地勤勉耕耘,怀着扩大土地的美梦、绝少参与政事;真正的山上人,齐天界打虎匠的女儿桃香一家,则带着更多蛮性气质,田土很少,时常要出远门找田亩耕种,对于人间的伦常、秩序,往往愚钝,在争勇武斗中也常常失却分寸。一个自然村落里不同家户的祖上根脉、农业经营、日常起居、家养礼教、禀赋德性乃至命运前途都是极为不同的,这些都在作家笔下得到精细妥帖的展现。
而事实上,不同家户之间尽管多有不同,时有冲突、磕绊,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相互支撑、合作,人们在经济生活、社会角色上有着井然有序的分工,连同着已经被沙湾村村民们讲述为神话的先祖创业史,让读者意识到,沙湾村俨然就是一个依托于血缘与地缘,浸润于乡土性义理文化,在经济、风俗、政教、信仰多个层面自养自足的小共同体。小说以一桩械斗事件的发生与解决来开篇是特别有意味的,沙湾最能打架斗狠的四跛子在械斗中砍杀了邻村的亲外甥,积累了几百年的两村矛盾即将爆发的时候,佑德公依靠两村之间的亲缘关系将之巧妙化解,它暗示着,一个在传统农耕文明上生长起来的自然村落,几百年间的生息、安定,其内在始终依托着血缘纽带和附着其上的伦理来稳固秩序,而如佑德公这样的士人正占据着伦理道德秩序的轴心。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沙湾村不同的农民在生活、教化、命运方面参差差异很大,但他们之间是瓜瓞绵延的结果因而联接甚深,并且始终有一个轴心式的士人,在承托着、稳固着共同体的生活秩序。
正是这种数百年不变的血缘繁衍和附着其上的乡土生活秩序,将《家山》与过去的乡土写作区分开来,血亲乡土超越了一切时间带来的变动性要素,成为一种托底性的、永恒的文化存在。《家山》里,我们看到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农民的政治倾向多有差异,接受现代思想观念亦程度参差,但这些见解、观念乃至实在的经验经历的不同,最终都消解于亲缘的脉脉温存之中,收束于吾土吾民的归属与认同里。一次春节,远逸公家的几个孩子——一直在上海作医生的大儿子陈扬甫,在南京从政的陈扬屹,时隔多年回到家乡。作者对于第三代——分别成长于南京、上海和沙湾的孩子们的描写显得意味深长,几乎未见过的堂兄弟妹们尽管穿着不同、经历不同,相互之间却透着温煦、和谐。从小在乡下成长的修岳领着堂弟妹们玩耍之后,得到远逸公的赞语,“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离散的现代人、现代经验,像茎叶一样自然收束于亲族血缘的根脉,而远逸公用《论语》的话来表扬修岳的大方得体也很有意味,它意味着一种深厚的儒家教养的蕴藉。这样的例子,在小说里几乎俯拾即是。
费孝通曾经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依托于亲缘关系的社会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把中国的乡土社会比喻成石头落水,费孝通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无论波纹的近与远,社会中始终有投入石中的中心;另一方面,波纹能够推出去多远,地缘亲缘、伦理秩序、人间情义能够走到哪个位置,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伸缩自由。
作为一部乡土社会的百科全书,《家山》把依托血亲缘的差序格局写到了骨子里,它是整个沙湾村得以运转的根本法和本底性的逻辑。那颗投入水中的石头——伦理教养的中心,在《家山》的文本里,便是佑德公、陈扬卿这样的村庄士绅,在沙湾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是家族绵延的过程里,他们始终是关键性的轴心。而这些士绅在变动性的人-家-族-国的网络中,也得以不断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解决沙湾村中复杂的矛盾问题。因而尽管沙湾村在不断走入现代,青年人们不断接受着现代世界的召唤,并把新新的观念、事物引进到沙湾,但正是乡土社会中富于伸缩性的道义脉络,成为托底性的秩序和文化存在,让沙湾村得以顺畅地、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小说的最开端,当两个村子即将发生械斗时,佑德公利用与舒家坪的远方血缘关系,巧妙地化解了两村之间的矛盾,这是“以私化公”;扬卿留学归来,从闭关读书到逐渐走出书斋兴办实业,信仰的是“只做自己能做之事”,这是“由己及群”;沙湾的乡贤们在村中兴办学堂、救助红属、兴修水库,亦始终要在公私之间的关系上来运作;而村中新一代的年轻人走出沙湾,参加现代政党和战争,则依托的是“由家而国”的逻辑。
因而,《家山》不仅因为它展现了乡土社会广袤的风物景致、婚丧节庆、经济活动、人物谱系等等,成为一部博物学意义上的乡土百科,更因为它在文化质地上皈依于乡土、呈现出乡土社会几百年不变的内在运转的“差序格局”式的秩序,辅之以文字风格上的纡徐、深沉从而得以对乡土做出文化史意义上的深描。
由“山”出发的变迁史
“文明史”不仅仅是静态的百科全书,它的第二层意涵,还在于蓄积巨大的叙述能量、气度,能对于所展现的社会大变动做出深刻、贴蕴的透视以呈现这一变动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驳杂的关系变动,展现出历史变迁熵增过程的复杂性。《家山》里的乡土毕竟不是静止的存在,小说所展现的时间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正是现代中国发生最为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处于大湘西地区的沙湾村,自然也被卷入到其中,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了几百年的乡土秩序,亦会发生变化。《家山》与过去的历史叙述不同的是,它选择站在沙湾村人的视角,从乡土秩序的内部和留驻在这里的人的视野,来描绘乡土进入现代的变化情境。对于放公老来说,重要的是武状元考不成了,祖宗传下来的刀枪打功将没有用武之地了;对于佑德公,现代则意味着世道的变乱,儿子劭夫不再读书反而去外面做了军人;而对于桃香来说,现代意味着不再裹小脚。原有的乡土秩序、人伦道德、生存观念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更变,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劭夫、贞一、齐峰,则从沙湾走出,走向更大的天地,并用更现代的观念改变着沙湾。也就是说《家山》所写的乡土,始终由“山”出发,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观视视野。
其实,作者观照乡土的姿态和视野,往往会从小说的景致描写中直接鲜明地反映出来。或许可以对比一下《家山》与周立波《山乡巨变》两部小说的开头。《家山》是以村民桃香的视线来开篇的:
正月初六,天上好大的日头。桃香把糍粑皮、炒米放在几个大簸箕里晒,人坐在地场坪晒着日头纳鞋底,手边放着响竹竿赶麻雀。西边屋角下,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登在柚子树上,隔会儿就飞到簸箕边跳来跳去……
从柚子树下望过去,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田里长着麦子和油菜。山上有很多野物,有狼、熊、豺狗……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隔着万溪江,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南边的山越远越高,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
《家山》的开头,村民桃香深坠在山里的日常之中,沿着本地人桃香的视线,叙述者从山中居所往不同方位眺望,满眼的山间风物、水土。而具有象征意味的“北边的山”,则在更遥远的、沙湾村人看不见的地方。相比《家山》开头的“由内而外”,《山乡巨变》的视线则明显是“由外而内”。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涌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同样展现的是湖南一个山乡,《山乡巨变》开头的叙述者带有一种“上帝”的俯瞰视野,清溪乡作为资江水南面的一个乡,是由现代国家的机制“县委会”而引入的。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建制,进而沿着建制里的人——深入小说内部之后即是下乡干部邓秀梅,看见了清溪乡的风物山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家周立波一定带有着新兴国家建立的兴奋,因为对于乡土的表现,必须锚定于“国家”的意义,叙述姿态、观照立场,也须始终具有国家视野。而创作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家山》,乡土自身就是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国家的内涵重新由乡土赋予,正如王跃文反复强调的,“乡土里有最大、最完整的中国”,历史、意义和世界,就从“山”出发。
正是这种从“山”出发的叙述姿态,让作者在讲述乡土的现代变迁历程时拾得了一种深厚的气度,往往能贴着乡里人自身的情感和观念,贴着那些深深受教、生长于儒礼文化之中的人的立场上,写出新旧之变里人们复杂的情绪、艰难的抉择。这种复杂包含着佑德公的无奈、凄凉,一生勉力去维护沙湾的传统政教秩序,终被儿子、被县长的言行所打动,逐渐接受传统即将被时代替代的命运;这种复杂也包含着扬卿的无力、心酸,学西回乡后扬卿创办新式学堂,曾教过自己的私塾老师无法融入新式教育体系,勾背离开,扬卿何尝不感到苦楚;当然,这种复杂更包含着一门心思热血推行新政却深陷现实泥潭的县长李明达,离开沙湾的雪夜里刻骨的孤独,包含了贞一为了解放妇女而奔走,反造成女性新的压迫时深深的自责。新道路与旧秩序总是好坏善恶交织、问题与希望交互,《家山》写出了在历史之中的人,如何在各种力量、传统的撕扯之中艰辛地赶路。历史的伦理不再如过去一般,是一种明确历史走向的、乐观的言之凿凿,而是一种色厉内荏般的体贴,是忧喜与共的理解。
当然,新世界与旧秩序之间不仅只有龃龉、矛盾,《家山》所展现的复杂的变迁史内涵,还在于新旧之间相互的自然转化,以及协调、交织。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小说对于红花溪水库修建过程的展现。以耕种为基本经济活动的乡土社会,灌溉工程往往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如何修、依靠哪些力量,往往体现着一个乡土社会的运转逻辑。过去的农村题材小说里就有过对灌溉工程的描写,赵树理写于一九五五年的《三里湾》,就有过“开渠”一节。在当时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氛围里,小说给予的逻辑是,先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扩大,即“扩社”,而后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力量再来“开渠”,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现代性事件、现代的新生事物,“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公’的传统在现代世界的延伸”,旧的传统转化了新的事物。
《家山》里则不然,它对于旧伦理、新事物,有一种更包容,或者说更兼容的气魄。在红花溪水库修建过程中,是扬卿利用现代的科学测绘,精准找到了最适宜修建水库的位置;而有喜对于本地水文、地况的熟稔——一种非常本土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同样在水库选址时起到关键作用。在真正修水库时,县政府建设局、扬卿与村民们之间经过充分协商,最后由县政府主持全局,灌区农民们筹资金,管理人员由灌区百姓公推。可见,水库的建设过程中,科学探测与乡土地理知识,现代的管理机构、方式,以及自治的“公”传统是如此融洽地协调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乡村治理的关键工程的成形。在乡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过去的文化逻辑与现代的观念、机构交织互照,或许亦是某种真实。
因此,由“山”出发的现代变迁史,便不仅仅意味着站在乡土内部的视角,来观照这段历史的新旧更替,贴着历史行进中人的心境,来描摹他们的艰难心路,更意味着一种阔大的历史襟怀,包容历史进程内部所有的复杂肌理。既写出新与旧之间的排斥甚至是龃龉、冲突,也写出它们之间的自然转化、调度互照;既看到氏族农耕传统的低效、幼稚甚至荒诞,也看到它的温存、护佑;既写出现代规划的摧枯拉朽,也真实地指出现代允诺的空洞与危机。所谓的“文明史”,也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宽阔、深厚、涵容的历史书写伦理。
“文明”:新的历史书写刻度
广博、深邃的气度与品格,是《家山》迥然区别于文学史上其他乡土写作、现代史写作的所在。我们看到,无论是小说由“山”出发的现代史观察视角,还是对乡土世界极尽精细、深刻的复刻式描绘,无论是贴着人物内在精神的写作姿态、静水流深的文学风格,还是涵溶深厚的历史伦理、温煦宽广的体量格局,《家山》都呈现出一种浩茫丰厚的史诗品格来。对于史诗品格的追求,作者是有着深深的自觉的,在谈及《家山》的创作初衷时,王跃文动情地说:“正像佑德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作者将这种对“丰厚”的追求,导向为文学风格,但《家山》对于文学书写的意义,对于当代国人精神和心灵烛照的意义,又绝不仅止于此。《家山》可以看作是一部乡土风俗史、家族变迁史甚至可以是国族现代史但“乡土”“家族”“国家”这些名目都不足以囊括小说如此丰饶的体量与内涵。我想,《家山》的写作正呼唤着一个新的“文明”概念,小说正是一部用文学铸就的阔大文明史。
怎么理解“文明”?如何理解《家山》的“文明史”性质?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指出,历史时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地理时间”指向了“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社会时间”是“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而“个人时间”则是“个人规模的“事件史”。布罗代尔认为,一种真正的总体史的书写,一定是将这三种时间进行一种融汇、综合。
《家山》里的“家族”叙事,大概能够覆盖个人时间所指向的“事件史”,沙湾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能汇聚在每个农村家户的命运之中;而小说的“民族”叙事、“政治”叙事,则处在社会事件的层次规模中,诸如日本侵略、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等重大的国族转折,在小说里亦牵动着沙湾村乡亭叔侄的心魂精神,牵绊着年轻人的命运导向,并通过沙湾村的变迁史折射出来;小说最为丰厚深广的,其实是对积淀在村子日常生活里的山川风物、节庆礼俗、文化秩序的表现,那些于此绵延、传递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存在,往往能包容看似正当下的家族命运、国族事件,显现出它的悠远、深长。它们是处于“地理时间”的范畴下而得以显现的所在。在此,我们必须震撼于文学所开的“天眼”,《家山》通过一个村庄的变迁故事,着手于沙湾最细碎也是最普通的日常,却自自然然地将布罗代尔所说的三重时间贯通了起来,抵达了一种更丰沛、更深厚的历史观照。
或许许倬云的说法更为简练。长期专注于中国文化史的学者许倬云曾在访谈中相当简练地提及过他的历史观念:“我的历史观,个人的地位最小,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某种程度上,《家山》里的沙湾,就是一部既勾勒出“个人”“政治”“经济”“社会”,又深耕于“文化”“自然”的描绘,并在情节演绎之中深深勾连起不同层级文化范畴之间关系的一部文学长卷,只有“文明史”,可以为这样一种丰厚的写作赋予名目。
当代国人对乡土的叙述,第一次走到了“文明史”的位置,“文明”,是新世纪国人书写现代史的新刻度。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作家们从未停止过对于乡土的叙述。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新兴民族国家建立的时候,表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小说《山乡巨变》充满了欢欣、愉悦的情绪,如批评家所言,小说几乎就是一曲献给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深情赞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诉求涌入到创作领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充满了野性的气息,它要推重的是乡土民间自由喷薄的生命力,“国族”和“政治”,只是民间能够承托的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叙述开始向民族精神回归,陈忠实的《白鹿原》讲述的乡土历史,由此浸透着对民族精神的皈依,显现出了一种深邃苍凉的气质。新的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勇猛挺进,对于文化传统的悲悼情绪弥漫在文化人群中,《秦腔》可算作是献给秦汉文化的一曲挽歌。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喜悦欢欣、八十年代的野性喷涌、九十年代的沉郁苍凉、新世纪的戚戚悲悼,如果时代本身有着自己的心性——文学正彰显出时代之心,那么到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在中国崛起不再是一场梦而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的时刻,以文学为表征的国人心灵终于走向了丰厚辽阔,面对乡土,国人的叙述腔调第一次那样地从容笃定、娓娓道来,却又如此饱含着款款深情。而对于“历史”的理解,也终于胀破了以往“民间”“政治”“国家”或者是“乡土”这些单一的范畴,祛除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判决,经由对“自然”“文化”这些土地上更深远存在物的注目观照,让这些不同的范畴在历史叙述中走向了综合。《家山》所显现的辽阔、深厚气度昭示着,中国的作家终于褪去了许多情绪化的判断,面对中国现代变迁史,王跃文将新旧鼎革的故事收束于土地之上,冷静地深入到文明的内在肌理,去真正体贴这场文明荡气回肠的变奏。
值得一提的是,批评家陈晓明一直在提“晚郁风格”——萨义德和阿多诺的说法,用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余华、王安忆、格非这些更加先锋的小说家们突然进入的沉郁之境。而同样诞生于九十年代之延长线上的《家山》,虽然深沉,但却少有忧郁之感,倒是有开阔、深厚、蕴藉之美。常年深居湖南的王跃文身上,也带有更多传统士大夫的气质,那种借法古典语言的努力,那种重造传统精神的决心,多少让人想起“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古文运动的倡导。如果单线度的现代历史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致郁”,或许宽广的内陆地区为文学的发育提供了深厚的自留地,用以调试、缓解现代历史最前线带来的震荡,一如《家山》里的沙湾村那样。
无论如何,我想,王跃文深刻地领受了此乡此土赋予他的时代命运,他凝聚了十年心血的《家山》,当之无愧是一部广博、深厚的文明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