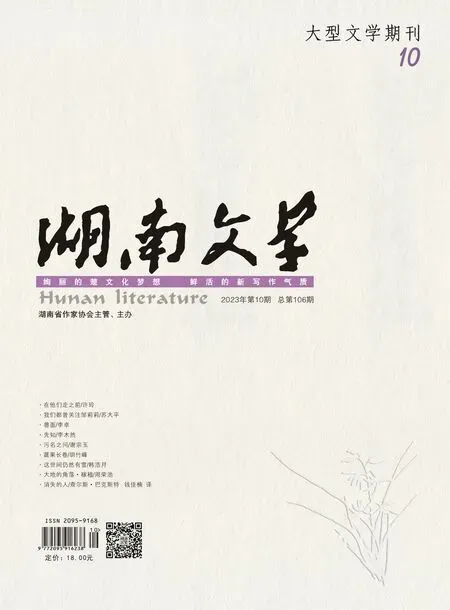门前一棵树
张 镝
一
每年中秋将近,一缕淡淡的清香翩翩而来,从从容容地拜访张家大屋的所有住户。男女老少,一夜醒来,便察觉到了空中的异样,鼻翼接二连三地连掀了几次,很快便心领神会地接受了这份神秘礼物,这是一种心流相通,另一端延至门前的那棵树。这缕缕香气不同往日的厨房饭菜香,也不是浓烈的果木花香,更不是猪栏鸡舍的浊气,它像一股清流,淡然、高雅、清新,像是一年一度来访的贵客,周身素雅、洁净,袅袅婷婷,朝人靠近。
桂花开了。明明心里有数,可还是忍不住奔走相告。不少人奔向那棵树,仰起头来,欣喜地望向那棵高耸的桂花树,打量着它的枝端。花骨朵儿似开未开,娴静而羞涩地躲在墨绿的叶片之下,星星点点,黄澄澄。挑担子的,扛锄头的,打树下经过,一边埋头走路,一边细嗅花香,像是得了一份福利,不发一言不出一语,心里美滋滋的,嘴角漾着笑。待到树前,停下脚步,抬头望上去,见小桂花儿果真在枝头闪烁,一份念想得到印证,心下踏实,又忙着赶路。人们在树下停顿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甚至看起来毫不经意,几乎难以让人察觉他曾有过那么短暂的停顿。也有一时腾不出时间跑来的姑娘媳妇,人在家里忙着洗衣做饭,灵魂却出了窍儿,随着花香来访,心儿早已礼数周全地跑树前回访去了,停泊在她们眉眼里浅浅的笑,不小心泄露了她们心头的秘密。老祖母也惊动了,她吃过早饭,干干净净地用帕子洗过脸,用老木梳将银白的发丝梳得一丝不苟,再将身上的灰尘扑打干净,一切停当后,拄着手杖,颤颤微微地来到树下,像是老朋友打招呼般轻轻唤一声,你又开啦!那声音轻得,只有桂花树能听见。
待到第二三日,花苞儿又绽开了些,从刚来人间的娇羞模样变得落落大方起来,呈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坦然接受着命运的来去。老练的家庭主妇搬出楼梯、凳子,带着长竹竿、叉子、塑料布来了。有时是夫妻两个,还有时是母亲带着孩子,他们将楼梯搭于桂花树干,凳子置于树下,塑料布在树底铺开,手持长竹竿,爬上楼梯或踩在凳上,开始敲打树枝。枝干抖动,桂花微小,纷纷扬扬地簌簌下落,飘起一阵桂花雨。塑料布上,很快一片金黄。取花人不贪心,有那么手捧两三把的量便停了手,笼起塑料布,收好工具,回家去了。一股浓郁的桂花香跟随着他们,在屋子里安营扎寨。当天下午或晚上,嗅觉灵敏的人便捕捉到了桂花与茶叶交好的信息。第二天串门,一杯新鲜的桂花茶端上来。茶叶依依,桂花晶莹,茶香与花香相得益彰,让人心荡神怡,话匣子随即打开。客走时,主人不忘用旧报纸包出一点新鲜桂花茶,托来人带回家去给老人喝。也有的只是举着长叉,以两齿叉的一齿为轴心,让另一齿旋转成圆,很快扭下一枝桂花来,拈在手里,边走边嗅,美美地带回家去,图个室内生香。老祖母有时在旁边看着他们打桂花或折桂花,便瘪着一张缺牙少齿的嘴,用有点漏风的声音叮嘱道,慢点啊,好生点,别摔了。老祖母温和的目光,与其说是望着忙活的人,不如说是望着那棵桂花树的树干,有一丝忧戚,更多的是朋友间的理解和安然。树干灰褐,中部呈竖条状空了一大块,空缺处边沿犬牙交错,像是咧开一张大嘴,或是佝偻着身躯,呈现出生命渐微的迹象。大自然不知用什么法子,雷劈斧砍,日晒水蚀,虫雕鸟啄,将它侵蚀得这么衰败?树皮上有了青苔,中空处好多腐烂的木屑,用手一掏,一块,再掏,又一块,还有的,放在指头上一碾,碎成齑粉。而靠里的那侧,仍然透出一丝新鲜的木质,证明它生命犹在,老当益壮,稀释着人们的担心。
桂花凋谢后,远在邻村的表哥们来了,他们用两根竹子绑住一把小木椅,做成了一台简易轿子,扶着祖母坐上去,然后蹲下身来,各抬一头,站起,祖母便升到了半空。表哥们大约是抬惯了这种轿子,配合默契,两人一步一摇,轿子便一悠一晃,想想祖母大约是舒服极了,不然,她不会显出那么高兴的样子。这可是她大闺女接她去住呢。大约一个月后,祖母又像走时那样,坐着轿子一摇一晃地回来了,不过,这次轿夫不是表哥,而是堂哥了。我们想祖母了,堂哥去接的她。祖母仍旧高高兴兴的,好像接去也好,接回来也好,都是好事情。母亲悄悄说,你们这姑母啊,不是你祖母亲生呢,可真是有孝心,每年都要接你祖母去住些日子,光有这片心都难得啊。
桂花树垂垂老矣,大家都担心它随时会倒下来,可它依然活着,一年年开花,一年年让大家做桂花茶,一年年陪伴着老祖母。
即使拄着拐杖,祖母也不能外出了,她静卧床上,后来眼睛也失明了,母亲和两位伯母轮流给她送饭,扶她去屋角的尿桶里小解。祖母太虚弱了,都坐不住尿桶的边沿了,父亲刨光了一块木板,搁在尿桶上,祖母坐上去时表情放松多了。
除夕晚上,父母陪着祖母在她房内聊天,大伙在屋外地坪里燃放烟花爆竹,堂哥说有款烟花里面有降落伞呢。大家翘首盼望,那喜滋滋的心情比真尝试着乘降落伞坠下来还要兴奋。果真,烟花点燃,腾向高空,绚烂一片,随即一顶顶红色的小伞或高或低,这里那里,徐徐降落下来,简直如仙女下凡。我们好想得到一把,想把那鼓着风帆,腾腾然慢悠悠的感觉握于手心。待它们落地之后,分别朝着自己盯着的地点冲去。可这些小红伞啊,在天空时明明看得真真切切,可真找起来才发现,我们所在的地坪,以及道路、屋边根本没有几个。大约,有的坠入池塘,有的蹚进小溪,有的扑向稻田,还有的躲进了竹林,被黑暗收入囊中。好不容易在池塘边捡到一个,兴冲冲地奔回家里,想去告诉母亲。只见祖母突然道,儿子啊,我看见你了!父亲一怔,随即移动一下位置,祖母道,你别动,我真看见你了!
春节刚过,祖母不行了,她已经咽不下一口菜大人打发我去喊姑母回来,我拔腿就跑。飞奔在田间的小路上,只觉天空低垂,像要压将下来,周边的山峦也暗沉沉的,肃穆极了,只有路边的溪水发出轻响,听起来却像是有人呜咽。祖母真走了。她走的那天,是正月十三。其实,春节还没完全过完那年秋天,桂花没有来。抬头一看,枝叶枯黄着,像在闭目养神,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没等它倒下来,人们将它锯掉了。一来不安全,怕它突然倒下砸着人。二来,村里要修路了。
二
春雨一来,柿子花簌簌下落。它们经不住雨水,从繁密的枝头败下阵来。湿漉漉的地面,到处是张着绿色翅膀的小果,铺成一张绿色的地毯。可雨季再怎么连绵,风再怎么摧残,总有果子未被雨打风吹去,越来越壮硕,特别是秋季,一个个从枝叶间鼓胀出来,皮肤光滑,果肉厚实。越往季节深处它越发艳丽,由绿转黄再转红,引人注意,也将鸟儿吸引。
我家只一棵柿树,就长在地坪边一角,高约三丈,抑或更高。架电杆时,它差不多要挨到电线上去了。为了用电安全,父亲只好搭了梯子爬上去从顶端砍掉几枝。这棵树是母亲亲手种下的。随着我和弟弟的出生,母亲想方设法弄来树苗,栽种到房前屋后,让它们陪我们一起长大。它果然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意,成活后就噌噌往上蹿着个,长得比我们快得多,不几年工夫,就到了让人仰视的高度,还挂上了果。等我和弟弟的牙齿长得足够结实,可以咬水果时,母亲就摘下柿子塞到我们嘴里。甜丝丝的果肉,柔糯香软,嚼不了几下就自动滑进喉咙里去了,简直像流质。有的,我们让它们自然熟,等软了,表皮透明了,就撕掉那层薄薄的皮,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还有的,我们只要轻轻“拧”开那个花式“盖子”(就是蒂),把勺子塞进去,就可直接舀出来吃,一勺勺棕黄的果肉,晶莹剔透,像琥珀。有时,我们等不及,便拿几个塞进米缸里,让大白米包裹住它们,好像能起到催熟作用;还有的,就拿茶叶石灰水浸泡起来,等一周左右,拿出来,洗干净,削掉皮,果肉虽硬,但嚼在嘴里,又甜又脆,似乎再也找不出可以匹敌的美味了。香香甜甜里,我们偎依着母亲,听她给我们讲柿树不卖的故事。一个人去买树,却不认得字。卖主跟他商量好了,山坡上的所有树都卖给他,只有柿树不卖,还签订了书面契约。结果账款付清,卖主却不肯交树了。官司打到衙门,官老爷一看,哟,这白纸黑字写的是树不卖,没错呀,你当初认账的事,怎么能反悔呢?买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故事说完,母亲和煦的目光望着我们,好像在说,没文化,吃大亏啊。
很多年我都被母亲编的这个故事骗着,并由此生发了一些学习的动力。年岁渐长的如今,细想这个故事,很轻易地发现了破绽。如果收了款,难道不要在契约里写明金额吗?收了买树的钱,怎么能够什么树都不卖呢?故意拿字蒙人,算不算合同诈骗?当官老爷的,只凭唯一推论?不过当时,这样的故事还是很有嚼头的,够给那个年龄的我们足够的消遣。我们吃着盼了很久才长大的柿子,听着母亲讲着故事,嘴里甜甜的,心里暖暖的,感觉与母亲的关系,更亲密了。这份陪伴,从春到冬,四季相依。
母亲如愿以偿。原来,她担心孩子没有零食吃,害怕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别家吃东西而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她知道,这影响的不仅是孩子的口腹之欲,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会悄悄地刻进孩子的心里。她要想方设法地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她不仅栽下了柿树,还栽下了板栗、柚子、柑橘、桃子。板栗树苗是从外婆家后山挖来的,一共三棵。只有这棵栽在猪栏屋后的荆棘里的才得以保全,另外两棵,不是被人随手折断,就是连根蔸都不翼而飞。看着小树苗一天天长大,母亲的希望随之飞涨。她的孩子,也从襁褓娃娃成为了小学生。
年轻的板栗树元气足,精力充沛,就像年轻的父母,给予孩子的总是很好的基因。没几年,板栗树就挂果了。毛绒绒的小刺球越来越大,大成一个小拳头。秋风吹拂,阳光明媚,天高地远,有颗毛球咧嘴一笑,蹦出一颗大黑籽来,砸在母亲头上。板栗熟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提着竹篮,带着竹棍和工具,来到树下。竹棍带着主人的旨意,轻轻地敲打枝头的板栗毛球,毛球坠落。我和弟弟急急地奔跑过去,用火钳夹住刺球,放到脚下,用鞋底将刺球压在地上来回揉搓,刺球变成长筒状,中间黑,两头绿,绿是刺球的原色,黑是沾了土的缘故。我们用脚压住刺球的一端,手握剪子轻轻地剪开刺球另一端,一颗颗嫩白的板栗便蹦跶了出来。顾不上洗手,剥开柔软的内壳,撕去嫩皮层,一眨眼工夫,淡黄色的板栗玉体便呈现眼前,顾不上细看,也不知哪只手,飞快地就把它送上了舌头。那脆嫩芬芳的板栗肉啊,吧唧吧唧几口就被我们嚼得唇齿生香,都忘了往竹篮里夹板栗球。母亲看着我们一副馋相被满足的样子,笑了,仿佛从她动念栽果树那刻起,就期盼这个时刻的来临,真盼到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她感到甜蜜和欣慰的呢?刚才尝的是嫩板栗吧,怎么样,要不要再尝尝老板栗呢?母亲停下在枝叶间挥舞的竹棍,指着那咧开嘴巴的毛球示意我们。浑身是刺的板栗也有可以进攻的破绽,那便是它自然成熟后会自然裂开,露出里面深褐色的板栗来,这层深褐色,相当于板栗的夹袄,而那层毛球,不过是它的外套。只要是自然裂开外套的板栗,夹袄便是深褐色。也就是说,只要板栗自然成熟,它就由内至外有了二重性特征:一是毛球开裂,二是夹袄颜色变深。其实还有一重,便是里面的果肉变得金黄,且肉质变老变硬。真要吃到果肉,还要剥掉一层毛乎乎的内衣。这层倒不刺手,摸起来还挺有质感,像毛线绒,不过不能吃,看着那毛乎乎的样子,都觉得喉咙里发痒,所以得把这身内衣脱干净了。如果是嫩板栗,内衣也嫩气,轻轻一扯,整件内衣就剥掉了;而老板栗呢,新鲜时还行,如果放久了,内衣就粘附到果肉上,很难脱下来,得用开水泡一泡,才能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像剥嫩板栗一样脱下它的内衣。当然,老与嫩是相对的,别看板栗刚从外套里出来是白色或淡黄色,只要放几天,它们就会转成深褐色,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我们照着母亲指引的方向,很快找到几颗老板栗,直接用剪刀从裂口处挑开毛球,老板栗便滚了出来。有时,那个裂口大,连剪刀都不用了,戴着帆布手套,将毛球倒过来,板栗就从裂开的豁口里落下来了。这个带内壳的板栗,头顶上还有根朝上的小刺,像天线宝宝的天线,可以用小夹子夹住它,从毛球豁口里取出来,这也是一种取板栗的好方法。老板栗肉质有点硬,咬起来要多花那么一点点力气,随着嘎嘣一响,板栗在口腔里碎开,咀嚼起来,那种甘甜劲道的滋味,是嫩板栗所无法匹敌的。老有老的滋味,嫩有嫩的味道。我们把从树上将板栗敲打下来的方法叫打板栗。打板栗的当晚,一筐板栗躺在墙角,一碗板栗炖鸡摆上餐桌,金灿灿的鸡汤,黄灿灿的板栗,真没辜负我们姐弟俩将秋火望了三个季节,从春到秋,从竖条状毛绒绒的板栗花开始。
采过板栗不久,柚子由青转了黄。一个个,或高或低,或显或隐,随着柚子树,在那片荆棘丛生的竹林中秘密生长。我们似乎只是偶尔想起它,即使母亲带着我们去采摘,也不是特别兴奋。树太高,又是斜坡,没有哪次能一次摘完,没有一次我不担心母亲的安全,生怕她从树上或搭不稳的梯子上摔下来。那样的话,我宁愿不吃柚子。母亲似乎并不在意,只交代我扶楼梯,让弟弟看清楚柚子滚落的地方,好到时寻找。这样摘来的柚子,大大小小,每年居然有十来个。将柚子们背回家,母亲并没有立即找来最大的那个剖开来给我们吃,而是让我和弟弟一起给伯伯家送柚子。刚开始我疑惑不解,父亲兄弟四人,母亲与他们之间矛盾很深,平时都不说话,为什么要送他们柚子呢?母亲看着柚子树的方向,含着笑告诉我们,树是祖母栽的,虽然分家时分给了我们,但作为祖母的子孙,都应该尝尝。柚子柚子,又生一子,祝福大家多子多福。见我迟疑,母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慎重地嘱咐道,我们大人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大人的事,与你们小孩子没关系,他们是你们的伯伯,与你们有着用刀也割不断的血脉亲情,不管何时,遇到他们,要有礼貌,要叫他们,该怎样叫他们就怎样叫,不要受我们的影响果真,当我们欢欢喜喜把柚子送去,每次都收到了伯伯家真诚的谢意。
母亲不仅喜欢果树,还植下了泡桐、杉树、枞树、樟树……这些树长得快,泡桐树后来摇身一变躲进了新木柜后面,成了木柜的档板;杉树被架上墙垛,大的成了檩条,小的成了悬皮,悬皮就是铺瓦的木条;枞树韧性强,弯成了木椅的边沿及腿,沿腿一体,不用钉,也不用隼,光滑耐用;樟树做了家具,还有些被锯成了切菜的砧板,切肉食的时候,用力大,刀入砧板,带出木屑,菜里有那么点樟树的辛味。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察觉,爱种树的母亲,与做木匠的父亲,是否有着某种幽秘的关联?虽然我知道他们的婚姻并非由此牵起。
三
楼下花坛呈长条形,卧于前后两楼之间,与楼平行。花坛里,三点一线间距匀称地并排栽着三棵桂花树,即两端各一株,中间一株。不知是靠近道路人马穿梭惊扰了它们生长,还是树种原因,只有中间那棵长势喜人,团团华盖,耸立如云,都快超过二楼窗户了,而边上两棵,生长过于从容。特别是靠车行主干道的那棵,节奏慢得仿若穿越了时空三棵桂花树处同一花坛,遥相呼应。底下是草地还有金边四季青、红桎木等灌木丛,挨挨挤挤地拼成某种美学图案。另有几株茶花、绿叶四季青,颜色、品种还算丰富。也许楼盘刚建时设计师充满着美好的愿景,只是到了业主接手,没人懂得园艺,于是,一根接力棒悬至半空。每到春天,荆棘、臭皮藤乘机而入,捷足先登,在灌木里缠绕疯长,夏天更盛,大片大片地抢了灌木的风头,掠夺着雨露。灌木日渐消瘦、枯黄、稀疏。仿佛是看着灌木活得没劲,四季青也打不起精神,秋冬两季,不少枝叶干枯,翠绿的叶子斑斑点点,有如虫蛀。草地也没了青草的纯粹,洋蒿、犁头草、芒刺等杂草甚嚣尘上,喧宾夺主。一个花坛,写满疏于管理的荒芜。是可忍,孰不可忍。从小耳濡目染了树木的繁茂,又知悉了植树是那么轻而易举。俺不动手,更待何人?
娘家位于花木之乡,苗源丰沛。只是车辆运输,怎么整?县城的人,小车、楼房、朝九晚五,早已远离了十指沾泥的劳作,哪还有适合运树的货车?好在有老古,他住对面楼栋五楼。也不知他怎么赚到的人生第一桶金,又作了怎样的人生规划,在城里购置了这套房。老古没有正式工作,跑摩的,做保安,还有台啪啪响的三轮车,为人拖货。老古的老婆在沿海打工,他则带着孩子在城里陪读,早出晚归,傍晚按时回家给孩子做饭,经常手里拎着一把蔬菜几片豆腐。看得出来,他平时没有读书的闲心,也没有精力辅导孩子,但他把孩子上学的事,看得很重。听说要运树,老古当天就出发了。时间不凑巧,我没法陪同前往,老古独自驱车找过去,居然很顺利就找到了目的地。当时还没有导航来着。树苗运来了,他却只肯收油钱,说是邻居,哪有不互相帮忙的。
从车上把树搬下来,才发现弟弟帮我挖的树除了桂花,还有金丝楠木,株株挺拔、秀气。适逢儿子放假在家,便一起帮忙。挖坑的锄头哪里来,问了很多人,都没有,最后从物业的一位老人那里才借到一把。刚挖好洞,楼下邻居一家三口下楼来准备外出,好奇地看着我们。同一个院子长大的孩子,特别是性别不同,又有年龄差,何曾有过活动交集?突然动念,邀请他们一道栽树。邻家闺女犹豫着等父母表态,很快得到了肯定答复。家长们站在旁边动口,孩子们负责动手。儿子到底大些,满脸沉静,弯着腰,用锄头往坑里扒土;邻家闺女像是从没尝试过这种劳动,认真地扶住树苗尽量让它不偏不倚,青春的脸庞笑意盈盈,显得好奇与兴奋。没多久工夫,土壤就将树苗压稳压实,树苗稳稳地立在花坛里。一棵又一棵,那天,两个平时不打交道的孩子,一起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植下了一片绿。不知多年以后,他们身在何处,如果回来,那些树还在,会不会想起今天植树的情景?
栽下树苗,栽下希冀。就像捧着初生的孩子,由然而生对未来的憧憬。我们经常凑过去,围着这些树,左瞧右瞧,想知道它们渴不渴,会不会成活,期盼有一天,树能有所暗示。我等得焦急起来,便跑到树旁,专注地盯着那些树,从一根枝条望向另一根枝条,从一片叶子搜索到另一片叶子,希望发现蛛丝马迹。可它们缄默不语。也许潜伏在泥里的树蔸,正进行着殊死搏斗。谁说不是呢?本来它们在我故乡那片山清水秀的地方,由一颗种子长成一棵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长成如此这般青春靓丽,没承想,一把锄头,就把它们连根刨起,一台车,将它们运至此处陌生之地。从前它们的所有努力,如今都只能一切从头开始。一个树蔸,几条根须,想要在新地方立足,得先与泥土建立关系。好在大地母亲广博无私,只要植物本身不矫情,天气和季节不出来阻梗,她的爱便会无微不至,润树无声。次年春天,一个个褐色芽苞,偷偷地从枝叶间冒出头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几乎每根枝条上,都有好几个,原来是信使。看起来如此隐秘,却又悄然传达着让人欣喜的讯息——树活了!叶是根的形,根是叶的本。可以想见,树的根须已与土地深情相拥,达成默契。此刻,树的任督二脉已被打通,土地正默默无私地从树底为树输送养分,源源不断地将营养送至树的枝枝叶叶,周身各处。慢慢地,芽苞次第散开,展成一丛丛嫩叶。一片片,迎着风,散发出簇新的光芒。当年秋,老古的老婆回来了,在附近制衣车间上班,从此,他们结束了牛郎织女的不便,甜蜜溢满心间,写上脸庞。
不久,几台机器怪兽驶进小区,轰鸣着,咣当咣当,花坛左右两边各被裁掉一些,长条状的花坛更苗条了。几棵移栽后刚刚成活的桂花树连同花坛边沿的四季青被连根拔起。光秃秃的根部刺拉拉地翘向天空,被活生生地剥离了土地,就像将鱼从水中捞起,让它远离活命之水。拾起其中一棵根须尚在的桂花树,在小区里找到一处隐蔽的斜坡,顺手挖了个小坑,将它重新植入土壤。树挪死,人挪活,刚搬家不到一年又要搬家,不知这株桂花是否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或者说适应力。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可心里还是为它祈祷。与这几株桂花一同遭受厄运的,还有一株茶花。它不在我们楼栋前,而是原来好好地长在隔壁楼栋。见过它花容月貌,亭亭玉立,繁花满身,现在,它倒在地上,连根翘起,枝叶损坏,沾满泥渍,淡棕色的树干有好几处被沉重的机械撞损破皮,奄奄一息,甚至发不出一声呻吟。一棵树离开了土地,被虐待成这副模样,让人联想起灶台、柴火,好像那才是它的归处。我的心头有泪滴淌落,顾不得将会黄泥沾身,跑到它跟前,想要将它抱走,可是抱不起,拖,也拖不动,没想到这么一株行将就木的柴火,看起来体形并不庞大,可每一根树干,每一秆枝叶,都饱含体重。打量枝身,足有好几米长,还有树蔸,看起来也不轻。当然,要说轻也轻,那是大脑中描摹的具象,而实际,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有形体,有体重,体内饱含水分,难怪我搬不起,移不动。几个人站在旁边奇怪地看着,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后来终有一位好心人像是意识到什么,劝道,这个还有什么用?
我偏不信。回家找了把手柄锯,来到树前,一锯锯,将枝叶锯掉,再锯掉了几根被挖机挖斗砸烂的根须,终于从那堆遗弃的树木堆里将它拽了出来。尽管这样,还是太重了,茶树树干密度大,如果做柴火,那是很耐烧的,现在要搬动它,轻不了。移几步,歇口气,然后再搬着它往前移。终于搬到自家车库前,内衣全湿,外套全是泥。拍图给弟弟,问能否栽活。弟弟说,不要了吧,被挖机伤成这个样子,即使成活,也没了看相。如果你要茶花,家里有的是,随便你挑啊。可是,如果放弃,它就会死去。我不是要茶花,我要让它能活下去!
求助另一位。他有个苗圃,很会养兰花,原来送过我好几盆。爱兰的人,应该会爱惜生命,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植株。也不知这是什么逻辑,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吧。没想还真遇到了良医。他将图片发过来时,多了三根标注的红线,备注说明:红线之外,全部锯除,这样栽下,能够保证营养和水分,成活没问题。茶树不比梧桐、杉树,锯起来特别费劲。尽管这样,求活心切,再怎么难,也铆定了。眼看就要锯好,只差最后一根,准备将其与另一根相交处留个豁口,好稍后包扎那些破皮处,没想,眼睛看着别处,脑里想着到哪找胶布,锯子在手下拉扯移动突然手一麻,一滴滴鲜血像宰鸡般滴滴答答地往下坠,地上殷红一片。终于锯成如图所示。请人在花坛正中挖了个大坑,把茶树放了进去。看着只有几根主根,一放还放不进,卡在洞口。三番五次地把坑掏深掏大,总算让根须全部入坑。往回填土,拢起土堆,立住树蔸,浇了两大桶水,大功告成。当用保鲜膜将它受伤部位包扎完毕,一个下午过去了自此,出小区前,进小区后,都要去看那株茶花桩通过两次锯除枝叶,那蔸茶花树,只剩下一个冒出地面几十公分高的树桩了。观察茶花桩是否活过来的数个晨昏,经常在花坛边的林荫道上遇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天气还没有完全暖起来,可他光着膀子,跑得满头大汗。那是老古,他在为老年做准备,管理健康,锻炼身体,晨练。
立春过后,一个芽苞,两个芽苞,纷纷从灰不溜秋的树桩上冒出头来,探头探脑,虎头虎脑,可爱极了。又过了些日子,一片片肥大壮硕的叶片尽情地舒展,那么簇新,那么娇嫩,那么大气,简直扬眉吐气,我终于吁了口气,一颗悬在胸口的石头落下来
一天,茶花桩不远处,围着一些人,大家的脸色都不太自然,像是传递着不好的消息。平时不是很爱锻炼吗,好可惜啊,这么年轻,正值盛年啊……大家小声地议论着,随后黯然散开。啊,他们说的是老古!老古在乡下新建的房子里,突发心梗……
春天倏然而过,夏天来了。这个夏天,让人难忘。小城遭遇大旱,从夏旱到秋。县城主干道旁的银杏被夺走一半。我亲手救活的那个茶花桩,新枝嫩叶一片焦黄。尽管心急如焚地立马浇水,并隔三岔五就提一桶水去浇它,它还是没能再次发出新芽。站在那个毫无生气的茶花桩跟前,我怅然若失。一个青年走过来,温和地叫了声阿姨,原来是老古的孩子。不觉时间飞逝,他已大学毕业,考取了某个单位的事业编制,有了份正式工作。而顺手抢救过来栽在斜坡处的那株桂花,叶子依旧墨绿活得精神抖擞。年复一年,长出了很多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