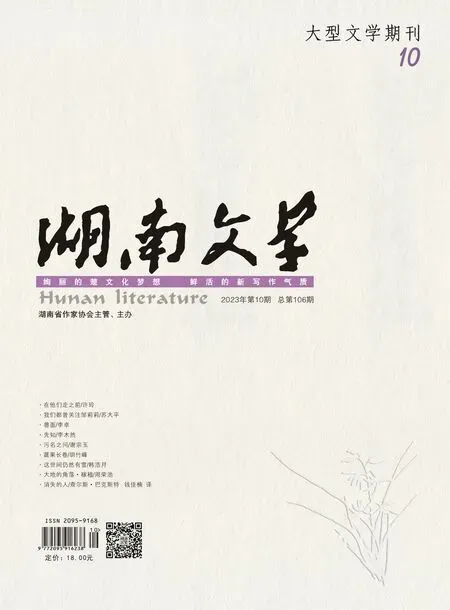资水之魅
张强勇
一
资水过邵阳,自东南顺流而下,一路磕磕绊绊,走峡谷,断峭壁,切山峰,弯弯绕绕,曲折往东流。沿途收纳无数小溪,经栗滩、茱萸滩、石滩,先前桀骜不驯的资水顿时温驯起来,一路深沉而平稳地继续向东流去。
发源于邵阳的球溪河与麻溪河,一南一北在沙塘湾交汇注入资水,互成对视,继续流淌充实着资水水域。球溪河居江左之上,挟两岸青山叠嶂而出,翻腾,激越,恣意汪洋,一路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北闯去;麻溪河居江右之中,水流平缓,自然又从容,从村头流入,从村尾流出,穿村越庄,潺潺而过,不张扬,不拘束,颇似大家闺秀;其他支流洙溪、雷公溪、马市口溪、柳溪,沿途有溪涧山泉汇而弥补,没了缺憾,清而不富,雅而有致。众流激荡,河面豁然开阔,奔向资水。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让人无法预料的偶然,又充满着令人惊奇的必然,就像流在平地上的水一样,前后奔突,纵横漫漶,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是千流向东,万川归海,在芜杂的局面中渐次展现,在这块土地上成就着一段传奇。
沿岸的球溪俨然一位不愿出阁的江南水乡女子,一路隐藏在深山峡谷与村寨之中。从雪峰余脉的沟壑间潺湲而出、逶迤而来,昼夜不息地流淌。聚峡谷之水,急转直下,一路奔腾,溪面时开时窄,溪水时涨时落,而入资江,水域渐开,水势渐缓。星罗棋布的古村、铺寨,新屋铺、老屋铺、木山寨、石槽铺,已然散发着时间的余韵,感叹着岁月的沧桑。走进村寨,古木葱郁,石桥横跨溪上,木板屋到处都是。百年老屋掩映在苍翠古樟之间,青砖黑瓦,雕梁画栋,基础石件雕刻精美,檐下壁画栩栩如生;迎客的白玉坐礅守护着大门,石门刻着“地远尘氛环水竹天开云锦列山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在六七十年以前,资水是与发达的洞庭湖区及汉口连通的唯一大动脉,毛板船无疑是这条大动脉中最活跃的细胞——本地有的从这里运出去,本地没有的从这里运进来。先民筚路蓝缕,涛头搏利,不止丰富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亦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回忆和精神源泉。
水运发达年代,新屋铺、石槽铺是资江沿岸重要的陆路通道,驾毛板船的商家,将沿路采集的货物、船只贩往下游益阳、武汉。船到目的地,船体被拆开,木板与煤一道被销售出去,商家怀揣获利的银两,结伴走陆路回家,至今还残留有部分当年的官道、茶坊与店铺。球溪码头,因扼锁了球溪与资水衔接的咽喉,在只有水运局限的年代,地理位置变得极为重要,成为水运要津,上宝庆,下益阳,出汉口,形成“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行旅出乎其途”的岿然要地。南来北往的商人、帮会在这里落足,留下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十八帮文化,盐帮、船帮、布帮、纸帮、炭帮、丐帮、袍哥……当年的江湖硬汉在资水河上、沿河村寨穿梭着,行豪侠、重义气,维护着各行各业的秩序。那时,没有公路、铁路,更没有国道、省道,只有乡间小道。河道便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通江达海、通衢大江南北的交通方式。及至公路、铁路的运行,曾经川流不息、人声鼎沸的码头、古道逐渐荒废无闻,黯淡无光,留下了斑驳荒芜的遗址,只能让后来者在寻找昔日的船来人往时,感受着过往的喧闹。
资水沿岸的集市与码头,由于毛板船的兴盛与持续扩大而日益成长起来,逐渐完成了从一个码头的货物集散地到小城镇的诞生与演变过程。它们是吮吸着资水的乳汁生长的生命,注定它的命运就是要在波涛流水上求生存;只有在与母体的同呼吸共命运中,它们才能开放出朵朵的似锦繁花。沙市、麻溪市,球溪、沙塘湾码头,这些集市与码头的命运更是如此。资水上的毛板船能驶多远,这里的脚步就能走多远;资水上有多少的毛板船能乘风破浪,这里就有多少的商贾、游子在逐利天涯。码头、集镇、商埠,它们与江面上的云樯帆影结下了多少代的宿缘。
行走在资水两岸,透过球溪、沙塘湾码头的细枝末节,窥探老街在沧桑岁月里留下的痕迹。砖木结构的房屋,青砖土墙、木屋黑瓦、雕花门窗,线条简单素朴,青苔爬满低处的台阶,也同样在高处的屋顶上滋生蔓延。阳光透过瓦隙洒落,给老街增添了光影交错的时空感。三五位老人坐在屋外的竹凳上,或静静发呆,或闭目养神,或叼了一根旱烟管在吧嗒吧嗒地吸着,任凭老树青苔生长,却也不管不顾。
历史的跫音已然远去,留在光阴里的码头故事,在资水的沿岸沉淀。如同悬挂屋檐下的陈年信物,抑或是刻满了岁月印痕的石阶。大宋熙宁五年,章惇奉旨来到离京城八百余公里的梅山,采用“怀柔之策”平复了梅山诸蛮。“将命出使,怀柔友燮……瑶俗于变,皇风大同,熙熙皞皞,天子之功。”章惇和仆从驾一叶扁舟,溯资水而上,缓缓而行,沿球溪码头上岸,来到大乘山下。伫立船头,眺望乘山,苍松翠柏中掩映着的气势恢弘的大乘佛教圣地雄踞于资水河畔的乘山之巅,章惇仿佛是感应了寺庙的铛鼓一声,钟磐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的礼忏,心中便有了一片澄净。遥望乘山群峰,写下了《过石槽铺》:“瘴霭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阔烟萝人逢杂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
顺着蜿蜒崎岖的江岸自西向东溯溪而上,江右的球溪两岸是连片青山,楠竹成林,屋舍、田园、溪流被悉数包裹其中。村庄或临溪而筑,或依山而建,好一幅千里江山图。荡击的水花溅在我身上清凉的风迎面扑来,把夏日的酷热一扫而光。行至河堤,阳光透过密密的杨树、柳树叶洒落下来,映照在河面,形成影影绰绰的斑斑点点,河道恰似小姑娘般穿着碎花的裙子。这时的球溪河分外静美,分外动人,不留意间,静美的山水林田在缓缓地舒展着。环视四野,远处青山朦朦胧胧,近处溪岸边一层薄薄的水雾涌起,野鸭在溪面游动,水鸟从空中飞过。绿的山、白的雾,轻轻柔柔,起起伏伏,令人陶醉。乡村别墅与古老的木板屋比邻而居,却仍能依稀看到原有的模样,古老与现代,遗韵与时尚相得益彰。
二
十七世纪初,资水岸边的沙塘湾就有人开挖煤矿。随着煤炭产量增长,河运船只远远不够。沿岸居民陆续发明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千驾船“洞驳子”。但是载重不多,最多的船只也只能装载三十吨。“呜……嗬嗬,嗨……嗬!水过滩头声声急船到江心步步难……”这是流传在资水两岸的《资水滩歌》,资水上毛板船头舵工的歌声悠悠荡开来一百五十年前,在资水上行船运货的船工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煤炭、玉兰片、茶叶、土纸、砂罐等商品堆积在沙塘湾码头,一时难以运出去,无法交易,困扰着生意人,苦恼着商家,而下游的益阳、汉口等地的经销商更急更盼,他们都渴望着能有一种搏击滩头又有较大运载能力的船只。商家、船工与造船师傅看到涨水时的“放竹排”,突发奇想,改造“三叉子”木船,首创“一次性使用”的毛板船,用于运煤外销。在资水沿岸的筱溪、王家坪、麻溪、石滩、沙塘湾、栗溪桥、青峰、游家湾、长风塘等地,就有了规模较大、手艺齐全的造毛板船的船厂,还衍生着上百家制作雨篷、晒罩、浆、铁钻等为造毛板船的附属加工场。自此,两岸的木材、煤炭、土纸、砂罐等货物,汇聚码头。球溪码头、沙塘湾码头成为了资水中游的咽喉要津,上游甚至下游的船只都毕集于此,商贾云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麋集而市肆鳞次。
毛板船不但造价低廉,其载重量也大增。一只毛板船能载物一百二十吨,最多者可以达到两百吨,运到汉口,可获成本五倍以上的利润。只是资水滩多险多,一不小心,便船毁人亡,货物更血本无归,但“十剩其三”,也就是商家开运十条毛板船,即便在资水上打烂七条,剩三条到汉口,也有赚头。毫无疑问,会吸引着沿江两岸的有钱人和城里的资本家与地主,纷纷来埠做起了毛板船的煤炭生意。
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资水万樯云集的盛况,但是穿越时空的文字留下了记录,沙塘湾商业发达,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上街、下街、向阳街、老街、后街、太平街、坨树街、石马街以及麻溪巷、顺兴巷、祥盛巷、里仁巷、宝和巷、里福巷等八街六巷。有乾福盛、两茂盛、瑞和庆、道源庆、合裕祥等有名有号的商贸铺子一百多家,还有提篮小卖和没有名号的商铺不可胜数。有名气的商号多半为本地商人,也有省城或者阜外的商人开的分号。他们经营着煤炭、毛板船、砂罐子、生铁、茶叶、黄酒、米烧酒、旅社、杂货、屠坊、染坊、漂洗、饮食、打铁、箍桶、磨豆腐、毛板篷、盆、中药材、缝纫、理发、戏院等五行八作的生意。
我想起小时候爷爷和我说起驾毛板船的事,爷爷就如一条鱼,驾着毛板船在资水里讨生活。资水七十二处险滩,最险的银滩和洛滩,打烂的毛板船只也最多,有时接连打烂几十只,河水都被煤炭染黑了。即使到了汉口,船靠在岸边,若遇长江或汉水涨大水,人和船带货都会被洪水冲走。
对于生命的逝去,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模糊的,甚至还有一种不确定,觉得还会回来。滔滔江水在这里纵横其界、负载千钧,演绎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给沿江百姓家庭带来难以泯灭的历史灾难。他们的生活非常清苦,收入极为微薄,漂泊无定却还要受河霸、帮会的盘剥。“船打滩心人不悔,艄公葬水不怨天。”资水滩多,它的通航凝结着万千船工的艰辛,有的甚至搭上了性命。这样的场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很难想象的。只是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这些朴实的船工丧失生活的勇气,反而激发了他们生活的热情。“千人拱手开毛板,万盏明灯天子山。”资水上的滩歌是他们在清贫、单调而又漫长的行船生活中创作出来的,那一声声滩歌号子是他们乐观精神的最好见证。
远隔时空,现在很难查找到经由沙塘湾码头起运毛板船的数量以及吞吐的货物量。装载着煤炭、土纸、玉兰片等货物的毛板船从沙塘湾出发,若是遇上顺风顺水的好天气,只要半个月的河运,就能到汉口,连煤带货、带船卖出去,船只不需返回。驾船的舵手和船工、水手们走“旱路”回沙塘湾,不但缩短了运输的周期,煤炭运量也大增。据在汉口宝庆码头经营煤炭生意的老人回忆,在抗战前后,每年到达汉口的毛板船达到一千只以上。抗战前,一艘毛板船上的煤炭可以卖到两三千银元,可以想见,这些船换回来的银元,数量很是可观。他们多半又会经营粮食、棉花和棉纱的生意,从武汉购回棉纱或从沿江各地买回棉花、稻谷、大米等。沙塘湾码头每年货物的吞吐量,粮食达到了五六万担,棉花达到了四五千包,还有棉纱二三千锭,又将这些货物销往附近及安化、邵阳等地。毛板船的出现,缓解了资水运煤的难题,沙塘湾沿岸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水上运输规模造就了资水上的毛板船,堪称当时的“航空母舰”,促使资水边闭塞的自然村落慢慢地向商业化的城镇转变。表面上看,资水上的运输主要目的是向下游的益阳、汉口甚至上海和海外等地供应物资,这里只是一个歇脚的地方罢了,或者是货物的汇聚地,但正如旅行的精彩之处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一样,沙塘湾以其“在路上”的独特处境而变得精彩异常。
依靠河运,沙塘湾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激增,加上各种本地物产,商船转贸四方,形成了“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服贾之民亦什苦其六”的局面。狭小的空间日渐见绌,商贾、市肆、屋宅被迫向周边滋生、扩张,沿江河岸向周边生长,成为了真正的商业繁华和运输中心。经营的商品非常广泛,包括棉布、丝绸、衣饰、铁器、煤炭、书籍、木材、茶叶、土纸等许多种类;经营典当、钱庄、票号等业务,对于当地的商业,手工业起到了促进带动作用。四处可见的绸缎铺子、茶楼酒肆、工艺漆店、玉器手镯、刺绣棉纺、檀香土纸以及铜器、铁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产业的发达,足可见沙塘湾的消费、交易与生产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惊人。
为适应河运之需,造船业、修造业飞速发展,成为当地手工业的支柱产业。造船业又带动着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缆索、桐油、铁钉、木材加工等行业的兴盛,另外有一些手工作坊,比如染坊、洗坊、豆腐坊等,甚至书坊。也有青楼妓院、茶社、戏台。戏台的繁荣来自沙塘湾商业资本的支撑,这些演出活动多数是商家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敦睦乡谊或者酬答地方乡绅民众而约请赞助。
鼎盛时期的沙塘湾有上千水手及数百驾船的舵师,船主、船工、锯工、簟工、铁匠、挑夫达两千多人均生活、居住于此。此外,警察所、厘金分局、区公所、学校、医院驻扎或设立在这里。沙塘湾已经成了周边十余平方公里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可以想见,毛板船运承载着资水沿岸人们发财致富的梦想,承担着官府的财力保障。
舳舻传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武汉三镇日益倚重来自资水上的木材和煤炭,还有茶叶、土纸和砂罐子。因此,资水的运输能力与规模越来越大,沿江居民逐利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逐利的人也越来越多。资水上的毛板船带来了沙塘湾的商业繁荣,而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将周边府邑的人流物流带回了沙塘湾,将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地缘甚至文化缘的人聚拢在一起,让他们为了一个简单却又残酷的目的在一起纠缠,成就了沿江集镇一种特殊的文化标签。
三
琅瑭,几乎是被时光抛弃了的一座古镇。这里有曾经的水路码头,码头上现存有历史的遗痕,明清时期修建的码头与石阶还在,只是上面布满着青苔和水草。百年香樟树枝叶苍翠,孤独地映照着澄碧的江水。江水岑寂地流淌,毫不疲惫。
我来到这里,正是山茶花初开的时节,空气中充满了好闻的花香。在一个夜晚,我坐在资水岸边,仰望夜空,半轮月亮掩映在夜色之中。微星如絮,流星划破天际,四周暗黑。被黑暗笼罩着的,有悠长而宁静的山溪,有溪边的灌木与杂草,还有倒映于水底的树影、房屋和我。
夜风从溪面吹来,清凉中带着温润,微微地吸入,沁入心底,让人陶醉。我渴望能在这里傍水而居,租一小船,驶向荷塘深处,那里有一位老者,在翘首而望。我会在清晨采摘山中野果,夜晚躺在溪边的杂草地上看繁星。桥头有一片杂草地,在夜色下的草丛里,萤火虫落满在一簇簇的狗尾巴草尖上,这些是我幼时的好伙伴,也是多年不见的小生灵,正打着灯笼和我一起寻找遗失了多年的记忆清凉的月光什么时候洒了过来,将我从记忆中拉回。我站在桥头,远来的山风告诉我:这里有水,有桥,有沧桑。
这座曾依资水而繁华的小镇有千余年的历史明清期间,琅瑭水路、旱路通达,不但是重要的水马驿站,更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关山万里,山重水复,马蹄声响彻在一条漫长的古道上。除了陆路,水路更是主要交通要道,一条茶船古道也延展在历史深处:新化茶叶被运到资江边的琅瑭码头装船后,出益阳,入洞庭,转长江,到汉口,再辗转经汉水至襄阳、安康、长安等地。无论陆路还是水路,琅瑭镇的杨木洲都是“茶叶贸易中心”,而苏溪村的苏溪关,是新化乃至宝庆全境茶叶运输的必经之地,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纳税关口,早在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官府便在此处设立巡检司,开设茶税官厅,额定每年收茶税银三千两。
眼前的建筑是一幢古旧的木质两层小楼,墙壁早已被日晒雨淋而显痕迹斑斑,对着江面的走廊上的扶手也被熏得发黑,这幢木板楼大概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古镇上,还有几栋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建筑,虽然古旧,甚至破损了,却还多少保留着质朴的韵味,也留下了原有的烟火味。灯影朦胧间,如果仔细看去,还依稀能看见雕花的门窗和屋檐的石刻,八角攒尖,飞檐翘角,雕甍绣槛,古韵盎然,有着精美的造型轮廓。我仿佛模糊地看见阁楼上倚靠着一位涂脂抹粉的妇人,双手扶着木栏杆,遥望江面,盯视前方。那里有一个驿站,那里有拴马桩,她在盼望着自己的夫君或是情夫,正策马扬鞭而来。
巷子蜿蜒地顺着资水的流向朝着东西走向延伸,路面是用鹅卵石、糯米和石灰混合打磨而成,发着青绿的光来,已经有了上百年光景。等到钻进巷子里,视线几乎全暗了下来,以前屋檐上悬挂着的烟雨灯笼,早就不知去向何方,我走过,是要靠嗅觉走路了。在狭小交错的小巷子之间绕了一阵子,犹如在一个陌生的迷宫里面。我闻到了弥漫在路面和房屋木质里面的马粪与马尿的味道,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驿站。在时间的堆积下,这是一种浸入建筑物体里面的气息,倏忽百年,难以消失。
巷子的尽头有一座祠堂。小时候常去祠堂玩,是最熟悉不过了。印象里,祠堂一直是一副破落相。就是现在,和街巷里的老人说起祠堂,流露出百感交集的情愫。祠堂是清朝道光年间建起来的,大门的门框是整块的长条形巨石,两边的巨石上刻着“宗功丕著钟麟趾,祖泽长绵起凤毛”,上方是“张氏宗祠”四个楷体大字。老人越说声量越大,那时祭祖可是头等大事,春夏秋冬四时大祭,还有清明、上元、重阳、除夕等节祭。祭前要沐浴、斋戒,大家都要穿戴崭新,梳洗整齐,齐集祠堂大厅,为首主祭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只是到了三月春汛,河水上涨,资水的水位过了印记后,街上张姓、王姓、曾姓、袁姓、黄姓等几大姓氏都会聚拢起来。各族都要在本族中找一位主事公道、气宇轩昂、识水性、有文化的中年男子,一起商议毛板船下水的吉日良辰。除了王姓外,其他几姓都是本地的望族,之所以要把王姓主事者邀请来,是因为码头的地段是王姓祖辈所有,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敢强占的。其实,也是其他几家大姓之间力量的平衡。主祭者是张姓,主祭地点当然也是在张姓祠堂,各族会将整头的猪、牛、羊,还要一坛没有启封的米烧酒行祭礼以壮行。祭祀后,水手们就会仗着桃花汛驾着毛板船下益阳过洞庭达汉口。
我又一次来到琅瑭古镇,照例会去祠堂走走,祠堂门口三三两两坐着几个老者和小孩,见了我一脸漠然,倒是几个小孩,却不怕生人的样子,见我朝他们走来,也不走远,有三两个还和我说着话,问我是哪家的叔叔。我回答着小孩子的问话,旁边的几位老者也许听到,用眼神朝我看了过来,有位老者还长长地“哦”了一声。祠堂的门口又多了一块石碑,以前或许被遮蔽了,或许是什么时候被当成了垫脚石,又是什么时候被人发现了,重新立了起来。老者说,前几年,这里大搞开发,拆迁了几户人家,在人家的门槛下,露出了这块石头,开始大伙儿并没注意,倒是几个小孩,在石头上玩耍,发现石头上刻了字。村里有识字的人一看,说,不得了,是一块道光年间镌刻的“族规民约”,石碑上篆有“勒石永遵”四字,小字斑驳不清。老人说,刻的是族规。一旁的另一位老人,嘴里叼着长长的烟管,却是闭目养神,冬日慵懒的阳光照着他脸上深深浅浅的沟坎。我正准备掏出手机给老人拍照,旁边的老者赶忙朝我示意着,意思是不要我拍照。老者说:老人在资江河里浪打滔滚了几十年,是驾毛板船的金牌舵主,一生都没娶妻生子,性格暴躁。
祠堂左侧是戏台,现在很少有戏班来唱戏了。偶尔有小孩子吵着要去台子上玩耍的,大人也会把孩子轰下台。戏台屋顶的瓦片落了不少,许多的廊柱、椽子、横梁也被蛀得不成样了,走在上面,战战兢兢。倒是这个驾毛板船的金牌舵主,遇上好天气,便会爬上戏台,坐在竹椅子上,拿了二胡,低声地拉着,却并不会唱出腔调来。小孩听到二胡声,会安静地坐在戏台下面的地上,双手撑着下巴,眼珠子也是不会眨的。天窗漏下的光落在孩子们的头上或者肩上,间或有灰尘随着二胡声落了下来,蜘蛛在空中荡来荡去,忙着结网。
傍晚,我来到岸边。那几天,我一直一个人在古镇的街道上徘徊着。晚上,我睡在江边,房子枕江,我将头靠在临江的那头。那时正是三月桃花春汛的时候,江面隆隆巨响,有如捶在心坎上,让人不舒服。从上游倾泻而下的江水激荡着江岸的石头,还有无数的小溪,汇入资水上的入口,澎湃着。那声响回荡在我的每一寸肌肤之间,每一处罅隙,让我整个人也氤氲着江水的气息,神情恍惚,似乎在江水上奔波击打了一程,有了些许疲惫,心里却是满心的欢愉。
现在的琅瑭,已失去光泽的路面与斑驳的苔藓,深深镂刻着时光深处的繁华与荣耀。依然还是江边小镇,只是古风古貌荡然无存,临江的房子,都是钢筋红砖混凝土结构,能抵御洪水,却多了呆板呆滞,少了灵性沧桑。那几条老街,却是寒素的,不起眼了。水面上,没了毛板船,采沙船也没有了,清静了许多。难得的大太阳,黄金通透,阳光铺洒在水面,资水宛如暖流。想起史料上记载的因涨水而繁荣的沿江小镇,想起曾经的辉煌,想起那站在书院吟诗唱和的文人,想起为一家生计在滔滔江水中搏击的水手。他们是真正的水手,是真正的摆渡人,心中不免有几分酸楚。当所有的一切都融入了漫漫长河中,我们只能在对史料的细细梳理中重温那曾经的辉煌和寂寞,寻求当年的精神痕迹。
这里有望得见的山水,有可延续的历史记忆。它从历史的根脉突围而出,一路延伸到蓝田、宝庆,到潭州、京城。只是溪水潺声依旧,往事云烟俱散。上千年的岁月眼看要将它湮没,那曾被脚印踏平的石板深陷枯槁的荒草,浸淫了遥远的信息,这是一条曲折着、起伏着的古道,一块块的石板,敲响着后来者的情愫。我的目光沿着它的方向往北眺望,茫然的视线之中,两岸农舍鳞次栉比,有袅袅升腾着的炊烟。远处山峦静默而横,像一道道凝固的厚实屏风,只有苍翠在绵绵漫溢。
岸边有几棵大樟树,我在它巨大的树影下来回,根部裸露却又深深地扎入了泥土之中,在苍老的身姿与斑斑绿苔里,粗壮的枝干伸向天空,彰显着不屈的生命。我撞进一幢老宅,我望见原木的挑梁上,有高悬的匾额,在诉说着时间的味道。多少年前,谁曾在这里声情并茂,谁又曾在这里屏息凝神。谁又在这里指点江山,又暗藏着多少乾坤。我凭吊遗迹,看到老宅在风雨中飘摇。
每一个人都是匆匆过客,但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一部分永久地留在了这里。溪流改道,沿江建了水电站,资水失去了长远运输的功能。那曾经繁忙的码头残骸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长满荆棘而干涸的河道。
四
资水发源于夫夷,过古都梁,下邵阳,出茱萸滩,浩浩淼淼,进入新化县境。即便是刚刚经过乱石林立、壁如刀削的茱萸滩,也看不出激情澎湃的资江有些许的疲惫。在长达十里的石滩、九折十八湾的浪石滩之间,它仍像一匹不受羁绊的野马,自由、豪迈、放纵、尽情地流淌。
流近新化县城,它突然令人费解地安静下来站在河东的南台山上,就可以看到澄净、清澈的江水如一匹白练,静静地围绕着县城,自南而西,缓缓回旋,流成“新化八景”之一的“资江带水”。明朝嘉靖年间,一位特别喜欢游山玩水的新化地方官胡有恒为此写下了两句优美的诗:“溪烟浅渡绡纹薄江月深涵练影闲。”
这里是资水的中游,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老县城。河边成荫的柳树与河水交相辉映,仿佛是凝固在河岸边的秀色画卷,有“南台凝秀”的美誉。南台山上曾有晚清建造精巧典雅的楼阁庙宇,南台寺青烟缭绕,晨钟暮鼓,隐约有一种清寂的情怀。登上楼阁,可以远眺资水八景之一的“资江带水”,令人抚膺叹喟,流连忘返。清初湖南巡抚卢震在游历资江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资江带水》:“环流浩淼欲寻源曦丽云融映茝繁。波细自教轻绮毂,砂圆可使重玙璠。乘槎乍泛宁招隐,荒渡归来尽手援。不朽禹功随地见,一时疏凿更何言。”几百年来,交游南北的文人墨客,奔走天涯的仕宦、商客不知曾有多少为之倾心沉醉,站在资水之滨对之仰望遐思。
资水上毛板船运的空前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沿岸文化的发展。沿资水中游上下溯及百余里,先后有五十余家书院,这些书院大都创建于毛板船运的鼎盛时期。那是资水沿岸经济发展昌盛,南来北往的物资文化交流繁荣的黄金时期,为书院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县城的经济和文化的发达远胜于码头边的小集镇,而县城的文化建设是县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驱动力。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对它作出卓著贡献的则是县城的特殊人群。一种是主事的地方官员,他们兴办官学,又竭力义学。在古老的县城有千年前创办的濂溪书院,有七百多年前的文昌阁书院。资水岸边的梅溪书院,也就是后来颇负盛名的资江书院前身。陶澍、陈天华、陈润霖先后在此求学,邓显鹤、谢玉芝也先后在此做过山长。
还有一种是乡贤士绅创办的书院,如西团书院就在资水之滨,三百多年前由茶商捐资创建,1876年,西团士绅王子寿又出资重建。资水沿岸的书院,数百年来,一直都是人才培养的圣地。古时候,历届官员上任,都会斥资修缮书院,以博取读书人的好感。无论官宦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攒取政声,实现个人抱负,还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的光大,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才鼎盛。另一种是有长远眼光、不迷惑于利欲的乡绅平民,他们为提倡家乡文化不遗余力,乃至损折个人名利,设立义学与学社。几百年之后,资水岸边的书院,多有坍塌,已成废墟,一些建筑也消失在历史的沧桑之中。只是资水岸边的北塔,是读书人无法绕过的神圣高地。
两百多年前,一个叫黄庆凤的读书人站在资水岸边南台山慧龙庵的峭壁上,览眺脚下资水,只见澄江似练,回环如带。与许多的读书人一样,他对这条母亲河有着极深的感情,面对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他的心中也涌动着诗情和温润的感动。目光掠过宽阔的江面,停留在县北——那里曾有传说中的木阁,但现在阁已经坍塌。呈现在他眼中的只是一片荒凉的野草和芦苇。
秋风渐起,江水扬波,夕阳铺满江面,慧龙庵低沉的诵经声杂着清脆悠扬的钟磬声不时飘进耳中。在黄庆凤看来,建一座高塔——塔的尖顶像笔尖,而笔是古代读书人的吉祥物,这样,必定可以为这座城市的读书人带来好运气。1807 年,一份以黄庆凤居首的乡绅的倡议书呈进到了新化县令的案头,这份倡议书列举了雄辩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数据陈述了建塔的必要性,并且在结尾慷慨声明不需要官府出一分钱,全部费用由新化乡绅募集。知县被这份慷慨激昂的倡议书深深打动,他执着地从自己的养廉银里捐了五十两银子,并当即答应届时主持破土仪式。
1834 年冬,北塔落成,它矗立在资江河畔,塔高四十二米,共七层,八角形,角上嵌石舫,状如翘角,覆铁瓦,铸铜顶。塔正门上由当时的新化县令林培钧书手“北门锁钥”四字,大门是欧阳绍洛撰写的对联“正欲凭窗舒远目,直须循级上高楼”。登塔凭窗,远处群山叠翠,脚下资水流碧,县城古貌尽收眼底,历来名人登临,赋诗甚多。明参政胡有恒有登北塔绝顶诗:“江流去处空,一塔锁奔欲。势镇县之北,气雄资以东。举头疑日尽,长啸直天通。拟更探奇胜,西南首望崇。”北塔成了资水两岸无数先人士子和现代读书人与文化人的一个精神圣地,他们和我们都在这里流连、朗读,都抚摸着前人的手迹,向着自己的梦想出发。
依城而过的河流就像城市流淌的血脉,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孕育、生长、兴盛、传承。先民逐水而居,因为耕种、饮用、交通离不开水,一座城市有了水就仿佛是有了灵魂,格外灵动。历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机缘,使它在明清时期保持了数百年的繁荣?历史又给它开了什么样的玩笑,使它在最近一百年来默默无闻?在以后的时光里,历史是不是会再一次青睐于它,让它再一次为人们所熟知?
资水不声不息地流淌,淌过山谷、丛林、田园与村庄,蜿蜒数千里,一江两岸,田野挤田野,乡连乡,村接村,人家挨人家。青山是绿的,资水是绿的,我行走在资水两岸,望着这一片充满着希望的旷野,心中涌起阵阵暖意。双脚踩在湿润的田地里,闻着紫云英的芬芳,看渔民驾着小船在江中往来忙碌。沿江两岸是平阔的田畴,溪水活了,鸟雀在鸣唱,绿意层层荡漾,土地正滋生着更大的诱惑,在升腾着繁衍不息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