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塑造中的伊拉克问题(1991~2003)*
李睿恒
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失去对手,开始致力于打造自身的全球单极霸权地位。由于1990年入侵美国盟友科威特和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与美军直接交手并拒绝执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伊拉克被美国视为其在塑造单极霸权道路上的首个拦路者和挑战者,伊拉克也由此成为冷战后美国首要遏制的对象。在2003年诉诸战争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展现其单极霸权意志的试验场,集中践行了各类遏制与干涉手段。因此,在美国持续塑造和护持其霸权地位的后期过程中,伊拉克事实上构成了美国政府一个重要的经验参考与来源。在诸多遭到美国霸权主义遏制与干涉的国家案例中,从不乏伊拉克的“身影”。从反向的角度来看,遭到美国重点和全面遏制的伊拉克实际上处在了对抗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的前沿。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和局势演变,与美国的霸权塑造形成对冲,推动着伊斯兰世界、法国和俄罗斯等利益相关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以及美国的战略转向。在这个意义上,伊拉克一定程度上阻缓了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与方式,成为影响后冷战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美国单极霸权的试金石。据此,探析1991~2003年间伊拉克与美国单极霸权间的关系互动,对揭露、理解和预判美国遏制他国以图霸权的行径,以及认知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世界格局演变,依旧有着典型的代表性和观照当下的启示意义。
关于美国与伊拉克话题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从时间维度上看,既有研究重点覆盖了美国对伊拉克战略关注的五波高潮:(1)1955~1958年,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反对苏联链条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核心;(2)1980~1988年,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弥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失去盟友伊朗的替代;(3)1990~1991年,伊拉克是美国领导下的中东地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4)2003~2011年,伊拉克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平台;(5)2014~2016年,伊拉克是美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恐怖主义威胁的战场之一。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主要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两方面切入。(1)代表性成果有Peter L.Hahn,Missions Accomplish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 Since World War I,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Mohammed Shareef,The United States,Iraq and the Kurds:Shock,Awe and Afterma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汪波:《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韩志斌:《从盟友到仇敌:美国和萨达姆的伊拉克》,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3-27页;赵伟明、孙德刚:《美国准联盟战略初探——以伊拉克统一战线为例》,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第46-50页。然而,从政策互动的维度和伊拉克反向视角出发、将伊拉克问题集中置于美国单极霸权塑造的框架下来开展的研究(2)相关研究成果有Samuel Helfont,“Saddam and the Islamists:The Ba‘thist Regime’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Religion in Foreign Affairs,”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8,No.3,2014,pp.352-366; Samuel Helfont,“Authoritarianism Beyond Borders:The Iraqi Ba‘th Party as a Transnational Actor,”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72,No.2,2018,pp.229-245;钱雪梅:《试析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的外交政策》,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48-52页;韩志斌:《伊拉克教派冲突与美国的战略困境》,载《亚非纵横》2006年第3期,第32-37页。,即把伊拉克与美国关系从“国家对国家”提升至“国家对体系”维度的研究,还相对有限。从更深层次的学理视角分析,该进程本质上属于国际政治中弱国与强国间不对称互动/博弈的概念范畴,即双方客观上处于实力悬殊的不对称状态中,强国理应拥有更大的资源和实力来支配弱国,但现实的发展结果可能出现强国政策失效和弱国转向主动的局面。对此现象现有的阐释视角大致有三种:(1)强调传统权力和经济相互依赖形成的额外权力为核心的“外援论”,即弱国得到外部支持来对冲强国的优势;(2)强调机制和观念的视角,即强国受到国际机制限制和他国非对抗观念的影响,无法实现其对弱国的政策目标;(3)强调战略路线的视角,即弱国主观选择非常规战略,从而与强国的常规战略形成不对称优势。(3)不同视角的细节阐述与论证,参见杨少华:《弱者何以能胜?》,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35页;程晓勇:《弱国何以在不对称博弈中力量倍增——基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52-69页。而伊拉克的外交博弈为回答“弱国何以得利?”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上述三种视角的生动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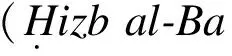
一、伊拉克问题与美国单极霸权进程的开启
要探析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塑造中的伊拉克问题,就必须厘清二者间内在的因果关系与互动逻辑。而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构成了我们提出与分析该问题的背景与基础。
第一,伊拉克引发的海湾危机让美国开启“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图借此抢夺科威特丰富的石油储备和抵消欠科威特的巨额债务,来消化两伊战争留下的恶果。一方面,八年的战争让伊拉克军队体量臃肿,达50万人的规模,伊拉克无力将他们重新吸纳进既有经济之中,军队内部变得焦躁不安。另一方面,伊拉克战时向外大量举债,且面临1986年后国际油价接连下跌,而战后伊拉克经济与社会亟待重建,伊拉克由此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4)[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张旭鹏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57-158页。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敢发起如此冒进的军事举动,原因在于其判定世界依旧处于两极格局之下,如若伊拉克未能赢得美国的支持,也最终能够由苏联来撑腰。同时,萨达姆认为美国大概率会默许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因为美国需要伊拉克继续来帮其遏制伊朗,并且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称美国无意介入阿拉伯人争端的暧昧表态,更加强化了萨达姆的这种判断,使其坚信美国会予以支持,尤其是当时伊拉克已将大量部队陈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境。(5)Eric Davis,Memories of State:Politics,Hist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Modern Iraq,Berkeley:Press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2005,p.227.
由此,海湾危机爆发。随即,美国于同日主导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并要求其立即且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在萨达姆拒绝执行该决议后,联合国于同年8月6日通过661号决议,宣布对伊拉克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禁运石油和武器,以及全面终止贸易和投资活动,直至走向11月29日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678号决议和1991年1月17日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原则上和行动上对美国的倡议予以了配合。这说明,萨达姆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1990年9月11日,即在海湾危机爆发一月有余,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简称“老布什”)在美国国会演说时指出:“这并非像萨达姆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在对抗伊拉克。事实上,是伊拉克在对抗世界。”(6)George Bush,“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and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September 11,1990,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the-persian-gulf-crisis-and-the-federal-budget,上网时间:2022年3月31日。此处所言称的“世界”,并非单纯地指代那些配合美国外交倡议的具体国家,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内涵。老布什总统随即在演说中宣布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的主张。而“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也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塑造其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单极世界秩序的前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冷战后美国的单极霸权塑造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根据对美国公布的总统档案统计,从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至1991年3月末,老布什总统至少42次提及“世界新秩序”的概念。(7)Eric A.Miller and Steve A.Yetiv,“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Worldview in Transi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1,No.1,2001,p.59.
据前美国驻沙特大使傅立民回忆,老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实际上是由他于1990年8月中旬首度提出的,其背景正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8)[美]傅立民:《美国在中东的厄运》,周琪、杨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傅立民评估,1989年苏东剧变可能意味着苏联“再也没有能力约束其加盟共和国的抱负”,因此伊拉克也可能会没有负担地占领科威特和武力威慑其他海湾小国,而1990年的海湾危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试图以‘强权就是公理’的断言来开启冷战后的世界秩序”。(9)同上,第4页。而傅立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应该通过国际社会以集体的形式扭转和惩罚如伊拉克这样具有侵略性的国家。这也奠定了后期老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论的基本论调。
第二,伊拉克引发的海湾危机为美国确立了打造全球单极领导权的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得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结论并非一厢情愿,因为其冷战对手苏联也近乎形成了类似的判断。一方面,和傅立民的评估一致,苏联对伊拉克的制衡力已经衰弱。根据俄罗斯前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回忆,在入侵科威特之前,萨达姆对于苏联没有做丝毫的沟通或暗示。(10)[俄]叶·普里马科夫:《揭秘中东的台前幕后(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初)》,李成滋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08页。另一方面,苏联对于冷战的行将结束也有着相关的预判。曾深度影响苏联中东外交决策的学者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就将海湾危机定义为“冷战结束后的首场重大国际危机”。(11)[俄]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唐志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9页。他指出,当时的苏联同样认为冷战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思想来处理国际关系,即“强调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呼吁在国际关系中输入道德理念,承认国际法无条件至上的地位等”。(12)同上,第313页。
这促成了苏联在海湾危机中对美国的配合,苏联首先应美国的要求冻结了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其次在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联合国678号决议上投赞成票,因为伊拉克最先反对了这种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但是,苏联很快意识到,与美国之间的高度合作,无法在实际的外交层面阻止“美国宣称它保留对‘什么是和平与稳定’的全部解释权”,并且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军事解决海湾危机。(13)同上。这意味着,美国“世界新秩序”背后单极霸权的内涵在海湾危机中逐渐清晰化。
第三,伊拉克引发的海湾危机是美国塑造单极霸权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转折点。
事实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剧变,已预示着冷战的终结。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相关学者早在1989年夏就提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历史的终结”。1990年1月,老布什总统也在其首篇《国情咨文》中指出,1989年的局势变化“标志着在世界事务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形成,美国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14)George Bush,“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January 31,1990,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ddress-before-joint-session-the-congress-the-state-the-union-2,上网时间:2022年4月1日。这表明,美国政学两界此时已经开始考虑打造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但冷战的行将终结只是在理论上为美国塑造“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潜在的条件,而直到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之后,美国才得以将“历史的终结”的政治理念付诸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实践。(15)Eric A.Miller and Steve A.Yetiv,“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Worldview in Transition,” p.57.
从“世界新秩序”诉诸的目标及手段依托来看,其经验来源无不与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直接且密切关联。在赢得海湾战争一周后一次面向美国两院的演讲中,老布什总统明确了这种联系。他称,“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出现在眼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十分真实的前景”。在1991年4月赴阿拉巴马州空军大学的演讲中,老布什则进一步表明,“我们必须利用‘沙漠风暴’的胜利,使这种世界新秩序出现新局面并得到发展势头”。(16)史洪江:《海湾战争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3期,第43页。
具体而言,美国“世界新秩序”的目标有三:一是防止区域冲突。因为伊拉克的入侵行为和苏联在海湾危机中的对美合作已表明,全球对抗不再是美国主要的安全挑战。二是防止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美国认为,伊拉克臃肿的军队和巨大的武器存量为其入侵科威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三是实现自由经济与民主化进程。在美国看来,如果不实现二者,产生类似于萨达姆入侵他国决策的国内环境就依旧存在。在中东地区,老布什总统也据此认为,美国在地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大挑战有四:对地区安全作共同安排;采取行动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创造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17)同上。
而在手段层面,老布什政府则在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相应增添了四点新的核心主张,以配合实现其“世界新秩序”:一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实力地位,特别是经济与军事实力;二是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三是强调盟友的团结;四是强化与苏联的“合作”。(18)张敏谦:《美国全球战略剖析——从“世界新秩序”到“克林顿主义”》,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13页。对老布什政府而言,这四点主张的有效性在海湾战争中均得到充分的验证。因此,无论是从客观上看,还是从美国的主观认定出发,伊拉克成为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首个挑战者,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对伊拉克取得的军事胜利,帮助美国扫除了心头的“越战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确立了其在冷战后塑造单极秩序的信心。海湾战争的经验也进一步演变为冷战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国防规划指导原则之一,即通过结成联盟“阻止敌对的非民主国家主导攸关我们利益的地区,并努力建立一个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国际环境”。(19)Dick Chenney,“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1990s:The 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January 1993,https://nsarchive2.gwu.edu/nukevault/ebb245/doc15.pdf,上网时间:2022年4月24日。但也应同时认识到,美国对伊拉克的惩戒固然有一定的正义性,却也无法掩盖背后美国谋霸权的本质动机,因为老布什政府将实力地位作为谋求“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手段已经表明美国的霸权诉求及其单极属性。正如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所指,“在集体努力不总是那么及时的时候”,可以单边派遣武力应对威胁;(20)Ibid.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也指出,“沙漠风暴行动”成为美国后期军事干涉的样板,尽管事实最终证明这是误导性的。(21)[美]理查德·哈斯:《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黄锦桂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8页。
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略认知在此过程中固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首先离不开伊拉克客观上对美国中东利益的重要性。总的来看,美国在中东的传统核心利益主要有四项:石油、支持以色列、保障阿拉伯盟友和维护核不扩散体系。(22)Kenneth M.Pollack,A Path Out of the Dese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Random House,2008,pp.37-82.而伊拉克作为中东的“大走廊”,在地区地缘政治中有着深远的辐射效应和导向作用。从地理交通上看,伊拉克向北可沟通欧洲和俄罗斯,向南可进入海湾与产油国;就地缘战略而言,拥有伊拉克,往西可策应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肥沃新月地带”,往东可对伊朗乃至中亚施加影响;在资源禀赋方面,丰富的石油储备和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拉克的战略地位。可以说,伊拉克本身及其局势的发展与美国中东利益的四大核心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美国控制伊拉克强烈冲动的背后,一方面是为了遏制德国和苏联这样的世界性霸权,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压埃及、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区性大国。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伊拉克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海湾危机的叠加效应下,伊拉克进一步转变为冷战后美国在中东谋求单极霸权的前沿。
综上,1989年“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和1991年冷战的结束,分别构成了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思想起源和历史开端,而伊拉克所引发的海湾危机则是衔接二者的重要环节。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伊拉克进入长期对峙,美国持续对伊拉克展开遏制与干涉,以改造伊拉克这样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伊拉克既是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由理念走向实践的转折点,也是美国展现单极霸权意志的起点与试验场。换言之,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自伊拉克而开启。
二、霸权塑造与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和干涉
探析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战略,有着超越伊拉克单一国别和中东地区的普遍意义,因为美国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政策经验,并在后期持续塑造和护持美国霸权地位时加以实践。例如,美国对伊拉克施以“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等指控并借此启动国际调查的做法,在对伊朗的长期遏制以及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进程中,都为美国政府频繁使用。再如,美国自1991年在伊拉克开启的周期性空袭行动,也构成了其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中发动连续性大规模轰炸的战场预演。1991~2003年间,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战略可以分别从战略目标、思路、对象与手段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 美国遏制伊拉克的战略目标
经老布什政府时期过渡,美国在比尔·克林顿政府时期放弃了冷战前在两伊间打造“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政策思路,转向打压两伊的“双重遏制”战略(Dual Containment),因为“均势”战略并未弱化两国并使其对美屈服。(23)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May 18,1993,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clinton-administrations-approach-middle-east,上网时间:2022年4月28日。在践行“双重遏制”战略的过程中,“虽然两伊同是对手,但1991年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爆发了海湾战争,美国与伊朗之间尚未发生过战争,因此美国与伊拉克的对立超过与伊朗的对立。”(24)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页。无论是从国际或地区层面来看,伊拉克在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政策的焦点和冲突的核心。相应地,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比对伊朗的更为全面、系统且集中。在伊拉克,美国意图实现以下三层战略目标。
第一,持续弱化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虽然“均势”战略被界定为政策失败,但该战略弱化伊拉克国力本身的作用与遏制战略并不冲突,也是实现遏制战略核心诉求的必要一环,即只有一个虚弱的伊拉克,才能够“把萨达姆·侯赛因关进笼子里”,并让局势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25)James A.Baker,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Revolution,War,and Peace,1989-1992,New York:Putnam’s,1995,p.441.从这个角度来看,遏制战略不全然是对“均势”战略的背离。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对“均势”战略的延续和调整。因为在以严厉的手段遏制伊拉克的同时,美国也担心过度打压伊拉克会促成伊朗的崛起。(26)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因此,“双重遏制”与“均势”战略事实上有着内在的逻辑延续性。
第二,推动萨达姆统治核心的更迭。尽管两伊同为美国遏制的对象,但在设定战略目标时,美国就明确表示要谋求萨达姆统治集团的更迭,而没有对伊朗表明类似的意图。(27)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45页。和老布什政府一致,克林顿政府一开始并不致力于推翻复兴党政权,而只是希望在其内部推翻萨达姆统治核心。(28)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鉴于复兴党对伊拉克社会有着严苛的管控,伊拉克海外反对派的国内基础薄弱。这意味着,美国若致力于更迭复兴党政权,就有必要在伊拉克做大量的军事部署及战后投入。同时,复兴党的倒台有可能引发权力真空、地区局势混乱和伊朗崛起,克林顿政府因此更希望伊拉克的变化来自于复兴党政权内部,而非实力有限的反对派。直至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人在国会中逐渐占据优势,新保守主义派别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以及美国策动政变尝试屡屡失败,克林顿政府才最终在1998年签署《解放伊拉克法案》(IraqLiberationAct),正式确立政权更迭为对伊拉克的政策选项。(29)Mohammed Shareef,The United States,Iraq and the Kurds:Shock,Awe and Aftermath,pp.12-13,15-16.
第三,打造外交亲美的伊拉克政权。弱化伊拉克或结束萨达姆的统治并非遏制战略的核心目标,因为萨达姆可能迫于虚弱转变对美政策。同理,萨达姆被推翻后的继任政权依旧可能坚持反美立场。对美国而言,只有伊拉克改变既有外交行为,遏制战略才有实际意义,而判定变化的标准则在于伊拉克是否愿意无条件全面遵循美国在联合国推动的相关决议,而并非伊拉克具体由谁来统治。正如克林顿指出,“如果他(萨达姆)想要和美国及联合国建立不一样的关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改变他的行为”(30)Bill Clinton,My Life,New York:Crown,2010,p.472.。“双重遏制”战略的设计者、美国助理国务卿马丁·因迪克也指明,美国在同意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之前,“不会满足于推翻萨达姆”,而是“希望任何(伊拉克)继任政府完全遵守所有联合国的决议”(31)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
上述三层目标内在密切关联且逐级递进,前一目标是通往后一目标的前提,后一目标则是实现前序目标的动力。其中,最为核心且不可轻易撼动的目标,是最终在伊拉克打造外交亲美的政权,因为任何折衷或妥协的方案都将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失败。尤其是同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及问题上不断确立自己霸权地位的“佳境”相比,伊拉克的反美立场变得更为显著并不容美国所接受。一方面,美国持续在中东成功践行着其强调盟友团结的理念,强化着与土耳其、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间的战略盟友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取得突破,推动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达成《奥斯陆协议》以及实现约旦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更重要的是,针对“双重遏制” 战略中的另一个子目标伊朗,在注意到1997年5月上台的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改善对美关系的意图和行动后,克林顿政府将对伊朗的政策从“全面遏制”调整为“区别遏制”。(32)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407页。这更加表明美国变更政策的标准是相对的而非客观的,是以相关国家对美霸权地位的认可程度及关系远近为依据。
(二) 美国遏制伊拉克的战略思路
要发挥遏制战略的效用,首当其冲地必须实现第一层战略目标,即持续弱化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基于下述的总结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为此实际上采取了一种“以分化促弱化”的战略思路。在此,“分化”绝非意味着对伊拉克的分裂,而是指在维护一个伊拉克的前提下从不同层面打造伊拉克碎片化的局面,牵制和分散萨达姆的精力,一方面让其无法举全国之力对美国的中东利益再度产生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多方消耗伊拉克国力,引发国内民众对萨达姆统治的不满,削弱其执政根基,从而迫使其承认美国的霸权来换取复兴党的政权存续。然而,这一思路有可能传递分裂信号并造成分裂后果,且容易引发土耳其等盟友的战略疑惧。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安东尼·兹尼在回应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提议通过秘密行动挑起伊拉克内部起义时就曾指出,如果该计划不能被小心执行,那很有可能出现“一个被削弱的、分裂的和混乱的伊拉克。”(33)Thomas Ricks,Fiasco: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New York:Penguin,2006,pp.22-23.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化思路下的遏制战略在某些环节有限的政策效力。具体来看,美国的分化思路可细化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执政合法性层面,从复兴党政权内部分化萨达姆派系和其他派系,并同时从外部分化萨达姆统治和伊拉克人民。
萨达姆1979年成为总统后,借两伊战争之机,清洗复兴党元老,排斥和疏远专业人士,将党政军权力垄断在家乡提克里特的族系手中。萨达姆的集权行为引起了复兴党内部诸多派系和官员的不安与不满,不少人移居海外,而大部分人则是迫于各种限制留在国内。(34)[伊拉克]穆罕默德·马邵特:《我曾在华盛顿做大使:我和萨达姆关于入侵科威特的故事》(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出版局2008年版,第21-22页。即使在提克里特族系内部,也有许多不满者密谋推翻他或者从伊拉克叛逃,如萨达姆女婿侯赛因·凯米勒(35)[伊拉克]瓦菲格·萨迈拉伊:《东部门户的废墟》(阿拉伯文),科威特:凯布斯书局1997年版,第395-396页。和前军情局局长瓦菲格·萨迈拉伊。(36)Hamid al-Bayati,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Iraqi Opposition to Sadda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p.64.正是在意识到萨达姆统治的局限性后,美国致力于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策划政变更迭萨达姆派系,而非推翻整个复兴党政权。因此,在秘密行动的实践中,美国实际上在复兴党政权内部区分了萨达姆派系及其反对派系,在全面否定前一派系统治合法性的同时,预留了给予其他派系合法性的空间。
同时,在公开表态上,美国政府刻意使用“萨达姆政权”“巴格达独裁政权”和“伊拉克人民”等字眼,将萨达姆统治和伊拉克人民相分离,制造对立情绪,否认萨达姆的执政合法性。例如,因迪克在阐释遏制伊拉克政策时就曾表述:“应该清楚的是,我们的分歧不是针对伊拉克人民。他们的困境完全是巴格达独裁政权的责任。”(37)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然而,在大众认知与政策宣传的层次上,萨达姆派系与作为整体的复兴党政权很难被相互区分和剥离。
第二,身份认同层面,分化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分化阿拉伯人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群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意识到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伊拉克阿拉伯国家身份间的张力,并于1972~1975年间发起“隐蔽行动”,积极向库尔德武装提供秘密支持,以服务其抗苏的冷战之需。而在1979年失去伊朗盟友后,美国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冲击和萨达姆向伊朗发动战争的影响,其内部逐步反向建立起伊拉克复兴党依托于逊尼派行教派主义统治的错误认知。在海湾战争后,美国认为只有支持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等非逊尼派力量,才能动摇萨达姆的统治。(38)Lisa Blaydes,State of Repression: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p.316.这种认知一度延续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并对美国设计的战后重建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9)Randa Slim,“Iraq:A Conflict over State Identity and Ownership,” Middle East Institute,May 15,2019,pp.4-5.同时,从实际力量评估来看,库尔德运动和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运动构成了伊拉克不稳定性的两大来源,是中央政府长期重点打压的对象。因为前者是伊拉克最大的分离主义威胁,后者对复兴党带来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双重挑战,二者共同组成反对派里的中坚力量。(40)Sherko Kirmanj,Identity and Nation in Iraq,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13,p.162.通过支持这两股力量,美国可以有效削弱两个群体对复兴党的政治认同,尽管这也在人为地造成强化二者各自民族主义与教派主义认同的副作用,乃至动摇他们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有悖于美国担心伊拉克分裂的政策底线。
第三,地理空间层面,分化禁飞区与伊拉克其他地区。美国1991~1992年先后在伊拉克北纬36度以北和31度以南设立两个禁飞区,任何飞入其中的伊拉克飞机都会成为联军打击的目标。禁飞区的设立,一方面有着人道保护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群体的功能,维护土耳其和科威特的边境安全,但另一方面更在于以此侵蚀伊拉克主权,挑战复兴党政权的权威,制造伊拉克内部各地区间的差异化局面,庇护反对派,触发伊拉克内乱。(41)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第387页。由此来看,以禁飞区在地域上分化伊拉克,也是对上述两层面的延伸。这既从主权上削弱着复兴党政权的合法性,也为次国家身份认同的抬头提供了实际的地理空间。
第四,中东地区层面,分化伊拉克与阿拉伯世界。海湾战争爆发前,萨达姆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相联系,坚持只有以色列首先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军,伊拉克才会从科威特撤离,并且在战争期间向以色列本土发射飞毛腿导弹。这为萨达姆在阿拉伯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也门和人口一半以上为巴勒斯坦裔的约旦都在危机中间选择支持伊拉克,约旦也是地区唯一没有配合美国议程的亲美国家。(42)Beverley Milton-Edwards,“A Temporary Alliance with the Crown:The Islamic Response in Jordan,” in James Piscatori,ed.,Islamic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Gulf Crisis,Chicago: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th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1991,pp.93-98.因此,要做到全面孤立伊拉克,就有必要淡化海湾危机和巴以问题间的联动性,防止萨达姆继续就此发力。为此,美国的海湾盟友一方面惩罚性地切断对巴解组织的经济支持,驱逐巴勒斯坦、约旦和也门劳工,锐减其外汇收入;另一方面,美国推进阿以和平进程,并在克林顿期间形成“西促和谈”的政策,试图把控巴以问题话语权,压缩伊拉克在地区的生存空间。(43)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第328、351-358页。
第五,国际舞台层面,分化伊拉克国内和海外群体。美国遏制伊拉克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通过与伊拉克海外反对派和侨民密切接触,支持其组织化活动,提升其国际地位。但这绝非意味着美国对反对派合法性的认可,美国支持和整合反对派的初衷不是要以其推翻和接替复兴党政权,而是为了打造一个“宣传性的组织”,以一个联合的反对派形象孤立和施压伊拉克。(44)Mohammed Shareef,The United States,Iraq and the Kurds:Shock,Awe and Aftermath,p.14.此外,鉴于反对派内部构成多元与背景复杂,美国担心不与一个整合后的反对派组织对接,可能会释放分裂伊拉克的信号,引发盟友的战略疑虑,如有着库尔德问题关切的土耳其和什叶派问题关切的沙特。(45)Hamid al-Bayati,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Iraqi Opposition to Saddam,p.42.
总之,美国由内及外分化伊拉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弱化伊拉克的政策效果。分化是实现弱化的操作理念,弱化则是转变伊拉克外交政策、使其承认美国霸权地位的前提。分化与弱化构成了美国遏制伊拉克战略思路的一体两面。
(三) 美国遏制伊拉克的战略对象和手段
根据“以分化促弱化”的战略思路,美国又将整体性的伊拉克细分为四个子对象,即复兴党政权、北部库尔德禁飞区、海外反对派与侨民以及国内群体和反对派,分别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秘密和舆论六个层面入手,践行遏制与干涉战略。
第一,针对复兴党政权,美国采取“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封锁、隐蔽行动、舆论污名化”的全方位干涉手段。
虽然美国试图区分复兴党政权和伊拉克人民,但在实操环节,美国无法将作为执政党的复兴党与其统治之下的民众相分离。即使美国刻意强调政权内部萨达姆派系与其反对派系的差异,也只能在特定层面施以有限的影响,作为整体的复兴党政权依旧构成了美国最核心的遏制对象。基于该限制,在政治层面,美国政府无法实现既要宣布结束萨达姆派系的统治,同时又无需确立政权更迭的政策目标。直到提出《解放伊拉克法案》后,政权更迭才正式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在外交层面,美国继续对伊拉克进行孤立,利用联合国等平台来表达遏制伊拉克的意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这也成为伊拉克战争的口实之一。在经济层面,美国对伊拉克加大经济制裁,重点对武器贸易和石油出口施以严厉的禁运措施。受此影响,1992~1999年间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有7%,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46)Adeed Dawisha,Iraq:A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227.在军事层面,美国强化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武器销售。目前美国中央司令部空军指挥部驻地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Al-Udeid )和前沿总部驻地萨伊利亚军营(As Sayliyah)就建立于该时期。同时,美国在南北禁飞区开展“南部监察行动”和“北部监察行动”,即国际联军出动战机空袭禁飞区内的军事设施,并在美国认为伊拉克具有威胁行为之时将空袭范围扩大到伊拉克的非禁飞区域。(47)Peter L.Hahn,Missions Accomplish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 Since World War I,pp.120-121.据统计,1991~2001年间,美国共对伊拉克禁飞区出动战机达3.4万架次。(48)Phillip Gibbons,“U.S.No-Fly Zones in Iraq:To What End?”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July 1,2002,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us-no-fly-zones-iraq-what-end,上网时间:2022年5月11日。美国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从内部削弱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外部对伊拉克施加军事封锁和威慑。在秘密层面,美国支持复兴党政权内部其他派系发动政变。1991年2月美伊断交后,美国失去驻伊人员,只能依靠海外反对派或侨民搜集相关信息,建立人脉。(49)[美]约翰·尼克松:《审判萨达姆》,钟鹰翔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9年版,第26-27页。例如,1996年6月的政变就是由海外反对派伊亚德·阿莱维与伊拉克退休军官穆罕默德·沙赫瓦尼策划的,这项行动企图以共和国卫队发动政变,但最终被伊拉克情报部门挫败。(50)[伊拉克]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莱维:《占领伊拉克: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出版局2009年版,第75-76页;[伊拉克]哈桑·拉提夫·祖贝迪:《伊拉克政党百科》(阿拉伯文),贝鲁特:阿里夫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72页。在舆论层面,美国给伊拉克打上多个负面标签,妖魔化其国际形象。1991~2003年间,伊拉克被依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无赖国家”“令人忧虑的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的行列,而对美国而言,这些国家最为根本的特点就是长期坚定的反美立场。(51)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39页。此外,美国还发动相关国际组织谴责伊拉克的“无赖”行径。其中,人权观察组织1993年发布报告控诉复兴党1988年化武袭击库尔德人。但此前,美国政府回避该问题,在1988年国会就此提案制裁伊拉克时,遭到国务院反驳和总统里根的否决。(52)冷雪梅:《“伊拉克门”研究:美国武装萨达姆政策解密(1980-1994)》,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75页。
第二,针对北部库尔德禁飞区,美国采取“引导政治分裂、经济资助、外交准认、军事训练、秘密庇护、舆论宣传”的干涉手段。
尽管南北禁飞区并立,但惮于支持南部禁飞区可能导致伊朗势力上升,加之库尔德运动在反对派中组织化和武装实力较强,美国更加重视北部禁飞区。据此,政治上,美国默许库尔德人的自治举动,默认1992年7月成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KRG)。经济上,美国通过联合国向库区提供资金和人道主义物资,改善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外交上,美国派专职官员与库区政府开展“准外交”,斡旋调解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以下简称“库民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以下简称“库爱盟”)间的军事冲突,维护局势稳定。(53)Michael M.Gunter,“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Iraqi Kurd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20,No.3,1997,pp.13-14;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London:I.B.Tauris,1996,p.388.美国给予库区如此的重视,是为了在秘密层面将其打造为庇护整合反对派、联系政变的重要基地。(54)Mohammed Shareef,The United States,Iraq and the Kurds:Shock,Awe and Aftermath,pp.150-152.军事上,美国起初并未提供过多实质性支持,但在1998年确立政权更迭的目标后,美国开始往库区派遣军情人员,武装和训练反对派。(55)Quil Lawrence,Invisible Nation:How the Kurds’ Quest for Statehood Is Shaping Iraq and the Middle East,New York:Walker Publishing Company,2008,p.238.舆论上,美国则配合妖魔化伊拉克的政策,突出库尔德人受害者的形象,积极宣传非萨达姆治下库区良好的生存状况,塑造美国“解放者”的形象。
第三,针对海外反对派与侨民,美国采取“政治整合、经济资助、外交承认、军事训练、舆论造势”的干涉手段。
代表性的组织有伊拉克民族和谐组织(INA)、伊拉克国民大会(INC)、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SCIRI)、库民党和库爱盟。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美国为反对派在库区或其他国家提供政治庇护,为反对萨达姆的政治活动提供空间,并指派专职官员对接相关工作。1992年的维也纳大会、萨拉赫丁大会和1999年的纽约大会,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商讨“倒萨”和“后萨达姆”时代的政治安排等,美国高级外交官弗兰克·里奇昂多则长期处理与这些组织的关系。(56)[伊拉克]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莱维:《占领伊拉克: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阿拉伯文),第98-99页。在经济层面,提供资金支持反对派海外活动和力量整合,特别在《解放伊拉克法案》颁布后,美国加大投入,向反对派拨款9,700万美元。(57)Peter L.Hahn,Missions Accomplish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 Since World War I,pp.127-131.在军事层面,1998年后美国将反对派集中在库区进行军事训练。在秘密层面,美国通过海外反对派和侨民搜集关于伊拉克的情报,并联系人脉发动政变。在舆论层面,美国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借反对派和海外群体之口揭露复兴党统治的“无赖”行径。
第四,针对国内群体和反对派,美国采取“政治声援、秘密策动”的有限干涉手段。
如前所述,由于断交后美国失去驻地人员,加之库尔德内战期间(1994~1998)库民党为打击库爱盟在1996年8月引伊拉克军队进入库区助战,导致1,500余名反对派被逮捕,(58)Michael M.Gunter,“The Five Stag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Kurds,” Insight Turkey,Vol.13,No.2,2011,p.99; David McDowall,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p.388.美国无从与伊拉克国内反对派建立联系,甚至在2003年入侵之前,对于日后在伊拉克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地下反对派萨德尔运动(Sadrist Movement),美国也知之甚少。(59)[美]约翰·尼克松:《审判萨达姆》,第27页。一方面,美国只能在言辞上号召伊拉克民众推翻萨达姆,另一方面则从秘密层面依靠海外反对派尝试对伊拉克国内进行思想与人员渗透,策划暗杀并刺激内部起义。(60)Samuel Helfont,“Authoritarianism Beyond Borders:The Iraqi Ba‘th Party as a Transnational Actor,” p.242.
总体来看,1991~2003年间,无论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伊拉克并非唯一遭到美国遏制的国家。但相较而言,美国对伊拉克的遏制要比其他国家都更为系统性、全方位和长期化。复兴党倒台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全球战略关注开始向地区其他国家或域外转移,但其在遏制伊拉克过程中践行的思路、手段和经验,在此后美国遏制他国的战略设计中持续产生影响。然而,美国最终发动战争的结果证明了遏制战略的局限性,除却美国自身的国内因素外,伊拉克外交博弈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度影响了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塑造。
三、伊拉克外交博弈及其对美霸权塑造的影响
美国遏制战略的对应面,是伊拉克旨在解除制裁和禁运的外交博弈。对伊拉克而言,这无外乎在于维持复兴党政权的统治地位。但客观上看,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实际上阻缓并对冲了冷战后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因为从美国的角度出发,这一进程的基础和起点正是其通过海湾危机形成的国际共识,而伊拉克在拒绝接受美国推动的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寻求外交突破,无疑是在动摇这种根基。在这个意义上,伊拉克与美国及相关国家的外交互动,事实上突破了“伊拉克国家对他国”的传统双边维度,而是有着“伊拉克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不对称博弈新内涵。
然而,必须指明的是,在伊拉克为应对美国的全方位遏制形成相关外交策略之前,萨达姆及其统治核心深知,最为快速且全面解决危机的关键,莫过于转变美国对伊拉克的态度。但是,萨达姆担心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结束伊始就向美国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会给外界一种伊拉克迫于压力而服软的印象,从而削弱复兴党政权的合法性,并且老布什政府也无意改变其政策。(61)B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Doc.Nos.3187-0001-484-487,February 10,1993.萨达姆将希望寄托于1992年新一届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之上,因为他的竞选纲领聚焦于美国内政和经济议题,而非老布什重点着墨的外交功绩。1992年11月克林顿胜选后,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向萨达姆表示,克林顿政府可能“不会对我们(伊拉克)采取特别的立场”,因此建议伊拉克“不应该对克林顿展现消极的立场”。(62)Kevin M.Woods,David Palkki and Mark Stout,The Saddam Tapes:The Inner Workings of a Tyrant’s Regime,1978-200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41.萨达姆本人对阿齐兹的建议予以肯定,并判断克林顿的获胜恰恰证明了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政策的失败。(63)Ibid.,p.42.在1993年1月克林顿正式就任前,萨达姆在高层内部讨论时进一步表态:“我相信在此人(克林顿)任内,会有所变化。”(64)Ibid.,p.45.这不仅表明萨达姆将美国政府换届视为伊拉克摆脱危机的机遇,更说明萨达姆及其政权在主观上其实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为此,萨达姆下令开展了一系列在美海外行动,来游说候任总统克林顿及其团队。(65)Samuel Helfont,Iraq Against the World:Saddam,America,and the Post-Cold War Or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pp.113-122.然而,“双重遏制”战略的出台最终宣告了此一行动的失败,也同时表明萨达姆再次对后冷战时代美国政治的演变研判失误。
(一) 伊拉克对冲美国霸权塑造的外交博弈
为突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遏制,作为弱国一方的伊拉克所开展的外交博弈,本质上是采取了非常规式的“迂回”战略路线,无法像美国一样形成某种全面且细分的应对战略。具体来看,伊拉克主要动用了观念和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利益两个要素,分别对以伊斯兰世界为核心的非西方阵营以及西方阵营展开外交突围。
首先,在观念要素层面,伊拉克借伊斯兰话语团结以伊斯兰世界为核心的非西方阵营。
基于复兴党左翼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伊拉克长期以来打造了一套“反帝国主义和反西方、积极团结非西方阵营”的对外叙事,并在中东的政治环境中将该叙事具化为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和反对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66)Ofra Bengio,Saddam’s Word:Political Discourse in Iraq,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7-139.虽然海湾危机爆发后萨达姆通过议题联动海湾危机和巴以问题在阿拉伯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但迫于西方压力很多阿拉伯国家政府均逐步采取了支持科威特的立场,尤其是萨达姆核心关切的与伊拉克相邻的阿拉伯国家。(67)[伊拉克]瓦菲格·萨迈拉伊:《东部门户的废墟》(阿拉伯文),第455页。因为伊拉克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实际上已让复兴党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话语在官方层面丧失了合法性和外交整合的功能。为弥补这一缺陷,伊拉克开始把视野转向伊斯兰世界,在继续强调阿以对立的基础上,将这套反帝反西方的外交话语向反异教徒的维度扩展。
1990年8月,萨达姆开始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对沙特、科威特及其西方发动圣战,因为“当他们将穆斯林的麦加”“置于外国人的长矛之下时,他们更挑战了真主。”(68)Samuel Helfont,“Saddam and the Islamists:The Ba‘thist Regime’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Religion in Foreign Affairs,” p.359.更重要的是,萨达姆将美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相联系,把美国驻军阿拉伯半岛和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相类比,从而实现了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斯兰话语间的衔接。(69)James Piscatori,“Religion and Realpolitik,” in James Piscatori,ed.,Islamic Fundamen ̄tali ̄sms and the Gulf Crisis,pp.1-27.换言之,萨达姆所要传递的信号是,美国在穆斯林领土上的驻军已使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对立退居其次,穆斯林与异教徒的对立才是地区矛盾的核心。因此,地区国家应该支持而非反对伊拉克。
萨达姆的策略成功调动了穆斯林大众最为朴素的宗教情感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情,进一步赢得了地区民众对伊拉克的支持。有鉴于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伊拉克在外交层面持续强化对伊斯兰话语的运用,并重点以伊斯兰民间会议组织(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zation)为活动的组织依托,通过动员穆斯林大众自下而上施加政治压力,以弱化或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该会议组织于1987年在巴格达成立,受沙特政府的资金支持,其初衷为对抗伊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海湾危机爆发后,沙特与伊拉克外交关系恶化,伊斯兰民间会议组织分裂为沙特和伊拉克各自主导的两个竞争性架构。
其中,伊拉克的邻国约旦是这一策略成功实践的典型案例。面对伊拉克对相邻小国的入侵,约旦事实上持反对立场,但在萨达姆强调海湾危机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共通性后,占约旦人口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裔都支持伊拉克。例如,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谴责了伊拉克,但很快就转变了立场。(70)Conflict Records Research Center Doc.No.SH-GMID-D-000-957,November 2,1990.迫于国内民意压力,约旦是中东地区唯一没有配合美国议程的亲美国家,以及唯一没有公开封锁伊拉克的邻国。由此,约旦成为了伊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唯一稳定的“出口”。约伊边境、红海口岸亚喀巴和约旦皇家航空实际上充当了伊拉克走向世界的陆海空通道,两国间大量的走私贸易为萨达姆的权力维系提供了基本保障。(71)安维华、钱雪梅:《美国与“大中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为保持约旦“生命线”的功能,复兴党还致力于加强密切与约旦的社会联系,如向约旦媒体捐款,安排约旦相关行业协会代表赴伊访问,观察伊因制裁而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以让约旦民间持续对政府施压。(72)B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Doc.No.3203-0003-0421,January 13,1992.此外,伊拉克也将相同的策略复制到与邻国土耳其和伊朗的边境走私贸易中,但其规模与公开程度则无法与约旦相提并论。不过此处应该明晰的是,伊拉克的外交策略固然奏效,但与邻国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经济依赖等刚性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利益要素层面,伊拉克以其人道主义危机和他国石油经济刚需为主要抓手,争取西方阵营的同情与支持。
虽然团结伊斯兰世界为伊拉克换来了相应的道义支持和“生命线”,但要有效解除制裁,就有必要撬动大国关系,特别是对配合美国议程的西方阵营,因为从调解效力和减缓制裁打击的程度来看,这些国家都比非西方阵营更具直接影响美国的能力。为此,伊拉克采取了“以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他国石油刚需为抓手,以非官方力量为途径”的策略。其中,在对俄罗斯和法国的外交行动上,伊拉克实现了相对突出的成效。
在对俄关系上,虽然苏联配合美国谴责和制裁伊拉克出乎萨达姆的预判,(73)Mohammed Shareef,The United States,Iraq and the Kurds:Shock,Awe and Aftermath,p.11.但海湾战争前苏联两次调停的努力和冷战思维惯性的影响,萨达姆在冷战后仍把俄罗斯视为帮助伊拉克平衡美国、突破制裁的首要对象。(74)Charles Tripp,“Iraq,” in Yezid Sayigh and Avi Shlaim,eds.,The Cold War and the Middle E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15.1991年苏联解体后,伊拉克最初依旧尝试通过官方途径来开展工作,多次向俄罗斯议会发出访问伊拉克的邀请,并保持两国间部长级别官员的频繁联系,但沟通多为电话形式,且在互访安排上未能得到任何积极实质的回应。伊拉克驻俄大使在1993年发回巴格达的报告中认为,俄罗斯的决策“受到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游说集团的影响”。(75)B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Doc.Nos.033-4-2-0663-0665,January 1993.
在官方途径受阻的情况下,伊拉克于1992年后期与俄反对派接触,发出访伊邀请,以使其了解伊拉克因制裁而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据伊拉克驻俄大使的报告,访问回国后的俄反对派在议会内外频繁游说,成功施压俄罗斯于1992年末派遣外交代表团访伊。大使认为,这标志着俄对伊政策一次积极的转变。(76)Ibid.随着1993年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获得多数票,俄罗斯内部关于伊拉克政策的分歧日益加剧。例如,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同年8月与伊拉克签署了一份经贸科技合作协议,但外交部两天后宣布该协议无效。(77)Ofra Bengio,“Jumhurriyat al-‘Iraq,” in Ami Aylon,ed.,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urvey,1993,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399.除反对派力量外,俄罗斯的商业集团也向政府施压,要求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为缓解商界形成的压力,俄罗斯政府于1994年同意与伊拉克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讨论双边的经济合作。(78)Conflict Records Research Center Doc.No.SH-IISX-D-000-148,1996.
与法国的关系则是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例子。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联军中美国坚定的支持者,改善和它的关系,对伊拉克有着更为重大的外交意义。和在俄罗斯的策略一致,伊拉克同法国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向它们宣传伊拉克恶化的人权状况,以此要求解除制裁。同时,伊拉克更加注重从经贸领域影响法国的政策。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法国对伊拉克的石油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并且法国曾是伊拉克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伊拉克欠法国近50亿美元的外债,但石油贸易和还款的前提是结束伊拉克的制裁状态。为此,1993年起伊拉克与多家法国石油公司磋商,讨论禁运撤销后合作开发伊拉克南部的油田。伊拉克还于1994年重启伊拉克法国友好协会,以此向法国政府施压。(79)David Styan,France and Iraq:Oil,Arms and French Policy Making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I.B.Tauris,2006,pp.183-185.
1995年雅克·希拉克选任法国总统后,伊拉克谋求改变或至少松动法国的政策。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宣布对法国企业提供商业特惠,这使众多相关的法国企业都希望尽快结束制裁,同伊拉克开展合作。希拉克也认为,要求伊拉克全面遵循联合国决议的制裁方法已被证明失败,国际社会应该让伊拉克渐进地接受相关决议,并据此渐进地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1996年4月,希拉克公开表态称,国际社会应该欢迎伊拉克的回归。(80)Ofra Bengio,“Jumhurriyat al-‘Iraq,” in Ami Aylon,ed.,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urvey,1996,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p.352.同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等国企业和商业代表团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访问伊拉克,争相签订了制裁后的重建工程及石油开发合同。
(二) 伊拉克外交博弈对美国霸权塑造的影响
从政策结果来看,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并未实现全面解除制裁的核心目标,但其产生的外交效应,实际上阻碍了美国实现其对伊拉克设定的三个维度的战略目标的实施进度,并进而对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塑造和护持产生了三方面影响。
第一,伊拉克的外交博弈维持了萨达姆与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地位。
美国遏制伊拉克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打造一个最终屈服于美国霸权、外交上亲美的伊拉克政权,因此持续弱化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和推动萨达姆统治核心的更迭,不过是达成此目标的必要条件和阶段性目标。其中,持续弱化萨达姆的统治则是最为基本的前提。然而,美国的遏制手段虽然弱化了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但并未弱化萨达姆统治本身。事实上,借助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石油国有化后巨额的石油财富,复兴党在伊拉克打造了一套食利经济体制,国民对于国家高福利社会保障和政府公职分配有着高度的依赖。而1991年后国际制裁的宏观环境,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伊拉克国家作为绝对且唯一资源分配者的地位,民众对国家的依赖加剧。萨达姆的权力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增强。(81)详见Lisa Blaydes,“Rebuilding the Ba‘thist State:Party,Tribe,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Iraq,1991-1996,” Comparative Politics,2020,pp.1-23。当然,实现这一局面的前提,是复兴党政府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获得经济资源。这与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密切相关。
此外,伊拉克长期宣扬国内持续恶化的民生状况和强调他国石油等经济刚需的策略,最终促成了多国政府与商界人士推动的“石油换粮食”(Oil for Food)计划。从1996年5月开始,伊拉克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95年4月的986号决议,出售定额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以换购食品和药物等人道主义物资。据统计,自该计划执行至2003年战争前,伊拉克与外国公司签订了5,000余份合同,金额达70亿美元。(82)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第380-381页。伊拉克前反对派、前财政部部长阿里·阿莱维认为,“石油换粮食”计划虽然缓解了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也赋予了萨达姆政权某种国际合法性,改善了萨达姆在国内的统治形象,美国的遏制政策因此面临两难的境地。(83)[伊拉克]阿里·阿卜杜·艾米尔·阿莱维:《占领伊拉克:战争之利与和平之损》(阿拉伯文),第92页。由此来看,在伊拉克外交博弈的影响下,美国未能实现三层目标中的基础目标,更遑论推促伊拉克转变外交政策、承认美国的霸权。
第二,伊拉克的外交博弈一定程度上分化了美国单极霸权所追求的国际共识。
美国在海湾危机中引以为傲之处,正是其在短期内就惩戒伊拉克凝聚的国际共识,这成为美国确立信心建立单极秩序的基础。如果说这种国际共识的破裂始于约旦、巴解组织等非西方国家或组织,那么随着伊拉克外交博弈的深化,这一裂缝逐渐拓展至美国核心依托的西方阵营内部。除重点关注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的民间组织和经济利益受损的企业外,相关国家政界也对美国的单极霸权行为日益感到不满,从而不再愿意配合美国借遏制伊拉克以图霸权的议程。
1996年9月的“沙漠袭击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rike)就是其中突出的例证。在中东层面,土耳其、沙特等地区盟友都惮于行动会伤及伊拉克平民,拒绝批准美国使用其空军基地,美国最终只能替之以其陈列于波斯湾的航空母舰来发起攻击,这极大地缩短了联军空袭伊拉克的纵深。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行动倡议还遭到了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多国的谴责。海湾危机爆发后,法国一直是美国空袭伊拉克行动积极的支持者,但在“沙漠袭击行动”中,法国部队仅有限地参与其中,并于1996年末彻底退出“北部监察行动”。1998年末,法国进一步宣布退出“南部监察行动”。同时,俄罗斯也以否决票相威胁,拒绝美国借联合国合法化空袭行动的倡议。此外,“石油换粮食”计划的推行同样是美国领导的国际共识破裂的表现。
第三,伊拉克的外交博弈为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误判埋下伏笔,进而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护持构成持续性挑战。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表明,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只是阻缓了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进程和改变了其演变图景,并未从根本上挑战美国塑造单极霸权的能力。但是,这却在客观上导致美国对伊拉克问题出现重大战略误判,进而为其单极霸权的护持埋下长期的隐患。
如前所述,由于萨达姆在两伊战争后不断强化对国内什叶派群体和库尔德人的打压,并持续将权力垄断在提克里特族系手中,美国将此误读为萨达姆在施行逊尼派主导的教派主义统治。而事实上,萨达姆的此番决策是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现实考量,而非原生的教派—族群身份,只是恰好提克里特族系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萨达姆的统治因此给外界以一种教派属性的错觉。随着海湾危机后伊拉克对伊斯兰话语的不断强调及对美国异教徒身份的批判,美国对伊拉克的错误知觉被进一步强化。(84)李福泉:《海湾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05-107页。尤其失去伊拉克在地人员后,美国研判局势的信息来源近乎只有长期旅居海外的伊拉克反对派。受自身什叶派伊斯兰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对萨达姆严酷打压国内两个群体和强调伊斯兰团结外交话语的政策观察,反对派坚定地认为萨达姆是一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伊拉克的社会构成已经按教派—族群而划线。(85)Zaid al-Ali,The Struggle for Iraq’s Future:How Corruption,Incompetence and Sectarian ̄ism Have Undermined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p.63-65.然而,据一份1996年的档案显示,萨达姆认为伊斯兰主义者不过是一群“两面派”,但这并不妨碍伊拉克对宗教力量的利用。(86)Ba‘th Regional Command Collection Doc.Nos.2982-0000-0595-0628,March 3,1996.可见,反对派及其深度影响的美国政界对于伊拉克的认知与现实情况出现了严重脱节。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宣布发动“反恐战争”。小布什政府错误地认为策动伊斯兰话语反对西方的萨达姆与“9·11”事件主谋“基地”组织有联系,并且有可能向后者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87)[英]尤金·罗根:《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46页。这一战略误判直接引导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错误认知还对其所设计的战后重建计划产生深远影响。根据反对派的建议,美国简单地按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来划分伊拉克社会,将复兴党统治等同于逊尼派统治,从而仓促下令解散伊拉克军队,并在执行战后“去复兴党化”(de-Ba‘thification)的过程中将该政策异化和泛化为一场“去逊尼派化”(de-Sunnification)的政治清洗运动,迫害和边缘化大量逊尼派无辜群体,转而扶植什叶派与库尔德力量,人为且制度化地在伊拉克各社会文化群体间制造政治对立,引发伊拉克战后严重的教派与族群冲突。(88)章远:《后“伊斯兰国”时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宗教困境——兼论西方推行世俗政治秩序的危险》,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第72页。
曾重拳打压“基地”组织的复兴党官员,因其原生的逊尼派穆斯林身份被美军错误地划定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并拘押。在牢狱环境的激化下,美国针对逊尼派无差别的集体性惩罚思路发挥出政治整合与身份建构的功能,推促曾势不两立的二者出于仇美情绪和抵御“去逊尼派化”的报复而权宜合作,构成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坚实基础。(89)李睿恒:《伊拉克战后去极端化的实践及挑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6期,第46-48页。在此意义上,极端主义的泛滥并非伊拉克战争的原因,而是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结果。而如若没有美国在伊拉克认知上出现的重大战略误判,难以想象伊朗得以顺利拓展自身西翼战略空间和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后期“伊斯兰国”形成的恐怖主义威胁,进而挑战和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护持。溯其本源,这与伊拉克动用伊斯兰话语及其观念因素突围周边封锁的外交博弈策略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
从更深层次来看,伊拉克外交博弈得以奏效的原因,不在于伊拉克本身外交能力的强大,而在于其提前顺应了冷战后世界秩序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从而赢得相关国家在特定议题上的有限配合。以法国对伊政策的调整为例,总统希拉克所秉持的戴高乐主义政治理念、法国外交中国际机制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原则(90)汪波:《法国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政策分析》,载《法国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1-149页。,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伊拉克实际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志在打造的单极秩序和国际社会渴望构建的多极秩序两大趋势间博弈的焦点。不把握这一宏观背景,就无从准确定位伊拉克的外交博弈得以反向影响美国霸权进程的内在逻辑。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冒险举动,显然背离了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决定了伊拉克外交博弈的有限性,即相关国家虽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霸权行径,但同样也不乐见于萨达姆侵略性的外交行为。因此,美国既未能如愿实现遏制伊拉克的战略诉求,伊拉克也无法全面破解美国的外交围堵,美国遏制伊拉克的战略和伊拉克的外交博弈面临着“双输”的困境。
四、结语
伊拉克绝非冷战后美国以谋单极霸权而遏制的唯一和最后一个对象,但它却是冷战后美国遏制的首个对象,也是手段最为全面、时间跨度最长和精力最为集中的代表性对象。在美国持续塑造和护持其霸权地位的后期过程中,伊拉克构成了美国决策者遏制与干涉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参考和经验来源。在后期美国对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域内外国家的干涉和打压中,这都有着显著的表达,伊拉克案例也因此能普遍折射出冷战后美国遏制他国的四组规律性特点:一是长期化与周期化。当美国将伊拉克体制性地认定为威胁后,便开始对其施以长期性的遏制,但在如总统换届、中期选举、“9·11”恐怖袭击等不同事件和时间节点下,对不同手段的运用又呈现出高潮与低谷的周期性特征。二是全面化与细分化。一方面,美国制定综合战略,来全方位围堵伊拉克,但另一方面,美国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将抽象的伊拉克概念细化为具体的子对象,并根据各自的特点在不同层面做政策细分。三是国际化与联盟化。从海湾危机开始,美国着重借用联合国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平台来赋权其遏制伊拉克的行动,以尽可能地凝聚国际共识;而在实操环节或无法获得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则拉拢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等盟友,共同遏制伊拉克。四是立法化与议题化。美国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和设定全球性议题的方式来制度化与规范化反伊认知,以此凝聚国内与国际社会的共识,达到遏制伊拉克的战略目的,如颁布《解放伊拉克法案》和开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
从伊拉克外交博弈来看,其得以在有限程度上打破遏制和封锁,维护复兴党统治地位,也得益于四点:一是对伊拉克海外群体的有效动员。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的组织网络不限于一国之内,而是跨越整个中东地区乃至辐射海外各大洲。这一国际架构及其吸引的海外侨民,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在封锁状态下对外开展行动的重要依托。无论是尝试联系和游说相关国家,还是帮助伊拉克开展走私贸易、缓解经济压力,海外群体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重点开展对非官方力量的外交工作。在传统外交受阻的情况下,伊拉克将外交重点转向目标国家的反对派、行业协会、商界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图自下而上地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三是对相关国家刚需与核心诉求的积极回应。相关国家政策松动与变化的基础,不在于对萨达姆侵略行为的接受,而是伊拉克在外交中对石油贸易、巴勒斯坦问题、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的强调,实际回应了相关国刚性经济需求与核心价值关切,从而换来其在特定领域和议题上的政策松动。四是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带来的外交空间。归根结底,前述三层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冷战后中东域内外多国希冀打造的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所给予的外交空间,因为无论是在冷战下的两极格局中或在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内,伊拉克外交策略发力和相关国家因应的空间都将极为有限。由此来看,伊拉克案例实际上融合了解释不对称博弈中弱国何以得利的三种理论视角,地区性与国际性的观念因素、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利益刚需、弱国非常规化的战略选择,以及国际政治中权力使用的机制等要素,都叠床架屋地从不同层次及周期在伊拉克外交突围中发挥其作用,进而对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塑造产生了短期和长远的影响。
综上,在冷战后美国打造单极霸权的发展进程中,伊拉克问题事实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是映射该进程的一面棱镜,是揭露、理解和预判冷战后美国遏制他国以图霸权的行径所必不可少的例证。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干预、价值输出、权力扩张、凌驾自身国内政治因素于国际政治之上、避免承担国际责任等单极霸权行为的特点(91)刘丰:《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21-22页。,都能在1991~2003年的伊拉克找到最初的身影。另一方面,伊拉克外交博弈得以在制裁体系下取得有限的突破并影响冷战后世界秩序演变的历史经验,反映了美国霸权主义有限的合法性与道义性及其政策困境。这也同时表明,拱卫与强化各国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刚性需求的相互依赖,以及维护和扩展世界多极化的外交空间或称打造世界格局里广泛的中间地带,是国际社会应对美国霸权主义和避免世界秩序滑向单极化或两极化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