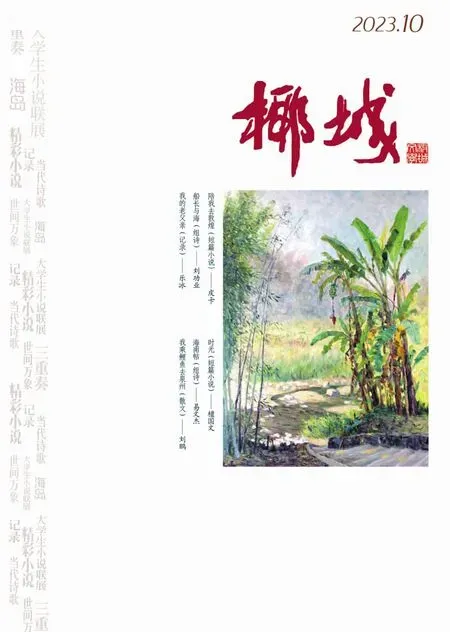恋父情结下的喑哑情殇(评论)
◎石凌
小说是语言营造的时间迷宫。小说要写出人在不可抗拒的时间面前的渺小感和失败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对逝去的时间镜像般的追忆。纳博科夫是一位擅长运用“各种复现、镜像、戏仿和错位来展现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处境和孤独的内心”的作家(评论家张鹤语)。让纳博科夫称誉世界的小说《洛丽塔》表面上描述的是12岁女孩洛丽塔对老男人亨伯特的魅惑,实际上,表现的是人物内心的孤独感与道德感的尖锐冲突。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从男性视角诠释了老男人的恋处情结,小说把四十岁的亨伯特面对稚嫩、单纯、无邪的女孩洛丽塔时无法自持的心理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因为触及人性最隐秘的内核,触碰社会伦理的各个层面,引发热议,成为社会学家研究人性的素材之一。作为20世纪备受瞩目的先锋小说作家,纳博科夫深深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
皮卡的小说《陪我去敦煌》是一篇由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生发而出,并在叙述格调上模仿《洛丽塔》的小说。与《洛丽塔》不同的是,《陪我去敦煌》不是站在老男人的角度去克隆一个纳博科夫式的“洛丽塔”,而是站在“洛丽塔”的角度去刻画一个有着恋父情结的女子对一个酷似父亲的老男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暗恋心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腻入微的、多维度的描写,堪称心理小说的典范。小说开篇,女主带着《洛丽塔》去敦煌。旅途中形单影只的人容易沉缅于往事的追忆。《洛丽塔》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一声声呼唤如同一颗颗石子投入主人公的心湖,勾起了主人公相似的情感记忆。“洛丽塔”可以置换成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包括文中的许玉成或蒲海棠。当主人公把“洛丽塔”换成了自己的名字“蒲海棠”时,心湖上立即产生了奇异的情感涟漪,暗藏的情愫随着奔驰的列车暗流汹涌。作品在多重意识流中撕开了蒲海棠与许玉成之间长达十年的情感纠葛与情路暗殇。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身体铭记事件,文学“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陪我去敦煌》就是一篇讲述身体如何铭记事件,事件如何摧毁身体的小说。恋父情结或恋母情结是根植于婴幼身体里的两枚深刻的印记,如果婴幼儿时期得到了父母充分的爱抚,孩子在成年以后就能顺当处理自己与社会、与他人,尤其是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一旦来自双亲的关爱中途退场,婴幼儿的心田得不到充沛的爱,就会患上情感饥渴症。《陪我去敦煌》中的主人公蒲海棠正是这种情感饥渴症患者,父亲留在她童年记忆的印象短促而美好——“凉白的花海里,我恍惚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他就站在那些树后,我仿佛走进了那个初春。喝了点酒的父亲,摇晃着身子,我踩着他歪斜的影子,慢吞吞跟在他身后……”这幅画面如此美好,以至于在父亲抛弃她和母亲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她对父亲生发出来的感情都是爱,而不是恨。一个因父爱缺失长期处于情感沙漠地带的女孩,潜意识里一直在找一个酷似父亲的男人能给她安全感。这种无处安放的情感在遇到老师许玉成以后有了着落。十九岁那年,正在上大学的蒲海棠遇见客座教授许玉成以后,彻底沦陷。人到中年的许玉成温文儒雅,沉稳内敛,声音富有磁性。蒲海棠与郑敏两个女孩同时恋上了他们的老师。蒲海棠对老师许玉成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渴望缺失的父爱得到补偿的情感。在主人公的意识流中,每当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她就会求助于许玉成。甚至在她一个人产下前夫的儿子时,也要把老师许玉成叫到身边。这种情感依赖更多的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儿对父亲的依恋。然而,依赖一旦产生,就是像毒药一样上瘾。许玉成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依赖,且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病,他的婚姻千疮百孔,他的心灵需要慰藉。于是,他们就从师生关系变成为精神恋人。小说以深情的笔调追忆了两人之间每次见面的细节,以及藏匿在心灵深处的欲望与道德感的冲突。这种因向往而悸动,因绝望而忧伤的情感被作者拿捏得恰到好处。老师毕竟是老师,何况老师已有家室,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渴望这种单纯的少女恋情浇灌自己已经板结的心田,但他很少会冲动到为了学生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家庭与事业。作为过来人,许玉成深谙师生相处之道,他很好地利用了女学生对自己的崇拜与好感,把蒲海棠变成他手里一枚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为自己的事业大厦添砖加瓦,但没有主动僭越师生情谊与上下级关系。所以,整整十年,许玉成活在蒲海棠的梦境里,左右她结婚、生子、离异、独自踏上旅途……《陪你去敦煌》中,多重意识流纵横交错,把一个童年丧父的女孩在成年以后被一个中年男人无形中操控情感,欲罢不能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许玉成不仅影响了蒲海棠择偶、生子,也将影响着她往后余生的情感抉择。她在发现丈夫出轨后毅然离婚,却因为梦见许玉成——她梦想中的亨伯特,便决然生下了前夫的儿子。一个童年缺失了父爱的女孩长大后,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把这种残缺的爱的渴望遗传给下一代。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皮卡的《陪我去敦煌》,可研究之处很多。老男人的恋处情结与小女孩的恋父情结一样,都是一种需要一生去治愈,却很难痊愈的心理隐疾。
一个人从父亲的阴影下走出来才能算一个真正长大了的人。蒲海棠怀着十二分的崇拜与好感接近许玉成,一次次触碰伦理与道德的底线,一点点深入到许玉成的生活肌理,发现那个令她无比心动的人在光鲜的外表下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软肋,正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过程中,那个原本高大无比的形象一点点地坍塌了——许玉成对名利的渴慕,对蒲海棠的利用……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富有心机的俗世男子而已。偶像倒塌了,人还得活下去。心无所依的蒲海棠决定去敦煌寻找梦想。敦煌是心灵的故乡,她渴望与许玉成一起外出旅行,共同修复他们的情感。最终,只有她独自带着儿子上路。与其说她是去寻找梦想,毋宁说她是去结束这段喑哑的情殇。
《陪我去敦煌》开篇显现出作者戏仿纳博科夫的色彩,后半部分则是向茨威格致敬。无论是故事的内容还是叙述的语调,《陪我去敦煌》与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有异曲同工之处。现代小说史上,茨威格与纳博科夫一样,是心理小说的高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刻画了女主人公因单恋无法自拔,一次次投入一个中年男作家的怀抱,最终使自己伤痕累累的故事。《陪你去敦煌》中的蒲海棠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主人公都是从少女时代就被老男人吸引的女孩。所不同者,蒲海棠对许玉成的渴望更多的是一种父爱补偿期待——渴望被关爱被呵护,许玉成大概是明白这种期待的,所以,在他们长达十年的交往中,他在很多次可以僭越的关键时刻刹住了车,留住了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主人公对男作家则是单纯的崇拜与暗恋,男作家也把她的投怀送抱看作理所当然。正因为如此,蒲海棠虽然一次次渴望着那个在少女时代就驻进她内心的老男人关切的问候与关注的眼神,但这种没有被僭越的感情已经成为她心田里的活水泉,在她每一次陷入情感困顿的时候都能给她以力量,而不是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主人公一样单方面地赴进烈火,直至把自己燃烧殆尽。
“艺术并不是对真实与真理的追求,而只是一幅心灵镜像的呈现;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并不是对旧世界的复活,而只是对旧世界文化表象的拼贴与整合……”(戴锦华评张爱玲语) 《陪你去敦煌》正是这样一篇拼贴逝水年华,呈现心灵镜像的小说。
——《洛丽塔》的成长小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