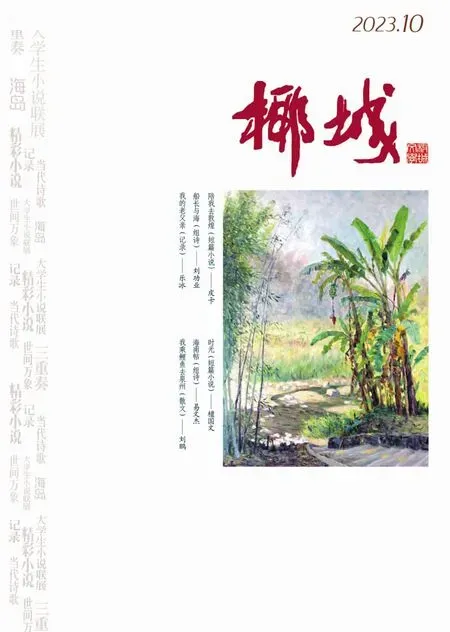不肯凋谢的青春之梦(评论)
◎远人
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读到皮卡这篇《陪我去敦煌》的短篇小说时,都会理所当然地联想到纳博科夫的巅峰名著《洛丽塔》。作者也无意绕开纳博科夫的小说,甚至在小说第一自然段就极为巧妙地将《洛丽塔》的开头移植了过去,而且,皮卡的主人公对自己爱慕对象的内心称呼也是《洛丽塔》的男主人公名字亨伯特。从这里看,似乎作者强行要求读者在面对自己的小说时想起纳博科夫的名著。
在纳博科夫笔下,亨伯特是对少女洛丽塔展开勾引的中年男人,亨伯特对洛丽塔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望,小说主人公的畸形心理和小说突破伦理界限的主题使得《洛丽塔》成为当时的禁书。它给今天的小说启示是,一部原本应属低俗范围的作品如何会成为令人惊叹的艺术珍品的?其理由当然不仅仅是纳博科夫的叙事技巧,更多的是对一种想象力的独特挖掘和一种对创造力的独特呈现。所以写什么重要,怎么写重要,最终写出了什么更加重要。《洛丽塔》对人的情感解剖相比寻常,甚至打开了人的某种被压抑的欲望。不陌生的是,人的多数欲望通常被压抑,也通常需要出口,亨伯特找到的出口未必是值得赞赏的出口,但一定是某种人性的出口。现代小说要做到的,也就是表达某种压抑的情感和情感需要的出口。
皮卡的这个短篇同样是对一种压抑的情感而做出的宣泄表达。与纳博科夫一致的是,皮卡的手法始终是艺术的,也是激烈的。皮卡笔下虽然有《洛丽塔》似的情感,但其手法却完全颠倒了过来。《洛丽塔》的情感描写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表现,皮卡的这个短篇则是女主人公蒲海棠对男主人公许玉成不顾一切的爱恋。在蒲海棠那里,将自己视为疯狂爱上亨伯特的洛丽塔,又将许玉成视为亨伯特——许玉成的年纪比蒲海棠大得多,这使皮卡主动将纳博科夫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自己笔下进行了换位。
近年来,时常能看到中国某位诗人作家将自己的某件作品称为是向西方某位文学大师进行的“致敬”之作。对此说法,我始终不以为然,写作的另一名称是创作,只有创作力平庸的作家才会为自己的模仿行为找一层自我解脱的遮羞布,好像只要宣称在“致敬”了,就有理由去明目张胆地模仿甚至复制一样。
读完皮卡的小说,我倒是觉得,皮卡没有丝毫向《洛丽塔》“致敬”之嫌——他用了《洛丽塔》内的称呼不假,但不等于他就在刻意模仿该小说。它说明的只是,纳博科夫的小说在中国年轻一代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地位。在皮卡笔下,蒲海棠意识到自己对许玉成的情感疯狂,二人的年龄悬殊让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恋。当然,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只对亨伯特有过短暂的依恋,在皮卡这里,蒲海棠反而对许玉成有了极不寻常的情感疯狂——这其实是青春期最无法回避的情感。哪怕蒲海棠后来有过婚姻、有过婚姻的破碎、有过孩子的牵绊,但都没有成为她对许玉成情感褪色和冷静的理由。
所以,皮卡这个短篇有激烈的表达和疯狂的色泽。如果没有激烈和疯狂,青春就很难说是青春,尤其蒲海棠是被文学浸淫过的女人,作者还赋予了她作家的身份。天生的感性和文学带来的幻想成为她性格的核心。这不是洛丽塔的性格,更不是亨伯特的性格,而是作为一种青春象征的蒲海棠的性格。小说的目的是塑造性格,皮卡塑造了蒲海棠,也就是塑造了一种性格。
就青春本身的性格来说,无疑是渴望。所以蒲海棠渴望许玉成的爱,哪怕不能得到,哪怕许玉成的成熟和年龄带来的生活阅历使他能做到蒲海棠在说有孩子需要照顾的理由后还是舍弃孩子赶来和他约会,也并不表示蒲海棠只具有一种单纯的爱恋冲动。在蒲海棠那里,不肯放弃的是自己青春的梦想,她将这一梦想内化成去敦煌的渴望和行为,甚至希望许玉成也最终能出现在敦煌,和她一起实现自己的青春之梦。
作为男主人公的许玉成又有什么性格呢?作者没有像交代蒲海棠那样直接。至少,皮卡的第一人称行文保证了蒲海棠性格的完整,尤其作者采用的蒙太奇手法,让读者眼花缭乱地看到蒲海棠的种种行为,这就使蒲海棠在读者面前有极为清晰的性格表现。即使她遭遇过好友的背叛,遭遇过丈夫的出轨,遭遇过许玉成的欲擒故纵,但读者能看到她不放弃青春梦想的性格核心;在刻画许玉成时,作者始终将许玉成搁置在“你”的位置,也使整篇小说如同蒲海棠在给许玉成写信一样显出某种程度上的飘忽——这一手法倒是让我想起茨威格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过,在茨威格笔下,“陌生女人”的卑微和那位身为作家的接信人的游戏人生的态度过于一目了然。皮卡比茨威格高明的是,他没有将许玉成界定在某个具体的身份之上,即使许玉成后来成为戏台上的角色,也不能证明许玉成从头至尾就是一个演员。所以许玉成的飘忽反而成为这个短篇的亮点。在面对蒲海棠的情感中,许玉成的态度始终充满暧昧。恰恰是这点,成为了小说最具张力的部分,尤其蒲海棠终于只身到了敦煌。这也是许玉成曾经对她的许诺。
当读者读到蒲海棠到了敦煌时,更意外的感受出现了。蒲海棠仅仅是因为许玉成的许诺而采取前往敦煌的行动吗?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许玉成的许诺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蒲海棠的敦煌之行更多是为了自己梦想的实现,甚至,蒲海棠不甘心放弃许玉成,也绝不是许玉成开始事业有成,而是蒲海棠将其看成了自己青春梦想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梦想中有许玉成的到来,如果有许玉成将她称为“洛丽塔”的话,蒲海棠会觉得,她实现的将是自己历经生活磨难后人生的完美。
谁都希望自己的青春完美,但蒲海棠遭遇的背叛与伤害更符合青春的本质。蒲海棠经历再多,受到的伤害再多,也不肯放弃青春时的梦想,也就无异于说明蒲海棠性格中的坚韧。这恰恰是值得今天的读者应给予重视的方面,也是这个短篇写得成功的方面。
很巧,在我动手准备写这篇评论前,正与《四川文学》副主编卓慧在微信上谈事。我顺便告诉她,我刚刚读完一位四川作家皮卡的小说。我问卓慧是不是认识他?卓慧说曾在《四川文学》上发表过皮卡的小说,还问我他这篇小说写得如何?我的回答是,我很喜欢皮卡的这篇小说,他的裁剪工夫和对人物的刻画手法,都让我觉得是一篇极为优秀的小说。
——《洛丽塔》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论《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