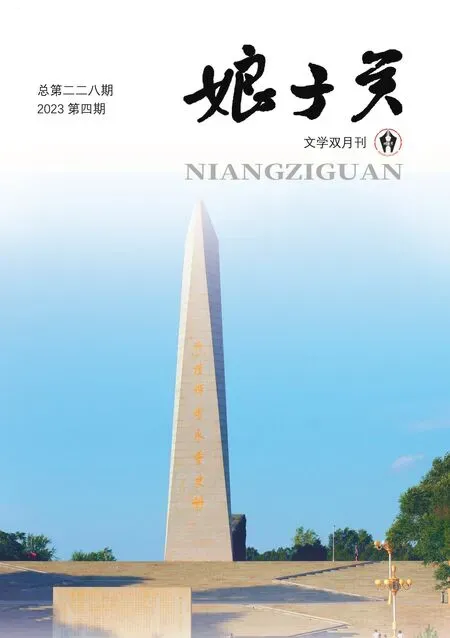隐匿和重现
◇指尖
我怀疑六轴沟因六轴子这种植物果实得名,但时隔多年,已没有机会向管村人求证了。
作为一个外乡人,很难打入管村紧密有致的秩序当中,更莫说它包裹隐秘的内部。虽然我常常出现在村里,偶尔,被一两个同龄女孩相邀,去往她们低矮的居屋,坐在黑漆炕沿边上。她们炙热而羡慕的目光让人心神不宁。她们和她们的母亲不停地向我打听村庄以外的山河,我满含羞愧,但不能明说,自己其实跟她们一样,也是生活在另一个封闭小村里的人,而管村,是我对外乡的初次体验。在尴尬叠着尴尬的气氛中,我端着一张涨红的脸,慌张无力地在不停的挽留声中告别。从她们家低矮破败的街门出来,站在坑坑洼洼的村路上,春天的风沙像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我。当然,其后的时间中,我对这个村庄逐渐熟悉。开始认识坐在街门前晒日头的老人,他的诨号和他的家人,学走路的婴孩和他的母亲。
晚上,管村的少年和青年们,都会爬上那道漫长的土坡,挤到林场会议室看电视。他们或站或坐在后面,即便最前面那条长椅子上空无一人。乃至倘若没有林场工人去触碰电视机开关,他们也会永远悄没声息地等在那里,似乎千年万年也不是问题。我在无数次从村庄往返村庄的过程中,渐渐变得大胆且左顾右盼。我跟同屋女伴已经有胆量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我们认识了售票的女孩,而她恰巧也是管村人。这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一个村庄而连接成牢固的关系,乃至我们的聊天内容,会触及绣花图案,或者有没有对象这种女伴间私密的话题。我们去县城,逛书店,看电影,靠在百货大楼的楼梯上,来来往往的顾客从我们身边走过,直到午后,坐在候车室里,乱糟糟的声音淹没我们的好奇。不到两年时间,我就对面前这个不是故乡的村庄,渐渐生出厌弃和逃离之心。六轴沟里,是否有种植物果实叫六轴子,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林场的二十多间平房,以及阔大的场院,院墙,其实均属六轴沟范围内的建筑物。但六轴沟的建筑物远不止这些。春天,管村的人,会扛着䦆头和铁镐,沿着崎岖蜿蜒的沟渠,进入六轴沟,他们在这里,将一块又一块青色的石头,用红泥牢牢夯住,堆砌成一个他们眼中满意的圆形墓地。通常墓地砌好后,他们家的老人会拄着拐杖,跌跌撞撞亲自前来视察一番。当他们从林场铁门前经过,那个最老的人,脸上总是带着一股满足而急迫的神情。
我们从未因跟那些死去的管村灵魂为邻而恐惧害怕过。尽管在冬天,会有老人往生,人们抬着黑棺,吹着唢呐将那个僵冷的躯体安顿到六轴沟,留下一些花花绿绿的冥币和小旗子,在风中凌乱。对于远方他乡的陌生幽灵,我们总是因无知无解而忽略它的存在,乃至亦有极大的耐心,跟他们和平相处。就像书里涉及鬼怪的故事,总是发生在旅途或他乡一样,似乎他乡不止增加旅人的阅历,还会加速他的成长速度。猫头鹰整夜整夜在六轴沟嘶叫,清冷的月色下,我们冒着春天的寒意起夜,踩在白寡寡的场院,犹如白云中穿行般自如。
推开林场的角门,就可以看见六轴沟的成片田地,一半紧靠东山,一半延伸出去,那些长条田地上,缀满起起伏伏的坟包,在白天阳光下,并不会有鬼魅之气。差不多每天下午,我跟女伴都会跨过陡峭的沟渠,向对面裹着万丈尘灰和泥垢的东山爬去。山腰处,有一片林场工人新植的油松,这些幼小的生命,作为试验品,不得不远离熟悉可爱的故乡,无奈定居于此,艰难存活。我们就坐在它们中间,像它们一样,瞭望对面同样枯败的山峰,远处飘移的山岚,看月亮缓慢升起来,太阳沉沉落下去,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村庄。
透山水沿着颠簸不平的沟渠流出,在一些低洼平坦处停下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池沼。夏天,蜻蜓喜欢穿过茂盛的荆棘和蒿草,向林场的院墙飞去,但我们从未在院子里遇见过蜻蜓。倒是有蝴蝶和蜜蜂,在场院的木瓜树,山楂树,李子树间忽隐忽现。有次贪玩,两个人向山上爬,一直爬到了山顶。山顶上,是一人高的蒿草和荆棘,虽然夏日万物郁郁葱葱,但它们并未欣欣向荣,而是蜗结勾缠一处,仿佛一群绝望中拥抱在一起的人,延延展展,覆盖了整个山顶,散发出浓郁的死亡气息。我们惊恐地转身下山,却早已找不到来时小路,从攀援着凸出山崖的大石头,从断崖处战战兢兢地下来,穿荆棘,被刺伤,女伴还崴了脚,在这种慌不择路之下,那片熟悉的油松林竟然也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听到流水声,视线中隐约出现场部的半面墙,我们的心才安稳下来。
天已昏暗,拍打掉身上的灰尘,胡乱将衣襟和裤腿上的鬼圪针扯掉,探身在水里洗去手上的灰垢,再抬头,两个人便被眼前迷人的景象唬住了。那是几十乃至近百只萤火虫啊,它们的身体上上下下浮动,小尾巴上的火,在这种有序的浮动中,竟构成一个完美的菱形图网,这张网,一会扯向东,一会扯向西,每一次移动,都会带起一小股微风,轻轻掀起我鬓角的碎发。但奇怪的是,无论扯到东南西北任何方向,最终,它们都会缩回到原有的位置上。好像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根指挥棒,一架定位仪,或者一块吸铁石。
青蛙急吼吼的叫声喊醒我们,夜已降临,该回去了。我们顶着半弯月明爬出沟渠,穿过窄条玉米地,回到角门那儿时,脑子里,还被那萤火虫网罩得死死的。忍不住回头,面前除去黑黢黢的东山,空无一物。猫头鹰适时叫起来。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蹲在六轴沟晦暗的池沼边,看见了碎石和淤泥,青苔和绿藻,蝌蚪和孑孓。我似乎在等待萤火虫和蜻蜓,好像跟它们在某个机缘里有过一个约定,但又不确定,我就那样百无聊赖地等,花喜鹊从头顶飞过去了,树叶也飞过,飞过去的似乎还有一些东西,沙土,石子,花瓣,但它们均让人心烦意乱,定睛时,人蹲在故乡的温河边,河底晃荡着细石和流沙,一些烂树枝和破抹布滞留其间,我试图将那些树枝和抹布扯开,让它们随水流走。但这肯定是件特别艰难的事,因为我挑起一块抹布,下面还有一块,拔开一些树枝,与之重叠的还有一些,恍惚它们下面有个涨白的物体。随着我的拨弄,水越来越细,六轴沟凸凹不平、布满锋利岩层的池沼里,石头和淤泥中间,树枝和破布下,挤出一张平展展的人脸……
这个梦让我迷惑好久。还查过析梦的书,反复求证过,但没结果。
女伴说,“难保那些居住在六轴沟的鬼魂,不以另外的面目呈现在梦境之中。但也或许,那天我们回来太晚,惊扰了它们的平静生活,作为警告,托梦给你?”
“那为什么没托梦给你。”
我不敢问。
照例月底放假。回家那天,林凤刚淹死在温河里。
温河是一条温暖而亲切的河流,虽然在夏秋之际洪水泛滥,淹没过田地,河坝和道路,以及河滩的树木和黑渣坡,我们也在温河里见过从上游冲下来的木头,农具,家畜,但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有人跌落溺死其中的记录。
母亲说,“林凤的死,是意外。”
没有一种死亡不是意外的,即便有人提前做好了准备。我的祖母在三十多岁就置办了绸缎,用了五年时间,做好她的锦袄,绣裙,缎面绣花鞋,黑绸帽。这些跟寻常穿着完全不同材质和式样的衣服,是为死亡那场盛典准备的。之后她用四十多个夏天来掀翻它们,晾晒它们,怕虫蛀,怕水浸,怕火烧,提心吊胆,从初时的欣喜,渐渐转为平淡,乃至失望。她预备好的四十九,六十三岁,均平安度过后,她彻底消失了对时间的信赖,并渐渐放松对死亡的警惕,在人前,坦称自己是老不死的。她年老时,要求我母亲给她购买一件水红的衬衣,一条粉花的秋裤,这些在她年月里从未出现的衣物,让她眼热。她为死亡做了四十多年准备,当萦绕她等待死亡登门的局促感渐渐淡去时,却毫无征兆地死去了,这种意外,不止令活着的人,即便死者本人也还是无法招架的。
林凤这个名字是我们村最好听的名字,好像树林里嬉戏的一只美丽小鸟,它会伫立于树尖婉转歌唱,也会徜徉于树下草地,姿态优雅,带着一股出尘的气韵。当然,他本人的形象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他低矮瘦小,脸色青白,沉默寡言,体弱多病,在农村,这样的人,基本就是废物。他的身影很少出现在村里任何地方,就像一张雪白透明的粉连纸。他家有一扇石磨,偶尔祖母带我去他家磨面,他的弟弟妹妹出出进进,但我从未见过他。林凤作为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从未预备应对死亡的来临,亦无体面而笃定的规划死亡过程,在他死后,家人没有替他购置新衣。尸体经过流水的浸泡,已经肿胀不堪,没有一件衣服可以成功地将他安放进去,家人用一张毯子盖在了他身上,又请人来念经超度,安点一番。如此敷衍潦草,将他送过温河,寄埋在远离祖坟的地方。据说他是下地时,遇见了河头。这也是模棱两可的猜测。他临终前那段时间里,被队里安排在饲养处打下手,那么,他下地的机会基本是零,这个理由就不成立。还有种说法,是为了抢救一匹骡子,不小心掉在水里淹死。但他抢救了哪匹骡子,也是个谜。
我一直觉得,他或许是自己把自己淹死的,想让自己的身体随流水消亡,化成游鱼,沙子或者无论任何一种河底生物。但随着假期结束,我离开村庄,渐渐把这个事弃之脑后。
我们这些进场不到一年的工人,最大不过二十,最小的我仅仅十六,毫无工作和社会经验,并不被师傅们看好,他们之所以隐忍不发,耐着性子容忍我们的幼稚轻浮,是因我们中有他们的子弟。那些年轻点的师傅,因孩子尚未长大,无法享受这样的优待,便会阴阳怪气地跟我们说话。
我跟一个女孩,被安排到食堂帮厨;另一个女孩比我们大几岁,去帮忙养貂。每次,当我把盛满的饭碗,递出那个狭小的窗口时,就会联想到那些水貂们的眼神,充满不信任乃至嘲弄的明亮,让人极不舒服。我想,我们三个是平等的,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只是对象不同罢了。男孩子中,有一个给司机当徒弟,另一个去了小料加工车间。
我们小心翼翼地适应着师傅们的冷嘲热讽,同时也享受来自管村人投来的羡慕眼神。但没有人知道,在刚刚来工厂的几个夜里,当我从睡梦中醒来,身下冰凉,伸手时,发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从床上掉下来了。对于习惯睡在暖混混热炕上的人来说,一张床的范围,太小太窄了。另一天晚上,我被物品掉落下的声音惊醒,朦胧中,听见她们的对话,原来是两个人都掉下去了。
男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天早上醒来,小司机找不到小木匠了,明明房门朝里插着,窗户也关得好好的,人哪去了呢?他就怀着这样的疑惑,上了厕所,去食堂打洗脸水,回来时,一眼看到小木匠裹着被子睡在床底下。
男孩子不懂掩藏,好像也不怕羞骚,到早上开饭,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床下睡过一夜的事实。我们三个女孩非常默契地掩藏着自己羞愧的秘密,紧紧地攥着,不放开。
一年之后,我们已经学会如何矜持而优雅地睡在床上,半夜不会掉下去了。
小木匠熟练地跟师傅拉大锯,师傅还教会他如何使用刨子。他每天将扁扁的木工笔掖在耳朵上,提着墨盒出来进去,挂着一张笑脸。他把做好的第一个小板凳送给了我们。我们没有笑话他。小板凳做得粗糙,也不知是宿舍的地不平还是板凳的腿不平,反正它常常会倒下,除非人坐上去。有天我回到宿舍,看到它又歪倒在阳光里,好像上面附着了什么东西,微细的光芒一闪一闪的,到近旁,才看到板凳底部有字,当然是小木匠的手笔。工厂时间无聊得能掐出水来,我们用这样的时间来练字,女伴回村时借来一本《古诗十九首》,我们边抄边背。而小木匠的用木工笔写下的,就是其中一首: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恍惚觉得他是写给我的,又怀疑他不过无聊无意之举。但在其后半年多时间里,我的床头,枕边,我看过的书里,都会出现一些纸片,上面写着一些诗句,其中,是否有他自己写的诗?不得而知。我悄悄把它们擦掉,撕掉,好像自己从未见过般羞愧难言,故作姿态。两个人碰到,各自跑开,并无问询和答言。
养貂的女孩正在谈对象,每周都会骑自行车去往县城,在那里有她的同学和对象。她们会做什么?像电影里那样,热烈地讨论,拉手风琴唱歌,朗诵诗歌?还是在林荫小道散步?不知道,反正每次她回来,总是很兴奋,眼睛里闪着光,黑红的脸上,绽着久久不散的笑意。但夜里,她会叹气,仿佛黑夜带着浓重的稠雾将她弥盖。在她眼里,显然我跟另外的女孩还是小娃娃,所以她不会倾吐自己的烦忧,只有像黑夜一样,慢慢将愁绪加深加厚,直到抛进梦的深渊。
不久,她通过对象的关系,借调到县城某单位,并派往省里培训。她走的那天,我们到管村车站等候。那弯弯曲曲的公路,像一个大大的迷宫,汽车这个咆哮的猛兽,很早就在我们视线不达的地方开始轰鸣,越来越近,响声越来越大。东面的车吭哧吭哧上坡,西面的车呼啸下坡,尘沙弥漫,久久不散。直到我们被尘沙打成灰人,日头移到头顶,她乘坐的长途公共车才出现。她从车窗里探身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约定回来见。新烫的满头小卷,让她的脸显得更圆更大,那张脸,随着公车再次缓慢地启动,渐渐融进陌生的背影里。
我们沉默不语。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感觉。尘沙漫过我们的身体,有液体,正在缓慢地挤出胸腔。
漫长的午睡,我们被外面的大呼小叫惊醒。场院里,那些师傅们都在笑而不语,脸上带着鄙视。不远处,小司机像一只惊骇的小狗,绕着院子慌张地奔跑,前额那缕头发,像一面小旗子般招摇着。他身后,是手持大棒的师傅,风从敞着的衣襟穿过去,后背鼓囊囊的。前面那个边哭边跑,后面这个边骂边赶。直到师傅终于气喘吁吁撵上了小司机,手里的大棒从他头顶擦过,打在背上,他终于大哭起来。
师傅眼中,闪过寒冰般的冷酷,扯着喊着问:“你敢不敢了,敢不敢了?”
被棒子逮住的徒弟,终于站在那里开始抽泣,他的脑袋变得软塌塌的,垂在胸前,“不敢了,师傅。”
众人们这才知道,小司机悄悄将解放车开到管村,在供销社那边跟人炫耀了半天,才美滋滋又开回来。他以为师傅回家了,大中午不会返回林场,没想到,在场门口,正遇推着自行车的师傅,所以才有这一出。
“没有出师的徒弟,未经师傅允准,是不能随便显露身手的。这是大人们的规矩和底线。看,这就是下场。”
离开燠热的院子,回到宿舍,同伴说。
傍晚,开始下大雨了。夜里,哗哗的流水声将我从梦里一次又一次拉醒过来,有次,我错以为自己回到了家,那声音,来自暗夜的温河。第二天早上起来,雨还没有停,场里的院墙被雨水冲出一个口子,哗哗的流水,从六轴沟的沟渠里溢出来,挟裹着草根和淤泥,在院子里横冲直撞。
这场雨下了好几天。我们的宿舍开始漏水,小木匠他们宿舍的地上陷下一个坑。
雨停后,工人开始收拾院子跟院墙,师傅说,小木匠们的宿舍地面需要重新用灰渣打一遍。小木匠和小司机担了十几担灰渣,师傅在里面掺水和好,只待明天铺地。
天明,小司机早上起来,又寻不见小木匠了。他这次也不急,蹲下身来,准备从床下将小木匠拉出来,这一蹲不要紧,倒把他吓了一跳,他看见小木匠的床下,有一个大洞,而小木匠,正裹着被子,睡在里面。他拉门出来,大喊。
小木匠隐隐听到喊声,觉得该起床了,但周围依旧黯淡无光,便又转身睡去。一根长棍子捅得他生疼,才发觉,所有人都倒立在自己的头顶,他以为是梦,揉揉眼,再看,还是,他惊得坐起来。于是,他看到蒙尘的棺椁、生锈的灯盏、砖头、小瓮子和香炉。
原来,不止六轴沟,包括我们床铺下面,都住着管村人祖先的骸骨。
单位给小木匠和小司机换了宿舍。但这事让小木匠骇怕了很久,乃至萌生离开之念。小木匠不再写诗,那支扁扁的木工笔,被扔在一旁,暗淡得,像要被遗忘。
借调出去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等待吃她的喜糖,等了好几年,终于吃上时,跟她结婚的并不是当初恩爱的人。她依旧烫着小卷的头发,消瘦的黑脸上,那双眼睛显得很大很大,眼周全是深深浅浅的淤痕;跟我同龄的女孩嫁给了她们村一个瘸腿的赤脚医生,他会吹笛子,会编席子,会唱歌,会修收音机。有几年,我在集贸市场常遇到他们,他们租了一个服装摊子,卖小孩的衣服;小木匠后来当了一家公司的经理,当然,跟木匠无关。有次我们乘坐同一辆车,除去上车打了声招呼,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我一眼;只有小司机留在了林场,他娶了管村的姑娘,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在一些时候,我们也会偶然遇见,比如街头,医院,或者旅游区,但五个人从没有真正地聚集过一次,像人群中任何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渐渐成为彼此记忆宫殿里缀满锈斑的墙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