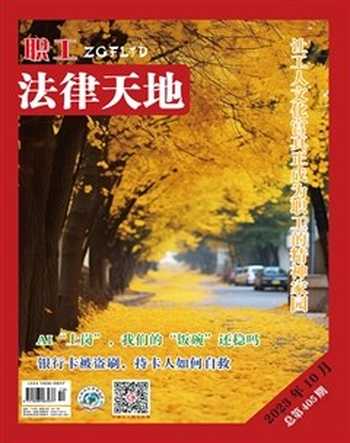国外森林碳汇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刘宇泽
森林作为地球的重要碳汇,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采取了一系列立法行动,旨在促进森林碳汇发展并鼓励减少碳排放。这两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了解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立法手段促进森林碳汇的发展,以及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一、澳大利亚森林碳汇立法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澳大利亚碳信用法案》提出了碳信用的概念,将其纳入国家的碳排放减少机制中。例如,新南威尔士州制定的《产权法案》中规定了森林碳汇权,旨在促进该州林业碳汇权的发展;昆士兰州也出台了《林权法案1959》,旨在支持该州的森林碳汇项目实施。
(一)碳信用法案主要内容
澳大利亚碳信用法案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至2015年,适用于澳大利亚的主要碳排放行业,包括电力、采矿、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制造、建筑和运输等领域。这些行业必须购买碳信用,以抵消其碳排放量,或减少其碳排放量。第二阶段从2015年至2020年,适用于所有澳大利亚企业,包括小型企业。这个阶段的制度设立了一个底线和上限,企业必须证明他们在底线以下的碳排放量,并购买充足的碳信用来弥补超过底线的部分。
(二)碳信用法案关于森林碳汇方面的特色内容
《碳信用(碳农业倡议———再造林和造林2.0)方法确定2015》是澳大利亚碳农业倡议中的一份重要文件,旨在促进和支持澳大利亚的森林碳汇项目。该方法规定了合格项目的指南、监测和测量要求、温室气体减排和碳封存的计算方法,以及核查和报告义务。通过实施这种方法,澳大利亚政府寻求鼓励森林恢复和造林工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恢复作出贡献。
二、新西兰森林碳汇立法
新西兰在森林碳汇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气候变化(林业)法规2022》《2007年森林(永久森林汇)条例》,针对永久性森林固碳项目,规定了认证、登记和管理要求,确保其在减缓气候变化和保护永久性森林资源方面发挥有效作用。这些法律的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保护和管理新西兰的森林资源。
(一)《气候变化(林业)法规2022》的立法内容
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法2002》的次级立法,由新西兰环境部制定的《气候变化(林业)法规2022》是根据《气候变化应对法2002》第一百六十七条、一百六十八条、一百八十条法规制定的。
其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规定了条例中使用的术语和概念的具体定义,以及与碳储存量和碳排放量计算相关的规则和舍入规定。
其第二部分规定了1990年之前的林地的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对森林砍伐的相关规定,旨在限制和监管1990年之前的林地的砍伐行为。
其第三部分规定了1989年之后的林地的具体规定。这部分涉及申请和通知程序,以将土地注册为标准或永久林业参与者。条例规定了现场测量方法和平均碳核算方法,用于计算1989年之后林地的碳储存量和碳排放量。
其第四部分包括本条例的相关附表,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导和信息。
(二)《森林(永久森林汇)条例2007》的立法内容
新西兰《森林(永久森林汇)条例2007》于2007年根据1949年《森林法》制定,为新西兰永久森林汇的建立和管理提供了指导方针。这些条例旨在鼓励土地所有者建立永久森林,以抵消温室气体排放。一旦获得批准,土地所有者成为契约人,并受到契约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这些条例的关键规定之一是在契约中规定的“限制期间”内禁止在森林汇区域内进行伐木。这一限制的目的是确保森林长期固碳。这些条例还概述了适用于森林汇计划各个方面的费用、收费和征费,这些费用用于森林汇计划的管理和运营。总体而言,这些条例旨在鼓励建立和可持续管理永久森林汇,为该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贡献。
三、中国森林碳汇立法
中国在森林碳汇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晚,目前没有针对森林碳汇进行单独立法,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的定义中有关于森林碳汇的概念。在法律这一层面,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以下简称《湿地保护法》)以及202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都提及了“生态系统碳汇”和“湿地生态功能和碳汇功能”的字眼。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在生态环境相关的立法中明确加入了“碳汇”这一概念。可以预想到的是,未来我国相关生态立法中将会有更多的法律增加“碳汇”概念,积极为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提供法律法规的保障。虽然暂时我国并没有系统进行森林碳汇立法,但对现有碳汇政策以及碳汇法律的分析对研究森林碳汇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下文将列举一些重点政策及法律,结合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相关森林碳汇立法这一方面寻找到对我国森林碳汇立法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法律方面
总结《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第八条和第十一条内容,可以知道国家积极鼓励和支持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与研究,特别强调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重要性,旨在深入了解其在固定、存储和转化大气碳的功能。此外,国家在统筹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布局时,将生态系统碳汇视为关键生态功能,旨在通过保护和增强碳汇,提升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质量、稳定性和持续性,从而增加生态产品供应和优化生态服务功能。
总结《湿地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内容,可以了解到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保护规划,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水体治理、土地整治、植被恢复和动物保护等,增强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碳汇功能。这表明湿地被视为重要的碳汇,能够固定和存储碳,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作用。
(二)司法解释方面
关于森林碳汇在司法解释方面的体现,主要有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内容,其中有关森林碳汇的内容总结如下。首先,林业碳汇可以用作担保物权,为债务或其他责任提供担保。其次,在确定侵权人应承担的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时,法院將综合考虑受损森林资源在气候调节、碳固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多个生态服务功能。最后,当事人在面临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如选择以已核证的林业碳汇认购方式替代赔偿,法院会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和不同责任方式的合理性来判断是否允许这种替代方式。这些法律规定强调了林业碳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及其在气候调节、碳固定和生态服务方面的价值。
(三)部门规章方面
有关森林碳汇在部门规章方面的体现,最重要的是2021年国务院出台的《2030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其第三章《重要任务》第八点重点提出了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主要内容:为了巩固并提升碳汇能力,国家坚持系统观念,采取一体化的生態保护和修复策略。具体措施包括构建利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严格守护生态红线,且确保各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等的固碳作用稳定。到2030年,国家目标是达到25%的森林覆盖率和190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加强碳汇监测核算体系的建设,开展对各种生态系统的碳汇本底调查、碳储量评估和潜力分析。同时,鼓励进行前沿科研并建立体现碳汇价值的补偿机制,与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相结合。这些措施表明国家高度重视碳汇的角色,并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来增强其功能和价值。
四、比较分析我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森林碳汇立法
(一)立法层面
相较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森林碳汇立法,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碳汇方面的单独立法。在碳汇这一方面,我国也并没有一部类似于新西兰的《森林永久森林汇条例2007》这样一部的单行森林碳汇立法,这是我国现在对森林碳汇立法方面亟待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何况没有相关的立法,这对我国森林碳汇的发展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尽管《民法典》和《森林法》都提及了森林碳汇,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此仍未明确定义。森林碳汇目前更多地被视作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一个子概念,仅作为环境侵权的被保护对象进行笼统的司法救助,这样的救助显然是不够充分的。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推进,森林碳汇的内涵也产生了变化,但我国的法规制度并未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二)政策方面
自我国提出“双碳”目标之后,国家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这一行动。在相关政策方面,我国提出了比新西兰、澳大利亚更细致的政策方案,其中“1+N”的相关政策为我国双碳目标的政策保驾护航。它主要包括“1”《2030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N”中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五、完善我国森林碳汇立法的建议
我国目前缺少一部有关森林碳汇的单独立法,对有关森林碳汇的定义、森林碳汇权的认定以及森林碳汇交易体系都没有比较全面的立法规定,但切实考虑到我国森林碳汇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笔者认为可以在未来《森林法》的修订中逐步加入森林碳汇的概念及相关内容,摸索一种合适的方法对我国的森林碳汇做出立法上的保障。同时,对森林碳汇权的定义也需作出进一步明确。对比澳大利亚两个州关于森林碳汇权是属于林权的一种还是自然资源产品这一问题,我国也需要有符合国家国情的森林碳汇权的定义。森林碳汇是追求碳中和目标的新兴领域,我国急需建立健全的法律支持体系。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