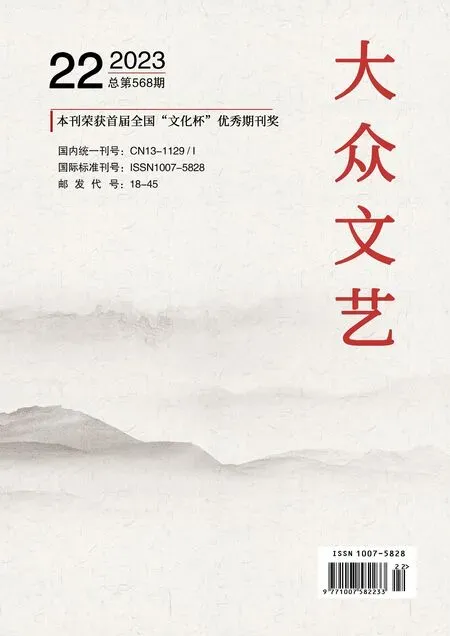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广西贺州土、客庙会音乐研究*
赵东东
(南宁学院,广西南宁 530200)
贺州市自古岭南走廊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三省通衢”“一行三河两界”之说,开放式地理空间的畅达为人员的流动、文化的扩散传播创造了足够有利的条件。“土”“客”是贺州两大重要汉族族群,①庙会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在这个空间场域中随时发生着际遇交往、音乐展演、信仰崇拜和社会行为,社会交往、族群交融等行为在庙会这个微型社会中结构、解构、重构了土、客族群身份与认同,音乐在土、客两个族群中共通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现况。
一、“土”“客”文化邂逅
(一)际遇需求的表层引力
族群边界理论的开创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Barth)在《族群与边界》一文中指出,“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隔绝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和组织。”[1]。在社会属性方面,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本族群的族群符号如姓氏、语言、血缘,在日常生活也存在着一定隔阂和摩擦,差异性的不可调适就会产生明确的族群边界,因而,民众渴望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与载体。庙会是一个集宗教信仰、文体娱乐、经济贸易于一体的节庆,也就成为土、客甚至是瑶族、壮族等不同族群进行交往互动、产生际遇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场合中你也可以随地听到本地话、客家话、普通话的交织,更甚有一方操着本地话、有一方操客家话。人的主观感受和的价值体系在这个际遇交汇的场合中体现,参与者即需要彰显自己本族和个性化的一面,同时也在参与过程中吸收同时也被其他族群所影响。因而无论是为了今后的生活需要还是出于现下个人际遇诉求,民众们为增进彼此之间的形成熟悉感、亲近感,潜意识地想要在这个开放的场合中进行更好的互动。
(二)传承谱系的交流互通
庙会的作用一直都不仅仅只局限于音乐本体的探讨和交流,实际上也承担着宣传不同音乐文化的作用。笔者在田野过程中考察了不同庙会的法事师傅、吹打师傅的成长经历、师承关系,在一场庙会里,这些师傅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乡镇甚至不同的族群。主办方也不会因为可以选择乐师和法师的族群身份,笔者在田野中参加过的一场完全由客家村寨主办安龙庙会,其中法师来自本村客家人,吹打乐班中也有本地人,晚上的娱乐表演环节邀请了瑶族的文艺队。另一方面来说,在谱系传承的时候老师傅不会因为学徒的族群身份而拒收,也有法师或乐师一个人同时传土、客两个谱系的情况。在庙会这个大舞台中,不仅展示了不同族群不同类型的优秀音乐作品,不同族群、社会属性、文化背景的乐师以“音乐”作为交流工具展开对话。他们的音乐观念、风格流派、审美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被不停解构吸收重组,一种跨越地界和族群的交流方式被建立起来。同时,谱系错杂、交互学习过程也是家族、村落、族群音乐思想的交汇,对族群、本村落文化的推广。这样不同语言和源流乐队交流合作,从内部来看是一种跨族群的合作,从外部看是汉文化圈整体性展示。
二、音乐的祭献与信仰
“互动仪式链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题,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2]庙会构成了多文化相遇的理想场所,该场所可以作为对他者的体验,也可以作为自我的体验。
(一)仪程与音乐的认同
吹打乐作为族群互动的重要载体,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与象征意义,但笔者调查中发现土、客在传承着相同的吹打音乐文化,也不分彼此地共享着庙会和打醮等公众性的民俗仪式活动,这种认同从两个方面来实现:
一是对吹打曲目共享的认可。在刚刚进入田野之初,笔者经常会向师傅们请教两个问题:“本地吹打和客家吹打有什么区别?”“师傅你吹的曲调是本地的吹打还是客家的吹打?”师傅的回答都是“本地曲调和客家的曲调是一样的!”笔者通常也会追问:“那这些曲调是本地人先演奏还是客家人呢?”,得到的答案也是统一的:“一直大家吹的都是这样的调子。”换言之,土、客族群在吹打乐与公众性民俗活动中不会有意识地划分出族群“边界”,而对当地民俗活动音乐的共通性文化认同。
二是仪式程式使用的认同。在贺州,汉族法事分文坛和武坛两种,释教属于文坛,由本地人主持,穿袈裟;而道教属于武坛,由客家人主持,穿道袍或便装,头系红布。在大型打醮等仪式时,两者兼有。故而从接受的这角度来说,土、客两族的民众都普遍认同文、武坛仪式以及仪式音乐的使用。法事师傅师承本地人还是客家人,并不影响民众的选择,土、客两族均未将庙会中的音乐、仪式与本族群的属性画上等号。从表演者角度来说,法事师傅也通过达成共识的仪式行为来获得社会认可。
(二)审美与感情的交流
“美的事物首先与我们的感官接触,所有现象都得通过感官。感觉是审美的愉快感之开始及条件,这是情感的基础,情感必须有某一情境作为前提,有时作为前提的情境是非常复杂的。”[3]贺州特殊的多元区域性文化生态,使具有地方性特色和历史记忆庙会音乐承载了土、客两个族群文化同感,参与庙会音乐活动是个体审美体验到集体情感汇合过程。
1.个体音乐体验
首先,在醮仪音乐层面,仪式中法器和吟诵的音声与神灵进行沟通,建构了一个信仰世界。这些音乐氛围的营造使民众安宁情绪效应,所有参与者在这场仪式中得到了身心的放松与追求喜乐平顺的期望,也激发了民众信仰层面的情感。其次,锣鼓欢天的吹打乐是流动的情感。在几天几夜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进行,音响效果从听觉效果达到一种热烈喜庆的氛围塑造。对于没有音乐基础的民众来说,音响效果和旋律性音乐直接作用于大脑传送,满足了民众喜庆欢乐的审美理想。最后,在庙宇前方的戏台上演的戏曲歌舞乐成为娱神、娱人主要方式。富有生活哲理的彩调山歌剧和对歌,无处不宣扬着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生活性的音乐能够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是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审美积淀中的过程。
2.集体情感交流
庙会中的音乐承载着集体共有的情感。在内容上,庙会中的大部分音乐都是有着美好的祝愿与欢快喜庆的旋律,契合民众祈福求安的基础情绪。在语言上,不管是醮仪上的诵词还是歌舞戏曲的彩调山歌剧,都用两个族群的日常生活语言呈现,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情感交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其一,在庙会中的音乐体验是开放性的,这强烈体现在外围的歌舞戏曲音乐中,如同讨论电视剧剧情一样他们在台下讨论艺人的表演和曲调,实际上是两个个体之间地对音乐感知评判与接收。观念交换也是一种情感能量的互动,是把个体的微小情绪融人强大的集体力量中,顿时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其二,在贺州大大小小庙会中,千百年来一直保持了打醮仪式和吹打乐演奏的传统,这些曲调在这岁月更迭中反复演奏,形成集体性的音乐审美认知与情感连带;其三,仪式化的音乐的祭献行为,也是民众们得到共同的情感寄托的回报。仪式音乐并产生的抚慰心灵,使得参与群众的关注焦点、共享情感状态达到一致。
(三)乡民与村落的凝聚
在柯林斯的理论中,互动仪式是一种有规律的不断重复的和程序化的社会行为,通过多次重复互动人们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障碍,进而建构社会秩序和共同归属感。贺州地区的跨村落的庙会活动更多地借助音乐象征符号及仪式体系,达到乡镇村落内凝聚的力量的作用。
1.神恩与教义
在早期在庙会的举行最初目的是酬谢神恩,以集体的力量进行仪式的祭祀和音乐的祭献体现的是人与神的互惠关系。也可以说为了在地方社会谋求人际资源和社会存在,民众们则需要通过共同信仰相互结盟,维系、强化血缘宗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认同。这是一场宗教的仪式,也是一场教育的仪式,仪式里的许多唱词、经文等都在向人们宣扬着“乡里和睦”“忠孝礼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灌输一种凝聚力和团结的社会观念意识,是一种由仪式吟诵调到社会群体认同的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社会组织结构的传播接受过程。
2.互帮与互惠
庙会时间临近前,理事会便开始找组织村内一些人帮工,请乐师请法师、请表演团体等一系列工作都由不同的帮劳者开展前前后后,需要花费5天左右才可完成。在现实的村落生活中,围绕着庙会音乐信仰与仪式展开的人际交往,搭建了村社邻里互惠互助相互关系。庙会就是这样借由集体性的活动集结了庙社周边的劳动力量,人情往来、家族商议、邻里互助,构建起和谐着人际关系和稳定的村落秩序。在这些集体活动中,邻里间彼此结成一个会社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加强扩大社会联系,从而形成互惠的村落社会情感网络。
3.秩序与治理
乡村族规、民间宗教、家族权威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对村落民众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灵活性、针对性和策略性地扶持传统庙会文化,对乡村社会实施间接性的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庙会的举行也加入了政府的介入,近年来为实践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各村镇都组织了文艺表演队,他们常常被邀请到庙会中进行演出,增加了村落集体的参与性情感、精神娱乐生活与公共性议题,强化人们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身份和主人翁意识,也是政府是对乡村群众的情感和行为进行引导的过程。庙会音乐文化在政府引导与村落支持中,唤起村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发挥出助力现代乡村治理的独特功能,它们的主旨都是鼓励民众和睦向善,创建和谐社会,重建社区共同体意识。乡土社会的治理,离不开民俗与艺术的交织,离不开民间信仰神圣的营造。
三、庙会音乐社会动机流
互动仪式是将短期的情绪转化为长期情感的转换器,“将产生四种重要结果:群体团结、个体的情感能量、代表群体的符号、道德感。”[4]庙会活动将不同族群的人吸引到节庆仪式中来,通过仪式的举行,构建出一个由开放的、多元化公共文化场域。
(一)音乐符号资源整合
符号是互动仪式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纽带,当不同的个体重视并同时拥有同一个代表性符号时,他们很容易在借助该符号展开互动,并予这个符号以高度的关注。庙会作为一个开放性文化集合地,试图把具原来分散的有地方性文化的音乐类型如醮仪音乐、吹打音乐和歌舞戏乐等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整合,并赋予它新的文化符号,塑造了一个完整的音响世界。作为表演者的艺人期望自己所拥有符号资本被他人所欣赏,也可以与其他音乐符号持有者进行资源置换,所以在这里通过语言、情感、仪式化行为进行有意识的互动融合。庙会规模越大,越是能够将音乐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参与者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能量,这使得庙会活动得到一种持续的、正向的循环。反过来说,互动仪式情感能量运行机制的驱动,庙会将醮仪音乐、吹打乐、歌舞乐等符号性元素凝聚成一股民众的情感,使得村落情感能量不断上升,这种情感能量不断凝聚并推动了庙会等其他大型集体性活动的发展。
(二)情感能量社会流向
在庙会场域中民众通过音乐行为互动、音乐观念认同、音乐审美喜好等音乐符号资源汇聚起来形成了重要互动仪式产物——情感能量,这些能量在某次集会趋于热烈中达到最大值,同时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而逐渐减弱,这唤起了民众想要再次举行互动性聚集场合的渴求,也是音乐符号得以长期传承进行的动力机制,情感能量随之在不同聚集场合中的流动。当人们离开庙会中,在婚礼、葬礼、岁时节庆民俗情景依然能看见吹打乐、醮仪音乐进行演奏,只是更换了一个场合,这由此形成一个社会动机流,并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认同。音乐符号带有群体的特殊标志和记忆,可以超越时空限制,音乐符号也将庙会中的短期情感转变为长期的情感能量动机流流向下一个民俗活动中,所以我们常说民俗活动是一种地方文化认同及地方民众共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承载。
四、结语
互动仪式链主要组成要素包括:1.群体聚集或身体共在。在庙会中,无论是作为节庆活动的主办者、民间艺人,还是作为接受者的民众,都积极参与到庙会活动各项流程中,都能通过即时性的面对面互动交流相互影响;2.相互关注的焦点。庙会中的仪式信仰的展示、音乐的祭献与共享成为参与者的焦距对象;3.共同的情感体验。这些要素因音乐符号产生强烈和短暂的情绪体验,两个族群通过音乐认同和交流中消除隔阂,共享的个人情感能量在具有仪式性的庙会氛围下变得越来越强烈,并在相互关注的焦点下产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和集体兴奋,最终形成集体情感能量,并将这股能量整体流向其他群体集聚情景如婚丧节庆。原来短期、剧烈的情绪,在反复仪式互动中形成情感连带。鼓乐喧天已经随着庙会结束散去,情感能量却久久在民众心中盘桓,他们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聚共欢。(图1)。

图1 互动仪式链情感能量模型
注释:
①“土”即较早期在贺州定居并世代在此生活的本地人,“客”即从清初开始大范围地迁徙到此地的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