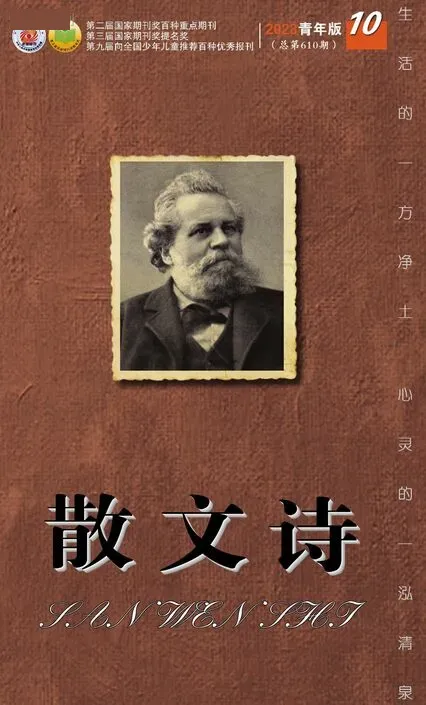从堂吉诃德到约瑟夫•K
2023-12-10 14:55:51
散文诗 2023年20期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 中起首就将西方现代小说视作“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 某种程度上, 现代性叙事正是一部关于堂吉诃德的规训录:“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 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 但他或许还不晓得,唯一的真理将会分裂成无数相冲的意见, 永恒的时间将会被击碎成分分秒秒。
如果生命被视作一种超越和征服的现象, 那么, 这一现象本身便内在地包含了一种界限——没有界限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超越本身必须由界限给出定位和导向。 冲突便在于此: 构成超越性的界限本身便是对超越性的否决,生命与形式相生相克。 这种冲突隐现于康德对启蒙的思考中, 也闪烁于齐美尔对货币的思考和韦伯对学术的思考中, 它当然也出现在一切现代性叙事的核心之中。 在主体视阈中, 启蒙同时是论证的对象和前提, 价值的形式化确立了货币这一上帝, 学术的超越性必须预设学术本身的永恒性; 至于主体本身——恰如在科学行为所示——必须被确认为暧昧不明之物。
视界的确立便是视界收缩的第一推动力, 而世界一经显现便因视界的确立和收缩而走向了物化, 逐渐失去反思的空间; 堂吉诃德终于变成了约瑟夫•K。 问题是明显的: 如果存在必须在时间中被规定, 那么, 存在如何才能豁免于随时间而来的物化呢? 如果堂吉诃德注定要策马远游, 他要如何才能避免遭遇那只名为约瑟夫•K 的甲虫?
猜你喜欢
当代人(2022年6期)2022-06-27 10:14:46
小学科学(学生版)(2020年8期)2020-08-24 08:13:02
小学科学(学生版)(2020年7期)2020-07-28 08:00:54
文苑(2019年24期)2020-01-06 12:07:06
阅读(低年级)(2018年11期)2018-05-14 09:37:53
通信产业报(2017年32期)2017-09-24 02:23:38
乐府新声(2017年1期)2017-05-17 06:06:31
海外文摘(2016年8期)2016-08-16 16:58:23
新民周刊(2016年23期)2016-06-20 10:22:06
鹿鸣(2015年6期)2015-06-10 14:3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