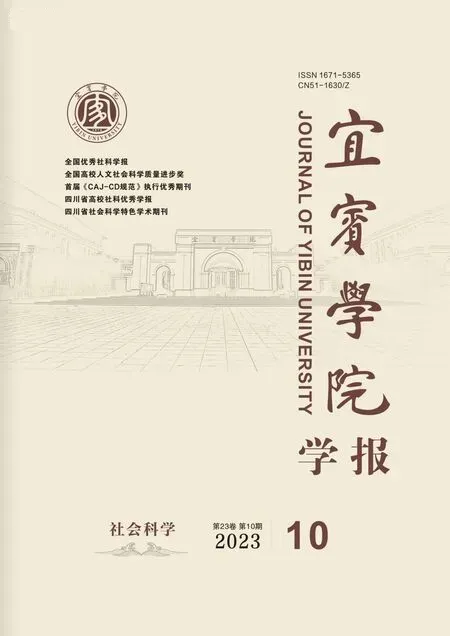华化西学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
——贺麟的文化翻译观
范先明
(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1933 年,贺麟在《国风》杂志上发表的《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开宗明义地指出:“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1]17。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人主张“中体西用”,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贺麟看来,这两种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都不可取。正如张学智指出那样:“中国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哲学绝不能为西洋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之体,亦不能以近代科学及物质文明为用”[2]47。为了追求“真理”,他远渡重洋,刻苦学习英文、德文、拉丁文,所以他在翻译时,能够从几种文本的比较鉴别中,真正弄懂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原著的深义。同时,通过学习、介绍、翻译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他也因此真正领会了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思想。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其译文明白晓畅、广为流传。
他从作文的角度指出:“作文应打破文言白话的界限,而以理明辞达情抒意宣为归”[1]17。这一点仅从其译著《鲁一士学述》《黑格尔》《小逻辑》《致知篇》《精神现象学》等就可以得到明证。纵观贺麟的译作,不论是英诗汉译、英文哲学著作翻译,还是德文哲学原著翻译,都明白晓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就其翻译中的语言风格,张学智评论道:“他的文字,全是白话文,而他的白话文是经过文言陶溶过的,一点也不俚俗”[2]47。
从翻译的角度,他也明确地指出:“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1]17。这里的“艺术工力”,即是译文要达到“融会原作之意,体贴原作之神,使己之译文如出自己之口,如宣自己之意”[1]17的至高境界,此即为钱钟书所谓的“化境”[2]696,亦即是张学智所说的“形式为内容服务”[3]47。贺麟的这一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了长期以来中西翻译理论中直译与意译的二元论争,是在新的语境下,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标准的批判性继承。
可以看出,他从谈学、作文和翻译三个层面,对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如何“华化西学”进行新的阐释。尤其是在翻译方面,他在严复逝世后,撰写了首篇“全面评述他(严复)的翻译成绩与理论贡献的论文”《严复的翻译》(1925)[4]340。从对翻译家严复翻译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中,贺麟创新地提出“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的观点,这正是我们通常说的归化翻译策略。
一、华化西学思想的提出及归化、异化策略
贺麟深受其师吴宓先生的影响,始终坚信中国文化价值的所在,认为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1921 年,吴宓成立了学衡社,次年,《学衡》杂志创刊。在创刊词中,吴宓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5]4。这一主张,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如何获得“文化自信”?在西化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以贺麟为代表的新儒家们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华化西学”。贺麟在《论翻译》中指出:“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洋学问中国化,灌输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学成为国学之一部分”[6]139。而所谓“华化西学”,即是要使“西方哲学中国化”,从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要解决这一时代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翻译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及荷兰的斯宾诺莎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
由此看来,“华化西学”正是贺麟解决当年译介时代之问所采取的态度。换言之,这即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既不妄自尊大,亦不妄自菲薄,而是采取“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的“洋为中用”的态度。他进而指出:“吸收外来学术思想,移译并融化外来学术思想,使外来学术思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乃正是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而绝不是埋没个性的奴役”[6]139。因而,翻译西方哲学,决不能仅仅立足于担当“传声筒”的角色,而应该张扬自我“个性”,并贯通中西哲学。也正是如此,他最后指出:“翻译外籍在某种意义下,正是争取思想自由,增加精神财产,解除外加桎梏,内在化外来学术的努力”[6]139。可以认为,贺麟关于翻译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华化西学”这一观点,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要尽量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正如孙迎春指出的那样:“这是颇为深刻而明确的归化理论,道出了翻译的本质”[7]52。
一般来说,从翻译的语言层面,译者可以采取直译或意译的策略;从翻译所涉及的语言形式与意义的角度,译者可以采取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的策略;从翻译的文化取向来看,译者可以采取“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两种策略。关于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策略,德国近代翻译理论家斯莱尔马赫曾提出了两条路径:即向作者靠拢的“异化路径”和向读者靠拢的“归化路径”[8]42。芒迪对此解释:“斯莱尔马赫赞成的是异化路径,即使读者向作者靠拢”[9]28。可以看出,异化强调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10]36;而归化则重点指采用通顺、流畅和地道的译文来代替原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在中西思想交汇的时代,贺麟在早期英诗汉译、中期欧美哲学文献翻译及后期哲学原著翻译的过程中,都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吴宓的话说,也就是“新材料入旧格律”。
二、贺麟归化翻译思想的渊源
在《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中,贺麟打破了长期以来翻译界在直译和意译关系上二元对立的传统认识,提出“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的独到见解。他阐明了自己对严复“信”“达”标准的赞同,还明确指出其“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与严复“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本质区别。对“雅”方面的认识,按照贺麟的理解,严复的“雅”指“声调铿锵,对仗工整……合桐城派的家法”,而他所谓的“艺术工力”指“融会原作之意,体贴原作之神,使己之译文如出自己之口,如宣自己之意”[1]17。换句话说,他所谓“艺术工力”也就是奈达所说的“在译语中用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11]12。按他的解释,即是“费一番心情,用一番苦思,使译品亦成为有几分创造性的艺术而非机械式的‘路定’”①。由此可知,贺麟的“艺术工力”侧重强调译文的创造性,也就是翻译界所说的归化的翻译策略。
1925 年,贺麟在学习翻译理论与技巧之余,小试牛刀,翻译了华兹华斯的“TheLostLove”(1798),节译了蒲柏的“AnEssayCriticism”(1711)一诗中的精华部分并命名为《卜蒲之八不主义》。1926 年,他翻译了罗塞蒂的“Remember”(1862),1928 年又节译了罗塞蒂的《无名的莫娜:十四行诗集》(1881)中的第十二首“Abnegation”。此后,在20 世纪30 年代,贺麟还翻译了几首德文诗歌,如海因里希·海涅的《我们坐在渔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河畔野蔷薇》,海因里希·迈尔的《最近五十年之西洋哲学》。此外,美国鲁一士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文1933 年也刊于《哲学评论》杂志。在这些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贺麟从哲学的角度,全面论证了英诗汉译的翻译策略,即“新材料入旧格律”。
可以认为,作为新儒家的代表,贺麟始终在努力融通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他之所以在英诗汉译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第一,他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朱熹的“太极说”进行对比,于1930 年8 月发表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该文是其学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文章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找到了出路。他后来回忆说:“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12]119。第二,贺麟始终想通过融通西方哲学,试图为儒家文化找到出路,来重振儒家文化。王思隽、李萧东就曾在《贺麟评传》一书中指出:“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一组文章……热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对抗战起到了激励民心、同仇敌忾的作用。”[13]5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他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从早期的英诗汉译开始,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华化西学,如何做到用“新材料入旧格律”。
三、贺麟英诗汉译中的归化翻译策略
纵观贺麟的翻译实践,他在英诗汉译中采用“新材料入旧格律”的翻译理念,即归化翻译策略。
事实上,关于诗歌翻译问题,历来是译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茅盾在《论译诗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提出:“翻译外国诗是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的办法”[14]345。周作人在《陀螺》序一文中指出:“诗是不可译的,只有原本一首是诗,其它的任何译文都是塾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15]398-39。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指出:“诗为文学品类中之最纯粹之艺术最为文字之精英所寄托的,而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16]430。中国古诗主要以抒情诗为主,重意合(Parataxis),在写作上习惯将不同的意象直接叠加,在表达上通常将起连接作用的虚词省略掉,而英语诗歌重形合(Hypertaxis),不仅会使用逻辑连词,还会有对应的时态、语态及人称方面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植根于不同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的部分,无论古今中外几乎都是不可译的。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诗歌是可译的。郑振铎认为:“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有许多诗,我自信是能够译得出的”③。朱自清在《译诗》中指出:“诗可不可以译或值不值得译……这要看那保存的部分是否能够增富用来翻译的那种语言”[17]737。成仿吾在《论译诗》中指出:“译诗应当也是诗,这是我们所最不可忘记的。其次,译诗应当忠于原作”[18]201。吴宓指出:“诗之媒质为文字,诗附丽于文字。每种文字之形声规律,皆足以定诗之性质”[19]68。由此可见,吴宓也认为诗歌本身植根于语言文字的部分(即诗歌的形式)是不译的。
尽管植根于语言文字本身的部分不可译,但不可否认,诗歌本身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是可译的。不过,也正因为中西语言的差异不可弥合,贺麟曾指出:“就诗之具有深切注明人所共喻的意思情绪真理言,则这一方面的诗应是可以用另一种文字表达或翻译的”[6]138。换句话说,就诗歌中人所共喻的思想、情绪、道理等是可以翻译的。同时,他还指出:“就诗之音节形式之美,或纯全基于文字本身之美的一部分言,那大半是不能翻译的,要翻译时,恐须于深切领会到原诗意义情境之美后,更新创一相应的美的形式以翻译之”[6]138。即诗歌本身的形式之美,由于是根植于源语语言本身,所以是不可译的。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诗是可以翻译的,一方面又要承认诗之可译性是有限的。译诗所需要的创造天才特别多……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拒绝诗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谬说”[6]139。可以认为,贺麟是反对诗歌不可译这一观点的。实际上,他曾在《论翻译》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个人如能明贞恒之道,知他人之意,未有不能用想(相)应之语言文字以传达之者”[6]138。由此可见,译者只要能明他人之思,知原诗之意,未有不能用语言文字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可以说,这就是贺麟关于诗歌可译性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关于诗歌可译性的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之后形成的。尽管他承认诗歌的可译性,但从翻译的角度,他赞同吴宓的用“新材料入旧格律”。可以认为,其所提出的关于诗歌可译性的观点,并非只是纯粹的理论思辨的结果。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贺麟深受其老师的影响,正如吴宓在《学衡》杂志简章中指出的那样:“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5]4。其翻译思想中充满了哲学思辨和弘扬国学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不同的是,他在英诗汉译过程中,始终思考能否和中国古代文学结合起来。和大多数中国传统译论家一样,尽管其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过,他对诗歌可译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在20 世纪初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研读贺麟所译华兹华斯的“TheLostLove”,罗塞蒂的“Remember”和“Abnegation”可以发现:贺麟以文言体翻译了这些英诗,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归化的文言体传达了异化的英诗内容。贺麟不仅以归化的文言体翻译英诗,还以归化的散文体翻译英诗,如其译蒲柏的“AnEssayon Criticism”(《论批评》)一诗时在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上的具体处理方式。
尽管蒲柏的《论批评》为诗歌,但从内容上看,该诗实际上应该为散文,这从该诗标题“essay”一词也可见一斑。此外,蒲柏有将散文写成诗歌的传统,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这)是蒲柏的一贯做法。除《批评论》和《论道德》之外,蒲柏还写过《论人生》和《论道德》等诗篇”。按支荩忠的说法即是“论文写成诗体作品,可以格外受人重视”[20]。由此看来,既然蒲柏写作该诗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贺麟在翻译此诗时,从语言形式上,直接将其翻译为散文,足见其“融会原作之意,体贴原作之神”[1]17,真正领会了原作的精神,而非草率译之。此诗的翻译,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散文译诗的传统,而且也是贺麟节译工作的开始,这为他后来节译西方哲学文献开启了先河④。
而贺麟之所以翻译此诗,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其师吴宓所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的启发,充分认识到蒲柏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是因为时代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译文之所以能融会原作之意,在于吴宓曾在文学课上分析过此诗。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此篇即就吴宓先生(清华文学教授)所选卜朴文学批评论长诗中极精粹扼要的几段译出”[21]。这一节译而非全译的做法,吴宓在1913 年就已经尝试过。该年他节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的长诗《伊凡吉琳》(Evangeline),就是“更以己意,增删补缀而成”,取名为《沧桑艳传奇》,吴宓的这一译诗传统也为贺麟所效仿[22]7。不过,更为重要的却是由于贺麟所处的时代正是白话文学盛行,文言文受到抵制,传统文化受到颠覆的时代。贺麟在新文化运动八年后翻译蒲柏的《论批评》,主要原因是对1917 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一主张的批判性继承。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针对当时的文学改革提出了八项具体的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需讲求文法,(四)不做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23]。
对于当时的新诗创作,胡适明确主张以新思想、新材料入诗。受吴宓的影响,贺麟一方面有保留地接受了胡适关于以新材料入诗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作诗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这从之前谈及的他对几首英诗的汉译就可以得到佐证。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借蒲柏的《论批评》,阐释了他有关诗歌创作(文学创作)应注意的问题,此即其“八不主义”:一不用怪异奇喻,二不尚辞藻,三不偏重声韵,四不趋极端,五不拘门户,六不随流俗,七不慕虚声,八不附权贵[21]。
比较胡适的八大主张和贺麟的八不主义,可以看出:胡适的八大主张明确地表达了以新语言、新材料入新文学的主张,主张对西方的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借鉴;而贺麟的八不主义则始终坚持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思想,主张华化西学——批判式、有借鉴地学习,是要“用归化的语言来传达异化的思想、内容”[24],这正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同时,贺麟在翻译此诗时,出于对当时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回应,从思想内容上,对该诗的进行了改写(Rewriting)。关于文学翻译中的改写问题,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其实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都会反映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25]vi。而贺麟翻译蒲柏的《论批评》,正是出于反对当时主流的诗学观念——提倡白话、反对文言;提倡新思想、新材料入诗,反对吴宓等人倡导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学观念。
实际上,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内容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而传为佳话也不乏例证。比如,《论批评》一诗的作者蒲柏在翻译《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Iliad)时就对原诗进行过改写,并因此被广为称赞,特别是塞缪尔·约翰生称赞这部作品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作家)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作品”。不过,蒲柏的改写是为了美学观念而不是意识形态,难怪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对蒲柏作了如下评价:“蒲柏先生,您诗写得是很漂亮,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风格”。又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对赫胥黎的原文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也进行了改写,其目的是想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中国只有实行变法维新才能实现“自强保种”,这一改写更多的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再如,潘建伟曾就朱光潜所译华兹华斯“TheLostLove”一诗采用旧体诗形式作了评价,并指出朱氏之所以用旧体诗形式翻译该诗,正是因为其要证明旧体诗和新诗之间并非只存在相“异”之处。由此可见,朱氏的这一改写则更多的是出于美学观念的需要。潘建伟对此还评价道:“中西诗形式难以弥合,理趣意境却可通可参,故而将外国诗译成旧体,并不是要为中国诗提供新形式、新意境、新词汇,也并不是要与新诗及新体诗相对抗、相斗争、相角逐,只为两两照映以发现一种独特的趣味”[27]。
因此,旧体诗和新诗之间尽管存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差异,但在思想内容的传达方面,确有相“通”之处。而贺麟等学衡派学者用旧体诗翻译外国诗歌也正是要证明中西诗歌之间的相“通”之处。因而,可以认为,贺麟等学者将外国诗歌翻译成旧体诗歌,并不是要与新文学抗争、角逐而争得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要是在白话诗盛行的时代,通过翻译英诗,以阐明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弥合。由此可见,不论是贺麟翻译华兹华斯的“TheLostLove”,罗塞蒂诗歌“Remember”和“Abnegation”时采用文言译诗,还是翻译蒲柏长诗“AnEssayonCriticism”时采用散文译诗并对原文所做的改写,都是为实现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理想,用归化的语言传达异化的思想内容,为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找寻一条新的路径。
不言而喻,贺麟的英诗汉译实践和几篇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研究论文,无一不是其融通中西语言、中西哲学和中西文化的典范,他的《论翻译》中对“可译性”问题的探讨,至今无人超越,他的英诗汉译实践中文言译诗的传统,也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其“比较参证”的研究理路,也开了学术研究中“比”的先河。
结论
为了中国的哲学事业,贺麟终其一生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其著述之丰、贡献之大,实为后辈学者学习的典范。不仅如此,其丰富的翻译实践和前瞻性的翻译理论研究,也确立了他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为了复兴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他融通古今,比较参证,始终致力于“华化西学”,尤其是在翻译中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不仅证明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也为诗歌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深入挖掘其翻译思想的价值,重新在翻译界增强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
——贺麟人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