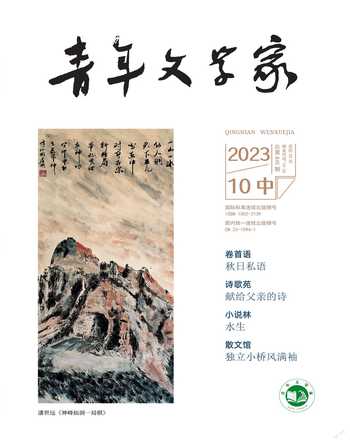论曾巩散文的“辞章尺度”
耿玮彤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师从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长,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艺术造诣极高。唐顺之评价他“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与王遵岩参政书》)。曾巩在散文的辞章运用层面,努力追寻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讲究辞章,又反对一味专务辞章。本文將这种文辞观念总结概括为“辞章尺度”,并阐述曾巩散文“辞章尺度”的具体表现、成因,以及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
一、曾巩散文的“辞章尺度”
所谓“辞章”,是指文章的写作技巧。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义理、辞章、征实之辨有着如下阐释:“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文史通义·说林》)按照他的说法,“识”是指阐释文章的义理、提出独立的见解,“才”集中表现为写作技巧,而“学”则是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料的总量。通过对才、学、识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三者彼此联系,相得益彰。这里的“辞章”可以等同于写作技巧,只有将才、学、识集于一身,才能称之为好文章。当代学者对于“辞章”有着这样的理解:“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该是辞章……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钱穆《史学导言》)这是从方法论角度来阐述辞章的功用,在具备“德”的前提之下,运用得当的技巧使得“言”丰富得当,这便是辞章的存在意义。“分寸”,也就是尺度的意思。注重文章写作技巧的“分寸感”,也就是所谓的“辞章尺度”。因此,我们可以把“辞章尺度”一词理解为文辞层面的写作技巧。“辞章尺度”包含很多个层面,主要有语言技巧、章法结构、表现手法。
我们可以发现,曾巩在散文创作中一直追求一种独特的“辞章尺度”。前人的研究曾经将曾巩散文中的这种文辞观概括为“辞工说”(周楚汉《曾巩文章论》),即讲求辞章,又反对一味专务辞章。这种富于平衡感的“辞章尺度”,在曾巩与好友的书信和对他人著述的评价中得以体现。
曾巩对待文章的基本态度一向是内容大于辞采,要先“明道”,再“急于辞”。李沿曾向他请教写文章的文辞章法。曾巩首先肯定了李沿“有志乎道”,接着评价他的文章中所想表达的内容“欲至乎道也”。曾巩指出李沿过分注重“辞”,而舍本逐末,导致其失去写作技巧上的“分寸感”。这种写作方式实际上就是曾巩所说的“务其浅,忘其深”(《曾巩集》)。在曾巩看来,“道”重于“辞”,若“道不明”时还一味“汲汲乎辞”,既不能表述清楚“道”,“辞”也和空中楼阁一样缥缈。文章之所以“浅俗不明”,是因为只看见了表面,而不能深入理解和思考,也就是没能够领悟“道”。那么,想要追求这种“道”,就必须依靠“得诸心,充诸身”(《王子直文集序》)的方式,之后再推己及人,“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王子直文集序》),应当“姑思其本而勉充之”(《曾巩集》),思考如何追寻“道”,找到问题本源。曾巩的这种文辞观念,在回复傅权的书信中也有所体现,他夸赞傅权文章:“指意所出,义甚高,文辞甚美。”(《曾巩集》)可见,他提倡文章应该内容充实,“辞”为“道”服务,最好能够“义”高而“辞”美,“文”与“辞”兼具。
但同时,曾巩强调“道”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忽略“辞”。曾巩评价自己祖父的散文“闳深隽美”,即立意高古深远,蕴藉悠长,同时又“长于讽谕”(《先大夫集后序》),即注重辞章方面的表达,后半句又可以体现出他对“辞章尺度”的偏重。《祭欧阳少师文》中赞扬欧阳少师“文章逸发”,读起来“醇深炳蔚”。曾巩认为散文不应只为了表达情感和描绘事物,更重要的是“称物引类,兴言寓怀”,蕴藉深远,让人们看到此物就能联想到彼物,启发思索;适当情况下,注重写作技巧的运用,让语言“丽兼组藻,美轶琼瑰”。他赞誉这种雄壮宽广、蕴意深长的“辞章尺度”,奔放的气势既能够充分表达事实道理,又使其情韵兼具,文道统一。由此可见,曾巩反对过度雕琢、崇尚自然平易的同时,又能兼顾文章的外在形式,质朴中独运匠心,这样的“辞章尺度”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魅力。
二、“辞章尺度”在曾巩散文中的呈现
曾巩的这种既讲究辞章,又反对一味追求辞章的“辞章尺度”,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章法结构、表现手法这三个方面。
(一)语言上追求质朴与雕琢的平衡
六朝以来,文坛上浮靡的风气日益严重。唐中叶,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团体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注重说理的质朴与雅正。从语言技巧角度看,曾巩的散文从容和缓,婉曲达意,言辞雅正。何焯称赞他质雅兼备,“不事雕琢,自然质雅,宋文中不多见”(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他文章的语句大多平实恳切,不一味追求排山倒海的气势,旨在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观点,很少炫技铺排。可简朴并非简单,他在句式和用词角度上能够恰到好处地雕琢,独具匠心。归有光曾评价曾巩曰:“文章意全胜者,词愈朴而文愈高……无一奇语,无一奇字,读之如太羹元酒不觉至味存焉,真大手笔也。”(《文章指南》)
在《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一文中,曾巩展现出了极强的语言功力,他先娓娓道来,阐述柳州风物,告知李材叔“故官者皆不欲久居”的缘由:南越地处偏僻,远离京城,风气民俗也和中州十分不同……车、马、船只需要辗转很多时日,才能返回京城,接着描绘柳州物产之丰富:“果有荔子、龙眼、蕉、柑、橄榄,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属,食有海之百物,累岁之酒醋,皆绝于天下。”这些内容看似与赠序所要表达的情感并无关联,实则藏而不露,婉转达意。同时,曾巩又运用疑问句、反诘句增强气势,先古今对比:“古之人为一乡一县”,他们的品性、道义与仁爱之心“足以薰蒸渐泽”;而如今“大者专一州,岂当小其官而不事邪?”这种委婉的称颂和期许脱离了平铺直叙的藩篱,增强气势的同时又起到发人深省的效用。
(二)章法结构上追求布置得当
曾文的构思排布很有讲究,逻辑严谨,可谓“字字有法度,无遗恨矣”(吕本中著,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朱熹称赞他“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朱子语类》)。这里的“布置”,指的是对材料谋篇布局的安排和文章结构的把握。在《王子直文集序》中,他先引用《诗》《书》,并得出从唐虞到秦鲁之际,相差上千年,而“其作者非一人”的观点,先说明三代之弊,再娓娓道来王道衰微之时,做文章要符合先王之意,因为国家的乱与治对文章影响很大,而文章的好坏又会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不同层面的反作用。
曾巩常常精心排布材料,文章笔走龙蛇,用线索环环相扣,严密照应。《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是一篇赞誉颜真卿平定叛军经历的作品,以第三视角记录并展现了颜真卿的从政经历:宰相不满于他的种种做法,“斥去之”;接着,他又被御史唐诬陷,“连辄斥”;后来,他率领官员们问候圣上的起居生活,招致厌弃,“又辄斥”;代宗时期,他与元载争论是非,元載和他政见不和,他极力与之论辩,“又辄斥”;杨炎、卢杞是德宗时期的宰相,也对他种种行为有所不满,“连斥之”……文章以“斥”为线索,将他被排挤构陷、被逐步边缘化的凄惨境遇描述得生动贴切,同时为后续的议论做足铺垫,使读者有极强的体验感和代入感,丰富了文章的层次。明代的散文家茅坤读过之后感慨道:“令人读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这种类似的材料章法,在曾巩的启和表等文体中都得到了彰显。
和他同时代的散文家比较,朱熹曾这样总结道:曾巩的散文“较质而近理”,东坡则“华艳处多”,和王安石散文相比“文亦巧”。由此可以看出,曾文在说理上更为朴实无华,内容设置上精巧且饱满,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失为一代古文大家。
(三)合理运用表现手法
《宋史·曾巩传》对曾巩散文特色有着这样的评述,认为他的散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是很难得的。他在创作时恰当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使得散文呈现出这种“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的特质,言语平缓朴素,娓娓道来,哲理深刻却不奥晦。
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曾巩采用对话体的表现手法展开论述,“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这样可以使得后代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这样就能够“以戒则明”。曾巩笃信儒家经典和圣人之道,他读书讲求博采众长,吸纳百家之言。因此,他认为当百家之书和儒家要义有所冲突时,不应该直接将其禁绝,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厘清其内在缘由、讲明道理,从而使得读者通过理性思考明晰百家之说的真伪。曾巩以两个人物的问答与辩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将不同思想的碰撞呈现出来,同时,其所运用的语言也具有生动、活泼、个性化的特点。
曾巩这篇序的主旨在于驳斥刘向关于策士们为了迎合君主而不得不用特殊谋略的观点:帝王们治理国家“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这都是为国家而效力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他认为,治国之“法”可以变革而“不必尽同”,治世之“道”应该坚持而“不可不一”,这些都基于他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文章内容先立后破,又自设问答,逐层深入,短短一篇既清楚地介绍了书籍的整理经过,又准确地概括了该书的内容主旨。如曾子固所评述:“无一奇语,无一奇字,读之如太羹元酒不觉至味存焉,真大手笔也。”(《战国策·目录序》)
三、曾巩散文创作“辞章尺度”的成因与来源
曾巩形成这种讲求辞章,而反对专务辞章的“辞章尺度”,与当时的文坛风气、他的生活环境与自身经历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文学复古思潮
曾巩成长的时代学界大兴复古思潮,主张回归文风的自然朴素,避免过多修饰和华丽辞藻。范仲淹曾痛心于当时的文坛现状:治学之人“不根乎经籍”,从政的人“罕议乎教化”。因此,此时文章大多“柔靡,风俗巧伪”,倡导有识之士“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上时相议制举书》),将宗经明道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在曾巩求学时,五经六艺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根据《子固先生行状》所记载,他“生而警敏”,“读书数百千言,一览辄诵”。他在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后,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随后又承担编校书籍的工作,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等职务,对经史子集的研究颇为深入。
在《读贾谊传》中,曾巩表达了三代两汉之书中“奇辞奥旨”,给自己带来的精神上“光辉渊澄,洞达心腑”的愉悦充实,使他的内心通达,气韵饱满。而这些古书之中存在着一些义理深奥的文章和见解,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思维广度。这些经学书籍语言往往古雅平正,立意高古深远,“其高足以凌青云,抗太虚,而不入于诡诞”,儒家经义可以使人“抗太虚”,坚定自己的意志品格,免于陷入荒诞境地。这也是曾文内容翔实,道理根基稳固、文辞雅正的原因。他正是在其中汲取养分,逐渐形成了自己“反对过度雕琢”的“辞章尺度”。然而,他又认为在这些三代两汉之书中,有些言辞出于“无聊”的部分亦有不妥之处,阅读之时不免会觉得“忧愁不忍”。
(二)师友影响与家学渊源
曾巩师承欧阳修,和苏轼、王安石是很好的朋友。欧阳修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复兴先王古道,追求淳朴简易、浅切易懂的散文风格。在提倡文章简易平淡的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对语言的锤炼,简易不是简陋,平淡却不寡淡。“事信言文”是他所推崇的观点之一,即认为文学作品应当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才能具有生动的鲜活感。曾巩继承了这种创作风格,在“辞章尺度”上努力做到简洁与推敲的二者兼顾,基于事实出发阐述义理。这种文辞观是对他的老师欧阳修“事信言文”的观点的继承。同时,曾巩也赞同欧阳修对于“言”和“信”重要性的强调,认为作品应当以真实的语言进行表达,注重语言的准确、简练、优美,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更为精准地把握了“文”“道”二者的关系。
家学渊源对曾巩创作的“辞章尺度”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祖父曾致尧和父亲曾易占都是北宋的著名大臣,父子两代皆以儒学立身,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散文创作注重关注现实,以言辞精准和艺术性高而见长。曾致尧也在朝廷中担任重要位置,兢兢业业。欧阳修曾高度赞誉他,称他“言事屡见听用”(《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曾致尧的文章多为雅致古朴之作,基本没有崇骈尚俪的痕迹,并且都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感悟。其子曾易占的文章也同样造诣很高。王安石曾评价他的文章“及试于事,又愈以有名”(《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父子两代皆以儒学立身,致力古文复兴。他们对经典的深入理解和辞章技巧方面的造诣被曾巩所承传,对曾巩文辞观念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在曾巩的创作和生活中根深蒂固,从而促使他形成了守成持重的个性。曾巩做事不喜张扬,性格温和,很少与人冲突,在从政生涯里也往往深藏锋芒。曾肇评价他“性严谨而待物坦然,不为疑阻”(《曾巩行状》)。因此,他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个性也体现在了文学创作中,在“辞章尺度”上追求义理与文辞之间的平衡,恰到好处。他在创作时常使用对话体等较为含蓄的表达方式,追求客观真实,很少代入自己的感情色彩,在评价事物上始终坚持着公允的原则。曾巩认为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公与是”的墓志碑铭,而且指出辞若“不工,则世犹不传”(《寄欧阳舍人书》)。在他的文辞观念中,文章中所蕴含的“道”是立言之基础,他注重作品的内涵和真实的表达,不浮夸堆叠。与此同时,他又运用较为丰富的“辞”,使文章更有艺术感染力。
曾巩以高超的文学造诣扬名于世,他的文章受到广泛追捧与赞誉。许多文士“皆称其有才”(陈襄《古灵集》),争相传抄他的文章。王安石肯定他的文学论著水平,并称其“不见可敌”(《临川文集》),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樹立起了一座丰碑。这和他独具特色的“辞章尺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以其质朴文风和注重技法的风格,为后世散文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曾巩的文辞观,促使他更加注重真实情感的表达与形式技巧的考量相结合,使得艺术感染力加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鉴赏产生了影响。《古文关键》是南宋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古文选本之一,吕祖谦在编纂之时,特意选用了韩愈、曾巩等八人文,分条缕析阐述其可借鉴学习之处,被时人当作学习的范本。吕祖谦追求文风刚健有力的品格,对曾巩《战国策·目录序》中“放而绝之,莫善于是”的观点,评曰“结有力”,“平易之中有千钧之力”,短短一段文字却“甚有力势”(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这种平易中的“力势”,看似平淡的语言中却蕴藏深意,这正是“辞章尺度”的彰显。
曾巩的“辞章尺度”也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文辞观念对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曾巩文章的语言自然淳厚、温醇典雅,这离不开对经学的深度接受。方苞曾评价曾巩“笃于经学”,故行文“颇能窥见先王礼乐教化之意”(《唐宋文举要》),认为曾文能够将“文”“道”二者合理地融合在一起,立意颇深且文辞并不晦涩,在质朴说理与文学技巧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曾巩散文文辞平雅和缓、雍容严正,语言“峻而不庸,洁而不秽”(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符合宋人平易质朴的审美需求。他文辞观念中讲求辞章,又反对一味追求辞章的“辞章尺度”,又恰好契合了宋人精神世界里对于“中庸”的追求,也启发了许多理学家的思考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