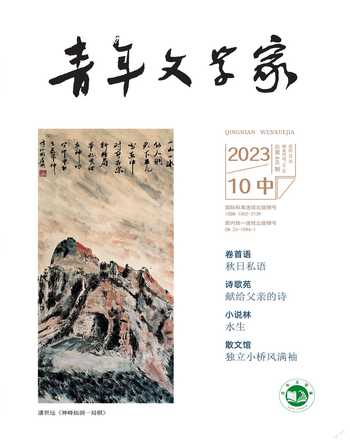时间的衣冠冢
刘晨曦
南方的九月向来多雨。晒衣服时要把天气的阴与晴“摆上赌桌”,再怎么权衡斟酌仍无法避免突如其来的大雨,挂上去的衣服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要“抢收”—我戏称之为现代城市的“双抢”。本以为我早就习惯了雨天,没想到空气中过多的水分仍然令我浑身难受。迟暮的夏天困兽犹斗,但终究逃脱不了四季的轮回交替。阳光虽然依旧强烈,但九月的遗憾已是“起于青蘋之末”了。余下的时光,是属于回忆的“物候期”。
前几天,好友打趣我,说我是个分不清主次的人。我对此大为好奇,连忙追问此有何意。好友抵不过我的坚持,敷衍道:“你总是记得一些没用的事情。”
此后的三五天,我都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记忆有用吗?什么是有用的记忆,什么是没用的记忆?如果一个人分得清主次—至少得是我的反面人物,那么他记住的都是有用的东西吗?
好友大概是说中了,我的确是个分不清主次的人。或者说,分不清“有用”和“无用”,让人觉得我分不清主次也在情理之中。我无法想象一个只拥有“有用”的记忆的人,他的这些记忆指的是知识吗?那他的大脑必然得是一台精密的仪器,除了必需的知识之外什么也没有,更不会突然陷入白日梦或旧日回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假设世上真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真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与他一定无法相互理解吧。
最近记忆总是莫名其妙地回到2011年的夏天,那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坏掉的电视机,《怖客》漫画,玩具反斗城,陀螺比赛……每一个夏日午后,我们或玩着电脑游戏,或扮演着福尔摩斯。某天,我正在哭泣时,他来敲门,我却没有理会。那时,我只想着不要让他看见我通红的眼睛,但没有想到这是十年里最后一次见面。再相遇时,我们都成了陌生人。虽然,有关他的消息仍然会在某些时刻出现在我眼前。他似乎一直都很优秀,知名大学,本硕连读,大厂实习,但是这些词语对我而言,仍然太寂寞、太不可思议,既接不上十年前的陀螺,又拼不出十年后的照片。
只有他四岁的妹妹很喜欢我,看见我回家就会准时来敲门。我虽然不喜欢和小孩子玩儿,但从来不会将她拒之门外,也许也是替我自己打开了十年前那扇紧闭的门,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在四岁。
后来,我遇到的另一个有意思的朋友,是一位小学的厨师。那会儿我在学校午托,每次都有厨师上来发饭盒,我就是这样和他说上话的。我留意到他,是因为他胡子很长,皮肤很黑,很像印度人。当然,那时候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印度人长什么样,只是觉得他有种让人想去印度养眼镜蛇的魅力。
童年的我,也是个很奇怪的人。比如,我会把午托想象成是一趟长途列车的中间休息,所以,得抓紧时间在走廊上活动筋骨。那时,他刚好路过,看见我在那儿蹦来蹦去,觉得我很奇怪。当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之后,他倒没觉得我很幼稚,而是和我一起蹦了几下。于是后来我常常去找他玩儿。但那时候流行“损友”的说法,试想,一个厨师和一个爱顶嘴的小学生之间有什么好话可说呢?总之,我们之前不是很和谐,总想着驳倒对方,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损友”吧。
那几年有一首歌很火,是汪峰的《春天里》。某天,我听到他在哼唱这首歌曲的一段旋律。于是,我很骄傲地对他说我也知道这首歌,可他没理我。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把我埋在春天里。”
我愣住了,而他没有再说话。
果然,他过几天就消失不见了。小学厨师的工作大多来来往往的做不长久。我看他没来送饭,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多年之后,我在高三的食堂再一次见到了他。我认为那一定是他,但我没有上前去搭话。而他只是用很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我打赌他没有认出我来。
我不上前的一大原因,是现在的他和我记忆里中的样子差得太多了。他的胡子还在,但是身上没有了那种带着一筐眼镜蛇闯荡印度的江湖豪气。
我确实很想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有过这么一首叫作《春天里》的歌,和一个谁也没当真的承诺。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把他埋在春天里了,十年前的那个春天。
文艺作品经常出现儿时玩伴十年后相遇的戏码,但作品永远是作品,现实中的十年只会让记忆里查无此人。说是意难平有些不妥,毕竟只有我还锁在2011年的记忆里,儿时的他们都在那个夏天之后离开了。
我记忆中的另一部分被食物占据着。食物能维系记忆的原因,也许是食欲在童年里填补不尽的欲壑。这类欲望往往伴随着欺骗,用一点儿油脂欺骗味蕾,然后再欺骗晚饭前的父母。我无法忘记那充满海水的游泳池,再次经历时,还是能闻到当初海水和氯水混杂的难闻又潮湿的气息。油脂的味道和海水都是一团幻象,一如长大后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吃进嘴里的究竟是食物还是童年的虚影,吃掉的食物难道只是欺骗吗?
当然,即便是欺骗,现在的我也已经失去了它们。这样的记忆是无用的吗?也许是吧,那依赖这些记忆拼凑而成的我呢?我是靠回忆活着的人,只有童年是一片空白,但它仍会在这片雾气里显出轮廓来。现在的生活越痛苦,过往的幻影就越会频繁地在我眼前闪回,并一次次地击中我。说不出是悲哀还是心惊,我怀念的仅仅是所谓时间的衣冠冢。
过去是失去吗?得到会失去吗?记忆是对失去的不承认吗?
小时候拿到新东西,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上名字。如今,我仍然在不停地签名,却不再为什么东西写上我的名字了。每个签名都代表我将自己分离出去的一部分,却再也不代表有什么确切的事物进入过我的生活。如果已经没有东西是真正属于我的,那么自然也谈不上失去。
因此,我试图抓住每一片记忆的虚影,只有记忆是我的,只有梦境是我的。几天前坐高铁途經广州南站,在进站的瞬间,我看到了高架桥下的人群,小吃摊儿,充满烟火气的街道。它们笼罩在暖黄色的街灯下。高架桥上却是如雾一般流动的黑暗。这一幕一闪而过,甚至没有占据我整个视野的十分之一。但一直到现在,我的思绪还总是会回到那个瞬间。这个世界触动我往往只需要用一个瞬间。六年前,我从高速路上回家,偶然一抬头,眼前只有两栋楼闪着灯光,在浓稠的黑暗里,它们就是全天下的灯光。这束灯光直直地撞进了我的眼睛。每当我恍惚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在我的视网膜上出现。我知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至少在这一刻,它们只属于我。
不要忘记,哪怕只拥有世界的一个瞬间。
古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夜以继日地编织人类的一生。我仍在徒劳而永不停歇地为记忆的碎片树碑立传。窗外的雨仍然在下。我已经不再纠结记忆的来处与归途。它们有用,也许无用;也许有意义,也许无意义,但至少它们做了一件事—让我成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