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多夜雨,岭南有春风》
聂雄前
湖南省双峰县人。现为深圳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兼任海天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出版有《中国隐士》《与时间拔河》等专著,电视专题片《道德的力量》《最后的村庄》《绿色家园》撰稿人。曾获首届南粤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首届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物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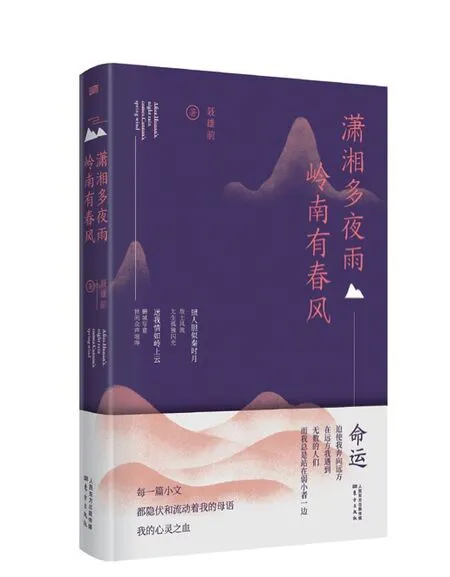
《潇湘多夜雨,岭南有春风》聂雄前 著/东方出版社/2021.3/59.80元
1992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加盟《女报》杂志社,急于一露身手。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深圳义工的报道,我觉得这是完全新鲜的题材,就拨通了报道中公开的义工热线电话联系采访对象。在荔枝公园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一间办公室和那位女义工见面的那个晚上,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双峰口音痛不欲生。那位清秀的潮州女孩在银行工作时间不长,或许还从来没有接触过湘中地区的人,从我自我介绍开始她就像遇见外星人一样惊讶,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一脸茫然,她很紧张,怀疑我的身份并检查了我的工作证,又打了电话给同事讲有一个人在采访她,然后她叫我把问题写在纸上,她一个一个回答。屋漏偏逢连夜雨,中间还碰上停电,她找蜡烛时我一动不敢动,汗如雨下……噩梦一般的采访终于结束了,我骑着单车回莲花二村蜗居的路上,第一次嗅到了前路险恶的味道。
那次采访稿在1992 年8 月号的《女报》杂志上作为头条发出,义工女孩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你的人、你的话为什么和你的文章完全不同呢?她还是很惊讶。她不知道这次失败的采访让我此后高度重视案头的准备工作,把能够找到的关于采访对象的资料都认真研究透,把想问的问题列出清单,现场只剩下简单的验证并鼓励对方讲故事。二十多年来我写过的人物稿有上百篇,从深圳本土诞生的全国道德模范陈观玉老人、海外归来创业成功的女总裁,到工厂流水线上冒出来的天才女诗人,文中我都尽量藏匿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让她们保留原汁原味的自己。然而方言之病在写作上能找到对症之药,在生活和工作中却无处不在释放它的痛感。
许多长者和领导对我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改。在《女报》杂志社干了四五年后,我动过调动的念头,把调函送到主席那里时,主席一脸沉重:“小聂,不是我不放你,而是你要想想你的短处。你年纪轻轻就当了老总,到别的单位谁听得懂你的话呢。”我一身冷汗。在《女报》杂志社工作二十二年期间,我参加过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写作组,为深交所、华侨城等大型企业当过多年的写手,不是没有机会,但自知之明总会自然地制止我的冲动。我从不在研讨会上发言,也谢绝过要我担任诸如市出版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娄商会会长之类的好意,尽量拒绝陌生人的邀约。唯有一次,作为“三打两建”专项活动调研的发起人,我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做过一次大会专题发言。我认真写了一夜稿,念起来抑扬顿挫、声音洪亮,但结束之后好几位相熟的代表都对我说:“聂总,你讲得很好,但我没太听懂。”
我再不能讲自己生命中的羞愧了。
事实上,这种羞愧对于从湘中丘陵地区走出来的乡亲而言肯定是普遍且深刻的。几年前,龙应台在《南方周末》上撰文讲她的父亲龙槐生:“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作为女儿,龙应台尚且是在送父亲骨灰还乡时听族中老人用乡音念祭文才有这份觉醒,才发出了“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的痛悟,我当然无法指望别人的了解或聆听。
其实,双峰人窘迫和羞愧的历史并不太久。以1955 年年底中国推广普通话为界,双峰人在此前都大大方方称自己为湘乡人,托曾文正公的福,至少享受过百来年的语言强势。湘军的组建依托于湘乡的子弟兵,湘军的胜利带来了清朝的咸同中兴,也带来了湘乡人才在全国各地的受重用,所谓国之督抚十之八九出自湖湘。我的父亲宗儒公、伯父宗藩公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到贵阳、成都做过生意,如鱼得水,他们从未跟我诉说过语言的隔膜之苦。而1955 年到1980 年之间,双峰人大多活在乡土社会的熟人之中,自得其乐,方言之痛只发生在极少数跃龙门的大学生和进兵营的军人身上,显得微不足道。我认为双峰话(老湘方言)成为双峰人的“痛”和“病”一定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有文正公留下的文脉,我们不怕高考这座独木桥的狭窄,初中老师的儿子胡庆丰第一年(1977年)就轻轻松松考上了北大;我们不怕吃苦,下深圳的百万打工妹中有许多双峰人的身影;我们不怕牺牲,中国无论哪一支部队都愿意招湘军的后裔……这个时候,双峰话作为祖国古音保留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所到之处遇到尴尬是无可避免的,遭受创痛也是无可避免的。他们难以用乡音演讲证明能力,更难获得升迁机会;他们难以用乡音念诗感动别人,很难找到异性朋友在异乡成家;他们难以用乡音说服对手,自然很难顺利做成生意。群体性的人口流动四处印证着老湘方言的土气和难懂,就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迂腐的孔乙己一样,但双峰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期待富裕,追求体面和尊重。
作为一个“把故乡天天挂在嘴上”的双峰人,作为一个普通话讲得很差的异乡人,我在深圳的遭遇和感受在走出双峰的游子中并不是特例。我在大学的老师陈宗瑜先生和王建章先生,在长沙工作时的师长谭冬梅先生,在深圳的好友宋渤海和李希光等师兄,都是同一个乡村走出的英才,尽管他们都事业有成、众人称羡,但在我看来,或许他们都没能达到自身期许的高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乡土赋予他们的口音和性格。我想说,湘军的辉煌岁月早已是久远的记忆,让全中国迁就湘乡话(含双峰话)在过去没能实现,在未来也绝无可能。因此,老湘方言的逐渐消亡应该就是几十年内的事了。
在我看来,双峰话所代表的老湘方言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存在啊!这种语言生气如此饱满,个性如此鲜明,古意如此盎然,结构如此合理。我们把出生讲成“落地”,是何等精辟!父母交代我们做任何事情,结果总是用“道路”来考量——“你咯哒道路做得么子样”“你咯哒道路都做不成,还能做么子”是何等高度!老人总是用“执古”来教育我们,“你看人家的手艺做得咯样执古,学着点呵”“你看人家的字写得执执古古,你怎么得了”,那一声叮嘱那一声叹息,是何等源远流长!我们在惊喜时大喊的是“妈得了”,在悲伤时大喊的也是“妈得了”,是何等的至情至性!在双峰话里,族群的文化密码若隐若现,把上厕所文绉绉地讲成“解手”,其中暗含血腥的暴政:我们的祖先从江西移民而来,大多数人安土重迁,不情不愿地被兵士捆绑而来,上厕所总得大喊“解手”吧。中国人都知道“敲竹杠”的含义,但竹杠是怎么与敲诈联系在一起的,却只有我们知道。当曾文正公率领的湘军攻下天京,洪秀全十来年间从大半个中国掠夺的金银财宝都成了湘军的战利品,既然是战利品,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往老家运,于是想出了把楠竹掏空的绝招。那个年月没有飞机汽车火车,由南京长江码头沿江上溯到洞庭湖转湘江再转涟水,竹排连绵十几里,沿途镇关守卡的清兵面对得胜还乡的湘军时就敲敲竹杠,湘军便大大方方奉上买路钱,彼此心照不宣。这样鲜活的语言,这样深厚的文化,这样自然的人性,这样悲壮的生命,也许很少有人理解其价值了。但毛泽东主席理解,他把极高的赞誉给了两个双峰人(原属湘乡)——“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故乡三里一公祠,五里一庄园,学校、医院、供销社和乡村政府机关都装在这些湘军祖先的遗产里。春日寂寞的下午,我有时就坐在神公祠的门槛上发呆,看春燕衔泥,看春雨打荷,看春风吹柳,看春牛犁田。教室里空空荡荡,偌大的天井长满青苔,耳边依稀有攻城的炮声滚过,有祖先的足音滚过,有大地的春雷滚过……现在呢,这些遗产连断垣残壁也很难寻觅,只剩下夕阳西下、芳草萋萋的景象。暮色苍茫,暮色很久之前就苍茫了;群山蹒跚,群山很久之前就蹒跚了。故乡只有蹒跚的老人与幼童,他们都一脸苍茫。
有心的故乡朋友所编的这本书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感到心痛。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选择故乡和爹娘,而故乡和爹娘所赋予我们的乡音尽管无与伦比的神圣与高贵,却往往终究会被抛弃。想一想,是操着这种乡音的曾国藩让湖南人异军突起;想一想,是操着这种乡音的蔡畅、唐群英、向警予、秋瑾将中国妇女从裹脚布中解放出来;想一想,是操着这种乡音的人让故乡成为了“院士之乡”“书画之乡”,我满怀敬意。而这种乡音一定是要消亡了,我又怎能不悲从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