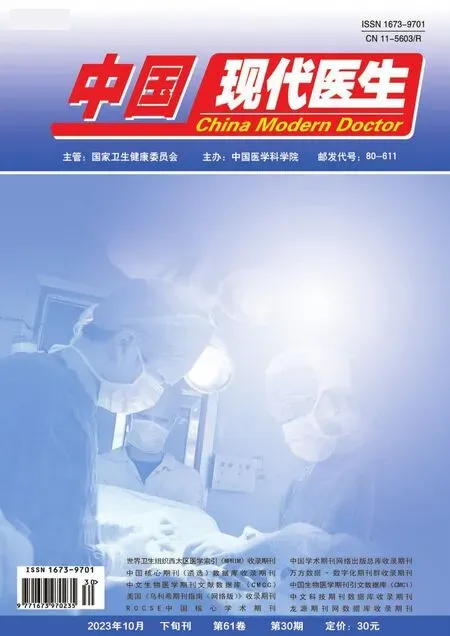健康中国背景下整合医学在乳腺癌防治中的应用进展
彭娟娟,白彤彤,吴勉华,刘振
健康中国背景下整合医学在乳腺癌防治中的应用进展
彭娟娟1,白彤彤2,吴勉华2,刘振3
1.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养生康复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2.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3.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其防治问题日益突出。利用整合医学将乳腺癌的防治措施有机融合,可更好地改善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更好地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本文对健康中国背景下整合医学在乳腺癌防治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健康中国;整合医学;乳腺癌;防治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是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整合医学为解决乳腺癌全过程防治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对健康中国背景下整合医学在乳腺癌防治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健康中国背景下“整合医学”的理念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以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逐年升高。2020年,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为226万例,超过肺癌的新发病例数,是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乳腺癌占女性恶性肿瘤的8%~12%[2-5]。实现全民健康不能不关注女性健康,守护女性健康不能不防治乳腺癌。防治乳腺癌离不开中医中药,“整合医学”理念为中西医结合防治乳腺癌提供理论支撑。
樊代明[6]研究认为,“整合医学”理念提出的目的在于“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专科划分过细、知识碎片化带来的诊疗局限性问题”。樊星等[7]研究认为,整合医学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并根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以人体全身状况为根本,进行修整、调整,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学体系”。具体而言,“整合医学”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以患者为起点;有机整合多种诊疗方式,呼吁中西医结合;最终使患者痊愈,守护人类健康福祉。肿瘤防治是整合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突破口[8]。中医体质辨识手段有助于乳腺癌的预防;中西医结合方式可更好地治愈乳腺癌;在身心结合理念下,神形兼顾的生活方式可更好地防止乳腺癌的病变和复发。
2 体质辨识预防乳腺癌
不同体质对疾病的易患性和倾向性有决定性作用。在肿瘤疾病中,体质与肿瘤的发病过程关系密切[9-10]。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患癌与不患癌的根本原因在于体质的不同。通过中医体质辨识,可调整偏颇体质,达到预防乳腺癌的目的。体质辨识和调理是乳腺癌防治的核心[11]。
郭鹏等[12]研究表明,单一乳腺癌高危者体质分布规律(由低到高)依次为平和质、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气虚质和血瘀质、阴虚质、气郁质和特禀质。马然等[13]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体质主要为气虚质(21.3%)、气郁质(15.3%)、阴虚质(15.3%)、瘀血质(14.7%)。这与雷叶雁[14]、张晶等[9]、岳立云[15]的研究结果一致。气虚质、气郁质、阴虚质、瘀血质人群更易患乳腺癌。研究认为,平和质是乳腺癌发病的保护体质[16];气郁质是乳腺癌的危险体质[17]。
中医体质中的特禀质与现代医学中的易感基因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乳腺癌的预防措施上,以达到平和质为目标,纠正偏颇体质,调整阴阳平衡,从而减少乳腺癌的发生。在临床应用中,可通过体质评估量表对患者进行体质评估;对于偏颇体质患者可通过纠正不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对症调理,将患者体质调整为平和质,从而预防和减少乳腺癌的发生。
3 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癌
乳腺癌是多因素引发的复杂性疾病。目前,手术治疗仍是乳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并辅以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18]。外科手术等临床治疗会给乳腺癌患者带来一系列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中医表现为正气亏虚,余毒未清,癌毒隐匿,毒性猛烈,易走窜,易致虚、致瘀、致痰,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病死。通过中医疗法辩证论治,补气养血,消癌解毒,达到固本培元,提高生活质量,降低乳腺癌的复发和转移率[19]。
术前,可使用具有补益气血作用的四物汤、四君子汤加减,具有补肾益髓生血作用的补骨脂、菟丝子等,通过中医药调整乳腺癌患者的整体状态,提高免疫力,提高身体机能。术后,亦可通过中医药改善患者的消化不良、食欲减退、便秘、伤口疼痛、伤口感染、皮瓣坏死、焦虑抑郁、继发性失眠等不良反应。焦神曲、砂仁、淮山药等具有促进消化吸收的功能,焦山楂等中药可增加患者食欲;绿梅花、合欢花等可调节患者的焦虑、紧张等情绪;石斛、沙参、麦冬等可改善患者易口干、口渴等症状;地榆、鸡血藤可改善患者血小板减低症状;荜茇、生姜等可改善患者经化疗后而产生的恶心、呕吐等症状;炒枳实、瓜蒌仁、火麻仁等可改善患者大便秘结症状[20-22]。
晚期乳腺癌较难治愈,但通过辨病灶,可控制肿瘤进展,延缓疾病发展。半枝莲、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具有消癌解毒的作用,且通过辨证论治进行全身和局部调节,可达到防止肿瘤复发的目的[23]。
临床实践证明,乳腺癌的综合治疗效果好于单一治疗方法[24]。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癌的方法可将整体中医治疗与局部西医治疗相结合,优势互补,效果更加全面;同时可减轻不良反应,提高治疗效果,减少肿瘤的转移和复发率,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患者生存率,提高生活质量。
4 神形兼顾防范乳腺癌复发
《丹溪心法》[25]指出,乳痈患者应戒七情、远厚味、解郁结、养气血。乳腺癌患者在术后,精神上应畅养情志、安心休养;起居饮食上应适时适地有度运动、调理饮食,养护身体,不劳累,不忧伤,坚固战胜癌瘤、回归生活的信心。
4.1 精神上:遣情逸志,减压安心
研究表明,情志失调是乳腺癌发生发展的重要诱因,同时也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转归密切相关[26]。《外科十三方考》[27]曰:“乳岩则因七情气郁而成。”《金匮翼·积聚统论》[28]曾载:“但凡多忧善思,且长期无法化解者,常患此疾。”《疡科心得集·辨乳癖乳痰乳岩论》[29]谓:“夫乳崴之起也,由于忧郁思虑积想在心,所愿不遂,脾气逆,以致经络痞塞,结聚成核,”以上均说明,情绪是乳腺癌发病的重要因素,气机郁滞是乳腺癌发病中的重要因素。
经络理论认为,乳房属胃,乳中属肝,病位归属脾胃肝经脉,故此类病症应予以调理肝脾、疏肝解郁,使气血畅达、津液顺畅,痰瘀不得凝结。以情胜情、转移注意力法、开导法、正念减压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方式可调畅乳腺癌患者情志,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30]。
压力是生物体对环境扰动的自然反应,压力反应的急性激活使个人更具适应性。但慢性和创伤性压力源会产生相反效果,导致大脑和其他器官发生有害变化,乳腺癌便是其中之一。黄体酮和雌激素水平的变化与雌性应对压力的反应方式有直接影响,升高的应激激素会对生殖神经内分泌轴产生负面调节,从而对循环性腺激素的水平产生负面影响[31]。适当减压安心有助于改善体内激素水平,确保身体健康。
4.2 身体上:动静结合,食疗护身
《吕氏春秋·达郁》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提示应适当体育锻炼,促进气血流畅,达到增强免疫力、提高抗肿瘤的目的。研究发现,保持规律运动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可降低14%[32]。Mishra等[33]观察发现,适度锻炼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主要的运动干预包括有氧、无氧、有氧与无氧组合形式,侧重于心肺、肌肉骨骼、神经肌肉调节。Kim等[34]推荐步行、跑步、瑜伽、太极和普拉提等运动类型,但是认为运动量需适度。吴瑕[35]研究认为,“劳倦内伤”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饮食和营养是肿瘤预防的有效策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要求患者改善不良饮食习惯,包括戒烟戒酒,改变高钠、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新鲜时令蔬菜、水果和粗粮类等食物的摄入[36]。水果中高含量的多酚可使其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有助于降低肿瘤的风险[37-38]。西兰花、花椰菜、豆瓣菜和布鲁塞尔豆芽十字花科蔬菜是对乳腺癌细胞具有较强抑制作用的蔬菜[39]。一些香料及其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乳腺癌活性,如生姜中的姜酚、大蒜中的有机硫成分、黑孜然中的百里醌[40-42]。Li等[43]研究证明,蘑菇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其摄入量与患者患乳腺癌的风险呈负相关。Park等[44]研究认为,高粱、大麦和小麦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潜力。
5 小结与展望
“整合医学”理念贯穿女性健康始终。未病之时做好预防;发病后采取中西兼治,并注意防变;病后养护,心身俱调,防止复发。中医体质辨识和改善体质的思想有助于女性远离乳腺癌。对于确诊乳腺癌患者,手术治疗是其首选治疗方法。中医诊疗可通过辨证施治,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而减轻放疗、化疗的不良反应,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延长患者的带瘤生存期。术后修养应做到动静结合、神形兼顾、内外兼修。中医传统养生方式有助于患者形成“正气存内、身健固本”的良性循环。“整合医学”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更多福祉,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积极理论支持。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2023-05-31]. https://www.gov.cn/zhengce/ 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 孙怀庆. 中药湿敷联合淋巴按摩对缓解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作用分析[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22, 35(15): 2589–2591.
[3] 陈茂山, 吕青. 《基于人口登记数据2000—2020年全球乳腺癌发病和死亡率分析》要点解读[J].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2, 29(4): 401–406.
[4] CAO W, CHEN H D, YU Y W, et al. Changing profiles of cancer burden worldwide and in China: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J]. Chin Med J (Engl), 2021, 134(7): 783–791.
[5]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 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1, 71(3): 209–249.
[6] 樊代明. 整合医学纵论[J]. 医学争鸣, 2014, 5(5): 1–13.
[7] 樊星, 杨志平, 樊代明. 整合医学再探[J]. 医学与哲学, 2013, 34(5): 6–11, 27.
[8] 顾芳慧, 仲西瑶, 孙光宇, 等. 整合医学模式在肿瘤专科医院管理中的应用实践[J]. 中国医院管理, 2021, 41(4): 91–93.
[9] 张晶, 万冬桂, 毛万鹏, 等. 118例乳腺癌中医体质类型与分子分型关系的临床研究[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9, 13(1): 140–142.
[10] 张晶. 乳腺癌中医体质类型与分子分型关系的临床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11] 卢雯平, 卓至丽. 乳腺癌的中医药防治现状及展望[J]. 中国医药, 2022, 17(3): 321–325.
[12] 郭鹏, 邹志东. 北京社区乳腺癌高危人群中医体质分布特点研究[J]. 河北中医, 2017, 39(6): 839–843.
[13] 马然, 张立清, 鲁海燕. 乳腺癌患者体质与证型分布情况及相关性研究[J]. 中医药导报, 2017, 23(19): 99–101.
[14] 雷叶雁. 乳腺癌高危因素与中医体质类型的相关性研究[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8.
[15] 岳立云. 高危乳腺癌患者的中医体质特点及个体化治疗探讨[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4.
[16] 吕晓皑, 王蓓, 杨瑞文, 等. 302名乳腺癌高风险人群中医体质研究[J].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 25(10): 974–976.
[17] 邹彩婷, 张梦霞, 王诗韵, 等. 中医体质类型与乳腺癌相关性的Meta分析[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24(12): 157–162.
[18] 华利勇, 张琼. 中医中药在乳腺癌化疗中的应用效果[J].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5, 10(2): 76–77.
[19] 侯公楷. 中医药防治乳腺癌进展[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18(5): 249–253.
[20] 刘翠芳, 万冬桂. 乳腺癌术后继发失眠相关因素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0): 6188–6192.
[21] 刘文文, 孙喜波. 乳腺癌与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进展[J]. 老年医学研究, 2022, 3(2): 51–55.
[22]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 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乳腺癌整合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 乳腺癌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J].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21, 13(7): 44–64.
[23] 吴晓晴, 崔永佳, 卢雯平. 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试析乳腺癌的中医诊疗特点[J]. 吉林中医药, 2021, 41(12): 1558–1561.
[24] 陈正堂. 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J]. 重庆医学, 2002, 31(2): 65–67.
[25] 朱震亨. 丹溪心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74–275.
[26] 马胜男, 王志鹏, 曹芳. 基于情志伏邪理论探究乳腺癌病因病机的研究进展[J]. 河北中医, 2020, 42(7): 1101–1105.
[27] 张觉人. 外科十三方考[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4–5.
[28] 尤怡. 金匮翼[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145–146.
[29] 高秉钧. 疡科心得集[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55–56.
[30] 乔元鑫, 樊志龙, 马艳苗, 等. 从情志致病探讨乳腺癌[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2, 34(3): 409–412.
[31] RIVIER C, RIVEST S. Effect of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 axis: Peripheral and central mechanisms[J]. Biol Reprod, 1991, 45(4): 523–532.
[32] MCTIERNAN A, KOOPERBERG C, WHITE E, et al. Recre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cohort study[J]. JAMA, 2003, 290(10): 1331–1336.
[33] MISHRA S I, SCHERER R W, SNYDER C, et al. Exercise intervention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with cancer during active treatment[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8): CD008465.
[34] KIM D R, SOCKOL L, BARBER J P, et al. A survey of patient acceptabilit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during pregnancy[J]. J Affect Disord, 2011, 129(1–3): 385–390.
[35] 吴瑕. “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黄帝内经》的现代养生价值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18, 29(2): 404–405.
[36] 张蒙, 崔永春, 王春平, 等. 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负担及其危险因素变化趋势分析[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22, 29(7): 456–462.
[37] FU L, XU B T, XU X R, et al. Antioxidant capacities and total phenolic contents of 62 fruits[J]. Food Chem, 2011, 129(2): 345–350.
[38] LI Y, ZHANG J J, XU D P, et al. Bioactivities and health benefits of wild fruits[J]. Int J Mol Sci, 2016, 17(8): 1258.
[39] LIU X, LV K. Cruciferous vegetables intake is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breast cancer: A Meta-analysis[J]. Breast, 2013, 22(3): 309–313.
[40] JOO J H, HONG S S, CHO Y R, et al. 10-gingero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MDA-MB-231 breast cancer cells through suppression of Akt and p38MAPK activity[J]. Oncol Rep, 2016, 35(2): 779–784.
[41] ALTONSY M O, HABIB T N, ANDREWS S C. Diallyl disulfide-induced apoptosis in a breast-cancer cell line (MCF-7) may be caused by inhibition of histone deacetylation[J]. Nutr Cancer, 2012, 64(8): 1251–1260.
[42] SCHNEIDER-STOCK R, FAKHOURY I H, ZAKI A M, et al. Thymoquinone: Fifty years of success in the battle against cancer models[J]. Drug Discov Today, 2014, 19(1): 18–30.
[43] LI J, ZOU L, CHEN W, et al. Dietary mushroom intake may reduce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J]. PLoS One, 2014, 9(4): e93437.
[44] PARK J H, DARVIN P, LIM E J, et al. Hwanggeumchal sorghum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through Jak2/STAT pathways in breast cancer xenografts[J]. PLoS One, 2012, 7(7): e40531.
(2023–05–31)
(2023–10–07)
R737.9
A
10.3969/j.issn.1673-9701.2023.30.026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1SJA0324)
刘振,电子信箱:wgbf_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