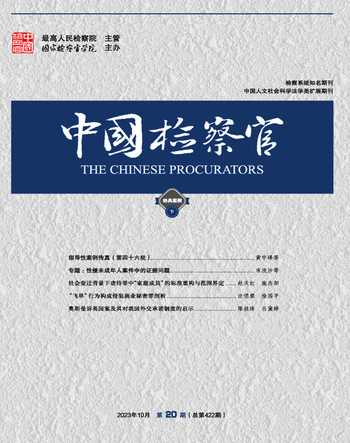奥斯曼诉英国案及其对我国外交承诺制度的启示
陈桂珠 吕黛婷
摘 要:在奥斯曼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制定了判断外交承诺充分可靠性的十一项标准。外交承诺内容明确与主体适格作为外交承诺的生效要件,系外交承诺具有充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由于大部分国家作为《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缔约国负有“不推回”义务,因此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免责”功能。不过外交承诺的适用空间仍然受两国关系、一国法治发展程度以及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待死刑或酷刑态度等因素影响。借鉴奥斯曼诉英国案,我国应该完善外交承诺的要件性规则,构建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制度,有针对性作出外交承诺。同时,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以化解外交承诺的瓶颈问题,并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度发展。
关键词:外交承诺 充分承诺 不推回原则 国际追逃
一、问题的提出:奥斯曼诉英国案
奥斯曼诉英国案,是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法制定外交承诺充分性标准的关键性案例。
约旦公民奥斯曼(Othman)(在案情介绍中简称“申诉人”),于1993年9月逃往英国,并以曾被约旦当局非法拘留、施加酷刑为由,在1994年被英国当局承认其难民身份,并获准居留到1998年6月30日。而在约旦国内,1999年和2000年針对两起案件的审判中,申诉人被认定参与恐怖爆炸袭击活动而被判“串谋制造爆炸罪”。2002年10月23日,英国以国内反恐法案为依据,逮捕了申诉人。2005年8月10月,约旦与英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保证被遣返者能够获得适当的治疗、对被遣返者的拘留进行司法审查、拘留、逮捕或指控等事项及时通知被遣返者、被遣返者能够获得独立机构代表至少两周一次的探访和交流的机会等保障人权标准,同时,约旦表明其有能力在个案中不判处死刑。2005年8月11日,英国国务大臣向申诉人送达驱逐出境的意向通知书。基于此,申诉人向英国国内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上诉法庭认为,外交承诺与返回安全的相关性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上诉法庭无管辖权。因此上诉法庭于2008年4月9日驳回申诉人就谅解备忘录、酷刑以及外交承诺问题的上诉。
最后,申诉人于2009年2月11日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声称申诉人被遣返约旦存在遭受酷刑的风险。欧洲人权法院考察了加拿大等国家,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关于外交承诺充分有效性标准的相关判例。在此基础上,提出判断外交承诺是否具有充分性、可靠性的十一项标准。这十一项标准分别是:(1)承诺的各项条款是否已向法院披露;(2)承诺的具体内容,是具体的还是笼统和模糊的;(3)作出承诺的代理人是否能够约束接收国;(4)如果承诺是由(被遣返人)接收国中央政府发出的,是否可以期望地方当局遵守这些承诺;(5)这些承诺所涉及的待遇在接收国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6)承诺是否由缔约国提供;(7)两国关系是否牢固持久,以及(被遣返人)接收国是否遵守类似承诺的记录;(8)是否可以通过外交或其他监测机制客观核查承诺的遵守情况,包括不受限制地接触申诉人的律师;(9)(被遣返人)接收国是否有防止酷刑的有效保护制度,包括它愿意与国际监测机制(包括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及是否愿意调查酷刑指控并惩罚责任人;(10)申诉人以前是否在接收国受到虐待;(11)承诺的可靠性是否已经过派遣国国内法院的审查。
结合联合国报告等材料对约旦人权状况的评估,欧洲人权法院重点考察“谅解备忘录中包含的外交承诺以及双方指定的独立机构‘Adaleh(the Adaleh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Studies)的监督是否消除了虐待申诉人的任何实际风险”。最终,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和约旦政府已作出真正的努力,争取并提供透明和详细的外交承诺,以确保申诉人返回约旦后不会受到虐待。基于谅解备忘录已经得到约旦政府高层和国王的批准与支持,因而约旦有充分动机严格遵守谅解备忘录。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得出结论:申诉人返回约旦不会使他面临遭受虐待的真正风险,因此将申诉人驱逐回约旦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待遇)。[1]
可以看出,充分可靠的承诺,才能使外交承诺得以履行或执行的现实可能性最大化。从上述列举的因素来看,不仅涉及“历史”的要素,如接收国是否遵守类似承诺的记录,也涉及“未来”的要素,如未来是否可以通过监测机制核查承诺的遵守情况等等。而且,在国际法实践中,往往反向消极的评估要素在决定外交承诺是否可靠问题上所占比重更大,如欧洲人权法院最为看重请求国是否遵守承诺的人权记录[2] 。另外,相较于部分学者以及国际人权机构对外交承诺持否定性态度,即认为其不足以预防或改变个人可能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风险,反对外交承诺[3],欧洲人权法院更倾向于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不仅认可各国以驱逐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国民的方式打击恐怖、贪腐等犯罪,同时,也并不禁止那些曾经存在酷刑与虐待现象的国家寻求适用外交承诺,而是在具体个案中考察外交承诺是否能够消除申诉人遭受酷刑的风险。
二、外交承诺制度的充分性规则适用
目前在国际法中,并没有以统一的方式明确界定何为“外交承诺”。不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关于外交承诺和国际难民保护的说明》中,将外交承诺定义为“在将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接收国承诺将按照派遣国规定的条件,或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对待被转移人”。[4]这一定义主要针对遣返或驱逐出境等移民法措施,虽然指出了承诺的方式,但未能展示外交承诺具体的内容和种类。结合外交承诺的适用背景,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国际追逃追赃合作过程中,请求国向被请求国作出的关于被请求人被移交到请求国后,对于被请求人的刑事追诉、量刑、相关诉讼权利以及其他人道待遇等方面的正式承诺或保证,并有相应机制和规定保障其承诺兑现的制度。
(一)前提性条件:外交承诺的要件及效力
首先,外交承诺的内容需具体明确,内容含糊的承诺不被认为是有效的承诺,反而可能仅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政治声明。如果一国作出的承诺内容既没有明确被追诉人回国后的权利和可能的待遇,也没有包含有效的监督保障措施,这种承诺往往被视为没有法律效力的“政治声明”。[5]其次,外交承诺由实际主管机关作出保证或承诺才有可执行的效力,这近似于行为能力要件。例如,有关监狱条件和被拘者待遇问题,美国当局难以提供具体、有效的保证。因为美国监狱管理局和各州监狱当局依法有权行使自由裁量权[6],而美国国务院没有法律依据“指挥”或“代替”监狱当局作出具体承诺。如果提供承诺的国内当局,对承诺内容是否得以执行根本不具有控制力,则并非作出外交承诺决定的“适格”主体。
(二)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的“免责”功能
《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推回原则”或“不推回原则”,要求任何缔约国不得将某人驱逐、遣返或引渡到有充分理由相信该人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另一国家,因此缔约国承担“不推回”的义务。而且,《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迄今已有172个国家批准加入[7],这使得“禁止推回”原则已经成了大部分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因此,对于被请求国/遣返国来说,当请求国存在判处死刑或施加酷刑的可能性时,往往只有在确保请求国作出了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后,遣返国基于此作出遣返决定,才有可能不违反国际法义务,从而“免责”。正如上述案例,英国在决定将约旦公民奥斯曼遣返回约旦时,已经和约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争取并提供透明和详细的外交承诺,以确保申诉人返回约旦后不会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因而,欧洲人权法院最后认定,英国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对于“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规定。
相反,如果作为缔约国的被请求国,在被请求人存在遭受酷刑风险且请求国未提供充分可靠的承诺的情况下准予将被请求人引渡或遣返,则被视为违反相应的国际公约。例如,在萨阿迪诉意大利案(Saadi v. Italy)中,欧洲人权法院据此判定缔约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8]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判例也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保障条款解释为,在可能存在酷刑的情况下禁止强制转移。[9]
(三)外交承诺的适用空间受多重因素影响
如上所述,在考察外交承诺是否具有充分可靠性时,欧洲人权法院还列举了非法律因素,例如“兩国关系是否牢固持久”。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不仅会影响被请求国是否愿意诉诸外交承诺,也会影响请求国遵守外交承诺的实际意愿。除此之外,请求国的法律实施与人权状况等一国刑事法治发展程度的检验性要素,往往也是被请求国决定能否“信任”请求国的外部因素。因而,欧洲人权法院也列举出“(被遣返人)接收国是否有防止酷刑的有效保护制度”“是否愿意调查酷刑指控并惩罚责任人”以及“申诉人先前是否在接收国受过虐待”作为外交承诺是否充分可靠的要素。
除上述明确列举的要素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待死刑或酷刑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外交承诺本身的适用空间。以死刑为例,尽管欧洲人权法院以务实的态度允许在个案中适用不判处死刑的外交承诺,然而,近年来部分欧洲国家在死刑问题上却弃置外交承诺制度。例如,2016年意大利修改《刑事诉讼法典》,第698条要求只有在“不判处死刑”的判决是“不可逆”的情况下,才有引渡的空间。[10]这一条款等同于宣告,当引渡罪名存在死刑的情况下,请求国几乎不可能成功向意大利引渡嫌犯。
三、乌斯曼诉英国案对中国外交承诺制度的启示
(一)完善中国外交承诺的要件性规则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以下简称《引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法》(以下简称《刑事司法协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外交承诺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的效力仍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官方对违反外交承诺的后果认知,侧重于对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消极影响。[11]而外交承诺的对内效力,也仅是强调有关人员应当遵守外交承诺,不得以其与现行法律规范冲突而拒绝。[12]然而,对于被追诉人在被引渡或遣返回国后,相关机关没有按照外交承诺的内容兑现承诺的情况,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且,《引渡法》《刑事司法协助法》并没有明确优先于刑法、刑事诉讼法适用的效力。[13]这容易使得其他主权国家在国际追逃合作中,不认可中国作出的外交承诺。
因此,应当细化并明确外交承诺在刑事司法中的法律效力,并明确在刑事司法中,办案机关不遵守外交承诺的法律后果。《引渡法》中的外交承诺,相较于刑法等对罪名及刑罚的规定而言,属于特别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在此基础上,对于检察机关未按照限制追诉的外交承诺进行起诉,一审法院未按照量刑承诺进行量刑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其为“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并作为二审或再审推翻原判决的法定事由。
(二)构建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制度,有针对性作出外交承诺
首先,在不违反我国国家主权、安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根据《引渡法》《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规范作出内容明确、具体的外交承诺,由我国的法定主体作出并向他国官方当局递交承诺,使用“确保”“确认”“承诺”等正式的文字。其次,提供材料,详细论证我国作出外交承诺具有法定拘束力,包括作出承诺的主体为法律授权的承诺决定主体,作出的承诺与我国法律规范相一致,能够保证承诺得到切实执行。最后,提供一定的监测机制。欧洲人权法院在奥斯曼诉英国案中,明确指出“是否愿意与国际监测机制(包括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合作”也是考察外交承诺是否具有充分可靠性的标准。而我国在追逃实践中,也曾做过类似承诺,在黄海勇引渡案中,中方作出承诺秘鲁可派遣其驻中国的外交官或领事官员,对黄海勇的刑事公开审判进行旁听。[14]本文认为,可以将允许被请求国使领馆派人旁听庭审的做法制度化,以展示承诺兑现的过程[15]。在必要时,借鉴奥斯曼诉英国案的经验,指定独立国际机构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督的权利。
同时,可以针对具体国家或区域性组织对待外交承诺的观念和态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充分的外交承诺。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外交承诺是否有效可靠的因素评估,不太关注承诺的形式和申请驱逐、遣返或引渡的原因,而最看重请求国的人权记录。因此,在向欧洲国家申请引渡或遣返程序时,可以侧重提供材料论证中国在促进与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如中国人权白皮书,以满足欧洲国家的充分外交承诺的标准,从而提高引渡、遣返或驱逐的申请成功率。
(三)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化解外交承诺的瓶颈问题
外交承诺是否充分可靠,往往建立在一国对他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评价和态度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我国恪守公平正义理念,坚持公正审判,严格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提高我国刑事法治的国际形象,才能在个案中推动外交承诺的适用,并使国际追逃工作顺利。除此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禁止酷刑问题。我国刑法第247条设置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以惩治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这符合“是否愿意调查酷刑指控并惩罚责任人”这一外交承诺充分可靠性标准。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也明确要求,应当排除以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这足以表明我国在法律制度层面,是坚决反对酷刑的。本文认为,除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外,还应该在法律实施层面贯彻“与国际法治与人权保障标准保持一致”的理念,这本质上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体现,更是坚持“国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涉及该国的涉外事务”的涉外法治理念。只有“淘汰”以牺牲人权保障的方式一味追求打击犯罪,坚持以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思维及方式,才能长效且制度化推动国际追逃工作。
另外,对于如何减少部分国家对待死刑及外交承诺的严苛态度所带来的障碍。本文认为,首先,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适用,通过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以表明我国对待死刑问题的严肃态度。其次,与其他主权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时,推进认可外交承诺成为死刑不引渡原则的例外。最后,在外交承诺中论证我国死刑的适用情况。通过详细说明我国死刑适用的规范标准、死刑在实践中如何被严格限制适用等,以澄清国际社会对我国死刑适用的误解。
(四)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度发展
良好的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对于成功推动外交承诺的适用,从而成功地引渡或遣返被追诉人十分重要。区域性国际合作平台是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朝纵深发展的重要“窗口”。首先,“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可以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刑事司法互助条约以及外交谅解备忘录等,为外交承诺的适用提供直接性的条约或法律文件依据。例如,2017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联合发表了《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这是中国与东盟首部国际性反腐败专门法律文书。[16]其次,“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能够将理念凝聚为共识,从而弥合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及文化差异,为外交承诺的适用扫除制度和理念差异带来的障碍。最后,“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能够深化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追逃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密切联络、交流机制,能够为引渡或遣返个案中外交承诺的适用,为双方提供及时顺畅的沟通、反馈以及协商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