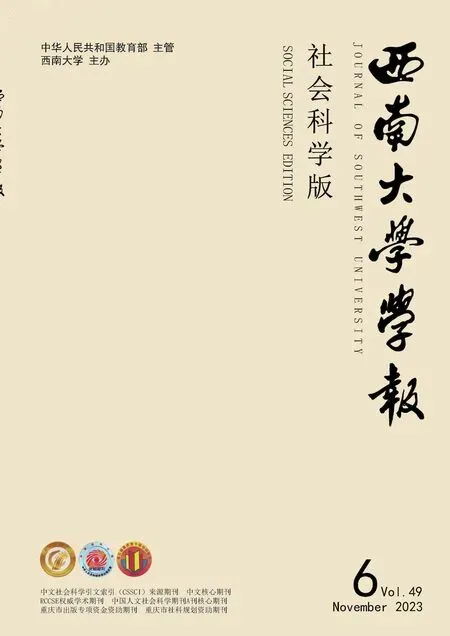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的贸易
——以北京会同馆和东莱倭馆贸易为中心
张 月 莹,刁 书 仁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长春 130024)
前近代东亚三国的经贸交流研究早有学者关注,并已有研究成果问世。例如,关于清代中朝贸易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存武的《清韩宗藩贸易》[1];关于日朝倭馆贸易的研究,有田代和生所著《近世日朝通交贸易史研究》等[2]。这些研究表明,前近代东亚地区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下,存在着政治、文化与经济贸易上的密切关联性。然而,已有研究却较少意识到日朝贸易与中朝贸易是互为前提的事实,相对缺乏以整体视角分析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并探究其相互关联的内在机理与互动逻辑的视角(1)廖敏淑所撰《清代中朝日边境贸易——以栅门及倭馆贸易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虽以清代的中朝日边境互市市场为考察对象,但与笔者研究视角多有不同。。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与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为考察对象,将东亚三国贸易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探讨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贸易实态及变化轨迹。
一、北京会同馆的中朝贸易
清朝入关后,沿袭明制,于顺治初年设会同馆。李朝贡使团到达北京入住会同馆,期间,除履行“事大”事宜外,还在会同馆从事贸易活动(2)李朝与清朝的贸易有公贸、私贸、密贸易(走私贸易)三种形态,会同馆贸易以公私贸易为主,而栅门国境地带盛行李朝商人与清人的密贸易。。李朝贡使团参与贸易人员分法定贸易人与私商两种。法定贸易人,多指使团中的译官。译官由司译院选派,为赴清使行正官。有堂上译官、上通事、次上通事、押物译官等随三使同行[3]卷3,事大,赴京使行。使团中,正使、副使只承担“使事”,书状官负责纠察使行员役的违法行为,而使行中诸务则由堂上译官“总察行中,主管公干”[3]卷1,沿革,等第,赴京递儿之称。“上通事”主要负责对清各关门纳付礼单,并掌尚衣院的御供贸易。“次上通事”掌内医院药材的贸易。押物译官负责岁币、方物、岁米等物品管理与运送,其余各译官也各自担负使行中诸务[3]卷1,沿革,等第,赴京递儿之称。上述三使和译官担负着使行中各自的职责,所以李朝依据译官职品,由政府配给马夫、驱人、骑驿马、卜刷马,并允许译官自费私雇一定数量的奴子、马头及私持马[3]卷3,事大,渡江状。
译官参与会同馆贸易,由政府提供一定数额的贸易资金,即享有贸易特权。具言之:一是八包贸易权;二是代行各官衙贸易的别包贸易权。
八包贸易权,是李朝政府为弥补译官赴清经费不足,而给予的私贸限定。即允许赴清译官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人参及银两从事私贸活动。朝鲜因金银缺乏,曾几次遣使赴明请免金银之贡,以他物代之,明廷于宣德四年(1429)准朝鲜所请。此后,朝鲜赴京使团禁用银两,代之以每人携带人参10斤,这一数额此后不断增加,以致滥觞。崇祯初年,李朝规定每人允持人参80斤,每10斤为一包,亦称八包。继而,又允准带银,人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4]财用篇五,燕行八包,204。清代明后,李朝仍申行此法。顺治十年(1653),定人参80斤。康熙初,始定以银子,堂上及上通事官3 000两,堂下官2 000两[4]财用篇五,燕行八包。此八包法,仅限于三使及译官等正官30人,马夫、厨子、引路、书者、牵马等其余使团随从人员都没有此项待遇。
上述八包额定银2 000至3 000两,最初由官府支给,后改为正官自筹。即“八包者,旧时官给正官人参几斤,谓之八包。今不官给,令自备银”[5]卷1,渡江录。而享有八包贸易权的译官,官府多不支给俸禄,所谓“译官本无田土,生理只在于物货之交易”[6]第97册,英祖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由此可见,译官赴京贸易,事关利益所在,所以即便费用自筹,译官亦在所不辞。特别是康熙朝以降,李朝要求赴清译官自筹额定银两就更加困难,致使译官不得不将八包贸易权转让给私商。康熙十六年(1677),大司谏李元祯云:“比年赴燕商贾车辆,倍蓰于前,弥亘数十里,此由于八包之法废阁,商贾赍银靡有限节故也。”[7]卷6,肃宗三年八月丁卯这条史料是对私商取得八包贸易权,赴清赍银贸易毫无节制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形至18世纪中叶,李朝因倭馆日朝贸易中,白银输入断绝,使得赴清贡使八包额银难以凑足,从而导致八包贸易权移让私商愈加普遍。乾隆年间,赴清使臣朴趾源言:译官辈“贫不能自带,则卖其包窠,松都、平壤、安州等处燕商买其包窠,充银以去”[5]卷1,渡江录。
赴清译官除八包贸易权外,还有代各衙署官贸的别包贸易权。这些衙署包括尚衣院、内医院、户曹、训练都监、御营厅、禁卫营等。其中尚衣院,王室衣物多由赴清上通事等从会同馆贸易中采购丝织品制作。内医院,相当清太医院,每年使团赴清,都由该院与典医监派医员一人与次上通事负责购买王廷所缺贵重药材[6]第69册,肃宗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户曹,主管李朝钱粮,其属司版别房,专掌“各样燕贸,随其遗在多寡,用处紧歇,历、节两行,给价贸来,以备经用”[4]财用篇四,户曹各掌事例,版别房。至于训练都监、御营厅、禁卫营等五军门,所用旗帜和军服的衣料等绢织物及用于兵器、铜钱铸造原料含锡、鍮镴等也都来自会同馆官贸[6]第90册,英祖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述官贸所需银两与八包贸易银不同,由官方配给。
私商,指义州、开城、汉城等地实力雄厚的商人。义州,临鸭绿江,为进出中国门户,自古就是两国贸易重地,旧号龙湾,称其商人为湾商;开城为高丽朝国都,李朝为留都,城中之民多以经商为业,因开城古名松都,故其商人称松商;汉城为李朝京都,其商人称为京商。私商从17世纪中叶始渗入中朝贸易,李朝法律虽规定:“凡于使行,禁断商贾。”[6]第44册,肃宗十六年十月十五日然而,李朝的商业具有服务于统治层的属性,从而决定其商人与统治层关系密切,私商多为中央与地方衙门御用商。私商法律上不允许参与使行贸易,但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对译官及地方官衙的贸易权加以浸透,最终得以在会同馆进行贸易[1]94。
私商或与使行员役相结托,或通过向京、外官衙请托等途径渗透会同馆贸易。如汉城私商多以三使子弟军官或使行员役马夫或奴子的名义潜入使行团[3]卷3,事大,渡江状。但大部私商皆利用三使臣或译官的地位,作为其私属随行使团中[6]第44册,肃宗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尤其是译官掌控使行中人马,携带私商并非难事,从而使私商潜入使行团中[6]第47册,肃宗十九年四月五日。
同时,一些京商、松商、湾商很早便以各官衙的“贸易别将”身份参与会同馆使行贸易。此外,他们当中的其他商人,或向使行官员奉纳钱财冒充驱人、奴子参与使行贸易[3]卷3,事大,渡江状,或向地方官衙交付马税后,获得“别将”身份,参与使行贸易,即文献所言:“近闻各处营府,或因商贾之图嘱,只捧其马税,称以别将,许令入送者有之。”[6]第47册,肃宗十九年四月五日“马税”中的“马”为各官衙视为公认的使行马匹,私商借交纳“马税”之名,取得衙署的贸易权。这些人参与会同馆贸易纯属私商性质。
清朝参与会同馆贸易人员,主要是清商。以乌商、刘商、于商、陈商、项商、黄商等京商为主。还有晋商、鲁商、徽商、广商、浙商、苏商等。较有影响的当属郑商、黄商。两家皆交结官府,仗恃荫庇,聚有财富巨万,而郑商,世泰家族尤甚[8]286-319。世泰继承父业,虽貌不惊人,但“交通王公连姻,又多一时清显”[9]卷7,燕记,铺商,成为甲于京师的富商。
在郑商处于全盛之时,会同馆中朝贸易也被其操纵。李朝贡使团“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出十万两外”[10]卷4,癸巳正月十七日。他囤积居奇,“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所以,李朝贡使团“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11]492。郑世泰凭借其所贸货物的奇缺、珍奇得以操控价格。如使臣崔德中所言:“郑胡随其多买之物,增其价值,寡买之物减价,以增比减,增多减少,每致见欺,诚可痛也。”[12]癸巳二月十四日郑商为达到垄断会同馆丝织品贸易的目的,于每年李朝贡使团入京之前,将购置于江南丝绸产地的价值七八万两白银的丝织品运回京师。而后,再通过会同馆中朝贸易获取巨额利润[9]卷7,燕记,铺商。然而,自乾隆十一年(1746)始,李朝为遏制白银外流,厉行“禁纹缎政策(禁止输入清朝所产带有纹饰的丝织物)”,给予郑家丝绸生意以致命打击,“郑家所先贸者(丝绸品—引者)既不见售,又中国所不用,因此而大窘,渐以消败”[9]卷7,燕记,铺商。郑商死后,子孙赌戏败家,不能世守家业,导致郑商衰败。黄商资本实力原本不如郑商,然子孙犹世守其业,从而使黄家生意兴隆。黄家与贡使团关系密切,经营的丝绸多为贡使团所贸。
郑商衰败后,继起的清商约有50余家。这些清商中,有项姓者,邦均店(今河北三河市)人,颇有经商头脑,每逢贡使团到山海关,项商都“率其子迎劳诸译,欢笑款款”。清商中,有位笃信天主教的山西人陈商,“为人端良,语音明白,无诸商粗浊气味”,还有“美须髯”的于姓商人,因祖上有军功,抬汉军旗。于商善于交际,与贡使团关系密切,“买卖多付之,”因而生意兴隆[9]卷7,燕记,铺商。诸清商中,还有会同馆朝鲜通事乌林哺之弟“乌商”。这些朝鲜通事为清入关前征朝鲜之役时,被掠的朝鲜人后裔,清入北京后,以其语言优长,在会同馆为通事。他们近水楼台,与朝贡使团贸易。总之,会同馆参与贸易的清商,可谓“不可尽记,岁杪入京,诸商遍馆”[9]卷7,燕记,铺商。
会同馆主要贸易品,18世纪中叶前,李朝贡使团主要以白银或人参贸易清朝所产丝织品,即清商以丝织品与贡使团交易,换取朝鲜白银与人参。清朝的丝织品为会同馆贸易中,输往朝鲜的大宗商品。这些丝织品产自以太湖流域湖州府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上述地区至清中叶前,以织布为专业的市镇非常发达,在苏杭等地达到了织机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专业化程度[13]200-201。如上所述,清朝商人参与会同馆贸易多达50余家,这些清商多经营丝绸贸易。顺治年间,丝织品通过会同馆中朝贸易开始输入朝鲜。在康熙年间,朝鲜输入的生丝多由东莱倭馆转输日本。康熙十六年,为了从会同馆中朝贸易中购得更多生丝及丝织品,李朝朝贡使团赴清时,运输所带银两及人参的驮马与押运役员,“倍蓰于前,弥亘数十里”[7]卷6,肃宗三年八月丁卯。
李朝朝贡使从会同馆输入清朝的生丝等商品,除部分国内消费外,大部转运至倭馆贸易给日商,日商将生丝等经由对马销往京都等地。如朝鲜文献所载:“我人之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一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矣。”[14]卷22,显宗十一年三月庚申可见,朝鲜所贸丝织物不仅数量大,且可获近3倍的利润。由于朝鲜利用生丝贸易的差价,从中牟利,结果造成“倭馆物力,不能抵当”,致使生丝等囤积倭馆,“倭人之未偿者,百万余两”的窘状[7]卷6,肃宗三年八月丁卯。输往倭馆的生丝数量之多由此可见。朝鲜从会同馆贸易输入倭馆生丝的数量,从1652年朝鲜对倭馆输入始,至1751年朝鲜停止白丝输入为止。这期间,1684年朝鲜输入倭馆白丝30 396斤,1687年129 178斤,1688年102 119斤,1689年150 678斤,1694年141 382斤达到高峰[2]281。由于朝鲜从会同馆输入的生丝数量不断上升,致使中日长崎贸易生丝输入量处于劣势。长崎中日贸易生丝交易高峰,在宽永年间(1624-1643),曾从20万斤上升到40万斤,从贞享、元禄年间(1684-1703)明显减少。据韩国学者金钟圆统计,宽文元年(1661)清朝输入长崎白丝198 924斤,宽文二年为357 990斤,而元禄元年(1688)为40 520斤,元禄十年为45 671斤,元禄十一年为11 618斤。[15]相反,生丝输入倭馆数量则飞跃式地增加。从1684年至1710年,朝鲜向倭馆输入生丝总量为1 626 265斤,其中,白丝1 625 574斤,年均输入量621 445.4斤[2]280-282。上述朝鲜向倭馆生丝输入量与同时期长崎中日贸易生丝输入量相比,朝鲜向倭馆输入生丝的数量明显处于优位。1688年,长崎从清朝、荷兰两国输入的生丝中,白丝、黄丝为99 860余斤,同年,朝鲜向倭馆输入的生丝中,仅白丝就达102 119斤[2]280-282。据17世纪末朝鲜文献《杂物折价》载:白丝每百斤,北(清朝)一百二十两,东(朝鲜)一百九十两,南(日本)二百四十两[1]245。也就是说,朝鲜在会同馆中朝贸易输入白丝价格,转运到倭馆的日朝贸易,白丝价格飙升2倍以上。即便如此,倭馆白丝价格仍明显低于长崎输入的白丝价格。1688年,日商从长崎购入白丝的价格,100斤为2贯728钱(3)银1贯,约合朝鲜重量100两银。,同时期倭馆白丝100斤价格为2贯496钱;1712年,日商从长崎购入白丝100斤价格为3贯954钱,同时期倭馆白丝100斤价格为3贯610钱[2]283。可见,长崎的生丝价格明显高于倭馆。
二、东莱倭馆的日朝贸易
日朝贸易主要在朝鲜东莱倭馆展开,贸易始于李朝建国之初。李成桂建国伊始,即遣使日本禁止倭寇,谋求通好。随之足利义满派九州岛守将刷还朝鲜人口,两国缔结邦交,进行勘合贸易。壬辰战争爆发后,这一贸易被迫中断。而后,随着日朝两国关系恢复,并于1609年(庆长十四年,光海君元年)签订《己酉约条》,倭馆贸易再度开始[16]238。
倭馆日朝贸易种类有二:一为进上(1635年改称封进)与回赐,即对马藩每年向李朝进献胡椒、明矾、苏木等,与李朝回赠人参、毛皮、棉布等,这种赠答品应属对马藩与李朝间礼仪性贸易[2]60-63。二为公贸易、馆市贸易及密贸易。公贸易,指对马藩向李朝输出铜、锡、丹木、水牛角等,朝鲜对等向对马藩输出棉布等。显而易见,这种贸易属于对马藩与李朝间定品定量的公贸;馆市贸易,朝鲜称为私贸,即对上述公贸而言是私贸,但绝非走私贸易。这种私贸,是对马日商与东莱商人在彼此官员监督下进行的,其交易品及数量、价格不受限制,因市而定。通常对马日商输出倭银,其次是铜、锡、胡椒、水牛角等,东莱商人输出主要是从清购入的丝织品及国内产的人参[16]238。密贸易(走私贸易),是在馆市交易后,对马日商与朝商潜入厢房中私下交易,或日本对马、博多、长崎商人乘船私入朝鲜海域,与朝商的私密贸易。这三种贸易,以倭馆馆市贸易最为繁盛。
馆市贸易在倭馆大厅内进行。因釜山旧倭馆(豆毛浦倭馆)馆舍陈旧狭小,对马藩多次向李朝请求搬迁,肃宗四年(延宝六年,1678),李朝遂在釜山草梁建新倭馆[3]卷5,交邻,倭馆,新倭馆直到明治六年(1873)为日本外务省接收为止,一直为日本通过对马藩从事日朝外交及贸易的场所。倭馆分东中西三馆。开市大厅作为日朝贸易场所,有四十间[3]卷5,交邻,倭馆,宴享大厅三十二间,公须厅二十五间,守门四间(内二间为军官厅,一间为开市监官厅,一间为小通词、部将厅)[3]卷5,交邻,倭馆。倭馆最初开市,每月3次(3日、13日、23日),从光海君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始,改为每月6次(3日、8日、13日、18日、23日、28日)开市,若“倭人有请,或物货委积之时,则别开市”[3]卷5,交邻,开市。
日本参与倭馆贸易的人员由对马藩派驻。人员以馆守为首,由裁判、代官、东向寺僧、通词、医者、目付、鹰匠、陶工、请负屋(御用商人)、水夫等400余人组成。“馆守”,统摄倭馆诸事务,“裁判”和“东向寺僧”担负日朝外交与文书诸务,“代官”,负责倭馆日朝贸易,其他员役各有分工[2]176-194。
李朝参与倭馆开市人员有管理者与商人。管理者有主导官,即“训导”(任期为30个月)和“别差”(任期为1年),由李朝司译院派遣倭学译官交替担任。户曹还差派收税官(任期为1年)负责收纳商税。此外,东莱府还委派开市监官,负责监视纠察倭馆违法商贾[3]卷5,交邻,开市。商人,主要有莱商(东莱本地商人)、京商(汉城商人)、松商(开城商人)及湾商(义州商人)等。倭馆贸易之时,前来贸易的商人踊跃。据《边例集要》载:“近来商贾之数,至于七八十人,私贱马主辈,亦入于商贾之中,滥杂之弊,职由于此,不可不痛革其弊。”[17]上,卷9,开市,戊午(1678)闰三月《通文馆志》也载:“康熙辛未(1691),朝家以为京外务商之类日繁,而颇有滥杂之弊”。为此,李朝政府不得不对参与贸易的商人数额加以限定,结果造成商人“买卖失利”,至肃宗三十四年(宝永五年,1708)不得不废除限定商人贸易人数的规定。这样一来,前往倭馆贸易的商人又踊跃起来。每逢开市日,商人凭从东莱府领取印有字号烙印的“受牌”,携带货物至倭馆“守门”处,由“训导、别差及收税官、开市监官眼同检验,置簿入送”,进入馆后,诸商到入坐开市大厅的训导和别差前跪拜之后,始交易各自的货物,经过充分讨价还价一次性将货物全部卖出[3]卷5,交邻,开市。
倭馆贸易中,对马藩“进上”物品与朝鲜“回赐”物品,属公贸易性质。对两国而言,并非将追求利润作为目的,是两国外交上的一种礼仪,或为交邻的手段。相较之下,馆市贸易和密贸易则不然,其贸易双方均为获取利润,且贸易数量也未加限制。馆市贸易中,日本银(丁银)、铜、锡、鍮鉐、钍钢及类似诸矿产品为朝鲜的主要输入品,占输入品总额的八成。这其中55%左右的输入品为日本银,在朝鲜输入商品中占据主要位置。日本从倭馆输入朝鲜产人参、清朝产生丝等丝织品,其中占绝对优势的商品为生丝中的上等品白丝。也就是说,大部分(至少至18世纪中叶前)经由北京会同馆输入朝鲜的白丝、匹缎等“燕货”都通过倭馆日朝贸易输往日本[18]卷164,市糴考,馆市事例。上述丝织品与位列其次的人参,共约占倭馆对日贸易输出额的90%。与此同时,对马岛主临时向朝鲜的求请、求贸,也是通过这种贸易来完成。以下就日本银在倭馆贸易的实态加以考察。
日朝贸易中,朝鲜多以人参及从明输入的丝织品贸易日本银。清朝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中日之间通过长崎直航贸易。但因日本银矿开采呈衰退趋势,德川幕府遂限制银的输出。贞享二年(1685),颁布《贞享令》,限制长崎中日贸易中的白银输出,从而导致长崎与对马在东亚白银贸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2]269。倭馆日朝贸易遂成为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东亚地区最为繁盛的贸易圈。这一时期,倭馆日朝贸易与长崎中日贸易,以白银输出为例:1686年,倭馆贸易中,日本输出朝鲜白银为2 887贯345钱,占倭馆日朝贸易输入总额的75%,而同年长崎中日贸易,日本输出白银仅为464贯574钱,即倭馆为长崎的6.2倍;1694年,倭馆贸易中,日本输出朝鲜白银2 579贯49钱,占倭馆输入总额的55%,同年长崎贸易,日本输出白银仅为2贯537钱,即倭馆为长崎的1 000倍[2]270-271。有学者统计从1684年至1711年间,倭馆贸易中,日本输出白银总额为48 356贯482钱8分6厘,年均输出白银1 790贯980钱8分4厘,而同时期长崎贸易,因《贞享令》限制白银输出,年均输出白银仅300贯[15]。可见,倭馆日朝贸易中,年输出日本银为长崎中日贸易年输出日本银的6倍。至17世纪末为止,倭馆日朝贸易中,日本向朝鲜输出白银,年均应在20万两左右,如果加上公贸易额,估计日本每年向朝鲜输出银应在30~40万两以上。正如李朝副承旨洪重孝回忆倭馆贸易时所云:“中古则日本与中国不相通,所用燕货,皆自我国莱府转买入去,故一年倭银之出来者,殆近三四十万两。”[19]第1152册,英祖三十四年正月五日此外,人参在日朝贸易中也占较大的比例[20]。有学者统计,这两种商品,在肃宗十年(1684)到肃宗三十六年(1710)的27年中,占倭馆贸易总额80%~90%有15次,占60%~70%有11次,50%只有1次。其中生丝占总额的50%~70%[15]。
倭馆日朝贸易白银来源及运送方式:一是对马日商经倭馆贸易朝鲜商人的白丝等物品的获利银;二是对马日商从“京都银主”,即对马藩倭馆贸易的投资者,贷出的倭银。对马日商将筹集到的上述银两集中于他们在京都所设的藩邸,而后经由陆路运至大阪,再从大阪走海路运至对马,最后由对马用专门运输白银的“御银船”输送釜山倭馆[2]331。
对马藩白银的运送时间与李朝贡使赴清朝贡时间密切关联。朝鲜原本银矿资源缺乏,为筹措岁贡额银曾开矿采银,结果产银量少,“旋采旋废”[21]卷79,光海君六年六月庚子。因此,倭馆日朝贸易中,日本输入朝鲜的白银,多不在朝鲜国内流通,而是由赴清使团携带赴清贸易。这就使得对马藩运送白银时间与朝贡使赴清的时间相吻合。1681年,对马藩家老写给京都代官的信中云:皇历银,即每年赴燕皇历使所携带银应在六月中旬;冬至银,即每年赴燕冬至使所携银应在八月中旬运送到对马[2]215。日本学者据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宗家记录《(馆守)每日记》中有关白银运送记录进行整理的结果表明:从1711年至1750年的40年间白银每月运送量来看,大体上白银运送多集中在每年七月(9.5%)、八月(15.8%)、十月(21.3%)、十一月(13%),即这四个月占全年运送量的60%[2]331。可见,白银运送数量的变化与朝鲜每年向清“事大”所派贡使的时间大体吻合。就是说,白银作为特定商品,其运送量的变化与自然环境影响并无关系,而运送量的变化是与东亚三国贸易商圈,尤其与李朝向清朝贡所派使节有密切关联。如前所述,清与李朝确立宗藩关系后,李朝每年定期遣使赴清朝贡。“冬至使”使行,每年阴历十一月出发,次年四月归国[3]卷3,事大,赴京使行。“皇历赉咨行”,简称“历行”,每年阴历八月出国,十月抵达北京,接受清朝时宪历后返国[3]卷3,事大,赍咨行。此外,朝鲜还经常派遣临时性使行,包括谢恩、进贺、陈奏、奏请、陈慰、进香,以及告讣、问安、参核等使行。不容否认,上述赴清朝贡使政治外交活动是第一位的,但为获得经贸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赴清使团须携带数量众多的白银在京会同馆贸易,所携白银多来自倭馆日朝贸易。所以,朝贡使赴清时间与对马藩向倭馆运送白银的时间相吻合。
上述事实表明,18世纪中叶前,朝鲜通过倭馆日朝贸易,将从会同馆中朝贸易中输入的大量生丝,经倭馆日朝贸易卖给日商,朝鲜将所赚白银再投入会同馆中朝贸易中,获取更多利益。朝鲜这种中介贸易不仅在中日两国间搭建一条“银丝交易”的贸易管道,也助推了东亚三国贸易商圈的发展。
三、18世纪中叶以降东亚三国贸易的变化
17世纪中叶至该世纪末,东亚三国贸易商圈由初步活跃发展到鼎盛。18世纪中叶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其变化的脉络,通过以下史实加以考察。
变化之一是,自18世纪中叶始,倭馆日朝贸易中,日本银的输出减少,从而影响会同馆中朝贸易生丝的交易,最终导致三国贸易呈现衰退趋势。如前所述,朝鲜凭借中日间优越的地理区位,成为中日间银丝贸易中继商。朝鲜贡使团每次赴清,均带大量白银贸易丝织品等,甚至“一岁渡江之银,几至五六十万”[4]财用编五,栅门后市。可见,每年会同馆中朝贸易将有50万~60万两银流入清朝。而朝鲜原本银矿缺乏,流入清朝的银多为倭馆日朝贸易中所获日本银。十七世纪中叶,日本银矿资源充足,银产量丰富,加之德川幕府锁国与清朝海禁,致使两国不能直接通商。这样日本所需清朝生丝、药材等,只能经倭馆日朝贸易输入。如文献所言:“英庙丁卯(1747)以前,清人不与倭人互市,故倭人之贸唐产者,必求之东莱,以此莱府银甲于他处,行于国中者,多倭银。……其后清人与倭通市,倭人直至长崎岛交易,而不复向东莱。于是遂专用矿银,产亦渐减于昔,自此国中银大绌。”[22]卷36,正祖十六年十月辛未揭示了18世纪以降,日本银输入朝鲜明显减少的实情。
倭馆贸易白银输出减少,直接影响东莱府和户曹税银收入。倭馆贸易流入朝鲜的白银也是东莱府和户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朝鲜副承旨洪重孝对十七世纪中叶倭馆贸易有如下追忆:
中古则日本与中国不相通,所用燕货,皆自我国莱府转买入去,故一年倭银之出来者,殆近三四十万两,本府收税十分一,而又三分其税,二纳户曹,本府用一,故能支用矣。自雍正年间,中国直通倭国之长崎岛,故倭银之出来我国者甚少,而又自被执人参之见塞,倭银元无出来者,而莱府之经用,如前浩繁,更无出处,所以逐年凋弊,今则至于不成样矣。[6]第134册,英祖三十四年正月五日
可见,东莱府从倭馆贸易中征收十分之一税,每年征税银达万余两[19]第261册,肃宗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这十分之一税,三分之一用于本府,三分之二缴纳户曹。如肃宗六年(1680),出任东莱府使仅9个月的赵世焕,就向户曹缴纳税银14 000余两,据此推算,是年倭馆贸易所纳税银为21 000两,而贸易额为其10倍,即21万两银[23]350。足以说明倭馆贸易之盛。至18世纪40年代,倭馆贸易萎缩,东莱府税收逐渐减少。如户曹判书金在鲁所言:东莱府税收银,“近年渐减,而犹为七百、五百两,今番税纳,则只是一百八两,诚可寒心。岁入则至少,而逐年应用,则有加无减,其何能支过乎?”[6]第93册,英祖九年三月十四日倭馆税收银减少导致户曹税收银明显减额。李朝肃宗年间,户曹税银收入,年均在3万两以上。如肃宗二十七年(1701)为39 519两,肃宗三十九年为66 780两,肃宗四十年31 280两。而英祖以后,户曹税银逐年减少。如英祖六年(1730)28 332两,英祖八年12 922两,英祖二十五年16 530两,正祖四年(1780)716两,正祖九年,只有620两[18]卷155,财用考二,户曹一年经费出入数。上述户曹年收税银在肃宗三十九年,竟达最高额66 780两,至英祖年间税银逐渐减少,至正祖九年时,仅有620两,这一年税银与肃宗三十九年最高额相比仅为百分之一,户曹税银减额之剧由此可见。户曹税银减额皆由倭馆日本白银输出锐减所致。
倭馆贸易日本银输入的减少,导致朝鲜贡使赴清朝贡银两短缺,资金严重不足。由于赴清贡使赴京途中,需向清官员打点的“人情费”增加,所需银子逐年递增。如谢恩使韩德厚所言:“一使之行,八包之银,多则十数万两,小不下七八万两。”[24]542赴清贡使所带银两多来源倭馆贸易银,由于倭馆贸易的银两减少,赴清使行员役不得不向各军门、衙门借贷银两,致使“户、兵曹、司仆寺及各军门银货,多数贷去”,而贡使团用所借银两从会同馆贸得的生丝等再转卖倭馆,因倭馆购买力低,造成生丝等滞销,结果使臣所贷银两非但不牟利,反倒血本皆无,为还贷,不得不“以物货愿纳,甚至以田土、家舍,折价请偿”[25]卷47,肃宗三十五年六月己酉。这种窘状的出现,皆因倭馆贸易银子减少所致。雍正五年(1727),领相李光佐言及朝贡使赴清用银的开销时说:“今京外银货之荡竭,专由于入送燕行,前则皇历、赍咨之行入去之银,几至十五万两。”[26]卷13,英祖三年十月丙午可见,一方面赴清使团用银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倭馆日朝贸易银两不断锐减,赴京使臣八包额银难以为继,身为领相的李光佐岂能不忧心忡忡!
变化之二是,倭馆日朝贸易白银输入减少的同时,朝鲜从清朝输入的生丝也逐渐中断。倭馆贸易中,“丝缎逐岁凋零,商路寂寞”[17]下,卷9,开市,辛未(1751)三月,朝鲜向日本输出清朝的生丝几乎中断。如倭馆馆守所言:“近来我国商贾残败特甚,丝缎诸种,绝不出入。”[17]下,开市,乙亥(1755)十一月
东亚三国贸易中出现上述日本银输出减少与清朝生丝输入中断的变化,其深层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限制银等贵金属输出政策,致使倭馆贸易银输出减少。如前所述,日本的银、铜产量自宽文以来日益减少。为了限制金、银、铜外流,德川幕府在新井白石的建议下,颁布了《贞享令》。规定,倭馆日朝贸易,银输出限定额年为1 080贯,后因日本货币改铸,以纯银含有量低为由,元禄元年增额至1 800贯[2]334。该限制令的下达,给倭馆贸易银的输出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第二,日本白银的输出,深受其货币改铸影响。日本自17世纪末以来对输出白银几度改铸。为降低货币成色,增加货币流通量,德川幕府于元禄八年(1695)将庆长银(纯度为80%,朝鲜称丁银)改铸为元禄银(纯度为64%)。受此影响,白银质量明显下降,通货膨胀甚为严重。随后,德川幕府又于宝永三年(1706),改铸纯度为50%的宝永银、纯度为40%的永字银等[16]154。而朝鲜对日本所铸恶币,在日朝贸易中不予承认。因此,为维持日朝贸易,德川幕府于正德元年(1711)又铸造了纯度为80%的特铸银。然而,京都银座(特铸银铸造所)对对马藩的供给并非十分顺畅,因而特铸银也相应减少。从1710-1714年和1738-1747年的变化来看,减少得尤为明显。到了英祖三十一年(1755),停止铸造[27]。由此可见,日本货币改铸,深刻影响了日本银的输出。第三,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输入清朝生丝,严重冲击了东亚三国的生丝贸易。17世纪末以后,英商逐渐开始从广东输入生丝等货物。通过非法贸易大量输入清朝生丝,导致清朝国内生丝价格急剧上升。面对这一境况,清廷曾中断生丝输出,而后又在英商的不断请求下同意恢复。根据学者研究,东印度公司是清朝生丝输出的最主要对象,从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五十二年的三十余年间,其所占比重由59%上升至83%。经过不断提升比重,从而独占了广东贸易[28]36。受此影响,朝鲜赴清使团从会同馆贸易中获取的生丝数量不断下降,进而阻断了生丝经由倭馆对日输出。在此种情况下,东亚三国贸易商圈必然走向衰落。
四、结 语
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以北京会同馆为中心的中朝贸易和以东莱倭馆为中心的日朝贸易互相联动,构建起东亚三国的贸易商圈。这个贸易商圈所经商路:从日本京都至对马岛,经朝鲜东莱倭馆,最终到达中国北京。如日本白银,当时不仅是日本国内的通行货币,也是具有较高信誉的国际货币。白银通过倭馆日朝贸易大量流入朝鲜,再经由会同馆中朝贸易输往清朝。而生丝,这一代表清朝的国际商品,恰好与白银所经路线相同,只是其流向正相反,即生丝,由李朝朝贡使通过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输入朝鲜,由朝鲜转运东莱倭馆,经由对马输往日本京都等地。这个贸易商圈作为东亚贸易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东亚三国的经贸交流。然而,至18世纪初,该商圈发生变化:日朝贸易中,日本输往朝鲜的白银数量下降,18世纪中叶后一蹶不振,输往朝鲜仅限定铜,而朝鲜输往日本的生丝、人参基本结束,中朝会同馆贸易中,朝鲜对清朝从白银输出转为红参输出,清朝的白银反倒流向朝鲜,朝鲜将从清朝输入的白银再输往日本,贸易日本铜,铸造国内货币常平通宝,从而确立了钱本位。上述这种变化表明,18世纪中叶以降,东亚地区清朝周边国家朝鲜、日本都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本国市场,从而使其对东亚市场的依赖性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