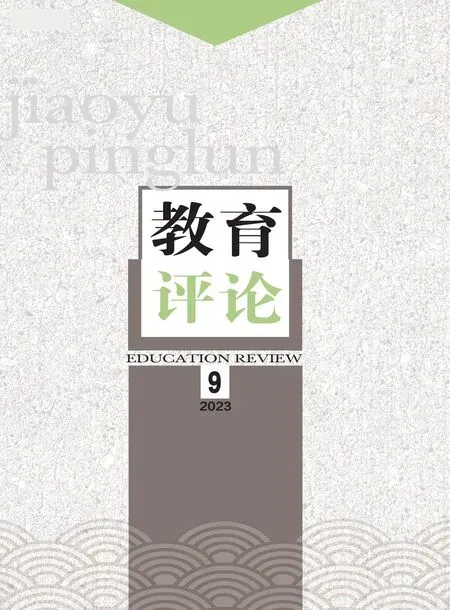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陈 权 王小蕾 张 晴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迈入数字化时代,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渗透,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全面走向“数字化”,“数字中国”建设已经驶入“快车道”。数字公民素养是数字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的新要求,是传统公民素养的深化、升华与发展。美国学者迈克·里布尔(Mike Ribble)较早对数字公民素养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2],历经10余年发展,数字公民素养已经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和接受。我国对数字公民教育和数字公民素养测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回顾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发现,在高校数字公民教育和数字公民素养测评方面研究相对薄弱,针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发展与评价研究更少。鉴于此,本研究以未来“数字中国”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析我国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持。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问题
数字公民素养是数字社会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生存技能,是青少年预防数字风险、有效参与数字社会、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必备素养。布雷弗曼(Braverman)认为:“在大多数高校,数字公民素养要么被认为是大学生理所当然具备的,要么被认为处于一个适当的水平,而不是得到评估与纠正”[3]。研究发现,数字化进程较慢地区,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对数字责任、数字安全等并不清楚,只有不到半数的大学生熟知并能践行数字礼仪及选择合适的数字技术展开学习。[4]在数字化进程较快地区,大多数参与调查者对数字公民有较好的理解,具备中等偏上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但在数字商务及其涉及到的数字安全问题等方面稍显逊色。[5]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在校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问题,迫切需要深入探究。
(二)研究假设
1.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存在年级和学科专业差异性
弗洛伦斯·马丁等(Florence Martin et al.)调查发现,不同年级学生在数字公民素养中的数字礼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6]李毅等将师范生划分为文科、理科和艺体学科,发现师范生信息素养水平在学科分类上存在显著差异。[7]考虑到不同学科的教学亚环境对学生的认知发展及学习生活方式存在间接影响,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本研究提出假设1:年级和学科专业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有显著影响。
2.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存在学校和地区差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在2021年发起居民数字素养发展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很大。汪凡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城市学校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明显优于郊区和农村学校学生。[8]由此可见,数字公民素养可能存在学校和地区差异。本研究提出假设2:学校和地区差异会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产生显著影响。
3.数字化设备的使用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具有显著影响
卡拉(Kara)在调查中发现,每天至少沉浸在网络世界中6小时以上的大学生约占比50%,日均网络使用时间10小时以上的大学生在数字公民素养的人际网络关系维度得分更高,更擅长数字交流,在数字世界更为活跃。数字技术通过视频、音乐、游戏等可以为个人提供刺激性和满足性体验,这些让人获得满足感的内容与活动在数字环境中被经常接入,对个人的注意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难免会造成负向影响。[9]由此可见,数字化设备的使用可能在个人数字公民素养的不同方面同时存在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本研究提出假设3:数字化设备的使用情况会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产生显著影响。
4.数字公民教育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具有显著影响
欧美国家进入信息化时代早、数字化进程较快,数字公民教育已纳入标准化学校课程。[10]然而,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些举措是否成功。早期有学者通过设计为期四周的数字公民课程并设置对照组和测试组,开展衡量数字公民课程有效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在数字礼仪、数字权责等方面的认知和行为有显著改善。[11]伯恩等(Bowen et al.)通过前测和后测发现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中的各项子素养在短期课程结束后并无显著提高,但在数字礼仪与数字法律方面得到轻微改善。[12]由此可见,不同数字公民课程学习经历对数字公民素养及其子素养产生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4:数字公民教育会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产生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改编自阿卜杜拉赫曼(Abdulrahman)设计开发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测量问卷[13],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采取目的抽样法和随机抽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江苏、陕西和湖北7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76份,专业覆盖经济学、工学、管理学、理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等门类,年级覆盖大一至研三。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四、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总体分析
本研究从数字尊重、数字教育、数字保护三个维度呈现数字公民素养水平。通过对各维度和总体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生在数字尊重维度的得分最高,标准差最低(M=4.52,SD=0.47),其次为数字教育(M=4.46,SD=0.52),在数字保护维度上的得分最低,标准差最高(M=4.15,SD=0.64),总体得分均值为4.40分。由此看出,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处于中高水平,能够熟练地使用数字设备参与数字生活,具备一定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和信息生活技能,并且可以较好地遵守数字空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但是,相比之下,数字保护维度得分均值相对偏低,且低于总体得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在数字安全意识和信息保护意识方面存在不足。
(二)影响因素分析
1.学校地区差异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数据结果显示,除数字尊重维度,学校地区差异在其余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均未呈现显著差异。在数字尊重维度,学校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大学生显著高于非省会城市大学生(PDR=0.001),但效应较弱(Cohen’s d=0.198),说明影响相对较小。
2.年级和学科专业的影响
本研究中将学科专业归纳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对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业学生在数字公民素养总体水平及数字保护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但效应量均低于0.5,影响相对较小,在其余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从年级来看,年级变量对数字公民素养总体水平及各子维度均存在显著影响。由事后检验可知,在数字公民素养总体水平上,研三学生显著高于其余年级学生;在数字尊重维度,研三显著高于大一至研一年级,研二显著高于大二至研一四个年级;在数字教育维度,研三同样显著高于大一至研一年级,研二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在数字保护维度,研三显著高于其余年级。总体而言,不同年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存在一定差异,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并且结合检验力可知,年级对数字公民素养存在较大影响。
3.数字化设备使用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使用年限及日均使用时间两个变量,探讨数字化设备的使用对数字公民素养的影响。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设备的使用年限对数字公民素养总体水平及各子维度均未带来显著影响,日均使用时间仅对数字保护维度带来显著影响,且日均使用时间在1-3小时的高校学生在数字保护维度得分显著高于使用时间在4-6小时及6小时以上的学生。
4.数字公民教育的影响
本调查显示,78.5%的大学生表示,所在高校未开设数字公民素养相关课程或持不清楚态度,仅有21.2%的大学生明确表示,所在高校以选修课、必修课或讲座的形式开设了数字公民课程。那么数字公民相关课程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培养是否发挥了作用?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方差分析,探讨数字公民课程对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关课程教育对数字公民素养及各子维度产生显著作用(P<0.001,检验力>0.9),并由事后检验可知,所在高校开设过相关课程的学生,其数字公民素养显著高于没有开设过或不清楚的学生,这说明该类课程确实对培养并提升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有着积极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本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发展不够均衡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可划分为数字尊重、数字教育、数字保护三个维度。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在这三个维度的均分为4.40,但数字保护维度的得分仅为4.15,显著低于数字尊重和数字教育。说明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发展情况整体良好,这与前人研究一致[14],但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发展并不充分,在数字保护方面仍有发展提升空间,应加强数字安全意识和信息保护意识。
此外,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学校的大学生在数字尊重维度存在显著差异,省会城市的大学生的数字尊重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但是差异的效应量并不大(d=0.198)。说明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数字尊重维度发展不平衡,这可能是因为学校所处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差异导致了大学生在数字尊重维度的表现不同,但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身上同时也有生源地的印记,在大学学习生活的时间可能也并没有很长,因此地区差异可能受到了生源地和居住时间这两个变量的稀释,这有待后续研究开展进一步的验证。
(二)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存在人口学变量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专业类别对于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效应量很小(<0.5),不同年级虽然两两之间并不都有显著差异,但总体趋势是年级越高,数字公民素养水平越高,研三最高。可见,影响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关键人口学变量并不是专业类别,而是年级。与年级挂钩的人口学变量是年龄与受教育水平,这两者并未纳入本研究中,后续可就年龄、受教育水平与数字公民素养的关系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明确这两者的影响。
(三)数字化设备日均使用时间负向预测数字保护
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设备使用年限对大学生公民素养及其子维度无显著影响,而数字化设备的日均使用时间虽然对于大学生公民素养整体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数字保护维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日均使用时间越长,数字保护表现越差。这可能是因为日均使用时间较短的人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控制能力又直接影响规则意识,而数字保护意识正是一种保护性规则意识。因此可以说,数字化设备的日均使用时间可以负向预测数字保护。
(四)数字公民教育正向影响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
素养教育是我国教育向人本位教育进行转变的表现,素养教育可以通过课程去进行。[21]调查结果显示,开设有相关课程的高校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显著高于未开设的,且对公民素养水平的各个维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了相关课程的有效性。但是,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接受数字公民素养课程的专门教育,且开设有相关课程的高校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仅比未开设的高0.14,这说明相关课程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专门课程的普及性与专业性均有待进一步建设提升。
综上所述,在校大学生是伴随着信息技术成长的数字原住民的典型代表,受成长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整体情况是好的,但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现象。部分大学生数字保护意识不强,导致少数学生网络上当受骗现象时有发生。年轻一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技术一同成长,在数字化设备初使用时期,个人在使用行为上多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特征,如对技术产生依赖性、网络规范性差、个人主义强等。一方面,生活在泛在的互联网空间中并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数字原住民可以逐步掌握数字技术、信息生活等方面的应用技能;另一方面,数字原住民并不会自发成为数字公民,需要通过数字公民相关教育逐渐树立数字责任意识,熟知并内化数字礼仪规范及法律法规,提升数字化生存能力,唤醒自身数字公民意识从而向数字公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