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功博物馆
[乌拉圭]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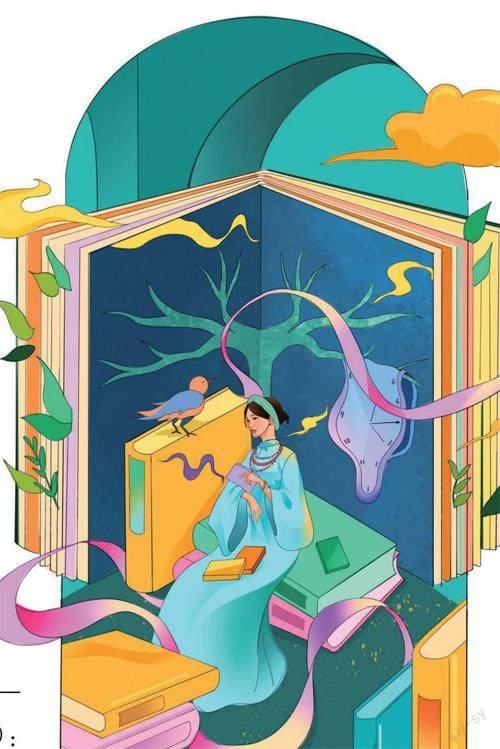
1
每天下午我都到无用功博物馆去,借出一卷馆藏目录,在那张大木桌前坐下。目录里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喜欢不紧不慢、一页一页浏览,如同翻动时间的书页。由于我是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之一,女员工弗吉尼亚对我十分关照。进馆之前,我仔细看了看挂在玻璃门上的牌子,上面印着:
营业时间:上午,9:00—14:00;下午,17:00—20:00;每周一闭馆。
尽管我基本上总是知道哪一件“无用功藏品”是自己有兴趣参观的,我还是会去借馆藏目录,让弗吉尼亚有点事儿做。
“请问您想借阅哪一年的?”她礼貌地询问我。“一九二二年。”我会这样回答她。
不一会儿,她就捧着一大厚本深紫色封皮、笨重不堪的书出现,把它放在我座位前方的桌子上。偶尔,我在归还目录的时候,会简短地评论几句。比如,我对她说:“一九二二年真是紧凑的一年。很多人都做了无用功。这一年的目录总共有多少卷来着?”
“十四卷。”她的回答十分专业。我仔细查看了那一年的几个无用功案例,有尝试飞翔的孩子,有挖空心思想发财的人,有从来没能动起来的复杂机械,还有一些情侣间的事情。
“相比之下,一九七五年要丰富得多。”她的语气略带悲伤,“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登记完所有的藏品。”“分类员的工作很繁重啊。”我心里想着,不由说出声来。
颇有意思的是,总有人反复做些没用的事情。一个男人曾经七次尝试飞翔,而且是借助不同的装置;有人想丢掉恐惧心理;几乎所有人都想长生不老。
弗吉尼亚肯定地告诉我,只有很少一部分无用功能够得到博物馆的收录。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部门缺乏资金,而且收藏不断产生的海量无用功需要大量人力,也不指望得到公众的回馈和理解。
2
博物馆建在城郊的一片荒地上,到处是流浪猫和残渣废料。地底下稍微一挖还能找到旧时战争遗留的炮弹、生锈的剑柄以及被时间蚕食的驴颌骨。
墙上的钟总是指向错误的时间,陈旧的钟框上积满灰尘。据说博物馆所在的地方在战争时期是一座防御工事。后来人们利用地基里的厚石板和几根房梁筑起了墙壁。博物馆是1946年落成的。
所有的“无用功”先是以字母编目,字母用尽了,就增加数字。排序方式冗长复杂。每一件都有专门的文件柜、介绍页和描述文字。弗吉尼亚灵巧地游走于藏品之间,如同一位女祭司、萬人膜拜的圣女,属于某种已经老得与时间脱轨的信仰。
有些无用功是美好的,有些则是阴郁的。不过,我们不是总能在这种区分上达成一致。
在浏览某一卷目录的时候,我读到有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地试图让他的狗开口说话。有的人长途跋涉只为追寻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追寻无可挽回的记忆,追寻早已不在人世的女人或是消失不见的伙伴。
还有人做过以下这些无用功:重建家谱,挖矿淘金,写书,以及不断尝试中彩票。
“我比较喜欢看那些旅行者的故事。”弗吉尼亚对我说。
博物馆里有一整个分区是关于旅行的。我们在纸页上重述这些旅行:畅游重重海域,深入层层树林,认识不同城市,在火车站月台的长凳上入睡,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旅人们已然忘却旅行的目的,却依旧不停出发。最终,某一天,他们悄无声息地消失,没留下任何痕迹与回忆。有的在洪水中丧生,有的困在地下,有的在某扇门外一睡不醒。没人再提起他们。
弗吉尼亚告诉我,以前有一些私人研究者和热心爱好者向博物馆提供资料。有一段时间很时兴收集无用功,如同集邮或者收集蚂蚁标本。当时,人们从各地纷至沓来,在博物馆搜集信息,对某个事件产生兴趣,走的时候带上几本小册子,满载故事而归。他们会重写这些故事,付诸铅字,附上相应的照片。种种无用功像蝴蝶和奇异的虫子一样被带到博物馆。
有的时候,她一边做着工作,一边发点儿牢骚。她说:“分类永远也做不完。这一堆报纸,上面全是无用功。”
3
在这里,我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而周一总是充满遗憾,每到周一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该如何生活。
博物馆晚上8点闭馆。弗吉尼亚亲自把简陋的金属钥匙留在门锁里,不做任何戒备,反正也不会有人想要打劫。唯独有过一次,有个人偷偷摸进来,弗吉尼亚告诉我,他是想把自己的名字从目录上删掉。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无用功,现在感到很丢脸,不希望留下关于那件事的痕迹。
“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个人。”弗吉尼亚说,劝阻他真是件难事。他坚称自己的无用功是个人隐私,希望我们能够归还给他。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态度斩钉截铁。那可是一件罕见的藏品,收藏价值极高,要是那个男人达到了目的,博物馆会蒙受巨大损失。
博物馆关门后,我都会失魂落魄地离开。最开始,我觉得等待第二天的到来漫长得难以忍受。不过,现在我已经学会了等待。
同样,我也习惯了弗吉尼亚的存在——要是没有她,博物馆的存续在我看来就是无稽之谈。我想馆长先生也这样认为,因为他已经决定给她升职。他任命弗吉尼亚为神庙女祭司,想必是考虑到这一使命的神圣性——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守护着生者那些转瞬即逝的回忆。
楚云飞//摘自《世界文学》2023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吴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