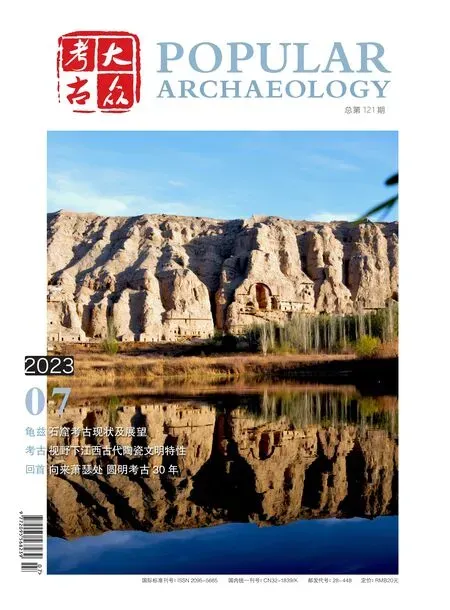跨越万年的圣殿
——哥贝克力丘
文 图 / 杨雅洁

哥贝克力丘建筑场景复原
哥贝克力丘遗址(Gobekli Tepe)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安纳托利亚地区尚勒乌尔法镇东北约15 公里的Germuş 山脉的顶点,占地约9 万平方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由早期椭圆形或圆形建筑和晚期矩形建筑组成,遗物主要发现于建筑回填物中。20 世纪60 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次联合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直至1994 年,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才认识到该山丘存在隐藏的建筑,并于次年开始主持发掘工作。至2014 年,这项发掘工作作为伊斯坦布尔大学、尚勒乌尔法博物馆和德国考古研究所的联合项目,由土耳其考古学家内克米·卡鲁尔(Necmi Karul)主持发掘。哥贝克力丘遗址以其独特的建筑造型、抽象雕塑、写实绘画、“T”形石柱等引起广泛关注,201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哥贝克力丘建筑
早期建筑
哥贝克力丘早期建筑也称作哥贝克力丘石阵,距今约12000—9500 年,呈圆形或椭圆形,中心树立一对巨大的“T”形石柱,其外侧由稍矮的独立“T”形石柱环绕,彼此以墙壁相连形成直径为10—30 米的圆圈,部分建筑环绕圈数达三重。通过地球物理调查手段发现,石阵覆盖整个山丘,除正发掘的9 处石阵,另发现10 余处建筑。考古队员按照字母顺序对已发掘石阵依次排序,A、B、C、D、G 石阵位于山丘南部洼地,F石阵位于山顶西南, H、I石阵位于西北洼地,E 石阵位于西部高原。其中D 石阵是迄今为止哥贝克力丘发现的最大且保存最完好的早期建筑遗址,中心树立两根“T”形石柱在0.2 米高的基座上,高约5.5 米,重约8 吨,周围环绕11 根独立“T”形石柱。值得一提的是,石阵并非一次性建成,而是经过多次建成。以C 石阵为例,由外至内共有三道围墙,分不同时期建成,内部空间逐渐缩小,部分“T”形石柱刻意从早期围墙中取出,再嵌入晚期围墙中。由此可知这类圆形或椭圆形建筑持续使用上百年。
晚期建筑
哥贝克力丘晚期建筑围绕早期石阵四周排列,形成台地,其年代稍晚或同期,距今约10800—8500 年,外表矩形,地面铺设水磨石,建筑规模不等,较大的建筑面积达29 平方米,较小的建筑面积不超过5 平方米。较大的矩形建筑内部也见“T”形石柱,高约2 米,但并不置于中心。除石柱外,部分建筑还配备石质长椅和台座。考虑到晚期矩形建筑大多相邻起建且共用一面墙壁,推测可能为同时期建造。
“T”形石柱
哥贝克力丘遗址的“T”形石柱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主要分布在早期圆形或椭圆形建筑中。根据所处位置不同,可分为中心石柱和围墙石柱,前者高达5.5 米,后者则稍矮,高约4 米。中心石柱一般成对出现,围墙石柱则面向中心石柱环绕排列。石柱的“T”形外观或是一种拟人化的表现,以D 石阵的一对中心石柱为例,“T”形石柱上端的横直部分可看作对人头的抽象表达,窄面代表人脸,“T”形石柱下侧的竖直部分,在其侧面可见两只手臂下垂,双手合拢于腹部上方,腰带和兽皮状腰布进一步强调“T”形石柱的拟人化特点。由于腰布的遮挡,尚不清楚“T”形石柱所代表的性别。但在Nevalı Çori 遗址发现的史前泥塑中,仅男性泥塑佩戴腰带,由此可知这对“T”形石柱可能代表两个男性个体。

“T”形石柱

“T”形石柱复原后
“T”形石柱不仅是一种拟人化表达,其上还多雕刻有写实的动物形象。A 石阵的一对中心石柱均装饰有大量浮雕,描绘的动物有蛇、原牛、狐狸和鹤。D 石阵的中心石柱和11 根围墙石柱均分布大量动物形象,狐狸、鸟类(如鹤、鹳和鸭子)和蛇最为常见,另还见野猪、原牛、羚羊、野驴和更为大型的食肉动物。其中43 号石柱的西侧宽面满饰各类浮雕,可能暗含某种叙事。主浮雕为一只大秃鹫,左翼抬起,右翼指向前方,右翼上方的浮雕可能为球体或圆盘。大秃鹫右侧的浮雕包含一只鸟(或一只朱鹭)、一条蛇、两个“H”形符号和一些野禽。石柱的竖直面板上,一只巨大的蝎子和一只鸟的头颈占据整个画面。鸟的颈部右侧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图案,虽然破损,但仍能辨别这是一个生殖器勃起的无头人形象。整幅画面可能预示着暴力死亡。另在H 石阵的56 号石柱上密密麻麻排列约55 只动物图像。
通过统计各建筑刻画的动物形象,学者发现每个建筑偏爱的动物各不相同。例如,A 石阵的图像以蛇为主,B 石阵则常见狐狸的形象,C 石阵的图像被野猪取代,而D 石阵的图像更加多元化,鸟类占比更大,H 石阵则以猫科动物为主。显然这些动物形象的选择暗含规律,并非随机选择。因此推测不同图腾信仰的人群在此相聚,一同参与营建哥贝克力丘的工作。
建筑回填堆积
哥贝克力丘建筑使用结束后即被有意回填。D 石阵的填土剖面显示,回填从两侧向中心快速进行,回填物包括动物骨骼和石器残片等。可能受回填行为的影响,哥贝克力丘遗址中几乎未见碳化大植物遗存,但根据植硅石分析可知遗址地层中均含有大量谷物,包括野生大麦和小麦。通过分析回填物中出土的石器残片,发现主要以磨具为主,包括磨石、磨碗、磨盘、杵和臼。石器原料为玄武岩,而在距哥贝克力丘约2 公里处发现大量此类岩石,可能为哥贝克力丘石料场。其中磨碗体型较大,最长直径可达50 厘米,其中几件磨碗上残留有赭石的痕迹,说明这类器物不仅用来捣碎加工食物,还可能加工其他材料。另有一类特殊的磨碗,底部有一小孔,应为使用一段时间后出于给谷物脱壳的目的刻意而为。磨石数量最多,有近3400 块。通过观察磨石表面的使用痕迹,一部分表面痕迹并不明显,可能是短时间内沿磨石边缘做环形或双向运动,另一部分磨石边缘磨平,中间形成圆坑,可能是长时间研磨所致。另外,磨石边缘所含的植硅石数量是断面和背面数量的2—3 倍,再一次证明主要使用磨石边缘加工植物。根据考古情境分析,大部分磨石位于建筑回填物上层或屋顶塌陷处,同时在矩形建筑和圆形建筑之间的空地上还发现大量磨石,说明研磨和加工谷物可能是在建筑屋顶或外部区域进行。

D 石阵的“T”形中心石柱

“T”形石柱上的雕刻

石钵
除石质磨具,还发现石质容器,包括石钵、石盘、石槽等。石钵体型较小,容量最大不超过5 升。根据壁厚程度,可将石钵分为4 种类型。石钵上可见制作时留下的琢痕、划痕,无使用痕迹,器壁虽然均匀但未抛光。石槽形状不同,既有圆形也有方形,直径在0.6—1.12 米,容量为30—165 升,其中6 件石槽完整放置在建筑地板上,或靠墙安放,或置于建筑一角。其中一个石槽四周附有灰烬且底部有火的痕迹,表明石槽的使用与火有关。
回填物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绵羊数量位列第一,原牛数量位列第二,除此之外,瞪羚和亚洲野驴骨骼也有大量出土。而瞪羚和亚洲野驴具有季节性迁移的属性,可在仲夏和秋季之交对其进行大规模捕杀,因此暗示当时在哥贝克力丘曾短时间内开展过大规模捕猎活动。
建筑功用推想
哥贝克力丘遗址所处位置十分特殊,位于荒芜的山脊之上,向下望去是相对开放的森林草原,主要生长阿月浑子树和杏仁树,地形多变且无法获得水源,最近的外流湖距此地约5公里。虽然有证据表明遗址西侧的石灰岩高原上有一个可能为新石器时代的蓄水池系统,总容量约为153 立方米,但季节性雨水补充仅能保障小部分人群长期在此居住。鉴于上述分析,哥贝克力丘显然并不是理想的居所。但在哥贝克力丘建筑回填物中,大量野生动物被猎杀和消费且出土大批量石质磨具和器皿,表明在哥贝克力丘的确活跃着一定规模的人群。值得一提的是,在遗址中并未发现大型筒仓等储藏设施,进一步证明生产并非为了储存而是立即使用,因此这些人群可能出于共同营建哥贝克力丘的目的相聚于此,举行宴饮和祭祀等仪式性活动。

矩形建筑中的石槽
哥贝克力丘建筑的营建工作繁重且复杂,无论是从采石场运输巨大石材,抬起并竖立石柱,还是对石柱进行浮雕装饰,均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除此之外,在整个营建过程中,除劳动用人,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在印度尼西亚西松巴的科迪地区,运输建造巨石墓的石头前需进行仪式,多数人作为见证者参与其中。因此考虑到计划、组织、协调建筑工程的需要以及劳动力聚集的方式,人群的数量很可能超过单个部落甚至当地狩猎采集群体人数。据此不妨想象一下,早在一万多年以前,不同部落的人群因血缘、亲友、伙伴等关系网络汇聚在哥贝克力丘,开始任务分工和建筑营建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在建筑中举行大型仪式活动,并享用大规模宴饮,以此缓解社会和工作压力。因为营建工作持续不断,所以不同人群定期在此聚会并开展集体活动,期间通过交换货物、信息等方式进一步增强社会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