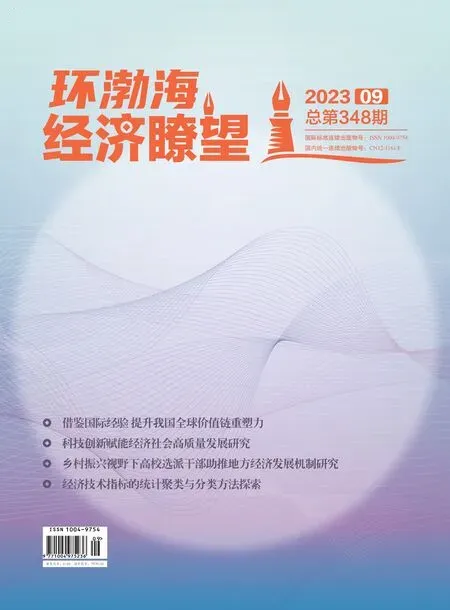借鉴国际经验 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力
许潆方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全球重要的经贸中心。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当前,全球价值链呈现非对称的结构性权力网络特征,在发展布局上受跨国公司主导,在主权国家影响下逐步呈现区域化、分散化倾向。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借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扩展经验,对于我国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国应以区域价值链为重点,以跨国公司为抓手,积极共建具有规则标准引领力的国际组织,更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上的塑造力。
二、价值链分工的内涵
随着制造业技术革新和运输条件改善,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重心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各类分工在不同国家间同时并存,呈现出多层次格局[1]。其中,“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演进过程,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形成跨区域或跨国别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供应活动[2]。
处于主导地位的厂商,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越的区位布局相应的产品生产加工环节,使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专业化分工,逐渐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3]。2002 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对全球价值链作如下定义:“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该生产链涵盖商品生产与服务环节,这种连通区域的生产、加工、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国性生产网络,可被解读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链。”[4]
三、全球价值链的特征
(一)非对称的结构性权力网络
有学者基于现代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非对称性和权力的来源进行了阐释。Albert Hirschman 指出,国家双向互动中的“相互依赖”是通过全球性生产网络实现的,“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则构成了权力的来源,体现了两国资源禀赋之间的差距[5]。有学者在复杂网络理论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进行了解构。余南平指出,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链接具有不同的权重、强度或流量参数,使得网络节点中的国家在对外链接中拥有不对称权力。全球价值链由于具有网络增量式增长特征,使得新链接在选择节点时偏向拥有更多链接的节点,强者愈强的集聚效应促成了全球价值链枢纽节点的形成[6]。还有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分析,庞珣等人指出,结构性权力并非直接对特定行为体产生影响,而是依赖于结构这个媒介。其中,结构性权力的敏感性体现在某一节点的变化对结构的影响幅度和调整压力,结构性权力的脆弱性体现在节点断联对结构整体造成的损坏程度和结构重返稳态需要的成本高低[7]。
所以,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科学技术、社会服务、熟练劳动力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承担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的分工环节,占据了U 型的增加值分配结构的两端。其中,价值链上游国家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通过稳固科技创新基础、抢占科技制高点,进一步强化自身在科技创新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依靠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承担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分工环节,所能获得的增加值相对有限。在获得较高增加值的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获取具有优势的层次地位和链接能力,通过产业链分工的链接传递和扩散国际权力,控制价值分配,影响国际关系。然而,发展中国家并非只能滞留在低端价值链环节。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枢纽节点不一定始终被一国把控,具有更高适应度的网络节点往往胜出并具有更强的枢纽优势。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借助分工合作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善分工地位,实现价值链位置由低端向高端跨越的目标。这使得后发国家具备创造新枢纽的潜力,具有后发竞争优势。
(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布局
当前的跨国分工中,跨国公司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了全球价值链布局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21 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跨国公司通过牵引全球资本、组织劳动力和技术的跨境流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使得生产网络链接呈现更显著的全球化特征[8]。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价值链中,掌握了附加值较高的中上游研发和零部件生产、下游的品牌和营销,主要在成本更低的地区布局中游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组装环节,通过自身的跨国经营网络和供应链管理体系,整合全球资源并降低成本。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跨国企业在全球的采购和销售网络将标准化的制造工序外包,并继续保有核心技术环节,由此形成了由技术发源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通过货物、服务和技术流动实现经济规模和资源优化效应,推广了新技术、新产品和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整合和协作提高了全球生产力和效率水平,促进了地区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技术水平有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设计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能被动接受安排,扮演加工组装的角色。跨国公司作为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决定了一国的哪些企业进入某种产品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参与国,对最终产品购买国保持贸易顺差还可能引起贸易摩擦。世贸组织前总干事Supachai Panitchpakdi 也指出,跨国公司组织的要素跨国流动协作,也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建议发展中国家留有充分的政策空间[9]。同时,跨国公司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与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存在一定分歧,跨国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并非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最大化。
(三)区域化、分散化倾向的全球价值链布局
在地缘政治影响下,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的选择成为兼顾效率和安全的折中方法。大国博弈激烈的世界格局导致价值链的市场化布局深受干扰。当前,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节点国家都在寻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而区域化、分散化的价值链布局则是跨国企业主动和被动因素影响叠加后的选择。
在区域经贸协定推动下,北美、欧洲、亚洲等“区域内”的循环和联系不断增强,全球供应链由原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事研发、高端与中高端产品制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事中低端产品制造和组装加工,中东和俄罗斯等提供能源的“大三角”格局向“三足鼎立”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转变,即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供应链网络,由德国、法国等国家主导的欧盟供应链网络和以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东亚经济体为核心的亚洲供应链网络,三大体系内部贸易增多,与外部也会发生关联。
四、美国主导全球价值链布局的经验
(一)以跨国企业把控全球价值链分布格局
在分工复杂、链条长且技术迭代迅速的产业中,结构性权力往往高度集中于头部跨国企业。美国是最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开展跨国公司研究的国家,吉尔平指出,跨国公司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扩张战略,不可能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目标[10]。英国学者戴维·麦克格鲁指出,跨国公司是国家体制的产物,其成功与母国的强大息息相关。苏珊·斯特兰奇分析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时指出,跨国公司由于在生产端掌握了技术、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在市场端控制了销售网络,所以能够对国家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11]。二战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快速扩张,美国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战略,推出激励跨国公司发展的系列政策。一方面利用资本市场掌握了众多高附加值两端的创新、设计、品牌等企业所有权,其中部分企业成为大型跨国企业,在拓展市场过程中获得巨额财富。另一方面,通过跨国企业掌握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而占据该行业的主导地位。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前100 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美国有18 家跨国企业进入百强,并且分布领域广泛,包括汽车、生物医药、石油炼制、电信通讯、计算机设备、计算机与数据处理、电子元器件、电子商务、零售、工业机械。
(二)以团体组织影响价值链标准制定
一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能够深刻影响国家间技术性贸易条款的制定和实施,影响特定行业产品的国家间竞争力。通过设定基准和标尺,影响特定产品的跨国投资和贸易,进而影响其生产和行业发展方向。美国的协会、商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标准化组织发展历程悠久,且有相当一批标准化组织在国内外拥有广泛影响,主导着产业行业领域的标准化活动。以美国标准化组织保险商实验室(UL)为例,在部分发展资金由政府拨款支持基础上,开展商业服务和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标准研制是重要内容,并且通过标准产出的市场化应用,为标准研制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及实践平台。在对内影响方面,美国标准化组织保险商试验室与美国国内标准组织合作,共同推动行业领域的标准发展;在对外影响方面,美国标准化组织保险商试验室与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合作,联合研制标准并开展相关活动,在区域合作领域,与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研制和协调国家标准,成为首个美墨加区域共同认可的国家标准制定组织,提升了区域标准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力。
(三)以区域价值链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在对华竞争战略和突发应急事件冲击下,美国认为单纯以追求效益为导向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形成了对中国等国家的制造业依赖,造就了竞争对手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供应链安全的威胁在突发应急事件暴发后进一步放大,为美国供应链体系安全埋下了隐患。在此背景下,美国倡导制造业回流,即通过推动在岸生产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伴随制造业回流的则是“近岸外包”(nearshoring)和盟友外包。上述政策激励企业回到美国本土,或者在美国的盟友国开展业务,将更多供应链转移到美国主导的区域供应链中,提高美国对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的掌控力,同时,提升对竞争对手的遏制力和国际竞争力。以美墨加区域为例,美国企业近年来更多考虑将生产基地迁移到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区域,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等“友岸外包”政策对部分行业的影响显现,墨西哥和加拿大成为更受美国企业青睐的供应链布局区域[12]。在美国制造业回流和“近岸外包”政策驱动下,墨西哥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大幅提升。由于美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网络枢纽地位,其推动全球价值链从效率驱动的全球布局向“分布式”网络布局转变,将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形态,尤其是拥有高端核心技术的未来产业或将呈现兼顾战略利益与效益的区域分布式格局[13]。
五、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重塑力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我国在区域价值链重构上的塑造力
形成以我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水平。未来,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更高的亚洲生产网络竞争力,抵御部分国家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武器化”倾向,增加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一是提升区域经贸协调与参与水平。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 版谈判中,围绕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快与框架内国家探索共同的气候利益,力争形成代表域内国家利益的标准和规则,推动具体领域绿色实践落地,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区域绿色产业链,提升亚洲生产网络在新经济领域的黏合度。二是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政策协调和机制合作。鼓励市场资金参与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建立援贷投项目相互推荐机制,推动援外和投贷联动,提升援外资金和私人资本合作水平,鼓励更多民营企业有序走出去。三是创新对外投资机制。探索与技术先进的跨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建立创新中心,拓展与全球创新融合的方式,为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深度和广度提供新的平台空间;通过与跨国资本设立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东盟地区独角兽企业,提升对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参与度。
(二)以跨国公司为重点推动价值链向U 型曲线两端延伸
跨国公司是创新研发、标准引领、规则制定、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主体。未来,要培育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持续吸引具有先进技术和市场影响力的国际跨国企业,推动我国企业参与的价值链向U 型曲线两端延伸,增加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话语权。一方面,培育国内具有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作用,高水平拓展区域生产服务网络。加强与跨国企业的“点对点”联系指导,研究在亚太地区特定行业生产和供应链网络中推广应用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的可持续生产认证标准,提升我国与亚洲区域生产网络的相互依存度,提高我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竞争力。推动具有一定核心关键技术和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工作,加强我国在国际行业标准制定话语权,培育更多具有引领性、前瞻性设计创新的龙头企业,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主动引导外资企业利用技术红利延伸拓展其他产品市场,扩大技术和零部件的在华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