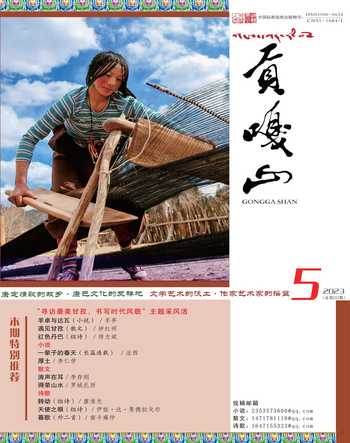三进九龙
庞惊涛
这是我第三次去九龙。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九龙是陌生的。它因辖区九个皆有“龙”字的村寨而得名。它和香港九龙区同名,但是却没有香港九龙区享有一样的知名度。一切皆因地理空间所限,足以抵消大多数人进入和探寻的热情。
虽然明知在途艰辛、到达不易,但对我这样一个贪图美景的人而言,九龙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它的宁静、旷远,它的静守深闺,它的清尘洗肺,甚至它的不事逢迎,都成为我最终选择单向奔赴的理由。
以新都桥为界,更深广庞博的高原向右,而自成一家、遗世独立的九龙向左。不用借助于无人机,只须在地图上稍作留心,便会注意到九龙西向靠近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地方,有一片面积不小的无人区。因此,九龙是四川当然而极为稀见的极地、边地小县城。其稀见正在于,既在藏羌彝走廊的核心位置,又保持了极大的独立性;既有其他走廊区域共有的雪山景观,又有特属于九龙层次丰富的雪山群;既融入了极地的生物多样性体系,又在这样的生物多样性体系里,保持了最大的全面性和私有性。这样的地理存在,对九龙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隐喻,它会在短时间内被人忽略,但必然会在人们的幡然醒悟之后,长时间地被追捧。
在这个短时间与长时间的转换过程中,的确还需要人,在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上,为九龙走出深闺助力添薪。
记得第一次去九龙的时候,正值俄色花开满甲根坝河谷地带的季节,它们散点分布在河谷、浅丘、村舍和道路之间,和藏寨外墙的色彩组合混搭,便成就了这高原上独有的美。我少见多怪,误将俄色花认成了梨花,当即向九龙县文旅局局长李世阳提出,以这样的梨花规模和立体化景观,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梨花节”了。李世阳告诉我说,这不是梨花,是高原特有的俄色花。因树冠高大丰茂、花开纯白色,所以极像梨花。
但我还是坚持搞一个俄色花节,并和李世阳讨论了怎么打造、如何传播、怎样品牌化坚守等具体方法和思路。这是对九龙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思路的第一次萌发。我明白,由于种种原因,我这样过客式的思路和观念萌发,只可能胎死腹中,而不可能很快变现。人作为这种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核心因素,一定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它必须具体到一个操盘手,或者一个文化传播主体。这个操盘手或者文化传播主体,不仅需要天时地利等因素的配合,更多的时候,还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甲根坝所在的区域行政规划上属于康定,而不属于九龙。虽然九龙的部分乡镇也有散点生长的俄色花,但规模和气势的确不能和甲根坝媲美。
用俄色花来承载九龙的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确实难了一些,也更牵强了一些。于是,位于九龙县魁多镇里伍村的天乡藏茶,便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
这是我第二次到九龙,虽然并不一定承载九龙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使命。
雅砻江高半山,海拔2500米以上,7万多株100年以上的老茶树……这些九龙独有的茶语言,一旦进入我的理解和阐释神经,便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会催生和撩拨起我那个看上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实际上深埋在心中的使命感:天乡茶清纯,回甘的口感和化之难去的独特味道,既能让我这样的老茶客得到一次意外的惊喜,也能让更多的爱茶人得到满足感。
眼前山绕带,杯中茶化诗。
一杯茶,或许更有机会成为九龙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载体。
半日行走里伍村,最爱静下来的那半个多小时。一个铁架和塑料速成的茶舍,要是改成竹石和茅草搭建的茶寮,會更切合天乡如天仙的意境。但即便如此,茶的底色是古典而柔软的,它消解了一切的物象阑人、情绪阑入和坚硬阑人。烟岚四围,霞光温柔,雨雪的意象在不紧不慢的聊天中明明灭灭,和四代制茶家族传人的一番晤对,让我坚信,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物质载体来完成九龙地理空间的推扬和口碑传说,那么就没有比茶更适合的了。
回到成都后,我将这样的想法和李世阳、魁多镇领导、制茶传人等关键人的多番沟通交流,说到人的因素,如果没有操盘手和文化传播主体,那么作为群体的、团队的合力一定可以承载这样的使命。我试图将这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普米记忆上升为整个汉族与藏羌彝走廊所有民族共同的时代记忆和文化记忆。茶马古道见证的这段历史,理应在这个时代承载崭新的文化使命,就像铁观音之于福建、普洱之于云南一样,天乡之于九龙,实在是天经地义的。
如今三进九龙。天乡茶当然在继续释放它独有的茶性和香气,但九龙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使命,并没有落到它的名分上来,它占据了天时和地利等优势,却未必在人和上得到最有力量感的机缘。
已是仲夏时节,进入九龙的体感却是清凉,甚至有一些微寒。车速80码,不急不缓之间,清晰看见河谷奔流浩荡的水和高大的树,想象假如这样的场景换在成都近郊,必是成人的水中麻将和孩童的水中嬉闹声,交织的繁盛热烈景象。一切因为到达不易而被政变,那么在物质载体承载不起或者没有机缘承载的情况下,观念载体能否成为九龙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救赎?
在河谷和大树之外,后来我又看到了依傍河谷和大树生长的草甸之间,那些蘑菇一般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帐篷。它们貌似毫无章法,实则井井有条地安扎在河谷地带,游人自带饮食和寝具,就为了享受这样一方遗世独立的极地美景。
在李世阳的补充介绍里,证明了我的某种猜想是成立的:对那些追求极地野外奢侈体验的小众游客而言,这样的河谷,的确不应该被世俗的麻将侵扰,被尚未建构起观念意识和精神享受的孩童所占据,的确也是因小失大。
一个超越于物质载体之上的观念载体就这样萌发:假如花与茶作为物质载体,皆不能承载九龙地理空间推扬和口碑传说的使命的话,那么作为观念载体的“极地野奢”,便是九龙突围最大的可能。其“人和”因素,不是操盘手和团体的主人视角形成的,而是从帐篷客、自驾客的客体视角形成的。大多数时候,客体视角比主体视角,更能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
在这个观念载体里,无论伍须海,还是猎塔湖,或者华丘村、猛董,都是“秘境九龙,极地野奢”观念先行的整体。围绕这个整体,九龙要主动吸引,争取追求野奢、自由的定制客群,与追求时尚、轻奢、浪漫、安静的中产等新生代客群。当然,帐篷不是随便搭的,规划和调控必须发挥作用、形成力量。
在我的想象里,当五颜六色的“小蘑菇”开满九龙的雪峰与河谷之间时,“不以山海为远”的九龙,就能从庞博神秘的高原、极地突围而出。假如约瑟夫·洛克重回九龙,我想,他也会为九龙的“极地野奢”由衷认可。
1929年,美国探险家、旅行家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进入九龙,立即被其遗世独立的美景所吸引。作为第一个走进这片秘境之地的外国人,洛克的九龙之行堪称奢靡,除了被当地宗教首领接待安排住在最好的住房里之外,洛克随行的豪华马队,也为他带来了随时可以安营扎寨的帐篷和折叠床,还有便于他就餐和写作的椅子、桌子,桌子上面当然还有优雅迷人的桌布和昂贵的瓷具。为了便于他随时记录一路景观和植物标本,笨重而稀罕的照相机,也是马车队带来的奢侈品。此外,供他闲暇时享受用的电池供电留声机,更是九龙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天外来物”。行走极地,享受野奢,洛克既是20世纪九龙海外地理空间推扬的第一人,也毫不争议地成为今天九龙“极地野奢”口碑传播的代言人。
在洛克走进九龙即将抵近100周年这个时间关口,作为观念载体的“秘境九龙,极地野奢”的自然形成,莫不是洛克早就形成,而未来得及对外宣扬的想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花与茶之后,“极地野奢”能承载得起九龙并帮助九龙完成这次突围吗?
从九龙离开往成都赶的时候,我内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不舍和眷怀。或许,从这一刻起,我和九龙便从此建立起了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谁说大地无情呢?只要那个“我”有情了,大地的“情”才会绵密厚实,渊海而来。
此刻,我竟然如此期待第四次进入九龙,不是以某种使命而去,而是单纯地因为想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