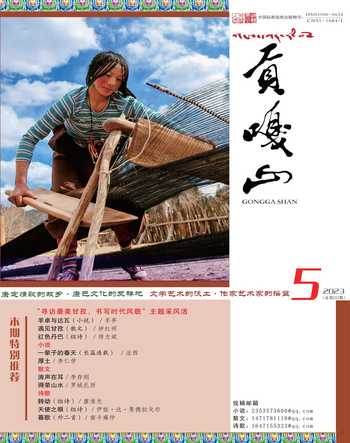倾诉
武俊岭
媳妇
我娘家袁楼村,我姓袁,名叫红云。七月的一天,娘生我时,爹爹看见天上飘过一块红色的云彩,就说闺女叫红云吧。
我嫁给刘庄的刘建功四年了。日本鬼子打卢沟桥的第二年,我与建功过了半年的太平日子。这天,建功对我说,我到聊城去,参加范筑先将军的队伍,打鬼子!
我听了,吓得一下子抱住他,像抱住不满周岁的娘家侄子。我的心快跳着,说,你是刘家的独子……
建功胸脯一挺,挣脱出来,说,咱俩成亲也不是一天了,你知道我不是在灶火窝里转悠的男人。日本鬼子要打聊城了,我不能在家躲着。
婆婆闻声走来,看看建功,看看我,说,功儿,你说的话我听见了。你去吧,放心家里!地,租给你叔算了。
我听了,立即对婆婆生出一丝怨恨:从成亲一个月开始,婆婆的眼睛就像刀子,一下一下地往我的肚子上剜。恨不能我的肚子像吹气那样大起来,给她生个大胖孙子。建功天天在家,还不能让我有孕,要是再跑到部队上去,生孩子更没指望了。
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家里,婆婆是说一不二的。我只好眼含泪水,为建功收拾衣服。
建功是与后村的一个叫长戈的人前往聊城的。一个多月后,聊城被日本人攻陷,范将军受伤自杀。
两个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半年后,两个人转到县抗日大队。再半年,建功当上中队长。
几年间,建功偷偷回家的次数也就六七次吧。偷偷地,是怕被汉奸、特务发现。
每次相见,建功都很渴,都很可怜。我像一个母亲抱住吃奶的孩子,又爱又怜地配合他。
我偶尔回一趟娘家,会遇到大娘、婶子拉着我的手,悄悄地问怎么,还是没有喜吗?
我的脸又红又热,羞怯得把头低下,不说什么。
看到与我年龄一般大的伙伴,很大本事似的抱着孩子回到娘家。不管是出五服没出五服的大娘、婶子,争抱孩子逗乐。那当母亲的站在那里,脸上一层荣光,像是一个功臣似的。碰上这样的场面,我立即躲开。
这次回娘家,我娘说,等建功再回家时,你俩看看杜远心吧。
杜远心是我们寿张的有名中医,擅长内科、妇科。
寿张城里有鬼子,建功怎么进去呢?
娘说,把杜医生请出城来。
回到刘庄,我把我娘的话说给婆婆。婆婆双手一拍,很脆地一响,说,这个主意好,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呢?
刚开春的一天夜里,建功悄悄回家。煤油灯下,婆婆向他絮絮说道。翻来覆去,强调的只有一句话:得给刘家留个后。
建功把手臂抡个半圆,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婆婆急了,骂,娘的,你才出去几年,说话怎么不像我的儿子了?
建功把头低下,右脚来回擦着地面。这时的建功,或许是想起了当娘的年轻守寡,拉扯他长大不容易。于是,建功说,好吧,我听娘的。
建功从衣袋里掏出三块银圆递给我。
我接过银圆,说,我明天一早就回娘家,见了我哥哥就让他去找杜医生。建功,你吃了中午饭往我家去。
婆婆、建功点了点头。
第二天晌午歪时,建功、杜医生先后来到我的娘家。
杜医生年近六十,白须飘飘,走路颤颤巍巍。杜医生的一双眼睛亮得像两颗寒星。杜医生先为建功把脉。他说,这是一位壮士,身体没事。
为我把完脉后,杜医生拈须沉吟,徐徐而说,你有宫寒之症,须调理之后,方可怀孕。
说完,杜医生从上衣口袋里抽出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张处方。
杜医生说,往我诊所抓药,可以;往药铺,也可以。半个月,准好。
我哥哥连忙说,自然是往杜医生的诊所去了。
杜医生笑一笑,起身离去。门外有一辆小马车,载上他,蹄声嗒嗒离去。
一连半个月,我喝那苦涩的药水。
在东屋空地,用三块青砖支起砂锅。婆婆坐在一个蒲墩上,把芝麻秆一折两截,放在砂锅下面。芝麻秆干干的,一点就着。火红红黄黄的,散发出芝麻香味。不一会儿,砂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着,往上冒着白汽。闻着,苦涩之中有淡淡的芬芳。我盼望着药水快点熬好,喝下去。更盼着半个月的药水喝下,病症消失。
一小时后,婆婆把药水倒入一只白瓷碗里。随后,往另一只碗里倒入白开水,里面放了一点白糖。
待药水不热时,我端起来。婆婆说,红云,屏住气,一气喝下。
我听婆婆的,张开嘴,把药水喝进肚里。
从口腔到嗓子到肠胃,一路苦下去。残留在口腔里的一点药水,让我想呕吐。婆婆连忙把水碗递给我。我喝下去几口白糖水,把恶心压下去。
按照约定,建功半个月后回来。为了完成心愿,建功好像十分在意。建功除了吃饭时走进堂屋,与他娘说说话外,其他时间就关上大门、关上屋门,时时黏我。他这样,把我羞得不轻,我说,你让我怎么面对婆婆呢?
建功说,我听娘的话,留个后,留个小战士,好与日本鬼子永远干下去。
三天努力,一个月后得知,瞎子点灯白费蜡:信水照来。
婆婆有点沉不住气了,说,都说杜远心是神医,这次,怎么不神了呢?
我的嘴角动了动,没有说出什么。
建功打仗,万一有个好歹,老刘家不就断后了。婆婆说完,脸庞痛苦地变长。婆婆流下两行泪水。
我的眼睛先是红,后是热,最后泪水下来。我恨自己不争气,我恨自己吃药不见效。
一连五个月,建功没有回家。
我对婆婆说,也不知道建功什么时候回家?
婆婆說,他是八路军战士,怎能随便?
婆婆见我不说什么,说,回家,也是白搭。说完,婆婆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婆婆这话,我不完全赞成。两口子睡觉,不能光为生孩子。我是一堆干柴,建功是一团烈火,遇到一块儿,烧上一烧,也是天经地义的事。鸟儿,还翅膀紧挨着往前飞呢。就连小小的蚂蚱,也知道配对。
转眼到了秋末,场光地净,北风多了起来。
两个女人,一个大院,除了进出,大门都是关着的。院墙老高。墙头用三合土固定上玻璃。玻璃尖朝上,如剑如刀。
我在油灯下,为建功做鞋。别看建功中等身材,脚却特别大。他的脚像刀子,特别费鞋。这样,我做鞋底时,就比平常的厚上一半,针脚也更密实。
油灯灯芯出现一个灯花,啪的响了一下。我困意上来,吹灯睡觉。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堂屋里的婆婆大声呼喊,建功,建功,你媳妇生孩子了。
我听了,立马没有了困劲。我侧身躺在被子里,对建功生出强烈的渴念,建功、建功,你怎么还不回家呢?既然睡不着,那就起来做鞋吧。屋子里很静,院子里也很静,静得能听见鸡窝里的鸡不时地咕咕叫唤。
婆婆梦话后的第三天中午,吃完饭后来了困意。
我说,娘,你睡吧,我给你关上门。
婆婆“嗯”了一声。
我返回东屋,为婆婆缝制棉袄。穿针引线的细微声音,把我对建功的思念轻轻压住。
感觉屋门口突然黑了一下,我一抬头,立即喜得张开嘴巴,想发出一声呼喊。
是建功,我梦里经常见的人,走进了屋子。
我说,大门不是关着吗,你怎么进来的?
建功嘿嘿一笑,说,咱家的大门,还能挡住我。
建功把屋门虚掩了,又把我手里的针线夺走,开始解我的上衣扣子。
我说,别慌,声音小点。对了,插上门闩吧!
建功说,在自己家里,插什么门闩呢?
我说,婆婆,有婆婆呢。
建功已是听不进我的话,把被子一下掀开。这时,屋门一下子哗啦打开。门声刚停,婆婆的声音响起,大白天里,怎么了这是?
建功连忙说,娘,是我,建功!
婆婆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你刘建功回家,也不向老娘请安,就跑到媳妇屋里来了。我还以为是野汉子呢。
“野汉子”这三字像是一把钢刀戳在我的心窝。我一下子坐下来,极快地穿上衣服。
这时,建功已是扑到婆婆面前。建功双手抱住婆婆的双腿,呜呜痛哭。
婆婆披散着半白的头发,一边哭,一边说,我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五六个月不回家,回家后不进堂屋门,一头扎进媳妇屋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你娘可是年轻守寡,把你拉扯大的。
婆婆说到这里,用手里的拐棍朝建功的后背打了几下。砰,砰,砰,一声一声,让我的心一下一下地疼。
我抢到婆婆跟前,抓住拐棍,说,娘,你打我吧,是我不好,是我没让建功向你打招呼的,我说娘睡着了。
不想,婆婆听了我的话,怒气更大了。婆婆破口大骂,建功,你娘的,你就是没老没少,回到家不向你娘问安,八辈子没见过媳妇吗?
儿子
我被娘骂得狗血喷头,在家里存身不住,只好低头急步走近大门。大门门闩是插着的,我先拔销头,后开门闩,出了院子。我是从东屋屋顶上跳进院里的。
我一路往北,从麦子地里。虽然是半下午了,一寸多高的麦苗上,还有一点晶亮的水珠。我知道,这是凝结在麦苗上的冷霜,气温升高后化成的清水。我的心里,有霜有冰。娘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儿子一时失礼,也不能那样对待儿子吧。再说,那样对待红云,更不公正。红云进刘家门后,一向规规矩矩。红云为闺女时有名地孝顺、正派。
娘,你进了门,知道了是儿子,就应该退出去。让儿子与媳妇把应该办的事办完,再请罪也不迟。娘,你不是盼着红云生下儿子吗?没有我,怎么能生出来呢?
红云是一个好媳妇。成亲那天,我掀开红盖头,红云抬头看我。她的眼睛明亮得像荷叶上的露珠,似旱地里的清泉。从头看到脚,俊;从脚看到头,俏。一根独辫,又黑又亮。脖子像蛋白那样白。黑、白两种颜色是那样分明。我时时凝视,恨不能把红云看到眼睛里去。虽然说娶媳妇,是要她的贤惠,不要她的颜色。如果贤惠、颜色两样都占,岂不更好。红云就是两样都占。我建功何德何能,能娶到这样的媳妇,真是烧高香了。
红云心灵手巧,我的、娘的冬棉夏单,都是红云一手缝出来的。红云不只衣服做得好,鞋做得也好。
结婚后,我在黑夜里大干一个月,挖好两条地道。堂屋一条,东屋一条。两条地道的出口,在堂屋东边的小门旁边会合。小门用两寸厚的枣木做成,并且在门板上钉上了厚厚的铁皮。平时,小门从不打开。大门也换成榆木的,有两寸厚。两道门闩,枣木的,裹上铁皮。并且,在门闩的两头钻孔,插上销头。外面的人,别想用刀子拨开。
不这样不行,有土匪,有鬼子,有这兵那兵的。
對娘,我是既敬又畏。我知道娘二十四岁守寡,把两个姐姐和我拉扯长大,不容易。我爹死后三年,我姥姥劝我娘改嫁。娘说,我带着三个孩子,三个拖油瓶,嫁给谁,又有啥嫁头呢。
娘为了养活我们,秋天里,带着两个姐姐扫榆叶。娘把榆叶晒干,用簸箕簸净,然后存在一个囤里。春荒时,就把榆叶磨成面,掺上地瓜面,蒸窝头吃。
夜里,不管冬天、夏天,娘天天摇动纺车纺线。纺车一圈一圈地转,嗡嗡声里,我在娘的身边睡觉。有时睡醒一觉了,要解手,娘还在纺线。
娘是好娘,就是脾气暴躁,家法多,礼数多。稍不如意,就会爹啊娘的痛骂。我自小怕娘,娘说话的声音稍微一高,我就会浑身哆嗦。我想,娘如果不是一个寡妇,大概不会这样吧。
我的脑子里想着这些,向北一阵猛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到了一个村子的东边。这个村子,是昨天我带着中队战士打下来的。
村子里原有三十多个皇协军,不经打。我与战友放了几枪,皇协军就投降了。这样,我们中队就得到三十多支三八大盖。我向大队长请假,让副队长指挥队伍,然后走回家里。没有想到,回到家后,被娘骂了个晕头转向。
失魂落魄的我,连村头没有一个哨兵都没有觉察。我莽莽撞撞地往里走,走到村子中间时,听到了日本兵呜里哇啦地说话,才知道情况有变。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
我急忙躲在由一面墙、一排玉米秸秆斜搭成的洞里。没有想到,这洞很浅,不到一米,往里是结实的木柴。
一个做饭的日本兵搬玉米秸时发现了我。
我的本事,对付一个日本兵没有问题。况且,这个日本兵年近四十,自然不是我的对手。交手三两下,我一脚踢中他的心窝。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哇哇叫唤。
三个日本兵围住我,费了一点劲把我摁在地上,捆了起来。我腰里别着手枪,自然被搜了出来。
一个身材像豆芽的翻译官惊讶地说,这人身手不错,是个硬茬子。
我骂,去你娘的!
一个鬼子军官走来,问了翻译官一句。翻译官回答,这个是抗日大队的。
军官让两个鬼子把我押进一口高大的堂屋里。
軍官说一句,翻译官译一句,喂,八路,投降不?
我把头一摇,说,你爷爷不投降!
这时,走进来一个皇协军军官,手里拿着马鞭。
皇协军军官又问,到底投不投降!
不投降!
我让你脖子硬!
皇协军军官说完,马鞭朝我脖子抽来。立即红印一道,疼痛如刀割。
我怒骂,×你奶奶!你敢放了我不?
皇协军军官会说几句日本话,对着那个日本军官说了两句。然后,皇协军军官对着两个士兵大声说,去挖一个坑,两米。
我双臂虽然被绑,但双脚是自由的。我感觉出来,坑肯定是为我挖的。是枪毙我后埋进坑里,还是用坑活埋我呢?如果是活埋,一定十分折磨人,不如一枪毙命痛快。
想到这里,我的怒火燃烧起来。我悄悄地观察,我离鬼子军官有三米多。我飞起一脚,踢不到他的脸面上。走近他,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身边,一边一个鬼子。那就对皇协军军官下手吧。
我说,狗汉奸,龟孙子,你过来,我对你说句话。
这汉奸以为我回心转意了,笑眯眯地向我走来。在离我不到一米的时候,我的上身往左猛然一倾,随即飞出右脚,踢在皇协军军官的大嘴上。皇协军军官扑通摔到地上。皇协军军官手捂嘴巴,吐出两颗门牙。皇协军军官气得嗷嗷怪叫,拔出手枪。
鬼子军官过来,把手枪按住。鬼子军官把手臂一挥,说了一句。翻译官说,押到街上去。
这时,天快黑了。暮色像是冷硬的北风罩住村庄,罩住鬼子、伪军,自然也罩住了我。一股新鲜、冰凉的泥土味儿钻入我的鼻孔。也怪,这时的我像是六七岁的孩子,竟然对这土味感到无比亲切。老子生下来,就睡在沙土布袋里。沙土布袋像是母亲的怀抱,让我温暖,让我的尿浸不湿我的屁股。五六岁时,我与伙伴们团胶泥玩:摔瓦屋、印泥模。再大一些,我就帮助两个姐姐翻地、耙地,往土地里播种。最后,鬼子、伪军要用土把我弄死。弄就弄吧,但是,要想让老子服服帖帖,没门。
我走到深坑边上,往坑里看了一眼。鬼子用手一推,我跳进了坑里。我的眼前立即一黑。这坑,有两米多。因为我估摸,我的头离地面还有半米多。
两个鬼子和两个伪军开始用铁锨往坑里填土。我闭上眼睛——临死也不能让鬼子把眼迷住。很快,土到了我的大腿根。
土到胸脯时,我感到了呼吸急促。超过胸脯时,我的眼睛好像在往外渗血。这时,一个念头萌生,如一把刺刀攥在了手中。我立即行动。我的身子猛一用力,竟然往上挺出几公分。土一锨一锨地增加,但我的身子不停地上挺。这样,时间不长,我的眼睛高出地面。
浓浓的暮色里,我看到村庄里的乡亲,或者站得远远的,或者趴在墙头上,观看鬼子对我的活埋。我运气于丹田,说,乡亲们,不要怕,今天鬼子活埋我,明天我的战友就会为我报仇!
我的声音听来异于往日,没有了嘹亮,没有了浑厚,有的,只是沉闷。但是,这沉闷的声音,乡亲们还是听到了。皇协军军官走到我跟前,说,如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皇军答应你,让你当皇协军的副大队长。
我吐出一口唾沫,骂,滚你奶奶的!
皇协军军官离开我,走向鬼子军官,走向翻译。三个人一阵子叽里呱啦后,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
我看到,一个石磙,就是打麦场上辗轧麦子的石磙,由两个伪军推着,一圈一圈地向我滚来。
隐隐约约中,我听到了乡亲们的啜泣。
但是,哪怕死在眼前,我仍然要痛骂鬼子、汉奸。我骂,小鬼子,老子化成厉鬼,也要咬死你们;二鬼子,你们不得好死。
石磙到了我的眼前。石磙就是勾魂使者,黑黑地、重重地朝我压来。临死之前的一瞬,我脑子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娘啊,你不骂我不行吗?
娘
世间要是有卖后悔药的,我即使拆掉房子,卖掉一砖一瓦,卖掉大梁檩条,也要买来一副,苦苦地吃下,挽救我那娇儿的性命。千不该万不该,我心里的魔鬼冒冒失失地出来,发了一阵子邪火,把儿子骂出家门。
想想我萧玉芳,二十多岁守寡,不容易。虽然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依然身子直直的,脸庞白白的。走在大街上,有不少男人的眼睛对我上下打量。我娘劝我改嫁,我也动过心,但一想到三个孩子要去当带犊儿,心里就疼得没法。干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一天一天地往前过吧。
这样,就不允许男人在我家门口转悠。这天,一个闲汉在大门口遇见我,说嫂子,你闲着也是闲着,让我用用呗。我听了,立即火冒三丈。我从家里拿出一把菜刀,冲向闲汉,一刀砍了过去。闲汉躲得虽然很快,上衣衣襟还是被我削下来一块。即使这样,我的怒气仍然不消。我一直追到他家的大门口。我一边用刀猛砍大门,一边高声怒骂。
有了这么一次,我家门口再也没有闲汉踅摸。我把院墙垒得高高的,把大门、屋门打造得厚厚的。每天天不黑,我就赶快把大门关上。
油灯光里,我一年到头纺线、织布。冬天里,夜那么长,女儿、儿子熟睡之后,我会想我那短命的死鬼。死鬼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老大据说是早天了。死鬼得的什么病呢,大夫说是黑病,紧吃慢吃了十几服中药,说不行就不行了。死之前,死鬼拉着我的手,说,舍不得你,舍不得你!
我舍得你嘛,你要是不死得早,我怎么会受那么多的难呢?
想得厉害了,我就一根一根地搓棉布剂。弹好的棉花堆在案板上,我站着,扯一把棉絮在左手,右手一拉,棉絮变长。随后,我把一根高粱茎子按在棉絮上。搓上两下,棉絮成为中空的一截,一根棉布剂便算是成了。我一边搓棉布剂,一边刚强地想,我既然决心守寡了,就要守出一个好名声来,就要守出好结果来。这样,就能让两个女儿长大后嫁一个好的婆家,儿子能娶一房好的媳妇。
十几年的光阴,把我的好名声传扬出去。两个女儿嫁的都是富有人家。儿子建功娶的红云,也是袁楼有名的好姑娘。袁家的老辈人考上过举人。
忘不了,建功成亲那天,白天的热闹过后,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了。两个闺女出嫁好几年了。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自然可以不管了。儿子,千万别像儿歌唱的那样,山马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想想吃我奶水三年的儿子,现在有了媳妇,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不只空落落的,且对儿媳生出一丝嫉恨。这是什么心思呢?不知道。
儿媳妇是好媳妇,就是不怀孕,男花、女花没有。我心里急啊,天天给观音菩萨上香、祈祷。我听说泰山顶上碧霞元君祠里供奉的泰山老奶奶很是灵验,贵州、云南几千里远的人都来上香、求子。我动了好几次心思,要去求一求。但是,这里打仗那里打仗的,没有去成。
红云,也让杜医生看过,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就是不管用。对打仗儿子的担心,对儿媳生不下孩子的忧愁,压得我的后背都快弯了。在这样的情景下,儿子回家后一头扎进媳妇屋里,惹得我生了气。
拐棍打在儿子后背上,疼在我的心里。当天夜里,我没有合眼,儿媳妇也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个远亲悄悄送来凶信。
一连两天,我与儿媳都没有吃饭。大门紧闭,虽然不时有咚咚的敲门声、呼喊声,我们也不去开。
第三天,两个女儿来了,她们先与我说了几句话,后走到儿媳屋里。不一会儿,传来三个女人的哭声。
哭声里,老三夫妻二人带着建业、建设、建立三个儿子,站在我的面前。
我这个小叔子,与他哥哥一样的身板。刘家兄弟,还有他们生下的孩子,都是中等个头,但都身手不凡。因为从祖辈开始,一代一代,都是练家子——大洪拳。
老三说,嫂子,你看建功这事怎么办?
我说,明天把他殓进棺材,入土为安。
建业说,婶子,是把建功哥拉回家来,葬在祖坟呢,还是埋在别的地方?
我说,先埋在北大洼吧。等日本鬼子败了,再迁回来。
老三说,这样,让建设、建立去北大洼挖好墓穴。我与建业,去装殓建功。
我说,好,我与红云、两个闺女明天都去。
老三说,咱老刘家的事,不用麻烦别人。其他庄乡爷们,一概不让去。
我说,好。
老三的三个儿子,见我低头悲伤,一齐说,婶子,建功哥没了,我們都是您的儿子!
我抬起头来,含泪说,好,好。
我的脑子里,一个念头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冒出:可以从三个侄子当中过继一个,当我的儿子。自然,老大建业最为合适了。建业小建功三岁,与红云同岁。建业找媳妇很挑,看花了眼,还没订亲。
老三一家离开后,各家各户的乡亲,远的近的亲戚,都来慰问;我娘家人,自然也来了。我与乡亲、亲戚们简单说上几句,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第二天,我们老刘家一家人,把建功安葬在北大洼。
我对红云说,孩子,你太年轻,要往远处看。
红云听了,摇摇头,悲苦的。
劝了几次,没用,红云针扎不透。我劝得稍稍急了,她就默默地流泪。我也就不再去劝。
大门自然是常常关着的。只在建业兄弟三人往水缸里挑水时,大门才开。兄弟三人,自建功参军后,就开始为家里挑水。
红云除了一天做、吃三顿饭外,像一只小绵羊似的,静静地坐在东屋一张小桌前做鞋子。
白天里,村子里还有点狗叫、鸡鸣;夜里,那巨大的安静,像雾一样笼罩着婆媳二人。
我还是经常纺线。我累了,透过屋门缝隙,看到红云屋里灯光金黄。细听,能听到纳鞋底的细微的丝丝声。我能想象到:一盏煤油灯下,红云不时地把针尖往她的头发里一划,针尖沾上头油,就会更加锋利。随后,她把针尖对着鞋底,扎下去,针穿透鞋底,用手一拉,一根麻线穿过鞋底,发出丝丝声音。这样,一个针脚就算纳好了。
半个月后,我到红云屋里一看,已是做好三双。两双放在叠篮里,一双放在枕头边。我拿起枕边的细看,看到鞋里各有两个字——“建功”。我把叠篮里的两双与这双一比,发现大小一样。立即,伤心让我的身体缩小,缩小成一只小猫。我说,孩子,建功已经……
娘,除了床上这双,另外两双不是为建功做的。
为谁?我发问的同时,脑子里想到建业或者是建设、建立的名字。
为建功的战友。
噢。
猜疑消失后的感觉,很好,像春风温柔地抚摸我的脸颊。
又过了半个月,我到红云屋里,看到鞋子已是做好七双。新做的五双,大小、肥瘦都不一样。红云知道,战士们几乎没有胖子,脚自然就不会又肥又大。我知道,这些鞋子送到抗日大队,双双都能找到合适的脚板。
红云做鞋,那我就做帽子。建功曾把戴旧的帽子放在家里。这样,我就把家里的白粗布拿去让人染成灰色。然后,就按旧帽的样子做起来。
建功牺牲三个月的时候,我做了十几顶帽子,红云做了二十双鞋子。正愁怎么着送给队伍上呢,大门被敲响了。
我走近大门,问,谁呢?
大娘,我是长戈!
我一下子想起来,是与建功一块儿往聊城参军的后村人。
我打开门,把长戈让到堂屋里坐下。
长戈说,大娘,我是代表大队长来的。这三个月,我们让小鬼子扫荡得好苦。我们跑到山东、河北边界待了几个月,前天才悄悄返回。大娘,您怨我们队伍上吗?
我说,不怨,不怨。
长戈说,建功哥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大队长让我给家里送来十块银圆。
长戈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放在桌子上。
我说,银圆我不要。我家里还能过得去。我不只不要队伍上的钱,我与儿媳还为队伍上做了鞋子、帽子。
长戈说,这样,银圆您更得收下了。
我说,你坐着,稍等。
我走到红云屋里。我知道红云的心性,建业兄弟仨挑水来家,红云没有正眼看过一眼。对长戈,她肯定也是不想碰面的。我们两个用一个包袱,把鞋子包了起来。
我把鞋子提到堂屋。另找一个包袱,把帽子包了起来。
看着长戈威武的身躯,我想到了我的娇儿建功。建功没了,红云这个美人没有了英雄。那么,长戈怎么样呢?人家嫌弃红云吗?我怯怯地问,孩子,你成家了吗?
长戈说,大娘,我有一个儿子了。
我听了,脸上极快地黄了一下,眼睛里积聚起泪水。为了掩饰,我对长戈说,喝水,孩子,你喝水。
长戈说,大娘,我不喝了,我得走了。
说完,长戈站起来,一手一个包袱,千恩万谢,迈步欲走。
我拿起银圆布袋往长戈衣袋里塞。长戈闪身躲过,快步离去。
建功一年忌日时,我与红云往坟上哀哀地哭了一场,建业陪着。
建设、建立不再挑水,建业一人承担了。夏天用水多,建业几乎天天挑水来家。建业的热汗像水一样流。我看见了心疼,便扯过一条毛巾递過去,让建业擦汗。建业摆摆手,说挑满缸再擦。说完,双眼看着东屋,走出大门。
建业挑水的时间一长,红云就不过分躲避了。这次,建业挑了一趟水,刚刚走出院子,红云拿着一双鞋走出东屋,眼看脚尖,蚊子似的细语,娘,我给建业做了双鞋。说完,把鞋递给了我。
我双手托鞋,仔细打量,又一次夸奖,手真巧!
建业挑水满缸,接过我手里的新鞋,脸红着露齿一笑,说谢谢大娘!
我的头向东屋一扭,说,谢你嫂子!
转眼之间,建功的两年忌日,也过去了。
两年间,建业一次亲也没有相。建设、建立等得心焦,先后订亲。
红云与建业两人能自然相看、说话了。红云托人在集市上买来一个搪瓷茶缸,每天一早灌上开水。建业挑水时,红云端着里面已是温水的茶缸走近。看到建业一气喝下,红云微微一笑。
建功牺牲半年左右时,我劝过红云改嫁。红云听了,不说话,只摇头。现在想想,红云真要嫁人离去,我这个孤老婆子可就凄惶了。
日本鬼子投降两个月,建功三年忌日。县政府、县抗日大队,为建功隆重迁坟。人山人海。老三带领三个儿子,与四个战士一块儿抬棺。大女儿搀着我,二女儿扶着红云,扶棺痛哭。建功的坟头挨着爹爹、爷爷,不孤单了。建功的坟前立一石碑,上写“抗日英雄刘建功之墓”——柳体,本地书法家张稷臣写的。
回到家里,红云屋门虚掩。半天过去,东屋里没有一点动静。我有点担心,悄悄推门进去。我看到,我那可怜的儿媳把那双绣着建功名字的鞋子抱在胸前,睡着了。我轻轻地为红云盖上被子。
——《空中飞鸟》中红云的“高飞”现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