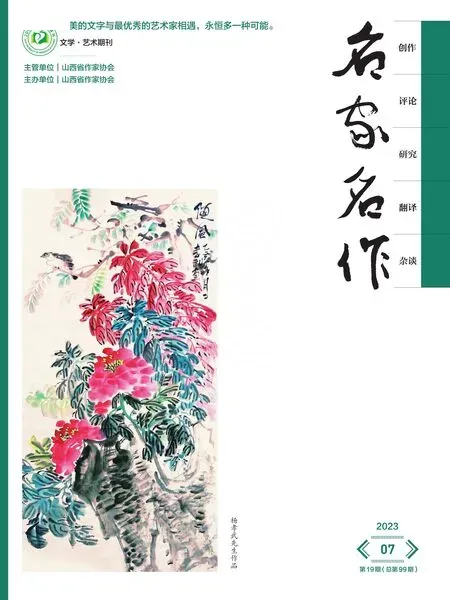浅析特殊即普遍的哲学思想
——围绕西晋一郎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
李立业
西晋一郎的哲学思想在1931 年的著作《忠孝论》中达到了学术的顶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隈元认为自西晋一郎就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以来的30 年是其哲学体系的形成期,此后的十数年则是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期①隈元忠敬:《西晋一郎哲学》,溪水社,1995,第67 页。。本文聚焦其最早发表的《伦理哲学讲话》,通过考察西晋一郎思想形成初期确立的学术方法和基本原理,试图揭示西晋一郎道德哲学的构造及其思想本质的一个侧面。
一、哲学乃修身之道
西晋一郎在《伦理哲学讲话》开篇便将哲学视作修身之道,他认为:学问是促进人自我改进、提高修养最有力的因素,而在各种学问中,专注于探究真理的哲学最符合这一目的。真正的哲学不应仅探索普遍性真理,更应借助普遍性真理去发现个体的独特天性。②西晋一郎:《伦理哲学讲话》,育英书院,1915,第2-8 页。(以下注解中都省略为《讲话》)其认为普遍性真理不能脱离个体特殊性存在,只有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的独特性,普遍性真理才能真正实现。
西晋一郎指出虽然事物在根源上是独立自全的,但事物独立存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关系,从而“自然地、必然地”产生为某一目的而存在的属性,学问亦是如此,所以应该以关联的视角看待学问。基于上述理解,西晋一郎将事物独立自足的一面称为“仁”,将为某一目的存在的一面称为“义”。仁是事物内在具备的特质,义则需要进行相对性的考察。相对性考察的方式即做学问的目的、动机,将极大地影响做学问的结果。目的和动机是左右整个修学过程的根本动力,为了获得正向的原动力,西晋一郎主张应该尊重贤哲的教诲③《讲话》,第9-12 页。。
以上是西晋一郎对于哲学或学问的基本观点,从中可以明晰其学术立场和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此外,西晋一郎基于事物皆独立自足又相互依存的观点,主张“在探究实在时,应该从绝对与相对、仁与义的辩证关系出发,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看作是各自独立的二元对立关系”④《讲话》,第13 页。。他的实体论正是基于此展开的,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贯穿其哲学思想的始终,是其哲学体系的根本出发点。
二、实在的真相
西晋一郎认为在探讨实在时应从普遍与特殊、不变与变化的相对性出发。虽然实在本身没有这些相对性,但由于我们以有限的意识无法客观全面地认识实在的真相,常常会偏执于某一方面。这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各种实体论相互对立、争论不休的原因⑤《讲话》,第15-16 页。。西晋一郎以伯格森的流动哲学为例,指出其过于偏重变化。因为在逻辑上,变化是与不变对立的,如果没有不变,变化也就无法成立。在实际经验中,我们体验到变化时必然已经承认其背后的不变,否则就无法区分出变化⑥《讲话》,第17 页。。
西晋一郎认为相即不离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普遍离不开特殊,同样特殊背后也必然蕴藏着普遍。西晋一郎通过“普遍中有特殊、特殊中有普遍”“因为普遍所以特殊,因为特殊所以普遍”等观点描述特殊与普遍相即不离的关系①《讲话》,第24 页。。
实际上这一理念适用于一切具体事物。比如以菊花为例,西晋一郎指出众多菊花中的每一朵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每朵菊花背后又蕴含着菊花之所以为菊花的普遍性。在主观层面,这种普遍性让我们具备了直接感受每朵菊花独特性的审美基础;在客观层面,它意味着一株菊花拥有繁衍出千万朵菊花的普遍力量②《讲话》,第26-28 页。。我们的精神世界亦是如此,在千变万化的精神世界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其背后存在着始终不变的某种普遍性,得益于此我们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才能成立。当特殊的精神世界生活越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普遍性,我们的人格就具有独立特质。西晋一郎认为普遍与特殊密切关联所形成的具体且唯一的境界即为实在,在其看来普遍和特殊是实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即不离、对立统一,实在的真相即是“特殊即普遍”。
三、实在与道德
西晋一郎的哲学立场是基于历史现实的道德实践,其理论探索始终与个人、社会、国家等具体现实的道德实践密切相关。
西晋一郎将实在视为纯动至变,“纯动”指流动而无间隙;“至变”指变化而无断续③《讲话》,第42 页。,这种无间断的变动意味着不断更新创造的过程。西晋一郎认为更新不止、流动不停则为纯,此等纯粹的状态也是至静的境界,纯粹是实在的存在方式。西晋一郎描述“实在的真面目在于纯粹无杂之处,在于其呈现出的无间无隙、充实彻底、无法拆分、浑然天成之处”④《讲话》,第42 页。。如果基于现实道德生活描述实在的这种纯粹境地的话,即是“一心一意、心无杂念”⑤《讲话》,第42 页。的心境。道德生活中的这种心境即为“诚”,在西晋一郎看来道德“诚”即是实在。隈元指出西晋一郎的道德哲学将实在与道德视作同一物,其一直通过道德来揭示实在纯动至变的本质⑥隈元忠敬:《西晋一郎哲学》,溪水社,1995,第15 页。,可以说其道德哲学的重点在于阐明实在只有在具体现实的道德生活中才能充分展现其真实面貌。
在个人、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层面,道德会展现出各种特殊形式,但在特殊形式的背后,存在着人类共通的普遍性。因此不能将道德中的人类共通性与国民个人的特殊性割裂开来。《论语》中有言,“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忠信笃敬是适行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性道德,西晋一郎指出普遍性道德是深藏在每个人内心的理,而此理运行能够衍生出各种道德形态⑦《讲话》,第66 页。。其以日本的楠木正成和中国的岳飞为例详细阐述了这一理念。他们作为个人只是历史洪流里一个特殊的小我,然而至今仍被视为道德典范就是因为隐藏在他们特殊生涯背后的普遍性道德 “忠诚”一直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忠诚即实在,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不受时空限制,其能够引导农夫成为良善之人,亦能鞭策教育者成为有良心之人。”⑧《讲话》,第66 页。忠诚即是具体的普遍性实在,其遍布在万物之中并推动事物朝着正善的方向发展,其在楠木正成和岳飞的人生经历中虽然表现形式各具特殊性,但内在的忠诚却完全一致。西晋一郎将此称为道德的同化原理并解释道:“因为具体普遍性是无法离开个体特殊性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它的现实显现始终采取特殊与特殊交相感化的形式。”⑨《讲话》,第67 页。普遍与特殊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相即不离,因此在提倡社会普遍性道德的同时应充分尊重个体的特殊性,而在彰显个体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现社会的普遍性道德。
四、实现道德生活
实在的本质是普遍一致的,但其作用必然通过特殊的形式显现,即实在只有在现实的特殊形式中才能显现出其普遍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特殊相立身于世、又该如何在保有个体特殊性的同时实现道德生活呢?对此,西晋一郎也基于实在的“仁”和“义”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西晋一郎认为实在包含纯动、至静两方面,动静交替则意味着生长,因此实在即是生命。生命包含了动与静,离不开新生与完结。实在的本质即为动而万物生起与静而完结自足⑩《讲话》,第78 页。实在的本质是纯动即纯静的观点,可以追溯至周敦颐(1017—1073)的动静学说。其在《太极图说》中表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并且在《通书》的第十六章“动静”中写道:“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可以看出西晋一郎在以动和静论述实在的本质时明显吸收了周敦颐的动静学说。。因此,其将实在动与新生的一面称为“仁”;将静与完结的一面称为“义”。西晋一郎在探讨实在的“仁”时又引入了“爱”的概念,主张实在即是生命,而生命便是“仁”或“爱”。其借用了程颢的名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来说明实在的“仁”即爱,是延续不断的生命流通,爱体现了实在的生生不息①《讲话》,第82-83 页。。
基于实在即生命、爱的论述,西晋一郎以施恩和报恩的关系来阐述道德生活的本质。“恩”即恩惠和滋养,代表草木万物萌生②《讲话》,第84 页。,意味着生生不息的真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将他人为我着想、为我付出的行为视为恩惠,而没有意识到即使对方并非有意为我,但我也得益于此立足社会,这一切皆是对我有恩。例如,“父母尽责抚养子女,子女尽心敬爱父母”③《讲话》,第88 页。,亲子关系中的施恩和报恩是生生不息的实在之理的具体表现。如果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来看,人们似乎都是为了自己工作,但事实上所有人的工作最终都成了互相成就。毕竟人类彼此依赖才能共存,“每个人努力工作既是依靠他人之助,同时也在回报他人”④《讲话》,第94 页。,对我们而言是他人的施恩之举,但对其本人而言却又是直接的报恩行为,因而施恩与报恩发生在每个人各自的人生道路中。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并实践施恩和报恩的意义,才能认识到我们生命本源中存在着的普遍性实在,实现道德生活⑤《讲话》,第97 页。。
随后,西晋一郎又从实在的“义”的一面探讨了如何实现道徳生活。实在的特殊相种类繁多,而基于人们特殊关系形成的特殊性更是广泛普遍。例如,“在家庭中,男子作为丈夫、父亲、子女、兄弟,每个身份都有着不能混淆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常常听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的描述,皆是为了明确各自身份的特殊性”⑥《讲话》,第125 页。。生活在集体中的人们应切实践行自身的责任,维护好自身的形象。如此一来,人们各自角色的特征才会日益明确,进而形成鲜明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人生的普遍性意义也能得到充分展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职责是个人立足于世的关键,因此更应该尽力保持其特殊性⑦《讲话》,第126 页。。在社会和国家中,人都是彼此依赖、共生共存的,而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存续需要每个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实现。因此“一方面应该像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一般,将自己的职责视作公共工具并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回报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展示出与普罗大众绝对不同的独立面貌”⑧绳田二郎:《西晋一郎的一生与哲学》,理想社,1953,第60 页。。职责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和国家层面显现出来的特殊形式,同时也是我们参与到实在普遍性的途径。通过履行职责,我们可以更好地对公共的社会生活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职责意识越强烈,生活的内在本质将越显现,我们也将进一步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为了论述方便,西晋一郎从实在的“仁”和“义”两个方面探讨了实现道德生活的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实在本身是一贯统一的,实在概念下的“仁”和“义”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仁”蕴藏着“义”,而“义”是实现“仁”的基准,因此在道德生活中并不能将“仁”和“义”二者割裂开来。在社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特殊职责中毫无保留地自我奉献,那么最终每个个体行为的实现同时也是普遍性道德生活的实现。
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是哲学实体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区别于对立看待特殊与普遍关系的传统哲学观点,西晋一郎在《伦理哲学讲话》中提出“特殊即普遍”的观点。这一“即”的观点并不是将特殊与普遍看作是对立的抽象概念然后寻求二者的相即性,而是将二者作为实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普遍离不开特殊,实在的普遍性只有借助个体的特殊性发展才能显现;同时特殊中蕴藏着普遍,个体只有通过实现实在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彰显出自己的特殊性。正如绳田评价的一样,在该书中西晋一郎首次形成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特殊即普遍”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概念,也成为后来西晋一郎道德哲学的根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