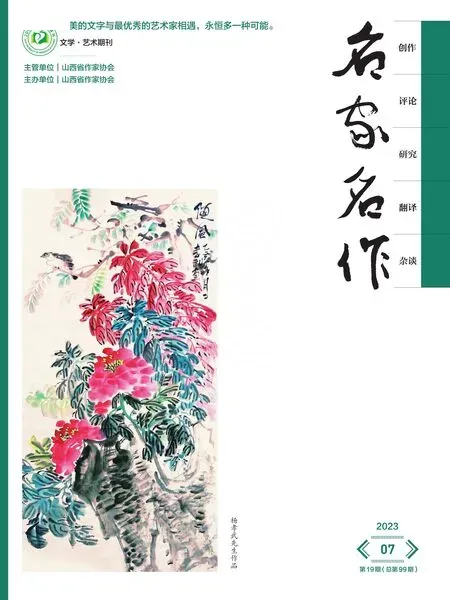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道形象书写研究
郑 翌
《玄怪录》《续玄怪录》系唐牛僧孺、李复言所撰写的志怪笔记小说,文中涉及大量精怪轶事与民间传说,历来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里,不少故事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僧道形象。唐代佛道盛兴,思想兼容并包,社会普遍“尚奇”的审美进一步影响到个体文人的创作思维,僧道与其相关的神异事件都成为笔记小说着墨的对象。这两类人群不仅活跃于特定的场所,更与文人墨客、王孙将相交游。同时,笔记小说中的僧、道不仅作为宗教形象出现,更是与仙人、山精、灵魅等传闻轶事相融合,因而成为目睹怪异、构造传奇之人。
本文拟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1]为基础,考察《玄怪录》《续玄怪录》中不同类型的僧人、道士,以期从中梳理出些许书写特色,进一步比对作者在书写僧、道形象时的异同点,发掘此二篇著作的艺术价值。
一、《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道形象概述
纵观《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其中有法号的僧人两位(妙寂、玄照),有俗家名号的罗汉化身一位(薛存诚),胡僧两位,其余均以“僧”字代替;有名字的道士八位,其余均以“仙师”“道人”等字眼代替。虽然僧人、道士形象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在叙事中,多数僧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简为梳理。
在《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人形象主要有“侠义复仇僧、识宝传话僧、作恶斗法僧、违戒被贬僧、诵经除灾僧”五种。
《尼妙寂》主角叶氏女从属侠义复仇僧,本文讲述了一位比丘尼的生平故事,叶氏女的父亲与丈夫在湖中遇上强盗,上天悯其遭遇,令二人托梦给叶氏女,用隐语告知其凶手姓名,叶氏女扮成僧尼找到线索,复仇成功。
《党氏女》中的僧人玄照、《崔书生》中的胡僧、《薛中丞》里的众僧为识宝传话僧,此类故事中的僧人多数只作为中间传话的媒介,或是向主角告知某件宝物十分珍贵。《党氏女》中富商王兰死于好友蔺如宾之手,转世为蔺家幼子,耗尽蔺家不义之财夭折,再次转生为党氏女,玄照作为传话媒介,替党氏女要来蔺家财产,彻底化解二人恩怨。《崔书生》中仙女玉卮娘子留下白玉盒,凡人崔生不识宝物,也是胡僧出面挑明,这类“胡僧识宝”的主题在五代笔记小说中十分常见。而《薛中丞存诚》则是借所谓“天界僧众”之口点出薛中丞乃是罗汉被贬下凡,客观上也起到了传话媒介的作用。
此外,经常出现的另一种胡僧形象为斗法胡僧,《叶天师》便是典型的一篇作品。本篇作品讲述了胡僧作恶欲吸干炎海、降获白龙,白龙向叶天师求助,叶天师打败胡僧救下白龙的故事。这类“佛道斗法”的故事里,胡僧、道士、龙等形象经常交叠出现,往往以“胡僧率先发难—龙向道士求救—道士救下龙”为发展脉络,本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在此不多加赘述。
《吴全素》中众多被羁押的僧人,《薛中丞存诚》中被贬的薛存诚,此二者都为违戒被贬僧。而《吴全素》中可以通过念咒驱赶阴差的另一种僧人,《钱方义》中主角撞到厕神郭登后请来的僧人,都为诵经除灾僧。除去以主角为面目现身的薛存诚,其他僧人大多数时候只起到点缀作用,虽然数量众多,且经常以“僧众”面目示人,但多数只作为线索,不作为正面的书写和神化对象。
而道士形象则更为复杂,通常有“斩妖除祸”“展示幻术”“引人飞升”“引渡仙境”四种道士形象。
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道士常作为斩妖除祸的角色存在,如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就出现了不少驱鬼、救灾的游方道士,这类道士的形象通常与民间术士类似,拥有治病救灾、驱邪救人的能力。在《玄怪录》《续玄怪录》里也有类似的道士形象,《萧志忠》里出现了一位黄冠道人严四,时逢刺史萧志忠将在腊日打猎,山中百兽十分畏惧,群兽便去找严四排忧解难,严四告诉百兽要同时找到滕六降雪、巽二刮风,这样萧志忠就会停下狩猎,百兽的祸患就能迎刃而解。而在《叶天师》中,也同样出现了为救白龙与胡僧斗法的叶天师;在《王煌》中,任玄言发觉王煌身边有耐重鬼存在,劝其离开耐重鬼,从客观上来说,这类都属于斩妖驱祸的道人。
同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方士、道士施展幻术的传闻,《许元长》中同样记载了道士令主角再见妻子的故事,而道士的神异幻术并不仅限于此;《开元明皇幸广陵》中叶仙师架筑虹桥,令唐明皇一路行到广陵;《刁俊朝》中猿猱化为道人可以在瘿中歌唱吟咏,甚至铺排宴饮等。这些都展现了道士们精通幻术戏法的一面,为“展示幻术”的道士形象。
而“引人飞升”和“引渡仙境”的道士形象往往相似,不过前者侧重于对人的磨炼,后者侧重于展现道家仙境的风貌。如《杜子春》中的仙师以炼丹之术引杜子春飞仙;《凉国武公李愬》中仙道传话引李愬飞升;而《裴谌》《张老》《柳归舜》《刘法师》中通过道士展现了各色仙境。道士或引生人入仙,或为误入世外之境的人们指点迷津,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中,大多数道士都作为主角出现,通常贯穿全文,展现了通天的神力,如云帔般呈现出某种统领、覆盖全文的艺术效果,且多数都拥有姓氏,或至少拥有代称。纵观此二文本,道士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只有《吴全素》中的道人以被贬、受罚的形象出现。
二、僧道形象书写特色
首先,《玄怪录》《续玄怪录》中的僧道形象在书写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僧人与道士在书写时存在一些相似点,如同样能够展现幻境、叙述常人见闻之外的神异故事,包括拥有慧眼、识得精怪宝物等,也同样可以驱邪除灾,为主角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等。作者书写这两种人物形象的目的几乎一致,都是为了增添故事的曲折离奇之处。
而僧道形象的不同之处则更为多元,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有意设置区分,使人物本身因立场不同而出现矛盾,此矛盾集中在“相斗”题材之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叶天师》中的斗法情节。龙因胡僧之祸,向道士或者涉道之人求救,这是唐代笔记小说中常见的主题[2],如同为唐代笔记小说的《孙思邈救龙》一书中也曾提到老龙将被胡僧取脑入药,因而向孙思邈求救一事,在这类故事里,“龙”经常扮演一种被拯救的角色。而在过往的研究成果里,学者们通常将“胡僧斗法—落败于道”视为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也有人认为这是唐代“尊道抑佛”的一种表现[3]。
除此之外,《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在书写时还呈现出与其他唐代笔记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矛盾的景象,在《叶天师》中出现了一处不容小觑的细节:即使胡僧作恶,白龙依旧称赞其“虔心,有大法力”,即肯定了胡僧的修行意义,而胡僧斗法失败也未伤及性命。在这则故事里,胡僧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作为点缀出现,却也与作为正面角色的天师一样,经由正统虔心来修行。由此可见,作者在笔下并未否定胡僧的修行之意,反是运用了不偏不倚的笔法进行记录,该篇中的僧道形象为立场不同的修行者代表,这类笔法更为冷静客观,通过细节彰显了胡僧与天师的品性,展现出了复杂的人物性格。
其次,在《玄怪录》与《续玄怪录》中,道士展现了种种神异的法术,如唤回亡魂、展示仙乐、架设虹桥、斩妖除魔等,可以称得上是上天入地。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道士们虽然拥有极大的法力,却没有被神化的色彩,这类道士形象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人性”,而非拥有十全十美的神话人格,如《刁俊朝》里化身道士的猿猱与恶蛟为伍,后被追杀,此处作者虽未明说,但想来猿猱也应是作恶众多的妖孽;《裴谌》中裴谌道士展现道术是为了戏耍他人,缺少神格化的庄严肃穆;在《王煌》中,因为王煌的私心作祟,道士任玄言也未能从鬼的手里救下王煌,这些作恶、救人失败的情节都与大量被神化的道教人物出现割裂,展现出了某种错位。大部分道士虽然拥有通天彻地的法力,同样悲悯、宽厚,却也有一部分道士同时在性格、行为等方面展现出了与常人无异的人性化特点,同常人一样有善恶两面,在这一类形象身上,折射出了人性和神性交织的复杂特色。
最后,佛、道的人物形象在书写时还与社会现实交融在了一起,如《薛中丞存诚》里众佛童迎被贬僧返仙,御史台官员对佛童大声相叱。《尼妙寂》在《谢小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结局以官员出手惩治恶贼、妙寂大仇得报出家还愿作终,作者有意将原有的侠义复仇结局转向报官得救,展现出了凌驾于“虚幻”上的“现实”,纵然神鬼托梦,但最后的审判依旧是由官员来完成,这或许都是政治大于个体人物神异的一种写照。[4]而既然写到现实,作者也会用神鬼故事来影射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如在《萧志忠》里,百兽为了躲避游猎之灾,祈求道士出主意,道士让百兽为司风、司雪的神明带去美女、美酒,这就好似对官场阿谀奉承现象的一种辛辣讽刺。人性和妖性在作者的笔下同样复杂多变,《刁俊朝》中猿猱兴风作恶,与恶蛟交好,但也会受恩回报,为刁妻求来治瘿病的良药,看上去又显得分外有礼。如此种种,也显示出作者笔下相应人物呈现出一种复杂性。
三、僧道形象书写的原因探析
倘若要探求作者为何会如此书写笔下的僧道角色,则需要从作者本人、宗教影响与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原因出发。
牛僧孺、李复言二人都有相当复杂的思想背景,这些都对《玄怪录》《续玄怪录》里的僧道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牛僧孺据传“不喜释老,唯宗儒教”,此类特征早有讨论,丁鼎先生的《牛僧孺论》一文中结合牛僧孺的生平经历,肯定了其对思想、政治的功绩,认为牛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同时带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5],参考此文可以得知,牛僧孺与大量唐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参与现实政治、追求精神自由、实现功业抱负为目的。文人笔下流露出的文字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创作心态,即使是娱乐性质的“温卷”、随笔之作,也能窥见牛僧孺的客观之处,牛僧孺在记录时保有一种不褒不贬、铺排浪漫的笔触,即使《叶天师》中胡僧作恶,白龙也依旧赞赏其“虔心,有大法力”,肯定了其修行的功德。
而与牛僧孺的创作态度不同,李复言的笔下更尖锐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众所周知,宦官祸起和牛李党争先后对唐王朝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现实中官场的黑暗也被反映在了文人的笔记小说作品中。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李复言的生平与身份还尚无确切定论,但从现有材料里可以得知,作者李复言身世坎坷,作《续玄怪录》讽谏意味更浓,寄托了自己对黑暗官场的不满和失望[6],因而不管是何种思想,或许都并非作者书写的重点,写作此类作品只是一抒己怀的一种手段、一种假借。李复言为作品起名为《续玄怪录》,或许乃是渴慕《玄怪录》的煊赫名声,故以《玄怪录》续书为自我标榜。李复言在创作时不但参考了牛僧孺的写作手法,也借鉴了不少前人的笔记作品,他记述了许多涉及精怪妖魅的故事,但记录手段里已不复《玄怪录》那般浪漫,而是充满了主观见解和劝诫色彩,也出现了很多与常规不同的僧道形象。从这一点看,作者都是在有意构思曲折离奇的故事,借精怪和非人之物之口讽刺现实,而非简单地使用脸谱化、模式化的方式书写僧道。
而如果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宗教在进入民间、流传普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些自己的再创造,使宗教与日常生活的分界线变得愈发模糊起来,某些典籍中的清规戒律也会以某种面貌投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正是此原因,在原有的得道人物形象之外,人们也赋予了这类人物新的内涵,让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富有人性。
同时,黑暗的晚唐官场现状又让文人们期待避世与游仙,从罗汉被贬后又重返天界、大仇得报后还愿为僧等故事可以看出,人们将避世遁俗作为一种身份转换的方式,一方面希望生活安宁,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更多机缘。这两种色彩不同的行为在文人笔下得到了艺术加工,在共同的愿望作用下,显示出了“斗争—趋同”的复杂态势,从中还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关心与强烈不满。
四、结语
牛僧孺、李复言所著《玄怪录》与《续玄怪录》,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僧道形象,其中僧人数量众多,但只作为点缀出现,而道士多为主角或主角的引路者。此二类角色虽然存在斗争,但僧道双方的矛盾逐渐减弱,且存在大量的相同之处。在僧道角色,尤其是道人角色身上充满人性与神性交织的特色,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现实状况,如此特殊的书写特色自然离不开牛僧孺、李复言两位作者的写作观念与时代背景,两位作者借僧道形象表达抱负,展现了对浪漫故事的追求与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