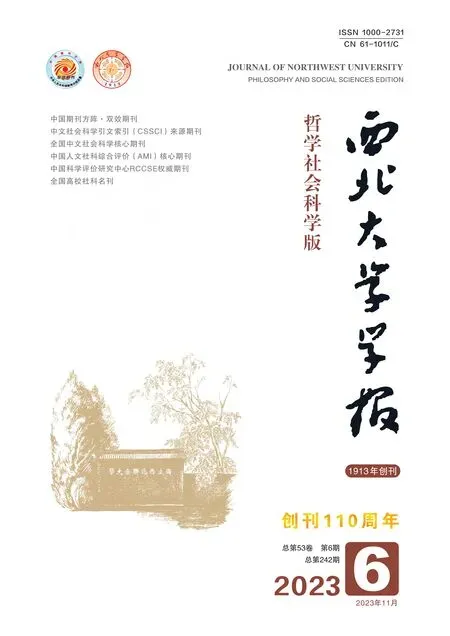石鲁《学画录》的创作美学研究
屈 健,张俊杰
(1.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陕西 西安 710065;2.西北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缘起:石鲁《学画录》的写作动因
当人们回忆起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石鲁时, 往往会将其与“新奇”“先锋”“反叛”等语汇相联系。 1961年10月, 他组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 受到业界关注, 旋即受邀在南京、 上海、 杭州、 广州等地巡回展览, 引发强烈的反响, 被誉为“长安画派”“长安新画”。 所谓“新画”是指其作品呈现出的新题材、 新构图、 新表达, 反映出他们对于新时代的热情讴歌以及对中国画进行时代创新的深切渴望。 不过, 由于石鲁等人的大胆求新, 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评, 称其作品是“野”“怪”“乱”“黑”[1], 石鲁反驳称: “人骂我野我更野, 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 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 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 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新意, 我为生活传精神。”“古法”与“新意”乃是当时论辩的中心, 时人认为石鲁等人的艺术创作过于求新, 似乎缺少了对绘画传统经典的浸润与习得。 石鲁是否真如其说, 只是一个艺术传统的反叛者,缺少对于古典绘画传统因应与理解, 他的《学画录》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
1963年,石鲁因病在西安常宁宫疗养,其间通过阅读古代画论,并结合自身的艺术实践,有感而发,撰写了一部未完成的画论手稿——《学画录》。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该文稿被长期搁置,十几年后才得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文艺研究》[2],后又经令狐彪整理以著作的形式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3]。亲历编撰的孙新元指出:“《学画录》是石鲁画论中有代表性的系统性很强的著述,是石鲁的重要艺术遗产,是他毕生艺术实践的总结和精华。”[4]石鲁说“(他)曾有心写一个比较系统的笔记,从理论上探索一下中国画在对待生活、造型、笔墨、立意、构图、设色、题款等方面的艺术规律”[2],但终因时间和精力的缘由,仅仅完成了“生活”“笔墨”“造型”三章的提纲。通阅其书稿,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天才艺术家对于传统绘画思想精华的创造性汲取以及作者在继承中求创新的深切渴望。虽然《学画录》有未完的遗憾,但就成书的文稿而言已然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本文拟就其中所涉及的创作美学展开深入解读(1)关于石鲁《学画录》创作美学的讨论,详见令狐彪:《“艺术的道路就在于探索”——试论石鲁国画创新道路》,《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刘继潮:《“以形写神”试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刘星:《传统精神的守护与超越——石鲁“以神造型”绘画思想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既有研究中令狐彪偏于石鲁艺术道路的整体评价,刘继潮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立场剖析石鲁形神观的理论价值,刘星侧重从石鲁的创作实践解读石鲁“以神造形”的艺术思想。
如所周知,创作美学主要涉及创作心理和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两个维度,从美学范畴的角度审视:前者以“心”“物”关系为主,后者则以“形”“神”关系为据。在中国古典美学语境中,有关“心”“物”“形”“神”的讨论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形成了一套以“意象”“意境”为特色的创作美学传统。宗白华先生指出,“中国画法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而在创造意象。”[5]134-135其言甚确。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倾轧使得士人归隐山林,藉由艺术寻求内在生命的安顿与解脱,形成了以“玄远”“超脱”为表征的生命美学传统,宗先生所言“抽象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即指此意。所谓“意境”和“意象”虽是缘发于外在之“物”的镜像,但所要表达的却是艺术家主体情感之内在“心意”。因此,“心”“物”“形”“神”成为生命美学的中心范畴,其中的“心—物”关系强调主体对外物的把握[6]105-106;“形—神”关系也不是单纯地对“物”的模仿与复刻,而是主体情感投射于物的自我纾解。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以形写神”“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等为特色的绘画美学传统,此类成就在既有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美学史的相关论著已有详论(2)参见宗白华、徐复观、李泽厚、叶朗、朱良志等人相关论著。。石鲁《学画录》除却对上述心物、形神美学传统予以承继外,更受到石涛《画语录》直接影响。他本名冯亚珩,青年时代因钦慕“石涛”“鲁迅”,故改名“石鲁”以明心志。在《学画录》中,石鲁大篇幅地引用石涛《画语录》的相关内容,并对后者的“一画论”予以高度评价,称其“非玄妙禅理之谈,乃为艺术之哲理”,并强调“余观其理,既以客观为基础,又以主观为能动。艺术之法则虽非现实法则,然亦源于受,基于万物一般性。夫人之识,不仅限于个别,乃至一般,故能识乾坤之规律也”[3]51。显然,石涛“一画论”中的心物关系、形神关系构成了石鲁《学画录》探究创作美学的理论根基。
二、反向格义与以神造形:《学画录》的取径与立意
“以神造形”是石鲁《学画录》关于创作美学的核心主张,粗看此语,似乎只是对顾恺之“以形写神”命题所作的反向推理,其实该命题的成立既是石鲁潜心学习传统的心得,也是他通过“主观”“客观”“一般”“个别”“抽象”“虚构”等现代概念和语汇对传统的“心”“物”“形”“神”等美学范畴进行的“反向格义”(3)“格义”本义是指南北朝时期用中土的经典概念解释外来的佛教教义,对应着英语中的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则是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简要而言,“格义”是以中释西,“反向格义”是以西释中。参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命题的立论逻辑包含三个层级:
首先,石鲁重塑了绘画艺术的造型属性,并重构了“心”“物”“形”“神”在艺术创作中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包含绘画在内的国学传统整体式微,西画的观念、技法对传统绘画产生了极大冲击,在西画的透视、光影、结构等美学理念的映照下,传统绘画被纳入造型艺术的类别。然而从文化属性来讲,中西画法在造型语言上各有其据,如果仅以透视、素描、色彩、光影等技术语言作为标准,用以剖析和审视传统国画的造型特质,显然会陷入方枘圆凿的窘境。石鲁在《学画录》中对此予以正面回应,他指出:“造型者,创造形象之型式也,故美术曰‘造型艺术’。”[3]28该定义突出了“型”与“形”在逻辑序列上的区别,既肯定美术作品的形式特征,又强调“造型”的关键在“造”。在他看来,“造”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因袭陈样”,而是要“亲目所睹”“亲手所悉”“独出匠心而创典型”[3]29。他将绘画的创作过程划分为“形”“神”“型”三个步骤:所谓“形”,是指艺术所表达的客观世界,即古代画论中的“物”;而“神”则指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即古代画论中的“心”;至于“型”则指业已完成的艺术作品,即他所说的“典型”。他认为艺术创作“当取于客观,形成于主观,归复于客观,故造型之过程乃为客观——主观——客观之式也”[3]29。显然,石鲁用现代语言重构了传统的“形神”关系:“形”指艺术的表达对象,在存在方式上属于“客观世界”;“神”指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属于“主观世界”;“型”是艺术作品的完成样态,表现为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统摄。因此,“造型”是在主体意识对外物的加工、想象之后,外化为实存的绘画作品。概而言之,他将传统的“心”“物”及“形”“神”的内在逻辑,重新解释为:“物”(客观实存的现实世界)、“心”(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物”(客观实存的艺术作品)三个环节,三者分别对应“形”“神”“型”。

表1 石鲁对美术创作过程心理图式的分析
此外,围绕作品的存在形式和感知方式,石鲁提出美术作品的审美特征包含“可视性”与“可想性”两个层级,其中:“可视性”指视觉形象构成了绘画作品被感知的“物”的基础,这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层”;而“可想性”指艺术作品所传达的内在的精神符号,属于创作主体及接受主体的“意识层”。他强调高质量的美术作品必然是“可视”与“可想”的融合,即“可视以通真,可想以通情”[3]28,绘画作品的审美意义就在于通过可视的艺术形象架构起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共鸣。石鲁强调,“造型”并不只是创造形式,更是树立典型的意思,是“个别寓一般,一般涵个别”的关系,他说“有个别无一般,则神不远,有一般无个别则神不显”[3]31。因此,“造型”的本质就是创造“神”“形”统一的艺术典型。
其次,石鲁以“心”“物”关系为核心,还原了绘画创作过程的心理图式,并通过“意”“理”“法”“趣”分疏“形”“神”在艺术创作中的意识结构。如所周知,传统的心物关系主要被运用在哲学认识论之中。如庄子提出的“心斋坐忘”“离形去知”及“游心于物之初”等命题,即是将“心”作为主体认知世界的通道,所谓“心斋坐忘”“离形去知”及“游物”皆是指摒弃外界的干扰,发挥“心”的认知作用,实现对宇宙及生命的体悟,由此进入“澄明”的境界。陆机《文赋》“罄澄心以凝思”、宗炳《画山水序》“澄怀味象”皆循此思路,将“心”视为主体认知世界的关键。《学画录》以“知觉”为理论中介对传统的“心”“物”关系进行了创造性地改造。石鲁提出:“造型是思维之活动过程,先知而后觉,觉而后造也。”[3]29显然,他所说知觉不是生物学中生物体对外界的生理反映,而是指艺术创作者的对于所要表现对象的抽象化的意识建构,他说:
“知”以悉物以明理,“觉”因物而寄意,“造”为知觉而生法,有法而无法则生趣,故言造型当以意、理、法、趣思之。此为艺道,不外主客观融合之理,识物与识我不可偏一。[3]29
此段引文实乃理解石鲁创作美学的关键,他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意识活动分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心”识“物”,由“物”寄“意”,即引文所谓“知以悉物以明理,觉因物而寄意”。石鲁细分了“知”与“觉”的区别与联系。就区别而言:“知”有认知、熟悉、知晓的意思,其意识的流向是由“人”及“物”;而“觉”则是认识主体对于认识事物的反思与消化,类似生物界对于食物的反刍,其意识趋向是由“物”及“人”。“知”在认知逻辑上,强调由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熟悉过程,所对应的正是客观事物的形式特征,因此“悉物以明理”就是要求艺术家应熟悉和掌握认知对象的形式特征,到达“庖丁解牛”“技近于道”的艺术自觉。就联系而言,“知觉”是主体意识“识物”与“识己”之后形成的意识超越。石鲁所说的“知觉”近似于现代艺术心理学中的“艺术知觉”或“审美统觉”(4)“艺术知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它总是在探索着和触摸着,一旦发现了适合它的事物之后,它就捕捉它,扫描它们的表面,寻找它们的边界,探究它们的质地,反省它们的意义。”“审美统觉”源于“统觉”(apperception),“审美统觉是审美知觉的综合和统摄,是对客体感知的理解的心理活动”。(参见鲁枢元、童庆炳、程克夷、张晧《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68-69页)。石鲁将“神思”视为知觉统摄的意识中心,他说:“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而为一者则全矣。”[3]31在石鲁看来,“神思”构成了知觉统摄、意识建构的桥梁,使得美感在“物”“我”之间得以双向流动,促成了“心物”与“形神”的内在链接。
第二阶段是将“知觉”视为整体,在艺术技法醇熟的基础上,通过发挥艺术家的思维创造力,重新审视和加工前一阶段的心物统摄所形成的知觉记忆,由此实现“造为知觉而生法”。他说:“夫物熟而生意,意熟而生艺,艺熟而生术,术熟而生美,美则动人感情之结晶也。”[3]29石鲁强调“技术”只是艺术创作的基础,通过“知觉”熟悉事物,而产生“意”(此处的“意”不是指审美意识的建构,而是与前文所说的“明理”相同,即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机理的熟悉),通过对事物内在机理的了解,实现技能向技艺的转变,技艺的进一步发展,上升到技术(这里的技术具有了艺术的韵味)。不过,石鲁明确反对缺乏思想指引、唯技术至上的形式论。他认为艺术创作的本质是“造象”,而不是“象物”,他说“然则写生不为之造型象物乎?余谓:按实肖像易,凭虚构造难,能构象造型,象乃生不穷。写生拘于实,可谓具象;虚构近于形,可谓抽象。是为典型当由实而虚,由虚而实,则近于神矣”[3]30。这里,石鲁显然承袭了传统的意象论,并以此驳斥西画的镜像论或模仿论。西画的哲学基础是“理念”与“摹本”,因此其内在的美学诉求是“典型”,即寻求客观世界(物自体)的理性、真理和规律,而国画的哲学基础是“意象”与“表现”,因此在创作上的诉求是“物我同一”,所追求的是气韵与趣味[7]。因此,传统的意象论注重“意识”与“物象”的双向交流,即《文心雕论》所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及“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8]248、413。石鲁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写生只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属于技术训练的范畴,也就是前文所谓“悉物明理”,此类写生只能描述事物的形象,其特点是单一的、固化的;而造象则是在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凭借主体在意识上进行想象与虚构,其特点是生生不息、象生不穷。他指出:“艺术之精醇,岂是无心闲手者所能梦得耶?”[3]30在他看来,艺术的纯熟包含外在的技法训练和内在的知觉训练,外在的技术是“手”,内在的知觉是“心”,“心手操劳,千锤百炼,由粗到精,由低到高”才能谓之“熟”[3]29-30。
第三阶段则是突破既有法则的束缚,产生艺趣,即引文所云“有法而无法则生趣”。石鲁强调,技艺的纯熟以及感觉经验的积累仍然只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他指出,“思维之序虽非定式,然亦不外观察、分析、想象、综合也”[3]30。但“观察”与“分析”仍属于感性经验的积累,要实现感性经验的升华必须发挥主观意识中“想象”与“综合”的能动作用,进行“心”→“物”与“物”→“心”的双向流动,才能打破旧有的陈规,进入艺术自觉的状态。他说“若行观察,务求精深博览,故当物进我出;若云想象,又当物出我进”[3]30。这里的“想象”与“综合”已不再是艺术家主观的写生与慕写,而是主体心智对客观事物的整体还原与抽象总结。
最后,石鲁提出“艺道”的命题用以概括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他认为艺术作品需秉持“形神兼备”“形神一体”的原则,因此必须“以神造形”。他说:“余谓形神兼备者,非半斤八两之分也,亦非形备而神兼,更非神离形而自在”[3]30。石鲁既反对将形神视为机械化的比例,也反对将“神”视为脱离外在形式的抽象理念,而是强调形神兼备、形神一体。他说:“造型当以神造形,以神为魂,以形为貌,何以以神造形?曰以魂附体,曰劈尸取神,曰解体再生。如是之谓,神而形也,形而神也,形神一体也。”[3]30这里的语言虽有些晦涩,但其主旨明确、思路清晰,其大意为:一是要发挥艺术家的意识构造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二是要求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必须高度统一;三是追求艺术技艺与主体意识的高度融合。在石鲁看来,形式只是艺术作品的外衣,故称之为“以形为貌”,而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才是作品的灵魂,即“以神为魂”。他说:“以神造形,则可变形;以形求神,则形神全微。”[3]30在他看来,仅仅通过绘画的技术来求得作品的内在精神,则作品的形式和韵味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作为支撑,则可以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彰显内在的精神力量。不过,石鲁所谓的“以神造形”,并不是将“形”“神”割裂,或者认为“神”重“形”轻,而是强调要在过硬技术的基础上,强化创作者主体意识的主导作用,即前文所言要在对于外在世界的知觉统摄中,实现由“我”及“物”、由“物”及“我”的双向互动,要将技术训练、知觉统摄的所有要素凝结在一起,化为艺术表现的手段,再经过创作者的凝神聚思,最后以泉涌式的爆发,将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经过笔、墨、纸的交融,外化为形神统一的艺术作品。他说:“我之观物,先神而后形,由形而复神。凡物我之感应,莫先乎神交,物神亦无睹神。神先入为主,我则沿神而穷形,以动而制静。形熟而可默想,故当以写生而默写为记载。然默想者非谓背临,乃潜移默化也。由此而想象翩翩,凝神聚思,一临纸则入生出神,形不克神,神不离形,出乎一意,统乎一笔。”[3]31
由此,石鲁通过“主客统一”“知觉统摄”“观察想象”“抽象虚构”“物我同一”“潜移默化”“心手相融”“凝神聚思”等中西语汇实现了对“心”“物”“形”“神”等传统美学命题的有机贯通,形成了“以神造形”的创新表达。
三、意理法趣与形神兼备:石鲁《学画录》的实践品格
如所周知,创作美学涉及抽象的理论推衍与实操的艺术技法,因此古典画论中的“形”“神”“心”“物”不仅只是形上的美学范畴,更是与形下的“笔墨”“章法”“色彩”“结构”等艺术实践相统一的技术语言。在《学画录》中,石鲁除却以“意”“理”“法”“趣”分疏“形”“神”“心”“物”的美学内涵,还以此为基础融汇了“笔”“墨”“形”“意”等技术原则,对国画传统“形神兼备”的美学诉求做出生动诠释,他指出:
造型之法虽微,概其要者,为取神、造形、变色、和韵也,亦求意、理、法、趣具之。其练习方式亦有动写、静写、临写、默写。然归根结底,当物化为我、我化为笔墨,然后则活矣。[3]42-43
此段引文为《学画录》创作美学的纲领,其中:“意”“理”“法”“趣”亦可称为“理法”与“意趣”,是艺术创作的主旨,构成了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中介;“取神”及“动写”“静写”“临写”“默写”,即“物化为我”,也可称之为“观物”与“取象”,对应前文所谓“悉物明理”“因物寄意”的知觉统摄环节;而“造形”“变色”“和韵”即“我化为笔墨,然后则活矣”,特点是“笔墨”与“形意”的融贯。
第一,理法与意趣。“意”“理”“法”“趣”是石鲁反复强调的创作美学原则。在他看来,“理”“法”分别对应“事物之理”及“前人之法”,二者均属于技术范畴。他说:“若画漫无法度,何以成艺?”[3]32虽然石鲁认为“法度”是成艺的前提,但是他强调要辩证地看待“理法”,“然法之法,乃在得宜,若简不寓繁、静不寓动,则单薄”,因此应“故先无法求有法,再化为无法,形虽简而趣无穷也”[3]32-33。对于“理法”不能以因袭为目的,而是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古今中外艺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实现技艺的融合与超越。他说:“余故谓形象当新,法则亦与古合外通,然必以当代形象为本。由本生理,由理生法,可谓活法、我法、今法,乃可开源导流,非坐吃山空也。”[3]34如何实现“今法”及“化法”,他认为必须以“意趣”为主导。他所说的“意趣”源自石涛的“一画论”,石鲁认为“一画论”绝不是野孤禅,而是在“艺术方法论中具有合乎主、客辩证规律之合理内核”[3]54,即不是固步自封与因循守旧,而是注重原则、善于权变。石鲁所谓的“意趣”包含“意象”与“韵趣”,强调“意在笔先,因意而成象,以象而达意”[3]58。如他1956年访问埃及时的写生作品《赶车者》(曾刊载于《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画选集》)在经过1970年的重画之后,原作中非常注重写实性描绘的泥泞道上的车夫,被重塑为置于高背椅上的阿波罗,加长了胡须、堆高了头巾、添加了胸章。椅背和脚下阴影处的墨色里,还夹杂一些无法辨识的类似字母的文字,赶车的鞭子也变成了神杖。画中衣纹经过这般抽象处理后,打破了以写生为依凭的原有结构,变成了曲折、坚硬,如刀刻般的线条,整体上被赋予了全新的意涵,彰显了石鲁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艺术哲思。
第二,观物与取象。石鲁所谓的“观物”不是照相机式的写生,而是发挥主体意识的统摄与观照作用,使得“万物已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进入心中,成了心中之物,加进了主观色彩,经过组合、改装,是在心中重新展开的物象”[9]321。从“观物”到“取象”恰是古典意象美学的核心,如宗炳《画山水序》云:“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写色”;“抚琴弄操,欲令众山皆响。”王安石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石鲁也对此承袭,提出:“观物当面面观、变动观、上下观、远近观、四时观、表里观,无所不观,无微不至,必熟才能活”;“凡物之形、质、动、静、神情、姿态,若不能活现于心中,则不足以言画。”[3]25此外,他还围绕型体、结构、线面、气色、远近等方面对国画创作技术作系统总结。其中,石鲁特别指出“线面”与“气色”构成了国画造象的关键,他强调:“国画之重线,唯线可兼物象与精神也。”[3]38这在他20世纪60年代后创作的《东渡》《逆流禹门》《黄河两岸度春秋》《延河饮马》《陕北秋色》等作品中均有生动的体现。石鲁女儿石丹、弟子侯声凯在回忆石鲁创作《东渡》的情景时说,“石鲁在构思阶段花的时间很长,光小稿画了十来幅。他为了画船工,还找了些医学用的能活动的人的模型,摆姿势来看解剖关系。”(5)石丹口述,刘艳卿整理,口述时间:2015年3月27日14∶00-18∶00。但在进行墨稿创作时,为了体现“船工们豪迈的身姿和那种激烈拼搏中爆发的撼人的生命力”,他果断摒弃了西画光影素描的效果,将由现场写生获得的形象,进行了大胆处理。“运用他独有的山水画技法,色破墨,墨破色,色墨浑然,在墨底或赭墨底上以朱砂,朱膘,少许洋红,赭石等,色皴,色擦,色染,表现船工肤色各不相同的差异以及他们雄健壮美的真力。”[10]形成作品形而上、表现性的意象,高亢激情、气势恢宏的格调,使观者产生强烈的心理震颤。
第三,笔墨与形意。笔墨是传统画论的中心议题。宗白华先生评价王维《蓝田烟雨图》“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称其中“诗中有画”,充满了“暗示的意味和感觉”[6]288。石鲁充分吸收了此种以“笔墨”表现“形意”的美学传统,他说:“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3]46不过,他认为“笔墨”显然不仅是对技术与程式的简单因袭,而是饱含审美积淀的文化心理。石鲁认为“笔”包含“笔法”“笔情”“笔意”“笔体”“笔韵”等方面,必须“因性以练笔,凝性而成体,结体而成法”,即强调主体意识为主,学习古法要遵循权变。他强调“笔、墨、色布置皆相生相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3]48,作为造型语言,“笔墨”的关键是与主体的情意想通,因此“最忌虚情假意、无情无意”[3]46。他认为,所谓“随类赋彩”及“墨色”都不只是对自然的模仿,因为“色亦有型,有强弱、冷热、庄严、活泼、浓艳、清淡、老嫩之分。可见色非纯自然之色,乃有长期社会实践所形成之审美观念。故色之于造型,亦具主、客二因也”[3]41。石鲁将之总结为“求笔墨当归之于性情、归于意志,于是不求风格而风格自来”[3]59。如其代表作《东方欲晓》(1962)通过窑洞中的摇曳烛光及窑洞前的枣树枝蔓所映射的微弱光芒,生动地表现了革命领袖通宵达旦的忘我工作。使其画面呈现出“无人”“无日”,却使人亲切捕捉到“东方欲晓”的一语双关。又如《古长城外》(1954),该作品以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为题,旨在表现以火车通达内陆山区的工业壮举,然而作品中仅有铁轨并无机车,但通过藏族女青年双手遮耳及羊群惊逃的生动景象,使我们感受到画中汽笛轰鸣。
四、余论:《学画录》与新中国“十七年美术”的创新精神
1960年初,石鲁主持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的工作,经过集体探讨,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学画录》显然是对该主张的生动诠释。通过《学画录》的撰写,石鲁受到了传统美学的思想熏陶,为其后的艺术腾飞奠定了理论根基。此外,石鲁积极而大胆地采用“主观”“客观”“一般”“抽象”“知觉”“意识”等现代哲学、美学及心理学的语汇,对传统的“心”“物”“形”“神”进行创造性的理论阐释,使得“神思”“游心”“物化”等传统命题实现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创新表达,并藉由“意”“理”“法”“趣”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美学体系。《学画录》所蕴含的丰厚的美学内涵,呈现出以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强烈的创新意识与拼搏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十七年美术”所营造的时代氛围。在当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发挥了美术家协会的团结、协作、组织作用,遂使石鲁等人在推进以批判的态度去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创造具有与新的时代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新的民族艺术形式,深化实践与理论双重探索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