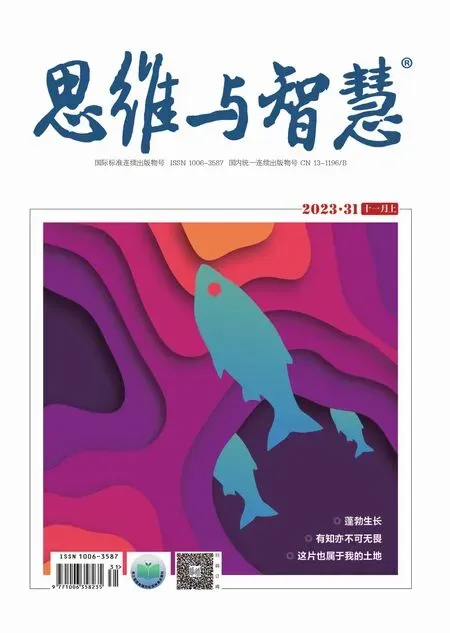难忘儿时蒸年糕
◎ 李吉伟

年糕是百姓过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过去一入腊月,农村的碾子便成了香饽饽。
到了腊月,母亲就开始张罗“敲糕米”,也就是套牲口拉碾子推面。糕米的初加工很是费时费力,母亲先将玉米用簸箕簸干净,然后再下锅煮一个多小时。我坐在母亲腿上,听着母亲唱着歌。一锅金黄的玉米弥漫着香气,火的红和玉米的黄,那是一道别样风景。
玉米煮好后捞出来晾着,接着将浸透好的黍子米也捞出来控水。一切准备就绪,母亲便一家一家地问“碾子”。腊月时分“敲糕米”在小村子里也是一道风景,早早就有人将簸箕、笤帚放在碾盘上,这叫“占碾子”。无论你起得再早,看见有人占着,都得按顺序排队,轮到你家才能将糕米的原料用车推过去。
经过漫长的等待,二婶子喊母亲来“敲糕米”,母亲推着玉米、黍米,我坐在车横梁上,浩浩荡荡奔向碾盘,开始一年一度的“敲糕米”盛事。借来邻居家的牛,把牛的眼睛蒙起来,玉米在碾子上围着碾盘心均匀摊开,一声“嘚儿驾”牛开始转圈儿,吱吱呀呀的碾子声,甚是好听。玉米碾得差不多的时候,将金黄的黍米在碾盘上铺开,玉米的白和黍米的黄再一次糅合在了一起。
母亲一边用铲子铲起被压扁了的玉米黍米,一边将碾碎了的用细萝放在架子上来回震动,不一会儿,笸萝里就蒙起一层细细的面。就这样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敲糕米算是结束了。卸下喘着粗气的牲畜,推着我和糕米面回到家中。
母亲负责“敲糕米”,父亲负责蒸年糕。回到家里时,父亲已将一锅开水烧好,一边将滚烫的水倒入大盔子里,一边不停地搅拌,直至比例合适。母亲拿来粗筛子,父亲将泼好的面用筛子筛,糕米面算是准备就绪。在泼面筛面的同时,泡在锅里的大枣的香气,已在小院的四面八方弥漫。捞出大枣,再次添水至篦子的四指高度。添水是个技术活儿,父亲很有经验,每次都按照多年来的经验添加。水少了篦子就烧坏了,水多了则水开后扑篦子,那样糕里有水,便坏了味道。
篦子上先铺一层白菜,再铺大枣。锅的边沿还要贴上白菜叶子,这样做,就是为了糕蒸熟后好起锅。
铺满了血红血红的大枣,开始烧火,不一会儿蒸汽就从篦子下面冒出来,这时候父亲将糕米一点点儿均匀在大枣上撒,哪儿冒气就把米面往哪儿撒,好像就是专门堵气口。不一会儿,白面在蒸汽的作用下,由白变成了黄。小院里的香气再一次绕过墙头飘向大街。我依然坐在母亲的腿上听母亲唱歌儿。父亲被白色的蒸汽环绕,不时还嘱咐母亲不要加柴,火的大小决定着一锅年糕的质量。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一锅年糕蒸好了。
父亲一人提着篦子上的绳子,将一锅透着米香和枣香的年糕反扣在簸箕里。那时候嘴馋,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催促父亲切一块下来,让我尝尝鲜。父亲沿边缘切下,糕很黏,一刀下去,还得拿出来沾沾水,再切第二刀。当母亲递给我时,口水早已流到了胸前。一口咬下去,烫得我直跺脚,含在嘴里像一块火炭,又舍不得吐出来,就这样在嘴里转几个圈,才开始尝到年糕的味道。嚼碎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一坨糖葫芦往下掉,枣的香黍米的黏,这一刻心都融化了。
后来,人们用粉碎机推面,也按一样的蒸年糕流程做,但是蒸熟后总觉得没有碾子上推出来的黍米有味道。
工作后搬到城里住,一入腊月父母亲就唠叨蒸年糕,为了满足二老的愿望,我把老家的那口大铁锅请进了城,又买了一个铁锅灶,将那口给我们一家增添欢乐的铁锅支了起来。有了锅灶方便多了,父亲母亲脸上绽开了笑容。但是母亲因心脏病离世,最终也没吃上从家里搬来的那口锅里蒸出来的年糕。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一到了腊月,我就到粮油店买来掺好的糕米面,凭着儿时的记忆,在岳父岳母的指导下开始蒸年糕。父亲吃着我切下的第一块年糕时老泪纵横。想不到住楼房也能吃上家里那口锅蒸出来的年糕。去年父亲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依然每年蒸一锅年糕,夜深人静时我悄悄将一块年糕放到阳台,告诉父母年糕蒸好了,你们尝一口黏不黏。泪水又一次像儿时的口水一样流到了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