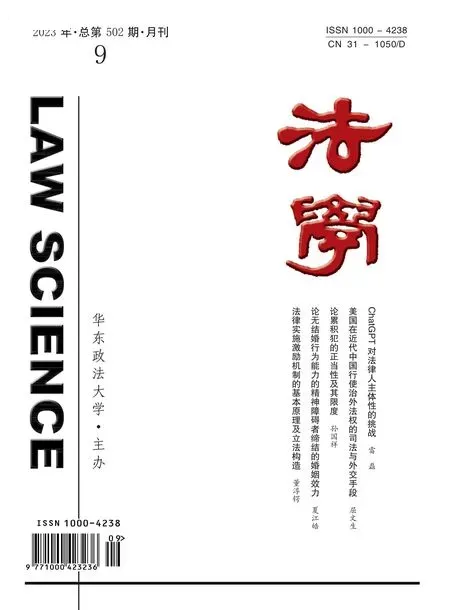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
●董淳锷
一、问题意识与理论脉络
(一)问题的意义
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之一。理论共识认为,良好的法律规则需依赖有效的实施机制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唯需讨论的是“有效的实施机制”是什么?既有文献中的多数观点认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是法律的基本特征。或许是受此观念指引,不少研究将法律实施低效和法律实效缺失归因于监管不严或惩罚不力,进而以强化惩罚为目标,探寻法律强制实施的权威路径,以及探讨法律规则统一适用的技术标准。
然而实践证明,强化惩罚只在特定条件下才具备功效,并非一般意义上改善法律实施效率、提高法律实效的必然对策。其一,法律规则具有多样性,强化惩罚对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难以强制履行的义务规则、事实调查成本高昂的监管规则以及边界不清晰的责任规则的实施均收效甚微。其二,强化惩罚必然带来更高的法律公共实施成本,预算约束可能导致此对策异化为运动式执法或选择性执法。其三,强化惩罚的功效有边际递减规律,惩罚超过一定强度后,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可能出现守法策略的逆向选择。其四,强化惩罚可能加剧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冲突,催生更多的法律规避行为或法律实施障碍。
弥补惩罚机制功能局限、强化法律实效的一个可能路径是为法律实施提供激励,即以利益给付、权益享有、荣誉褒奖、资质评定、信用公示、责任减免或替代承担等方式引导法律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使其行为符合立法目的。这一思路并非凭空设想。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已间接提示,合理的激励措施可以引导人的行为,而现有法律实施机制也确已存在少数激励措施并体现出一定成效。若进一步把法律实施问题放置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背景下考量,至少在规范分析层面我们有理由期待,构建激励机制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弥补惩罚机制缺陷,它还是凝聚全民守法意识的有效途径,是减少执法对抗、避免法律实施冲突的重要方法,也是有效降低法律实施社会成本的必要手段。但问题在于,立法层面旨在激励法律实施的措施尚未系统化,可用于论证激励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理论也未真正与法律实施问题产生化学反应并形成体系。事实上,以往数量繁多的文献尚未从激励视角系统论及法律实施机制,对“法律实施何时需要激励而不是惩罚”“激励机制如何设计”等问题,并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为了回应实践需求、完善理论板块,有必要对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设计原理和立法构造展开讨论。
(二)基本理论脉络
传统法学领域以法解释学为核心,本身并不直接关注行为激励问题。已有的论及激励问题的成果主要以交叉学科理论为基础,探讨如何通过法律引导相关主体行为,以实现立法目的。此类研究形成的是“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的学术范式,基本观点是把法律整体视为一种激励体系,〔2〕See George J.Stigler, 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s, In Gary S.Becker and William M.Landes (eds.), Essays i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By.Publish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 p.55-67; Steven Shavell.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Law Enforcemen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6, No.1 (April 1993), p.255-288.旨在“诱导当事人采取从社会角度来看最优的行动”,〔3〕张维迎:《信任、信息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66 页。“通过改变一个社会博弈的支付函数方式改变人们行为选择的激励,使人们的行为实现立法者的目标。”〔4〕丁利:《制度激励、博弈均衡与社会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4 期,第149 页。与此不同的是,以往文献并未充分关注法律实施的激励问题。事实上,“法律实施的激励机制”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命题,区别有四:(1)前者将法律(实施)视为对象,后者将法律(实施)视为工具;(2)前者目的是改善法律实施效果、强化法律实效,后者目的是通过法律引导主体行为;(3)“需要为法律实施提供激励”的场景不同于“需要法律提供行为激励”的实践场景;(4)两者依赖的措施不同。
经济学的若干理论有助于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理论体系。第一,法律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理论〔5〕See Gary S.Becker and George J.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 No.1 (Jan.1974), p.1-18; 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4, No.1(Jan.1975), p.1-46.可用于比较不同法律实施机制的效率,有助于解释如何通过“公共实施转为私人实施”来激励相关主体主动遵守法律规则。第二,交易成本理论〔6〕See Ronald 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1937), p.386-405; Ronald 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1960), p.1-44.可用于解释法律规避现象及“私益权规则”等法律实施问题,有助于理解强制性法律实施与任意性法律实施的区分。第三,与交易成本理论密切相关的产权理论可用于解释“共益权规则”和“边界不清晰的法律责任规则”等法律实施问题,外部性内部化等原理〔7〕See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No.2 (May 1967), p.347- 359.则是制定相关激励措施的重要指引。第四,委托代理理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模型可用于解释“非标准化义务规则”和“软法标准”等实施问题,相关的隐性激励理论〔8〕See Eugene F.Fama,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8 (1980), p.288-307;Bengt Holmstrom, Moral Hazard in Teams,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 No.2 (1982), p.324-340; David M.Kreps, Robert Wilson,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27, No.2 (1982), p.253-279; Ariel Rubinstein, Perfect Equilibrium in a Bargaining Model, Econometrica, Vol.50, No.1 (Jan.1982), p.97-109.和显性激励理论〔9〕参见李波:《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20 页。则是解决法律实施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依据。第五,激励规制理论〔10〕See David P.Baron and Roger B.Myerson, Regulating a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Costs, Econometrica, Vol.50, No.4 (July 1982), p.911-930.可用于解释“实施成本高昂的监管规则”以及“威慑作用有限的责任规则”等实施问题,有助于研究如何减少规制者对被规制者具体行为的直接控制,促使后者合理发挥信息优势,将行为调整到与立法目标相一致的轨道。第六,机制设计理论〔11〕See L.Hurwicz,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3, No.2 (1973), p.1-30;Roger B.Myerson, Optimal Auction Design,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Vol.6, No.1 (Feb.1981), p.58-73; Eric S.Maskin, Nash Equilibrium and Welfare Optim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6 (1999), p.23-38.有助于研究如何消除法律实施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探讨如何构造激励相容的法律实施机制,使相关主体的理性选择结果或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符合立法目标。当然,上述理论并非相互孤立。法律“公共实施/私人实施”是分析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框架,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需借助交易成本分析,激励规制理论离不开委托代理理论的支持,而机制设计理论也涵盖了委托代理和博弈论等理论元素。
基于理论的多元性和关联性,本文拟按照法律实施为何需要激励及如何激励的逻辑思路整合上述理论资源,结合商法、经济法领域的实践,系统分析各种法律实施低效现象的个性和共性问题,以期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法律实施为何需要激励
(一)法律实施低效问题的类型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得到执行或没有人援用的法律很难塑造人们的行为。”〔12〕[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0 页。尽管上述观点已近乎常识,但“法律得到有效实施仍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研究者往往都缺乏对不同类型法律的实施成本进行系统分析。”〔13〕Gary S.Becker and George J.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3, No.1 (Jan.1974), p.1-18.实践表明,“有多重原因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被改变。其或是因为复杂的立法程序使法律不可预测;或是因为政治经济环境持续变化引起的制度变迁,使法律被重新修改或解释”,〔14〕Peter Grajzl and Peter Murrell, Allocating Lawmaking Powers: Self-regulation vs.Government Regul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35 (2007), p.520-545.导致“形式上有效的法律有很高的非执行比例”。〔15〕[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7 页。
1.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
基于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的传统观念,以往研究多认为,权利规则是否实施取决于权利人意思自治,公权机关只需提供权利救济途径,不可强制其适用权利规则,更不必为其适用权利规则提供激励。此观点及其相应实践方案的不足在于没能细分权利类别。权利可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后者一般不会给第三方带来正外部性效应,即排他性更强,产权边界更清晰,因此权利人更乐于行使。一旦权益受损,他们也会主动寻求救济,除非救济成本太高而预期赔偿太少。
与私益权不同,共益权收益由全体权利人享有,行权成本由权利人分担。若每位权利人都按法定或意定方式分担成本,则共益权规则的实施效率也会较高。但问题是,“在一个群体中,即便所有成员在实现集体目标后都能获利,我们也不能推定这些理性、自利的成员会自愿为此目标采取行动。”〔16〕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因为共益权产权边界难以清晰界定,权益并非完全排他,行使权利所得收益具有正外部性,很多共益权人都希望不支付私人成本而是依靠他人适用权利规则来分享收益。〔17〕See Oliver Hart, An Economist’s View of Fiduciary Du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Vol.43, No.3 (Summer 1993),p.299-313.而且,共益权人之间往往存在重复博弈,当所有人都预见他人“搭便车”时,那么等待他人行使权利而自己分享收益将是“占优策略”,这必然导致共益权规则实施效率低下。
2.被权利主体主动放弃的私益权规则
在很多领域,虽然立法规定了大量权利救济规则,但如果“权利人经济实力不强,那么即使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他也可能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不起诉违法者。此情况下因公共实施威慑力不会发生变动,结果导致整体上对这类行为威慑不足。”〔18〕A.Mitchell Polinsky, Private versus Public Enforcement of Fine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IX, No.1, (Jan.1980),p.105-127.比如,在金融市场,尽管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出台了大量法律文件,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等机构也制定了很多自律规则、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制度,但损害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行为依然广泛存在。尽管监管部门加大了查处力度,但往往只是强化了对违法企业及责任人的行政处罚,至于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救济,执法层面并不会直接解决。
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处罚违法企业时一般不同步处理民事赔偿,这并非监管部门失职,而是立法很少作此授权;二是诉讼机制限制〔19〕最高人民法院2002 年出台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2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须以监管部门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已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前提。和诉讼成本可能远高于预期赔偿,权利人缺乏足够的维权激励;三是监管部门立案查处时,违法企业通常已将资产转移或隐匿,权利人即便胜诉,判决也无法执行。此类问题在证券市场、股权众筹、P2P 网络借贷等领域的表现最明显。多年来,这些领域的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常因企业内幕交易等行为频繁造成损失,但真正通过法律程序获得赔偿的数量有限。
3.难以强制履行的义务规则和法律标准
法定义务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判断消极义务履行效果的标准比较明确,只要相关主体不实施立法限制或禁止的行为即可认定其已履行义务,至于是否真正实施了禁止行为或限制行为,则属于调查、举证的技术问题。积极义务履行效果的判断标准则比较复杂。为便于研究,可将其区分为“标准化积极义务”与“非标准化积极义务”进行讨论。
“标准化积极义务”是立法上有明确标准可用于认定义务履行效果的积极义务。〔20〕例见《公司法》第166 条。由于义务履行结果可度量、义务主体是否违法的事实易查清,所以惩罚机制对保障该类义务规则的实施效果良好。“非标准化积极义务”是立法上用以判断义务履行效果的标准较模糊的那些积极义务。义务规则有效实施必须依赖以究责为核心的惩罚机制,但根据法律适用“三段论”,启动惩罚机制须以义务主体未履行义务为前提,若某一义务规则履行效果难以被标准化,则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效果就难以认定,惩罚机制便无法启动。比如,《公司法》第5 条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公司需要做什么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承担了社会责任,立法未予明示,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很难认定企业是否已承担了社会责任,进而决定是否对其实施惩罚。
有些法定标准也难以通过惩罚机制强制履行。比如,按《标准化法》的规定,法律意义上的标准包括强制性、推荐性和自愿性三种。强制标准是法定最低标准,其余两种是国家希望市场主体在强制性标准之上执行的更高标准。强制标准设定的是“标准化积极义务”,其实施可依赖惩罚机制。但推荐标准、自愿标准属软法范畴,只要其不低于强制标准,监管部门便无法将市场主体未执行推荐、自愿标准的事实认定为违法进而施加惩罚,除非市场主体事先承诺其将采用更高要求的推荐标准和自愿标准(此时的违法性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虚假宣传)。
4.实施成本高昂的法律监管规则
“禁止潜在违法行为的成本是高昂的。”〔21〕Gary S.Becker and George J.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3, No.1 (Jan.1974), p.1-18.实施监管规则的成本至少有两类:一是监管部门行使监管权的成本,如工作人员薪酬、办公场地建造或租赁成本、工作设施设备购置与养护成本。此类成本主要由财政承担;二是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规则而支付的成本,如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资产评估的费用,此类成本一般由市场主体承担。监管规则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与规则实施成本关系紧密。一方面,如监管成本过高,以致监管部门难以及时监管,市场主体将获得逃避法律约束的机会,此情形属“监管不能”;另一方面,如监管规则严苛,造成守法成本过高,市场主体会想法规避监管,以期降低守法成本,减少违法风险,进而架空监管规则,此情形属“监管规避”。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监管就存在此类问题。规范的市值管理本为法律允许,〔22〕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2 条第(六)项之规定。但实践中存在很多“伪市值管理”,如上市公司通过发布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甚至与公募基金或私募基金合谋恶意操控股价等。“伪市值管理”不是根源于立法缺失,〔23〕2019 年修订的《证券法》强化了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力度。也不能简单归责于监管不力,更直接的原因是事前监管成本过于高昂。一则,近年来企业上市门槛降低,“注册制”“科创板”等板块扩容使上市公司数量激增,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二则,绝大多数“伪市值管理”并非采用直接违法手段,而是以合法外观包装,这种行为涉及主体众多、模式复杂、过程隐蔽。监管部门除非获得有效举报信息,否则及时发现并事前杜绝此类行为的难度很大。
5.威慑作用有限的法律责任规则
从规范分析角度看,公权力机关可通过惩罚机制强制要求违法者支付违法对价,威慑公众放弃违法意图。但实践显示,法律责任规则和相关惩罚机制并非无所不能,威慑作用亦非无时不在。因为有效发挥威慑功能需以及时查明违法事实和公正适用法律为前提,但这两者的实现可能遭遇诸多障碍。例如,由于被监管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或被监管领域信息具有强隐蔽性,导致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不高,或者监管者执法不公,都可能弱化责任规则和惩罚机制的威慑功能。事实上,公众对规则的认知以及对责任风险的预判往往只有有限理性。他们可能基于认知错误而“无意识”地违法,也可能基于利益诱导以及违法行为并非全部被及时发现这一客观事实而侥幸违法。一旦责任规则威慑不足,以究责为基础的惩罚机制也将失效。
例如,多年来立法对工程承揽建设主体资质、承揽合同形式与效力等问题规定了严格的监管规则和法律责任,还规定因承揽工程不符合法定质量标准而造成损失的,施工企业及其挂靠承揽人或其他使用施工企业名义的单位及个人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4〕参见《建筑法》第65、66、67 条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等规定。然而,建筑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承揽等现象仍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一是多年来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建筑工程数量巨大,所涉监管事项专业性强、信息隐蔽,但监管力量有限;二是连带责任机制理论上可增强威慑,但在内部关系中,它也可能强化违法者合谋对抗监管以及构建虚假合法外观的意愿,这会大幅提高监管难度。
6.责任边界不清晰的法律责任规则
责任规则有效实施需满足若干条件:一是主体责任边界清晰;二是公权力机关能够查明事实;三是主体行为符合违法构成要件。其中,责任边界清晰是先决条件。一方面,如果责任边界规定不清晰,那么即便公权力机关能够查明事实,也难以准确判定各主体的责任;另一方面,责任边界规定清楚,但公权力机关难以及时查明违法事实,也可能导致另一种意义的责任边界不清,即要么无人为违法担责,要么责任承担者并非真正违法者。在此两种情况下,责任规则的立法目的都无法实现。第一种情况的典型实例是独立董事制度。虽然立法相对清晰地规定了上市公司董事的一般义务和独立董事的具体义务,但并未明确界定独立董事的责任边界。一旦上市公司违法,法官在判定独立董事责任程度、责任比例时,可能遭遇争议。〔25〕“康美药业独立董事民事连带赔偿案”即是广受关注的实例。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 民初2171 号民事判决书。质疑者的理由是,独立董事对公司经营管理重要信息的掌握显然不如内部董事,因此其注意义务应获减轻,若机械地适用法条而要求两者同责,不甚合理。第二种情况的实例是近年来困扰监管部门的共享单车乱停放现象。早期的监管规则将单车合理停放设定为经营者责任。但问题是,企业是共享单车所有权人和出租人,他们虽有义务引导单车合理停放,但其并非单车违规停放的行为人,难以每时、每地督促消费者合规停车。消费者是共享单车的承租人和实际使用人,如若他们仅需为骑行支付成本而无需为违停承担责任,则行为外部性不会被内部化,〔26〕例见《深圳经济特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若干规定》第6、7 条。在此情况下将缺乏足够激励使人将单车停放至合规地点,导致相关监管规则无法发挥实效。
(二)强化惩罚并不总是有效
以往很多文献认为,解决法律实施低效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强化惩罚〔27〕See Giuseppe Dari-Mattiacci & Alex Raskolnikov, Unexpected Effects of Expected Sanction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50,No.1 (2001), p.35-74.:一是加大惩处力度,包括提高罚款、罚金额度或降低违法行为认定标准等;二是扩大惩处范围、提高惩处频率、加快惩处速度。以强化惩罚来提高法律实施效果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针对前述各种法律实施低效问题,强化惩罚就可能收效甚微。
其一,“强化惩罚论”忽视了法律规则的多样性。以往文献在探讨法律实施和惩罚机制时,往往只关注义务规则和责任规则,忽视了权利规则也有实施效率低下的问题及权利规则难以强制实施的特点。虽有文献论及权利规则实施,研究者通常也是将其转化为“通过提高义务规则、责任规则实施效率来强化权利保护”的命题展开论证,此思路只是在法律实施“目的论”层面论及权利规则,并未从“过程论”视角探讨权利规则的实施。忽视规则多样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很少从标准化和非标准化视角细分义务规则,也未充分关注惩罚机制对非标准化义务规则实施的局限性。事实上,实践中存在很多实施效果难以度量的义务规则,也存在国家倡导实施的高于法定最低标准的标准,单纯依靠惩罚机制难以推动此等规则实施。换言之,“惩罚必然会局限在很有限的范围”。〔28〕[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28 页。
其二,“强化惩罚论”忽视了惩罚机制运作基础的复杂性。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是司法裁判或行政处罚的必然要求,但查明事实并非易事。受制于各种因素,通过证据重构的事实可能只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有的案件可能因证据缺失而致违法者未被究责。如果公权力机关无法准确判断义务主体是否已依法履行义务,或无法通过及时监管确定违反义务的主体,那么惩罚机制便无法对义务主体形成威慑。更重要的是,从违法者的角度看,惩罚机制缺乏威慑往往不是因为法律责任不严厉,而是他们知道公权力机关若无法查明事实就无法对其施加惩罚——在那些违法行为隐蔽、规避监管成本较低的领域尤其如此。
其三,“强化惩罚论”对法律实施成本的约束考虑不足。理论上,加大处罚力度和及时惩处违法者有助于强化法律实施效果,但强化惩罚需以增加法律公共实施成本为保障,问题在于:第一,预算约束可能导致不断强化的惩罚机制无法持续高强度运行,法律实施可能异化为运动式执法或选择性执法。第二,无论公共实施成本能否持续投入,强化惩罚的功效整体上边际递减,当惩罚超过一定强度后,相关主体可能出现守法策略的逆向选择,比如,以更具危害性的违法行为掩盖已有过错,或者放弃对已有违法行为的及时纠正。第三,惩罚机制属于公共实施范畴,过于强硬的公共实施容易引发执法对象与执法者对抗,加剧法律实施的复杂性。
三、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设计原理
(一)改变法律私人实施的效用函数
在私人实施意义上,法律是私人主体的特殊消费品。私人投入成本实施法律以获取法益将受到特定效用函数的约束。实践中,法律实施低效有多种原因,最常见之一是私人主体认为花费成本实施法律无法满足其效用。对此,激励目标应通过降低实施成本、提高实施收益来优化法律产品价值,进而改变私人实施的效用函数。
对公众而言,实施成本高昂会诱使他们逃避义务与责任,或者促使他们放弃行使权利。因实施成本高而放弃权利的实例并不鲜见。如证券市场、股权众筹和P2P 网络借贷的公众投资者,遭遇共享单车押金损失的公众消费者,以及居住环境被污染的居民,他们在权利受损后放弃法律救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预期的获赔概率与获赔额度的乘积小于救济成本。从激励角度解决上述问题有多种途径:一是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公权力机关或社会组织代表公众实施权利规则并承担相应成本;二是建立代表人诉讼制度,〔29〕如证券法领域投资者提起的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即可适用此类制度。其与公益诉讼相似之处是公众不必亲自参与诉讼,不同的是在代表人诉讼中,委托代表人起诉的公众仍需共担诉讼成本,其享受的只是免于参与烦琐的诉讼程序;三是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公众维权收益;四是降低公众行使权利的难度,如设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30〕例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 条。
私人实施的义务规则和责任规则的成本问题更复杂。法定义务和责任本质是公众应承担的守法成本。立法者设计义务规则、责任规则时需合理度量守法成本。成本太低则无法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结构(就义务规则而言),也无法带来威慑(就责任规则而言);成本太高则可能间接抑制公众依法行事的主动性(如董事因担心失职之责而不愿作出风险决策),甚至反向诱导他们实施违法行为。当社会实践已显著变化而立法滞后明显,扭曲了法律实施“成本—收益”结构时,公众更有可能逃避义务与责任,法律规避现象由此产生。此外,若轻微违法行为将承担严苛法律责任,也可能导致公众在计划或着手实施违法行为后,缺乏尽早终止违法或主动消除损害后果以期获得减责免责的动力。我们可把上述情况称为公众在守法问题上的逆向选择。当出现逆向选择时,义务规则、责任规则的实施效率就会低下。换言之,惩罚太严厉并不利于阻却违法。化解的思路仍是构建激励机制,改变法律私人实施的效用函数。立法者应抛弃“严刑峻法可实现所有社会治理目标”和“惩罚机制可推动所有法律规则有效实施”的观念,改为通过附条件的责任减免或责任替代承担规则,〔31〕可借鉴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激励公众主动履行义务,〔32〕可借鉴商业判断规则和董事责任险制度。或者激励公众主动交代违法事实、及时终止违法行为、积极消除不利后果以及提供他人违法信息。〔33〕可借鉴反垄断宽恕制度。
(二)将法律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
“社会应该放弃‘规则得以完全实施’观念的决定性因素是,法律实施需要耗费成本。”〔34〕George J.Stigler, 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s, In Gary S.Becker and William M.Landes (eds.), Essays in the Economic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By, Publish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 p.55-67.成本高昂导致实施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发生在私人实施场合,也可能存在于公共实施情形。事实上,无论是哪种实施,“若机制运行需要经济人或机构对信息的观测、沟通或其他信息处理过程的数量无限大,则该机制显然没有可行性。”〔35〕[美]利奥尼德·赫维茨、斯坦利·瑞特:《经济机制设计》,田国强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 页。公共实施的效率问题同样可通过激励机制解决,但在机制设计上,旨在降低公共实施成本、提高公共实施效率的激励措施与私人实施场景下的激励措施有着明显区别。于私人实施的场合,如实施成本高昂,激励机制应增加公众实施法律的收益或减少其实施成本。换言之,激励私人实施的特点是法律实施主体与被激励主体两者身份同一。但在公共实施的场合,实施主体是公权力机关或社会组织,但被激励主体不局限于这两者,有时也可能是其他主体(如被监管者),此时实施主体和被激励主体就出现了身份差异。
例如,在市场监管领域,若违法行为具有专业性和隐蔽性,〔36〕如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且市场监管技术、方法滞后,或者虽然违法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行为有普遍性,〔37〕如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问题。则监管部门查明事实和追究责任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昂。一旦成本超过合理边界,〔38〕只要观察一下中国证监会通过借用北斗卫星进行长时间海域观察才认定了某上市公司实施多年的违法事实,就不难理解文中结论了。参见中国证监会〔2020〕2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会降低监管者查明违法事实的概率,使监管规则无从适用。解决问题的激励方法有二:一是通过职务晋升、荣誉表彰或经济绩效奖励等措施,激励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更加勤勉履职,提高工作强度,以及改善监管技术方法。〔39〕例见《食品安全法》第13 条。二是通过经济奖励、权益优先享有、经营资质提升、信用公示、荣誉褒奖、义务减轻、责任豁免等措施激励被监管者主动遵守和实施法律规则,或通过经济利益激励其他组织或个人揭发违法信息,以此减少监管部门调查和处理违法行为的成本。上述第一种情况下激励对象是监管者;第二种情况下实施监管规则的是监管部门,监管规则约束的对象以及激励对象则是被监管者。就后者而言,激励机制实际上已把公共实施部分转化为私人实施,有效降低了实施成本,理由有三:第一,实施成本部分根源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对抗。为了消除对抗,监管者需要投入大量监督成本以便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并追究相应责任,若出现纠纷,还会导致司法成本。因此,如果激励机制能够促使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使被监管者主动实施法律,减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对抗,将有助于降低因内耗所致的效率损失。第二,相当一部分私人实施几乎不额外耗费公共资源。在一些场合,激励机制只是在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以守法获益为目标的竞争,它使公众意识到,若自己主动、及早依法行事,则可获得多于他人的利益。〔40〕例如,公权力机关可规定,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在申请各类行政许可或取得公共资源(如政府补贴)以及申请义务、责任减免(如税收优惠)时将获得优先权。此情形下激励机制成本主要是立法机关制定规则的成本。规则建成后,监管部门几乎无需为实施激励措施额外支付。例如,在总量恒定而资源配置具有竞争性的各种行政许可范围内,依法获得许可的企业数量有限,区别只在于是甲获得还是乙获得——在监管部门看来,谁获得不重要,他们需要做的是让最自觉遵法守法的企业自己通过行为显示出来,并赋予其优先于其他企业的权益。第三,即便是公共资源支持的私人实施,其耗费成本仍可能低于纯粹公共实施的成本。例如,作为激励措施的市场监管举报奖励制度,其有助于降低公共实施成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举报奖励显著降低了监管部门获悉违法行为的信息成本,而且举报者获得奖励的前提是举报的违法行为被查证属实,这可以避免监管部门在虚假举报误导下浪费执法成本;另一方面,奖金一般来自罚款,且只占罚款总额的一小部分,〔41〕参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2021)。而罚款又是监管部门根据举报信息查处违法行为后所得的执法收益,从整体上衡量,监管部门是以小代价换取了大收益。
(三)促使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
产权关系不明晰将导致行为存在外部性。实践显示,法律实施行为可能产生外部性,如果相关机制不能有效促使外部性内部化,即无法解决产权关系不清晰问题,外部性就会影响公众行为选择,使其作出不主动适用法律的决策,从而导致法律实施的效率降低。在权利规则范围内,共益权规则的实施容易导致正外部性,即权利个体主动实施法律规则、承担实施成本,但收益由全体权利人共享。这种正外部性如无法内部化,各共益权主体基于“搭便车”心理将会失去实施法律的积极性。〔42〕See 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4, No.1(January 1975), p.1-46.与此不同,在义务规则和责任规则的范围内,如监管部门无法及时查明违法行为,则难以追究违法者责任,此时行为负外部性无法内部化(本质上同样是产权关系界定不清),可能诱发更多的违法行为。
产权分析方法适用于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43〕参见[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7 页。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明晰与法律实施有关的产权关系。于权利规则而言,立法应规定公众可通过适用权利规则取得收益,也需承担法律适用成本,使公众意识到适用法律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涉及私益权的场合,成本收益统一归属权利主体是常态,有些情况下私益权主体已支付了行权成本,收益却被他人非法占有,对此可通过侵权法等事后救济规则予以矫正。简言之,对行使私益权的法律保障主要是事后矫正机制而非事前分配机制。在涉及共益权的场合,明晰产权关系的激励机制更具意义。为了实现事前激励,立法可以建立“行权代表人制度”,即由全体共益权人事先授权某主体代行权利。代表人依约取酬,其行使权利费用由共益权人分担。立法也可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即全体共益权人无需事先选定代表人,但如有某位共益权人主动适用规则且为全体共益权人带来收益,则行为人可请求其他共益权人弥补其适法成本,并要求获得收益分成或利益优先受偿。相较而言,第一种途径的效率可能更高。
在义务规则和责任规则领域,明晰产权关系的要点是负外部性内部化,即让公众为其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其一,从事前激励角度,使公众充分意识到如未按义务规则行事将被究责,但若及时终止违反义务行为,积极抑制损害后果,主动承认未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或检举他人违法行为,则可被减免处罚。其二,从事后矫正角度,使公众为自身违法行为实际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将违法后果转嫁他人。
(四)消除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概念。委托代理理论最初主要用于研究企业经营管理,〔44〕See Eugene F.Fama,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8 (1980), p.288-307.后期随着契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其他理论的发展,被广泛用于研究规制其他社会问题,〔45〕See David P.Baron and Roger B.Myerson, Regulating a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Costs, Econometrica, Vol.50, No.4 (July 1982), p.911-930.并被抽象为“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需依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但该当事人却无法充分掌握另一方当事人私人信息”的关系。法律实施过程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况。
就道德风险而言,“当代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不能被观察到时,标准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产生了——投入对代理人来说要付出代价,同时它也会影响到委托人的福利。”〔46〕[法]埃里克·布鲁索、让·米歇尔·格拉尚:《契约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王秋石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8 页。例如,在市场领域,如法定义务难以被标准化,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判断企业是否已充分履行了义务,企业就可能基于私利而不履行义务,或者通过规避手段迂回绕开法律规定。这是法律实施过程中道德风险的近似体现,此情形下的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类似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而企业类似于代理人。
就逆向选择而言,立法机关在市场领域制定了软法规范,其或以指南、指引的形式出现,或以鼓励、支持性质的法条出现。软法常用于鼓励企业以更高标准引导行为,以实现更高立法目标,〔47〕例见《产品质量法》第6 条。至于企业能否做到,监管部门无法直接强制。因此,除非市场存在针对商品优劣或行为好坏的识别机制和产权保护机制,否则消费者会因缺乏足够信息和辨别能力而宁愿选择以最低价格标准来评价商品。这是法律实施过程中逆向选择的近似体现。当然,基于消费者的逆向选择,企业也可能认为,即便适用更高标准投入创新技术,生产高质量产品,也会因消费者逆向选择而无利可图。若此,则企业同样可能以逆向选择的心态看待法律实施,宁可适用低标准规范。
“当参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任何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或自选择条件,这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48〕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 页。换言之,在经济学视角下,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行方法。〔49〕See Michael C.Jensen and William H.Meckling,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1976), p.305-360.
激励机制抑制道德风险的作用是促进非标准化义务规则的适用。〔50〕与“非标准化义务规则”有所不同,针对那些易于标准化的义务规则,因义务主体是否依法行事有相对客观、细致的标准可以评价,因此惩罚机制有其充分的适用空间。当然,惩罚机制并非唯一选择,为节约法律公共实施成本,亦可同时构建激励机制,鼓励义务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义务规则。其原理是:促成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激励相容,通过利益给付、业绩分成、职务晋升或其他权益的赋予,促使义务主体(代理人)个人利益目标与立法机关、监管部门(委托人)监管目标一致,激励义务主体主动适用法律。“法律在制裁欺诈方面的作用并不局限于阻却欺诈或使违法者无计可施,而是可拓展到改变委托人对欺诈的认知偏见进而激发更多有效私人措施来应对欺诈。”〔51〕Amitai Aviram, Counter-Cyclical Enforcement of Corporate Law,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25 (Winter, 2008), p.1-33.一般情况下,此类激励机制可由私人构建,但若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存在协商成本高昂等情况,则激励机制需由公权力主体提供。〔52〕例如,为鼓励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履行勤勉义务,公司建立的股票期权、业绩分成等内部激励机制是私人构建的激励机制,而公司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则是立法构建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抑制逆向选择的作用主要是促进更高标准软法规范的实施。逆向选择根源是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无法区分行为优劣与产品好坏,无法确证依法行事是否于己有利。因此,构建激励机制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点:第一,完善信用公示制度、资质评价制度、行业声誉机制、产品质量评价制度、产品认证制度,以及第三方评估制度、鉴定制度、公证制度,使企业行为好坏可得到识别,使产品质量优劣可通过价格显示,使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可在执法、司法程序中及时得到区分处理。第二,降低公众知悉企业行为好坏与产品质量优劣等信息的成本。比如,由公共机构构建信息收集、核实和公示平台并以低廉价格(甚至免费)向公众开放。第三,通过经济奖励、荣誉褒奖、资格授予、资质提升、优先权享有等措施引导企业按更高标准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和履行法律义务,使其意识到按高标准履行法律义务有利可图。
四、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立法构造
(一)激励机制的公共供给
既然激励机制对法律实施是必要的,那么应由谁来构建激励机制?是私人主体还是公权力主体?在法律公共实施的情况下,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可否以及如何并存?提出上述疑问的意义在于,虽然如“激励与惩罚是辩证统一关系”等观点已是共识,但对于是否由公权力机关构建激励机制或有争议。事实上,立法层面也尚未系统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虽然“应当提供合适的激励以鼓励人们诉诸和执行法律”,〔53〕[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2 页。但归根结底,激励机制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公权力机关不必介入。其依据是,整体意义上的“法律”具有强制性,而惩罚机制是法律具备强制力的重要因素,公权力机关只需惩罚违法者,不必奖励守法者。认为公权力机关不必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观点其实颇值商榷。私人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固然为法律所允许,但无论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还是实证分析的角度,都不应否认公权力机关构建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一,不管私人实施还是公共实施,激励机制的构建都不妨碍惩罚机制的运作。惩罚机制无法解决法律实施的所有问题,激励机制可发挥互补功能。即便惩罚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场合,激励机制的加入也无碍于惩罚机制运作。〔54〕See Omri Ben-Shahar and Anu Bradford, Reversible Rewards, American Lawand Economics Review, Vol.15, No.1 (2012),p.156-86.实例可见《土地管理法》第3 条和第24 条,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激励机制,两者并行不悖。简言之,在法律实施问题上:应当惩罚不等于不必激励,两者不必然有冲突;惩罚低效暗示着需要激励,即两者可能共存互补;而无法惩罚则通常意味着应当激励,即特定情形下两者可能互相替代。
其二,在公共实施领域构建激励机制并不否定法律强制力,也不减损法律权威。法律固然是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规范,但并不意味只有惩罚机制才能体现法律本质特征。一方面,有必要从技术层面将公共实施语境下的激励机制理解为有效实现立法目的的手段。就此而言,激励与惩罚是一致的。〔55〕See Gordon Wendy J., Of Harms and Benefits: Torts, Restitu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1(1992), p.449-82.另一方面,不应从意识形态立场将公共实施语境下的激励理解为公权机关向有义务遵守法律的私人主体示弱。事实上,只要激励机制能够推动法律规则被遵守和适用,国家意志即已贯彻,立法目的也已实现,此时法律权威不仅未受减损,反而被有效强化。
其三,私人主体无法充分供应激励机制。“私人产权并非激励人们有效率使用资源的唯一社会制度。如果排他成本相当高,公共所有权解决办法可能也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56〕[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3 页。如激励机制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此时构建激励机制对私人主体是激励相容的,或者说,产权边界清晰且结果有利——私人主体当然有动力建立激励机制。但若涉及公共利益,私人主体一般不会主动构建激励机制,因为此情形下惩罚机制和激励机制都属公共物品,纯粹由私人负责构建和运作,会出现行动收益的正外部性无法内部化的结果。
其四,公权力机关构建激励机制耗费的公共资源有限。以往观点多认为,惩罚机制是保障法律实施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耗费公共资源构建惩罚机制无可厚非,但激励机制并非必需品,即便需要,也只能私人构建,这是节约公共开支的要求。事实上,激励机制并不必然耗费过多公共资源。激励有多种措施,不同措施代表不同成本结构。有的措施体现为立法机关通过调整法律规则,协助公众重构产权关系,促使行为外部性内部化。为此,公权力机关只是建立或修改规则,无需为公众适用法律作出额外支付。有的措施虽需向公众支付利益,但该等利益并非来源于国家财政等公共资源,而是来源于其他私人主体。〔57〕如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成本补偿制度、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度。
(二)激励机制的立法模式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公共供给的重要途径是立法构造。法律需依赖公共实施、〔58〕如行政机关适用行政处罚法处罚违法企业。准公共实施〔59〕如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或私人实施〔60〕如当事人依据合同法订立合同。等多种机制才能将立法目的转化为现实。无论何种实施机制,其本身不同程度上又都需要以立法为基础。通过立法制定法律实施规则、构造法律实施机制的目的是规范公权力行使,确保法律实施公正,以及统一法律实施程序和标准。尤需指出,即便是针对私人适用私法解决纠纷的情况,立法亦为其提供了诉讼、仲裁或调解的程序规则,以此确保相关实体法得以有序适用,而不是将其完全留给私人解决。
立法机关制定的旨在指引和规范法律实施的规则(本文称其为法律实施规则,以区别于作为实施对象的法律实体规则),是构成法律实施机制的重要基础。法律实施规则的立法形式至少有五:一是通过专门程序法设定法律实施程序;二是在同一部法律中同时规定实体规则和实施规则;三是由行政机关配置专门的法律实施条例;四是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其他司法文件规定法律实施问题;五是通过地方立法规定法律实施细则。法律实施规则的存在表明法律体系的不同规则之间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某些法律规则的功能实际上是为促进另一些规则的实施。换言之,法律规则是在立法设定的程序中得以实施。有研究者称此为“法律的自我实现”,即“法律体系本身具有的法律执行的制度和机制,不需要通过其他的规范性体系来执行法律。”〔61〕李波:《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比较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3 页。
为了细致分析法律实体规则与实施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必要考察各类法律实施规则的内容,研究法律实施规则如何构造实施机制、促进法律实体规则的有效实施。基于论述需要,下文提出显性路径与隐性路径两个概念。
显性路径是指通过立法直接、明确地规定法律实体规则实施的程序依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法律实施机制。从形式上看,制定专门的程序法、实施条例、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都属于显性路径范畴。从内容上看,通过显性路径规定法律实施规则、构造法律实施机制至少包括:(1)规定法律实施主体;〔62〕例见《商业银行法》第62 条。(2)规定法律实施对象;〔63〕例见《外商投资法》第2 条。(3)规定法律实施方法;〔64〕例见《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第28 条。(4)规定法律实施流程;〔65〕例见《土地管理法》第47 条。(5)规定法律实施期限;〔66〕例见《审计法》第40 条。(6)规定法律实施责任(包括责任减轻、豁免)与惩罚;〔67〕例见《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37 条。(7)规定对法律实施的鼓励、支持和奖励。〔68〕例见《疫苗管理法》第63 条。
隐性路径是指一些法律条文表面上以实体法形态呈现,但立法目的不只是界定权利义务,同时还可以引导、鼓励、支持,或者限制、约束其他实体法规则适用。例如,《公司法》第28 条规定,股东应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这种宽松的出资制度有利于鼓励大众创业,营造便利化营商环境。为了防止股东怠于履行实缴义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法》第199 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并处罚款。此条文旨在建立惩罚措施,迫使股东及时缴纳出资。但问题是,如果股东通过章程约定漫长出资缴纳期限,此时第199 条规定能否有效督促股东出资?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担忧。为解决此问题,《公司法》第34 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从表面上看,此条文规定的是股东分红权和新股优先认购权——按传统理论这是实体法问题——然而,如果将第34 条与第28 条联系起来则可看出,第34条实际上为第28条立法目的的实现提供了行为激励。换言之,第34条实质上也是一种法律实施规则,有助于促进第28 条的适用。据此,可将第34 条理解为“以实体法规则构造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一种隐性路径。通过隐性路径设定激励型法律实施规则的其他例子还包括:《民法典》第537 条构成《民法典》第535 条的实施规则;《证券法》第90 条构成《公司法》第103、104、105 条的实施规则;《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第28、47、52 条以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第2 条构成了《公司法》第46、49、53 条的实施规则,等等。整体而言,通过显性路径和隐性路径设定实体法规则的实施规则,是立法层面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方法。
五、激励法律实施的具体措施及其完善
(一)经济奖励、利益补偿与加倍赔偿
1.经济奖励
经济奖励主要适用于公权力机关希望公众主动作出某些行为、遵守某些法律或标准,但又无法强制他们如此作为的场景。比如,希望公众主动举报违法信息,或者希望企业在法定最低质量标准以上主动执行更高的推荐性标准,等等。经济奖励有助于推动法律实施的原理本身不难理解。例如,在市场监管过程中,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对维护市场秩序有重要意义。但是,“信息也是社会必须花费资源才能产生的一种物品”,〔69〕[美]史蒂芬·布雷耶:《规制及其改革》,李洪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6 页。传统监管措施以惩罚违法行为为主,如果仅仅依靠监管者自己发现违法行为,信息成本非常高昂。因为“信息总是具有公共产品的维度……在不受规制的市场中,此类信息总会存在一个供应不足”,〔70〕[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0-41 页。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违法信息提供者(尤其是内部人举报者)进行奖励。
从实践看,除了食品药品监管之外,其他领域似乎还未就举报违法的奖励问题形成一致做法并建立制度,即便有,相关规定也较为空泛。此外,有的监管部门虽认可奖励,但又将其狭义理解为荣誉表彰,不愿给予经济奖励。在涉及市场规制、社会规制的立法中,虽已有条文规定对举报违法事实且查证属实的主体进行奖励,但明确规定给予经济奖励的不多,细化规定奖励标准的更少。应该指出,荣誉表彰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对公众激励仍有不足。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往往面临安全风险,若无足够的经济激励,一般不会单纯为了一次荣誉表彰而去冒险举报违法行为。故此,公权力机关有必要规定,对举报违法经营行为且查证属实者,应给予奖励,且该等奖励应以经济奖励为主。更重要的是,构建奖励制度时,还应重视相关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对于监管部门未按规定予以奖励的,举报者有权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寻求救济。〔71〕近年来已经陆续出现了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后未获奖励而寻求法律救济的案例。参见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浙集复33〔2017〕18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2.利益补偿
利益补偿通常用于推动共益权规则的适用。提高共益权规则适用效率的要旨是克服集体行动悖论:一是以法律公共实施替代私人实施,由公权力机关承担法律适用成本,此时不存在私人成本补偿问题;二是使用私人实施机制,同时由公权力机关设定规则,凡主动适用共益权规则且给共益权人带来共同收益的,政府、集体或受益人应向行为人提供利益补偿,弥补其适用法律的成本或损失。
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第一种方法。比如,环境保护涉及社会公众共益权,但其专业性、复杂性和系统性都决定了这一工作的高成本性,私人难以胜任,因此由政府统一执法更有效率。在涉及企业、社会组织或私人共同利益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第二种方法,即由企业或组织代表成员维护集体利益,或者建立补偿规则激励个体成员代表企业或组织行使共益权。
不过,在不少情况下,企业或社会组织还是无法像政府维护公共利益那样有效实施共益权规则。股东派生诉讼就是例证。在公司利益遭到损害时,公司自身并不总是积极寻求权利救济,因为侵权者可能就是公司高管或实际控制人。此时要求小股东和侵权人协商一致并推动公司诉请侵权损害赔偿,无异于缘木求鱼。换言之,若小股东和公司管理者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昂,他们将无法轻易形成共识并实施共益权规则。对此,立法机关需要做的不是出台规则,强制要求全体成员达成共识,而是制定规则,让主动适用共益权规则且带来实效的小股东有权要求全体共益权人补偿其适用共益权规则的成本。这一原理在实践中已获初步关注。为了激励小股东依法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6 条规定,若派生诉讼胜诉,则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的合理费用。应强调的是,通过利益补偿激励相关主体主动实施共益权规则,不仅适用于公司法领域,在所有涉及共益权的领域,这一方法都具有可行性。〔72〕例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 条。
3.加倍赔偿
加倍赔偿在立法上通常表达为惩罚性赔偿。其与利益补偿的区别在于:一是前者以赔偿者过错为前提,后者的实际支付人往往无过错,其适用多是基于公平原则;二是后者主要用于激励共益权规则实施,前者多用于激励私益权规则的实施。整体上看,惩罚性赔偿既有加倍惩罚、从严威慑违法者的功能,也有激励权益受损人积极适用权利规则的作用。但作为激励机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仍有争议,尤其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知假买假”者能否诉请惩罚性赔偿看法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事实上,在经营者侵权行为仍大量存在,而消费者又普遍怠于寻求法律救济的背景下,从促进法律实施、推进市场共治的角度理解,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知假买假”者,其诉请惩罚性赔偿对提高法律实施效率都有激励作用。考量“知假买假”者能否获得惩罚性赔偿,不能仅从价值评判角度权衡,还需考虑法律适用技术操作问题。
立法规定和司法审判根据普通商品与食品、药品的分类来区分处理“知假买假”的思路〔73〕这种区分适用的根源,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普通商品的惩罚性赔偿需以经营者欺诈为前提,而《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对食品、药品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则无此要求。值得商榷。第一,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实效有待提升。一般消费者遭遇欺诈时,除非涉及高额消费或涉及生命健康,否则漫长的诉讼程序和不菲的诉讼成本会抑制其维权积极性。若完全排斥“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的市场治理功能会大打折扣。第二,区分“知假买假”和正常消费的信息成本很高且标准难统一。现实中,不少消费者有特殊消费习惯,法院把“一次性购买商品数量太多”推定为“知假买假”的论证并不充分;以“原告是否有‘知假买假’历史”断定案涉行为必是“知假买假”亦缺乏说服力——难道一个消费者曾经“知假买假”,从此哪怕他/她真正遭遇经营者欺诈,也将无权诉请惩罚性赔偿?第三,区分对待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者和商品的“知假买假”者可能导致判决说理冲突。因为法官支持食品、药品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说理与其他消费领域案件中法官驳回消费者诉请惩罚性赔偿的说理难以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74〕例如,在广受关注的“韩付坤诉青岛市李沧区多美好批发超市消费合同纠纷案”[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 民终263 号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支持原告惩罚性赔偿的主张,但值得追问的是,若将此案的判决理由放到其他领域的消费纠纷中,还能否成立?如果成立,那么其他领域的“知假买假”者也应得到惩罚性赔偿,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指导意见的规定;如果不能成立,那么在食品、药品的法律纠纷与普通商品服务的法律纠纷之间将会出现法律适用和判决说理的矛盾。
(二)荣誉褒奖、资质评定与信用公示
1.荣誉褒奖
法律实施语境下的荣誉褒奖是指通过公开表彰,或者通过树立典范、宣传事迹,增强法律主体的荣誉感,鼓励其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在多数情形下,荣誉奖励显然不止有精神层面的激励作用,对企业而言尤其如此。一方面,获得荣誉奖励是企业提升形象、增强商誉的重要途径,而商誉本身就是企业整体价值的构成元素之一。在企业合并等商事活动中,良好的商誉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估值。另一方面,荣誉奖励有助于企业在声誉机制中获得公众好评,进而取得竞争优势。
声誉机制是调整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发展的“非官方强制”,它“实施的惩罚方式包括消极评论和排斥,而他们对遵守规则者所提供的奖励则包括表示尊重的评价和提供更多交易机会”,〔75〕Robert C.Ellickson, Law and Economics Discovers Social Norm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7 (1998), p.537-552.而“商誉或生意受损的威胁促使大多数企业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品质控制体系”。〔76〕[美]罗伯特·A.卡根:《规制者与规制过程》,刘毅译,载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27 页。声誉机制可降低失信者未来利益的贴现率。如果企业为了当前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相当于将未来可预期的利益提前贴现,除非这种贴现利益不少于可预期利益,或者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排除声誉机制约束,否则理性商人不会忽视声誉塑造。在此意义上,有研究者认为:“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有时需要法律外的影响力约束人的行为,如市场力量、社会强制和社会共同体中声誉的损失。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对法律强制构成替代。”〔77〕Steven Shavell,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Law Enforcement,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36, No.1 (April 1993), p.255-288.
2.资质评定
资质评定是指公权力机关通过设定评价标准,对企业的资信状况、生产规模、经营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既往业绩、诚信记录等进行综合评估并评定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业务准入门槛或监管优惠措施,没有取得资质、资格的,不能从事该行业相应业务。很多行业的立法都规定了资质资格评价体系(典型例子是建筑行业)。
资质评定是监管部门实行市场规制的重要方式,而资质等级本身,则是企业据以开展业务的重要基础。以资质等级为规制工具至少可实现三方面功能:一是信号功能。不同企业被赋予不同资质等级,相当于将不同企业贴上不同标签,有助于公众或其他市场主体无成本获取企业资信状况、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信息。二是约束、威慑、惩戒功能。资格资质依法可授予,也可剥夺;可提升,也可降低。把降低甚至剥夺资格资质作为法律责任形态之一,可对企业形成约束、威慑和惩戒。三是正向激励功能。企业资格资质与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有关。获得资格资质意味着可从事某类经营业务;提升资格资质意味着可从事范围更广、类型更多、规模更大的经营业务。将资质评定与企业守法情况直接挂钩,以获取或提升资格资质作为激励措施,可促使企业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
3.信用公示
法律语境下,信用是指相关主体遵守法律和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78〕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 条对“社会信用”的定义。在市场活动中,公众或企业需根据其他主体的信用状况和行动记录制定应对策略,此过程的信息至关重要。但是,公众或企业需支付昂贵的搜索成本、传递成本、核实成本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为此,政府有必要为某些重要信息建立统一的收集、发布机制,将本属于私人物品的信息转变为公共物品。信用公示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机制,它是指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建立信息平台,集中记录、公布相关企业或个人履行合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以便他人随时查询。
信用公示的基本功能是帮助公众或企业准确了解交易相对方既往的行为记录。在信息传递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信用公示的惩罚功能。惩戒可能体现为公众或其他市场主体的非议和排斥。经由信用公示,违法违约的企业或个人会被他人知悉,进而丧失交易机会甚至退出市场。信用公示的惩戒也可能体现为法律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被信用公示机制负面评价的市场主体在从事某些市场交易或生产经营时可能被课以更重的准入成本。
信用公示也有激励功能。一方面,公示使信用良好者被显著识别,在市场中获得认可并取得更多的交易机会,这是公示的间接激励;另一方面,激励也可能直接来源于立法,〔79〕例见《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2 条。主要体现为在申请行政许可的过程中,诚信者可获得简化审批、优先办理或从宽监管的机会,也可能体现为为诚信者增加交易机会或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功能在立法层面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有完善空间。比如,因应于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国务院出台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随后各地普遍建立了异常经营名录制度。〔80〕参见《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17、18 条。作为失信惩罚措施,如果能再建立一个动态调整的诚信表彰名录,将诚信经营持续达到一定期限和标准的市场主体纳入诚信名录,以此作为减免其某些法定义务或赋予某些优先权的依据,相信会有更多的市场主体把进入诚信名录作为目标,以更高的标准引导自身行为。
(三)优先权奖励与权利行使保障
1.优先权奖励
法定意义上的优先权〔81〕优先权有法定优先权和约定优先权之分。本文讨论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建立的法律实施激励机制,主要聚焦法定优先权。是立法机关按照一定标准,在利益竞争者之间确立权益获取的先后顺序。权益通常属于有限资源,一旦确立获取的优先劣后,实质上也就确立了主体之间的竞争规则。优先权可以创设竞争的特点,使其具备激励法律实施的功能。现行法律体系已有不少涉及法定优先权的规则,其最终目标不仅是设定实体法意义上的优先权,而且不同程度上也承担着促进其他法律规则实施的任务。就此而言,作为激励措施的优先权奖励是指由公权力机关规定市场主体如果自觉依法行事,那么可在市场监管或市场交易过程中享有某些优先于他人的权利。优先权可能是实体的,也可能是程序的。前者是指市场主体在主张各种民事权益或申请各类行政许可(包括资格获取、资格认定、资质提升、经济补偿、财政补贴、荣誉称号等)时,优先获得清偿、支付或许可;后者是指市场主体在办理各类行政程序(包括企业行业准入、新设企业、股份公司证券首次公开发行等)时,优先获得推荐、受理,优先启动程序。〔82〕例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
与前述经济奖励等措施相比,在采用优先权奖励的场景下,公权力机关除了承担制度初始建构的成本外,几乎不必耗费其他成本。因为对行政机关来说,只要严格遵循审批依据、标准和程序,无论把权益授予A 还是授予B,无非都是行政程序的正常执行及其结果的自然呈现,他们需恪守的职责只是在市场主体中挑选出最符合法定许可标准或相对更优秀的主体即可。
此措施主要用于激励法律义务规则和责任规则的实施,特别是在需要鼓励适用更高法律标准,或适用标准本身难以量化的场景下,公权力机关首先可设定最低标准,规定如果市场主体无法达标将被追究责任,但若市场主体积极执行更高标准,则将获得优先权奖励。有研究指出:“规制者采取的执法策略应当是,一方面给声名不佳的违法者以威慑,另一方面鼓励善意的雇主自愿守法,并对行为水准高于合规要求的企业予以奖励。”〔83〕[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140 页。当然,即便对于那些可量化的标准,设定优先权奖励也有利无害,因为它在促使市场主体依法行事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监管部门的执法成本。
在少数情况下,优先权奖励还可能被用于激励权利规则的实施。如《民法典》第535 条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债权人可代位向次债务人主张债务偿还。需考虑的是,当并存多个债权人时,次债务人清偿款项究竟是先归属全体债权人共同所有,还是归属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所有,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在并存多个债权人时,代位权行使已转化为共益权行使问题。为了克服集体行动悖论,《民法典》第537 条采纳了“起诉者优先受偿”理论。此实例中需激励实施的是《民法典》第535 条的代位权规则——这显然是一项权利规则,而作为激励措施的则是《民法典》第537 条规定的“起诉者优先受偿权”。
2.权利行使保障
法律赋予的权利可能被行使,也可能被放弃。权利人不履行权利规则的原因有多种:或是因缺乏维权意识;或是因行权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或是因错过行权期限,权利被消灭。多数情况下,权利人放弃行使权利是法律允许且不必干预的问题,但是,也不全然如此。如果某项权利的行使后果涉及多数人利益,或某项权利带有一定程度的“职权”属性(如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管理公司的权利),那么权利人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权利,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此时,公权力机关有必要考虑如何激励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笔者把此类情况下形成的激励措施称为权利行使保障,它是指公权力机关规定专项保障措施,为权利人行使权利和实施法律规则提供成本代付、技术支持或风险抵御,使权利人更便捷地适用权利规则。
最直接的权利行使保障措施是权利行使费用的代付。如《公司法》第53 条规定监事会、监事有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高管人员执行公司职务行为等权利(职权),为了推动监事(会)积极行使监督权,确保其职权不受非法限制,《公司法》第54、56、118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监事行使职权所需费用由公司承担;如监事会或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企业破产清算环节也有类似问题。企业一旦进入破产清算,即需破产管理人管理、处分财产,清理债权债务。破产管理人的工作需耗费不菲的成本。而现实问题是,破产清算企业的财产通常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此时,如破产清算工作的必要支出无法实现,破产管理人将失去行使权利(职权)的动力。为此,《企业破产法》第43 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
(四)明晰产权关系与构建产权交易
1.明晰产权关系
法律规则涉及主体越多,则产权关系越复杂、法律实施障碍越多。以明晰产权关系激励法律实施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完整界定每项法律实施行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合理分配行为成本与收益,由此形成激励相容效应,使法律适用主体获得守法、适法的剩余索取权,实现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确保其对行为后果形成稳定预期。〔84〕See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No.2 (May.1967), p.347- 359.
产权激励方法适用于多种场景。如前文提到的共益权规则、边界不清的责任规则的实施,均属此列。在此领域,可资借鉴的实例是以产权激励方法推动“邻避”问题的法律实施。近年来,很多城市针对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制定了大量地方立法,但垃圾处理场地的设置仍经常遭遇公众抵制,即便住宅小区内垃圾收集点的设置,也常引发业主争议。问题根源是,决策者设置垃圾收集点或处理场地时,潜意识都将其当成居民(业主)应承担的法定容忍义务。事实上,在初始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情况下,决策者应从产权完整性角度,或从科斯侵权相对性原理角度,〔85〕See Ronald 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1960), p.1-44.充分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如果场地必须长期固定,应建立规则对所在地居民承受的容忍义务作出合理补偿;如果场地不必长期固定(如小区内),则可建立垃圾收集点,定期轮流设置等规则,使全体业主轮流享有权利、分担义务。
2.构建产权市场
在惩罚机制难以发挥实效的场合,促进法律实施的可行之道是“放弃命令控制进路,将市场作为解决方案,或适用基于市场的规制”,〔86〕[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33 页。如构建产权市场。“在原先产权不明显的地方创造出了可交换的产权”,〔87〕[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31 页。使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购买产权的方式扩大消费,或者通过出售产权增加收益,此策略隐含的逻辑是:最珍惜私有产权的是产权人(市场主体)自己,如果能够使立法目的与私人产权交易结果达到激励相容,那么市场主体会有主动实施法律的动力。
以产权激励措施促进法律实施的典型例子是排污权交易机制。“完全私有所有权的产权结构会产生出不同但却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88〕[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99 页。排污权交易是立法机关构建的,激励企业遵守环境法的制度,其要旨是:第一,使排污成本与收益归于企业,实现对企业激励相容,鼓励其主动减少排污。第二,治理成本较低的企业把剩余排污权高价出售给其他需求者,再将此收益用于成本较低的污染防控或治理,实现盈余;对于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其购买排污权的成本可能低于通过技术改造减少排污的成本。因此,排污权交易可为污染治理能力不同的企业提供共赢机会,实现污染治理的总成本最小化。第三,实际排污量受到诸多变量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排污权初始配置难以精确。排污权交易有助于排污权从剩余者转移至实际需求者,实现排污权合理配置。这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的体现。〔89〕除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外,在《环境保护法》第22、31 条还有其他激励措施的规定。
(五)法律责任的减轻、免除与替代承担
1.责任的减轻、免除
法律责任是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传统理论与实践把法律责任视为惩罚机制核心要素,认为其有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功能。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人们对奖励通常比对惩罚更容易产生反应,这样,规范也更容易得到贯彻实行。”〔90〕[德]托马斯·莱赛尔:《法社会学导论》,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201 页。
法律责任与法律规则的激励实施同样关系紧密。其一,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提是确认存在违法行为,但大多数违法行为的查明都会耗费高昂成本,公权力机关需要考虑如何更容易发现和查明违法行为。可行的激励机制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为对价,鼓励违法者主动披露自己或他人的违法信息,这种激励机制在违法行为更专业、违法信息更隐蔽的领域作用明显。其二,法律制裁是“为了惩罚违法行为,促使潜在违法者放弃其目的;而且只有在制裁足够强大、印象深刻,并在紧急时刻能得到实施的情况下,方能实现这一目的”。〔91〕[德]托马斯·莱赛尔:《法社会学导论》,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203 页。但问题是,很多制裁都是事后的,无法在事前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因此,在行为人即将实施或已着手实施违法行为时,公权力机关需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违法行为实施完毕后如何惩罚,而是建立激励机制鼓励行为人尽早放弃违法意图,或尽早终止违法行为,或在行为实施完毕后及时抑制损害后果。特别是当违法行为损害后果严重、纠错成本巨大时,事前激励更具现实意义。其三,在有些情况下,监管部门将减轻甚至免除责任规定为激励措施,目的是鼓励当事人尽快解决纠纷。在另一些情况下,其目标甚至不只是鼓励被监管者主动停止违法行为或消除损害后果,而是期望以此鼓励被监管者事先建立合规体系或风控制度,更早防范违法行为。
2.责任的替代承担
法律责任会带来不利后果,因此,相关主体可能怠于履行法律规则、消极行使权利,意在避免因违法而担责。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责任替代承担的激励机制,即通过法定或约定建立机制,规定相关主体在从事某些正当行为、行使相关权利(职权)过程中如因过失或其他不可预测的原因而造成损害后果,那么本应由其承担的责任可由其他主体代为承担。责任替代承担制度的功能是鼓励那些工作职责繁重、行权风险较大的主体敢于决策和作出行为。
最常见的实例是公司高管责任保险制度。为了解决公司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各国立法都会对董事设定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此问题的根源是传统公司法理论强调的委托代理问题〔92〕See Michael C.Jensen and William H.Meckling,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1976), p.305-360; Eugene F.Fama and Michael C.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6, No.2(June 1983), p.301-325.),以促使董事忠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积极而谨慎地从事经营行为。解决勤勉义务履行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给董事提供经济利益激励,包括报酬、业绩奖金及股票期权等。勤勉义务规则可能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司经营本身富含商业风险,而公司法又为这种义务规定了责任规则和惩罚措施,因此有的董事在商业机会面前可能会选择不作为。这表明,勤勉义务规则及相关惩罚机制仅有约束作用而无激励功能,惩罚机制虽有助于防止董事违反勤勉义务,但也可能迫使董事做出逆向选择。
有两种方法可解决董事的不作为问题。一是沿用传统惩罚机制,规定如公司出现违法情形或者公司利益遭受损失,则首先推定董事未尽勤勉义务,除非董事能够证明其已勤勉尽责,否则将被追究责任。〔93〕参见《证券法》第78、85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31、51 条,《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36 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第25-30 条等规定。二是建立激励机制。立法可规定如果董事已履行勤勉义务,即便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受损,仍可减免责任;〔94〕参见美国法律研究院(ALI)的《公司治理原则》第4.01 条。也可通过市场机制减轻董事责任,或由其他主体代替董事承担责任。董事责任费用补偿制度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典型例子。〔95〕参见中国证监会出台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3、24 条;《美国标准公司法》§ 8.51-8.57 的规定。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保险公司建立的责任保险制度已不局限于董事,〔96〕参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第3、8 条之规定。而是已经涵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呈现扩大适用趋势。
六、结语
本文试图论证,在法律实施问题上,以往理论与实践所高度依赖的惩罚机制有其固有缺陷,动辄主张“加强监管措施、提高惩罚力度”对于强化法律实施效果、有效实现立法目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未必管用。为了克服惩罚机制在共益权规则、私益权规则、义务规则、监管规则和责任规则实施过程中的功能局限,应当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促使法律实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以及改变法律私人实施的效用函数为目标,系统构建法律实施的激励机制。
结合近年来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已制定的一些激励措施,本文阐述了从制度层面激励法律实施的具体对策。应指出的是,此类实例整体数量仍然较少,且其本身也有缺陷需要修正,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已经构建了完善的法律实施激励机制,但可作为今后构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经验指引。
法律实施的激励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抽象论题,更是实践层面需要系统构建、实际运作和持续改进的操作机制。无论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无论实体法领域还是程序法领域、无论国内法领域还是国际法领域,几乎所有法律规则都面临如何提高实施效率以及如何充分实现立法目的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法律实施激励机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持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