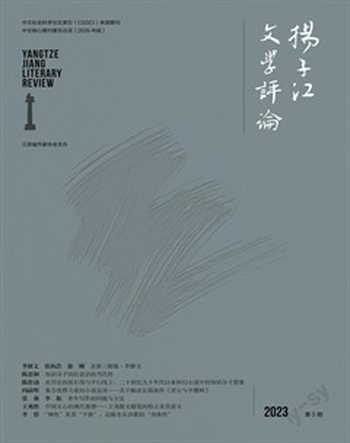“神性”及其“下移”:论陈东东诗歌的“身体性”?
李蓉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陈东东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诗歌除了新奇诡谲的语言、飞扬充盈的想象力、强烈的音乐节奏感,同时还洋溢着“一种从容、自如、优美、飘逸的诗歌感性”a,而这种“感性”也是现代诗歌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笔者注意到,相对于其他诗人,他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身体性”。如果仅仅摘取他诗歌中那些描写“身体”的词语,很容易产生误解,将其诗歌“身体性”的艺术方式作一般世俗性的考量。对一个在语言上有高度自觉特别是在诗歌观念上有成熟认知的诗人而言,“身体性”这样的语言现象也必须放置在其创作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辨认,才会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陈东东的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不断探索之中,从早期的“纯诗”写作,到后来具有神话、魔幻色彩的写作等,促成其诗歌形成和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诗歌潮流都对其产生了影响,而陈东东同时也是一个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浓厚兴趣的诗人,他诗歌的“身体性”与上述因素都存在着联系,这些因素最后都综合、转化为他的写作观念和语言方式,基于此,本文将综合这些因素考察陈东东诗歌不同时期的“身体性”表达,探讨它们对于当代新诗的价值。
一、“希腊梦”:神性的身体
陈东东的诗歌写作始于1980年代初,那是一个刚刚复苏的年代,当时,西方诗歌是一种全新的刺激,陈东东说他写诗最初是受到了惠特曼《草叶集》、特别是希腊现代诗人埃利蒂斯的影响。b惠特曼和埃利蒂斯的诗歌中充满了自然的欢唱和生命的原欲,埃利蒂斯深谙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精髓,他说:“梦,自动的写作,潜意识的解放,全能的想象,不受美学和伦理的拘束,所有这些使得他能够以实际生活中全部的神圣乐趣,同时以真正的诗之瞬间的浑身‘震颤,来描绘世界的美景。”c这也正应和了以布勒东为代表的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观念,他们强调写作的感官和非理性色彩。
陈东东1980年代的诗歌,尤其是他的那些长诗、组诗,充满着一个欢腾的“希腊梦”。在宏伟阔大的视野下,通过华美的语言、典雅的音韵,诗人将具有地中海气息的自然风物尽揽笔下,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满了感官声色的气息。就如埃利蒂斯在爱琴海的大自然中,找到了一种与精神对应的神秘存在,并将感官提升到神性的境界一样,陈东东也展示了以海洋为图景的原初生命景观,在这些昂扬而明亮的诗句中,诗人表达了一种具有神性的精神向往。这一时期陈东东的诗歌是冥想性、赞颂性的,爱琴海的清澈、纯净,也正是诗人诗歌语言的品质:“我清凉的冥想如水中之水”(《夏之书》),“我们用声音构筑的庭院里,有圣洁,泉眼/有按梦境塑造的纯粹之母”(《再获之光》)。
圣琼·佩斯也是陈东东喜爱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中谈到圣琼·佩斯的作品时说: “他的诗在内容上是无法把捉的。与颂歌体或者赞歌体类似的长诗句如同宇宙之流一样向读者泼洒,诗歌的技巧和热情都让人想起沃尔特 ·惠特曼。他自己把他的诗句比作海的浪涛。庄重鸣响的呼求驰掠而过,紧随其后带出的总是新的图像,后者既激起又扰乱了读者的幻想。它们中没有一个图像能抵达宁静。灵魂与世界的万有在浪沫飞溅的运动中翻滚起伏。这是一种陌生的万有,是一种‘流亡的宇宙。如果其中包含了现实,那现实就是一种未知的、特殊的现实,来自充满异邦情趣的国土、消失不见的文化、奇异少见的神话。”d弗里德里希的这一描述也同样适合形容陈东东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波浪般起伏的语言、乌托邦化的“特殊的现實”,都是陈东东创造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奇迹。
西方古老的海洋文化构成了陈东东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素材,《明净的部分》《夏之书》《再获之光》等都建构了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幻想之地,通过铺排的语言,诗歌力图抵达一个明净、清澈、静谧、神圣的世界,在这里,现实和神话、历史和幻想、自然和超自然交融为一体,如“这歌中之歌/这透彻的光 明净的部分/她的短笛 要永久吹奏 永久吹奏”(《明净的部分》),“歌中之歌”类似于马拉美所说的“终极之书”,而歌咏性、赞美性的基调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质是吻合的,“透彻”“明亮”“纯洁”“永恒”“无限”等词在诗中不断出现。诗人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想象世界,“最”字的出现频率很高,如“最平静的 最初的和/最单纯的”“最为纯洁的”“最素净的”“这也是真正的寂静之地 是永恒的晴天”(《夏之书》)。
“抽象性”是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追求,“纯诗”理论认为:“在纯粹的著作里,诗人的陈述消失,并通过被调动起的不均等的碰撞,把创造让给词语,它们就像宝石上的一条潜在的光尾用闪光的彼此照亮,取代具有古老抒情气息的可感知的呼吸,或者是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e“纯诗”追求声音的音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暗示效果。和很多中国当代诗人不同,陈东东的诗歌并不追求意义,他将诗歌的音乐性看得高于一切:“事实上我很难说清楚我在诗篇里到底想说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我的诗篇即使是清晰的、透彻的,却也很少有那种明确的主题意旨,我只想传达出我的节奏。”f这也正和臧棣对他早期诗歌“优美地专注于本文的快感”的评价一致:“他的诗歌是本文的本文,洋溢着一种漂亮的、华美的、新奇的,将幻想性与装饰性融于一体的,执着于本文表层的语言的光泽,犹如汉语诗歌的巴黎时装。”g也就是说,陈东东是个极其看重语言和形式对于诗歌自身价值的诗人。
因此,陈东东诗歌中令人目不暇接的意象(包括身体意象)主要是符号性、装饰性的,并没有明确的所指,词语在平面性地无限延展之中,不向深处拓进,也就回避了意义,正如弗里德里希对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的评价:“它是一种运动:朝向存在的运动,脱离混乱走向明朗的运动,脱离不安走向安宁的运动。光,作为存在毫无瑕疵的显像,是它的顶峰值;最能持有光的诗歌也是形式上最精确的诗歌。”h陈东东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有节奏的语言“运动”。他常使用意象并置和铺排的方法,并称之为“意象思维”:“诗的结构不是建筑式的,而是编织式的,由各种意象交错穿插的碎花大地毯。”i这颇似马拉美的“阿拉伯花纹”j,因此,他诗歌中的身体意象如裸体、子宫、乳房、嘴唇、腹部、腰肢等是和植物、动物、风景等一体的语像群,声音所形成的效果才是诗人的追求。“诗歌纯粹性的前提是去实物化”“在与或低于或高于传达功能的语言力量的游戏中,形成了具有强制性的、与意义无涉的音调,这音调为诗句赋予了魔术咒语般的力量”k,这样的观念来自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诗学。“身体”在陈东东的诗歌中除了显示一种原始性、赞颂性之外,也推动了语言的运动,构成了诗歌的节奏:
同样的女子从走廊到卧室
被神命名的躯体
镜子里的短发和早餐音乐
她醒在敞开的窗户之间
朝向神的窗户,也朝向春天和圣洁
——《春天:场景与独白》l
那赤裸的女朋友要再一次吹奏
当蝉音揭示 又一个夏天
我翻看一首 雨的赞美诗 在一扇窗下
——《明净的部分》m
处女们在岸上低声歌唱
弹奏光滑的玻璃足踝
她们像被我放牧的星辰 腰肢柔韧
小腹温馨 在甜蜜之中将凤蝶吸引
她们如纯洁而浩大的水 浑圆的双乳使百鸟
聚集 金属的黎明 新鲜的嗓音
每天我接触 太阳和赤裸的血肉一点
——《夏之书》n
这些诗的特点是声音大于意义,若实在要说意义,只能透过“神”“赞美诗”“星辰”和“黎明”这些相似的詞语去理解,而当“身体”在这样的氛围中被书写,它就具有一切新生事物的品质,带着人类原初的“善”和“美”,散发着纯净、芬芳的气息。在陈东东的诗里,“开花的乳房”(《春天:场景与独白)、“那赤裸的少女 微收起小腹”(《明净的部分》)这样的词句很常见。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绘画艺术中,裸体艺术包含着对人的理解:“在裸体中,躯体自然地包裹着存有全体,既无缺陷亦无裂痕,也没有断裂:裸体以其自然包含着‘灵魂。”o在陈东东的诗歌里,“裸体”并非欲望性的,它们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存在。
正是以这种整体上扬的风格为基调,诗人才坦然地使用“形而下”的词语。陈东东的诗歌将一切拉回到文明的源头,人类以最自然的方式对待身体:“双腿之间的生殖之花”(《夏之书》),“一滴精液注入无数个爱的夜晚”(《八月之诗》),“肉和肥皂的香味”(《春天:场景与独白》),“每一副性器官”(《A·R·阿蒙斯》),“在生殖之鱼和冥想之鹰的清凉之地”(《夏之书》)。和远古文明的生殖崇拜相对应,“身体”在这里主要是繁衍性、生产性的,是生命生生不息的保证,诗人赋予了“身体”健康、明朗、纯净的乌托邦色彩。
在西方诗歌发展中,对女性及其身体形象的艺术创造始自荷马史诗、但丁《神曲》以来的传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诗人都热衷于创造代表人类精神理想的女性身体形象。《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雅歌》中就有对女性身体的赞美;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写圣母“那子宫就是我们‘欲望的归宿”p,对母性和繁殖的书写包含着一种原始的返乡冲动;在美国现代诗人惠特曼的诗歌中,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都充满了生命的能量,而无论女性抑或男性,他们的身体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我说不单止外貌和脑子,整个形体更值得歌吟。/而且,与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q;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也将女性身体放在诗歌艺术的中心,马拉美在《牧神的午后》中书写的是唯美的充满梦幻感的女性身体,而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异域的芳香》《她的衣衫……》《舞蛇》《腐尸》《首饰》等诗中女性身体充满着沉迷肉欲的颓废气息,这是肉体之“恶”与“美”的矛盾纠缠,如“她的手臂和小腿,大腿和腰肢,/油一样光滑,天鹅般婀娜苗条,/在我透彻宁静的眼睛前晃动;/她的肚子和乳房,一串串葡萄”(《首饰》)r。
法国超现实主义也酷爱“梦”和潜意识,它和后期象征主义有直接的承接关系。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曾被瓦雷里诗歌中的“粉腻的趣味”所吸引:“每次我手头有了他的一首诗的时候,我却怎么也参不透其中的神秘和弄不清其中的骚乱。这种神秘和骚乱沿着梦幻和平滑的坡面心悦诚服而又带着爱欲地流淌。”他引用了瓦雷里的《安娜》一诗来说明这种感受:“安娜裹着与其肌肤相混的洁白被单, / 将秀发摊在惺忪微开 的美目前, / 目注她一双懒洋洋的玉臂/放在她裸露的腹 部带着微微的狐弯。”s这首诗正如布勒东说的那样充满感官的愉悦,可以看到,瓦雷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已经和古典的身体书写传统迥然不同,当有了“床单”这样私密的意象,具有“色情”意味的紧张感就产生了。
这样的特点在超现实主义诗歌中有更充分的表现,帕斯说:“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色情自由是想象力和激情的同义词。”t超现实主义诗歌相信直觉和原始欲望,认为“梦”和潜意识能真实地反映世界,对非理性的强调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和破坏的冲动,“色情”即是这一心理的语言演绎。陈东东说:“希腊更是被命名为海伦的绝对女人体,当对它的爱终于化为劫掠,新诗歌的阴茎在黑暗中插入,希腊色情伟大的身姿要激发神奇的勇毅去冲刺,改变英雄的智力、史诗和被安排的命运,甚至令一个帝国在失败中诞生并确立。”u从这样的话语方式中可以看到陈东东受超现实主义诗歌影响之深,诗人将“身体”和“性”置于英雄的伟业之中,并认为是它们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这显然也有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从一开始陈东东对“身体”和“性”的表达就有隐喻的特征,“身体”成为他特有的一种言说方式,与诗人的语言自觉是一体的。
臧棣在评价陈东东的诗歌时指出:“法国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无论诗歌还是绘画,色情意蕴都是其理解、描绘世界的主要的编码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的主要构成部分。”v迷恋肉欲感官的超现实主义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诗人来说,主要是完成了一种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启蒙。赞美性、肯定性、启示性是西方诗歌传统对待女性身体的基本态度,与此相统一,陈东东早期诗歌中的“身体”是抽象的、赞颂性的,并无世俗化的色彩,这也与他早期诗歌整体的超越性是一致的。
二、“身体”与古典的借用
陈东东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不仅散发着浓郁的地中海气息,中国古典诗歌对他的影响也同时存在,而无论是“西化的”还是 “古典的”,都呈现出空灵的、超现实的风格。作为一个南方诗人,陈东东对汉魏六朝及晚唐的诗歌有所偏爱,他的一些短诗有着李商隐、杜牧、李贺、温庭筠、晏殊、吴文英等南方诗人的气质。他在1980年代曾写过一些以古典诗人为题材的诗作,《买回一本有关六朝文人的书》写到嵇康和左思,《黑衣》写到了杜牧、李贺,此外还有《涉江及其他》《更早的诗人们》《途中读古诗》《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等。他解释说:“是庞德和罗伯特·布莱提醒我去重读古诗的。这种回头重读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它令我意识到我所崇尚的诗歌精神和信仰有着一个怎样的源头。”w陈东东看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艺术在西方现代诗歌中的回响,因此他也通过对古典诗歌的重读来启发并锻造自己的诗艺。
陈东东早期具有南方气质的诗歌充满了纯净、唯美的色彩,并无多少现代生活的气息。柏桦说陈东东的诗歌具有废名似的禅意x,这也并不奇怪,陈东东曾接触过佛教,甚至有在少林寺长住的经历,1980年代的很多诗歌都留下了这段生活的印记,如诗歌中常出现的僧人、寺院、麋鹿、晨钟暮鼓等意象,而这一时期的诗歌空灵而跳跃的想象也呼应着寺院宁静而充满冥想的生活:
夜营的角声吹破,降下了第一场寒霜。
寺僧在井口屏息谛听,
汲水的辘轱嘎然停转。
——两轮明月间,盛满黑暗的
木桶空悬。
——《秋歌二十七首》y
对于古典传统,陈东东并非亦步亦趋,在《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中他写道:“我们也必须有刀一样的想法/在载酒亭/苏轼的诗句已不再有效/我独坐,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睛/看山高月小。”当现代的经验介入古人书写过的自然中,对古典诗意的沉浸就会被打断,如这首《黄昏》:
黄昏能安宁到怎样的程度?倾斜的河滩
入夜的風
几块供人坐卧的石头
和一只羽毛丰盛的
鸟。他的茅舍就这样建成,一面窗对山
一面窗能看到初月上升
安宁,它的门前是石头的牧场
几匹马悠闲
看上去像几棵秋天的树
安宁,他想起那时候他在城里
另一个黄昏
汽车从他的身边擦过z
大自然的各种事物通过诗人的感觉被组织在一起,这样的画面有着宁静、悠远的禅意,是所有受过古典诗歌熏陶的诗人面对自然时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感受。然而,诗人的思绪却在古今之间发生了跨越,由眼前的景物突然想起“另一个黄昏/汽车从他的身边擦过”,这是在超越性中突然降临的现实感,它使人联想到废名的《街头》:“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这是由“寂寞”产生的无尽联想,它虽有古典的禅意,但与古典诗歌对自然的依赖迥然不同:现代意象的加入,疏离而非融合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赋予了现代诗歌不同于古典的气质。
中国现代诗人往往能在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的相似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陈东东同有绮丽之风的何其芳说:“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7而陈东东则提出“禅的超现实主义”@8,表明他和现代诗人一样试图融合东西方诗歌在思维和表现方式上的相通之处。超现实主义重视“梦”和“想象”,这与“禅宗”的“坐悟”是相通的,它们都注重想象空间的营造,“越来越膨胀的梦之飞艇掠过了人类/他走到旷野里。他仰面看星斗/大月亮涌出生命和万有”(《传记》)。
如果说中国古典的“禅意”追求人和自然相融中的虚空之美,那么超现实主义诗歌对感官的重视传递给予陈东东的就不是对肉身的抵制而是接纳。1990年代,可以看到诗人“禅的超现实主义”的写作,他对生命的领悟都是在具体的肉身中展开的,而其最终的指向仍然是精神的超越,他的《秋歌二十七首》(1991)这样写道:
翻山见到满月的文法家即兴歌咏:
在鹰翅之下,沟渠贯穿白净平野,
冷光从牛栏直到树冠;
长河流尽,崇山带雪,
明镜映现的娇好容颜由发辫环绕。
长河流尽,崇山带雪。
秋气托举着群星和宁静。
紫鹿苑深处的讲经堂上,
朱砂、环佩、明辨之灯把女弟子照亮。
他翻山而至,头顶着满月,
手中的大丽菊暗含夜露。
他站在拱廊前即兴歌咏:生命解体;
爱正醒悟;火光之中能被人认清的
难道是幸福?
肉身之美在紫鹿苑中,
被一个文法家以词语编织。
肉身之美在诗歌的灯下,
远离开秋天,被音节把握。
莲花之眼。红宝石之唇。
讲经堂上,一部典籍论述万有,
另一部典籍证明了起源。
应和的女弟子舞蹈的脚镯,
一轮满月横贯裸体。
白净平野间物质倾斜。文法家翻山
把精神启示。丰乳。美臀。
三叠细浪的秋天的小腹。
中立无害的茸毛之中有神的笔触。@9
这是一首“领悟之诗”,仍然延续了1980年代诗人空灵、唯美、具有启示性的风格,对自然的描写显示着一种纯净、宽阔、盛大的气象。诗中的“文法家”“讲经堂”“典籍”“莲花”“女弟子”都是宗教性用语,而穿插其中的则是一些女性身体意象,如发辫、朱砂、环佩、夜露、脚镯、裸体、丰乳、美臀、小腹等,自然、宗教、女性身体这三组意象的交织构成了一种超越性的情境和氛围。整首诗落脚在“神的笔触”,诗中的“身体”是具象的,更是抽象的,“肉身之美”中充溢着神性,而赋予“肉身”这种神性的是“诗歌之灯”,“肉身”成为连接此岸和彼岸的桥梁。
与其他当代诗人对中国古代一流的大诗人的兴趣不同,陈东东偏爱诗风华丽秾艳、非主流的古代诗人,这里面有文化地理和个人性情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语言、修饰上的。诗人柏桦这样评价陈东东:“每当我读到‘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吴文英《莺啼序》),或‘素秋不解随船去,败红趁一叶寒涛(吴文英《惜黄花慢》)这些诗句时,我就会立刻想到诗人陈东东。他写下的《梳妆镜》、《幽香》、《导游图》等许多诗篇简直就是吴文英(文英为宁波鄞县人,此点特别指出)的手笔。”#0柏桦注意到的是陈东东的诗歌对传统继承的一面,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审美情调和语言方式。但实际上,用现代的方式和传统对话,才是陈东东长期以来的写作诉求。他说:“现代汉诗在处理它跟古老中国的传统文明和古典诗歌的传统之美的关系时,无论如何都会将其自我和自主性放在首位,就像它在处理跟域外文明及其诗歌的关系时,总是将其自我和自主性放在首位。”#1即诗人对中西方诗歌的继承不是被动的,而是从写作自身出发主动选择的,这也成为陈东东处理传统资源时的一种自觉态度。
陈东东早期的诗歌场景主要是以地中海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空间,或是以寺庙禅院为代表的宗教性场所,诗人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十分活跃,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身体”具有超越的神性意味。1990年代以后,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陈东东笔下出现了具有东方气质的“幽闭”的私人空间,这说明他对古典的化用所形成的诗歌风格也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南方诗人,陈东东对南方特有的颓废、享乐、逍遥的文化气息有着天然的偏爱,而艳情诗、宫体诗也是南朝诗歌的一大特点,陈东东喜欢的一些古代南方诗人几乎都写过艳情诗和宫体诗,在他的诗中,也常可见“宫体”一词。艳情诗和宫体诗因为诗格不高,在诗歌史中向来遭到贬低和轻视,而它们之所以受到陈东东的重视,除了其同为南方人性情上的相通之外,更重要的相合之处是感性化的语言方式。陈东东的《幽隐街的玉树后庭花》(2003)一诗显然就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应,其名取自宫体诗《玉树后庭花》。该诗的作者陈叔宝是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一个亡国之君,传说陈灭亡的时候,陈后主正在宫中玩乐,其诗如下: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此诗用华丽的辞藻赞美女性的情态之美,而正是对欲望的沉溺,导致了生命的幻灭感,整首诗在颓废、虚无的情绪中收束,被称作“亡国之音”。中国古代的艳情诗、宫体诗包括后来的花间词等,通常极少直接写“性”,南朝的艳情诗、宫体诗主要是描写女性的容貌、体态和服饰,带有男性眼光的凝视。“浮艳的文风与香艳的内容有着天然的联系,追求文辞的艳丽必然导致情调上的哀艳,最终,以妖艳的女性为中心的闺房世界便成为艳诗所铺陈的主要对象”#2,对女性的物化和文人贪恋声色之欢的空虚和颓废互为表里,而由于诗教的传统,一些古诗也会在“艳情”之外补上必要的道德训诫,如李商隐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感观的身体诱惑和道德的警示兼而有之。
中西方有不同的人體艺术传统,对裸体的重视奠定了西方艺术的基础,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近现代的西方艺术,描绘裸体是非常普遍的艺术现象,而中国艺术却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从中西哲学的差异出发,考察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绘画里的裸体,并分析了中国艺术里没有裸体形象的原因。他认为,古希腊艺术中的裸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近代西方的裸体艺术则是解剖学、有机体意义上的,而裸体之所以具有美感,是由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所确立的,裸体是“美的观念”的最为理想的范型,“只有由裸体之中才会形成典范(canon);而为了制作合乎标准、甚至可作为典范的裸体所需摆的固定姿态,乃是美之分析及整合的感知所要求的”#3,也就是说,在西方,裸体的形式符合理性分析的原则。与西方对身体的本体性认知不同,中国文化对身体的理解则是以“气”“神”来统摄的,它将“身体”作为“过程”来看待,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极少西式的具有形式和审美意义的“裸体”,“身体”更具有世俗的性质,表现在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中,则是常常通过身体的姿态、衣服的褶皱、饰物等来传达一种情色意味。
陈东东的《幽隐街的玉树后庭花》这首诗很明显借用了古题,它表面上似乎与古典的“艳情”有关,但其内容和语言方式全然不同于古诗。这首诗写的是一次都市夜生活中的“猎艳”,或者说是一次欲望的实验。虽然诗中有大量情色的场景和细节,但因为诗人将其放置在繁复的语言修辞之中,时而显露、时而隐晦,故显得扑朔迷离,因而这也是一次语言的“猎艳”。“化学实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烧瓶”等科学术语的引入与欲望的“实验”并置,同时,诗中还引入了时下的战争新闻,严肃的话题与“色情游戏”之间充满了一种悖谬的气息,再加上旁观者的视角以及调侃、反讽的语调,使得该诗虽包含着一些与“色情”相关的细节和场景,却又有着一种明显的间离效果,和古典艳情诗的沉溺全然不同。
姜涛认为:“在陈东东这里,语言的幽闭则与一种南方文人的享乐主义气息相连。在超级情色之诗《幽隐街的玉树后庭花》中,那种曲尽其妙又苦苦沉溺的情调,被发挥到了极致,诸多感官被诗人既云卷云舒,又古奥生涩的句法拖曳着,混入一个细颈的烧瓶,剧烈地化合出无穷。但在语言放纵的背后,暗藏的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种文人纤细的矜持感,二者相互勾兑,终于使得那‘反应不至于更化学了。”#4陈东东的这一类诗歌到底是否就是古典南方文人艳情诗的翻版,还需要细究。如果从隐喻的层面来看,陈东东诗歌中的“情色”明显具有双关的性质,“情色”和“写作”在陈东东在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同构的文本,诗人是以“情色”的方式探讨着写作和语言的问题,“身体”因而成了一种修饰方式、表达方式。
现代汉语的“元诗”写作是张枣等诗人提出的,而将“身体”用于“元诗”写作,用“身体”的方式揭示写作的秘密,陈东东是发明者。他的《形式主义者爱箫》(1992)一诗,文本表层的“吹奏”“双腿”“竹床”“涨潮”“乳房”等词语似乎都具有“性”的指向:“形式主义者爱箫的长度/对可能的音乐/并不倾心……优美的双腿盘上竹床/涨潮的乳房/配合吹奏”,但该诗显然是以此隐喻诗歌的创作活动,“赤裸的女性的吹奏”在诗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吹奏”正如诗人所说“仿佛是为梦而梦”,很显然,这也是1980年代“纯诗”观念的延续。
陈东东新世纪的诗歌继续从古典的“艳情”传统中寻找“现代”的可能,《梳妆镜》《何夕》《幽香》等诗都与“艳情”的传统有关。然而,正是作为逝去的传统的旁观者(一个现代人),面对消费性的现实,在掂量现实与古典的距离中,他与现实的关系也进一步清晰起来。在《梳妆镜》(2001)中,对感官声色的怀旧描写中有诗人对欲望、梦幻和时间的思索:
在古玩店
在古玩店
手摇唱机演绎奈何天
镂花窗框里,杜丽娘隐约
像印度香弥散,像春宫
褪色,屏风下幽媾
滞销音乐被恋旧的耳朵
消费了又一趟;老货
黯然,却终于
在偏僻小镇的乌木柜台里
梦见了世界中心之色情
“那不过是时光舞曲正
倒转……”是时光舞曲
不慎打碎了变奏之镜
鸡翅木匣,却自动弹出
梳妆镜一面
梳妆镜一面
映照三生石异形易容
把世纪翻作数码新世纪
盗版柳梦梅玩真些儿个
从依稀影像间,辨不清
自己是怎样的游魂
辨不清此刻是否
当年——
在古玩店
在古玩店:胶木唱片
换一副嘴脸;梳妆镜一面
映照错拂弦回看的青眼#5
“镜子”是当代诗人普遍偏爱的意象,镜像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虚幻易碎,陈东东在《过海》中写道:“你看见你就要跌入/镜花缘,下决心死在/最为虚空的人间现实。” 这首诗回应了好友张枣的《镜中》一诗。而在《梳妆镜》这首诗中,诗人抚今追昔,进一步表达了“镜花水月”之空幻。古董唱机放着“游园惊梦”,对应的是古旧的故事和时间。在全球化的时代,带有怀旧意味的“情色”也是褪色的,但人类对于它的喜好却不会褪色,只是因为快餐式的文化使它变得更不可得。从“偏僻小镇”到“世界中心”,传说中的故事继续在被消费,满足着人们对情色的想象。该诗就像电影蒙太奇,“梳妆镜”将过去和现在交叠在一起,但它映照的过去却是变形的,“缘定三生”自是空幻,物是人非,数码播放器播放的不再是胶片时代的声音,但它却让人有恍惚的时空错乱之感。
该诗中的“错拂弦”来自一段典故。唐朝李端有一首《听筝》的诗:“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其中,“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来自《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周瑜精通音乐,弹筝的人为了博得他的青睐,故意把曲弹错,以引起他的注意。陈东东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意在表达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错位,而“梳妆镜”所映照的一切之所以是“错”,是因为时光不在,古典的传奇在当下只能是被消费的命运。可以看到,在古今交错、意识恍惚之间,现代人的身体感知已不属于自己。
总之,陈东东对古典传统的继承,禅意的空灵是一种,艳情则是另一种。然而,禅与超现实主义、艳情与色情都显示了诗人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努力,古典中的虚空冥想和感官享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在陈东东这里,它们在语言层面是统一的,对传统的缅怀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反观现代的视角,它最终落脚于诗歌的感性修辞以及超越性的想象,而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为诗人提供了一种写作的可能。
三、都市、“色情”与上海经验
随着理想主义的瓦解,陈东东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发生了一些新变。相对于过去诗歌的纯净高蹈,陈东东1990年代之后的诗歌多了一些现实元素和题材。他不再单纯追求声音的华丽流畅,语言的陌生化更加突出,戏剧场景,反讽、戏谑的诗歌手法,拼贴、游戏的语言方式等改变了以往纯粹的抒情风格。他写道:“音乐之光收敛尽净/如今唯有/长途旅行者/猎艳在梦中”。(《新诗话》)当代以政治话语、消费话语为主导的时代语境带给诗人新的体验,当诗人将其经验以一种更具现代感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对身体的书写也降低了唯美色彩而更具反讽意义。当诗人从早期的本质主义、理想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解构主义,“身体”的易逝性、碎片性就呈现出来,下面是陈东东诗歌中的几个“身体书写”片段:
当我的中指,滑过了那道/剖腹产疤痕,她恣意扭动……语言是诗,是裸露的器官,没戴/保险套
——《解禁书》
保险公司姑娘/敞开了明亮阳光的胸……它桃子般的表皮有色情的细毛……什么样的乳房开出了花朵/一瓣嘴唇,被水鸟柔弱的羽翼轻拭/她的腰款送
——《插曲》
手之工蜂滑过小腹去采撷花和蜜……沦陷之夜射向本宫的黏稠/兴奋剂令本宫瘫软得起不了身”,“坐过来,拥吻孤,孤喜欢你/曾经是一部分汽车的身体。
——《傀儡们》
“身体”在这些诗句里明显具有隐喻和反讽的特征,集中呈现了1990年代以后文化语境下的个体欲望。当但丁笔下的“永恒之女性贝特丽采”变成了“风韵被稀释的电梯女司机”(《解禁书》),“身体”已失去了崇高感,它不再是圣洁、纯净的符号,也不再具有典雅的美感,颓废和宣泄是身体的日常状态,戏谑、狂欢的语言释放出摧毁、破坏的快乐。因此,1990年代以后,“神性”的“下移”是陈东东诗歌中一种新的现象,并且,相对于早期诗歌的纯净,一种恶魔性、反讽性的语言在他的诗中出现。他的《恶魔的诗歌》充满了波德莱尔式的颓废和反叛:“在上海一幢由臆想构筑的/骷髅之塔中/狐媚的发辫又加长一寸/谁的手推开了彩绘玻璃窗。”陈东东显然接受了波德莱尔“审丑”的现代传统,在对现代文明的书写中,波德莱尔《恶之花》首开以“丑”写“美”的先河:“那时,我的美人啊,告诉那些蛆,/接吻似地把您啃噬:/你的爱虽已解体,但我却记住/其形式和神圣本质!”#6
在消费文化中,欲望无处不在,而“色欲”则是其突出的体现。在陈东东的诗歌中,时常可看到“色情”一词,由于它具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当诗人频繁地使用它,一定出自某种自觉。相对于“艳情”“情色”的古典性质,“色情”则是一个在西方当代哲学中具有文化分析功能的概念,阐释它的哲学家代表是巴塔耶。他极力赞扬萨德的“排泄性”,认为人类文明即世俗世界是通过否定人的兽性而建立的,而“色情”是对功利的物质文明的否定,巴塔耶称之为“神圣的兽性”,“色情是性,但不仅仅是性,是被改造的性和被改造的‘自然,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7,巴塔耶之所以认为色情和原始宗教的献祭一样也具有神圣性,是因为其非功利的“耗费”性质。“宗教”和“色情”对世俗世界的超越位于不同的两端,“神圣形式二元性,是社会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这些形式必须分布在对立的两个阶层之中,即纯洁的事物和污秽的事物之中”#8。恰好这两种不同的“神圣”,在陈东东的诗里都能找到踪迹,如果说早期的“明净之诗”具有宗教的神圣性,那么按照巴塔耶的观点,1990年代以后陳东东诗歌对“色情”的书写就具有了另一种神圣性,只是它以反叛、破坏的方式出现,偏离了优美和崇高的古典美学范畴。
帕斯回顾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时说:“他们将爱视为对社会约束的侵犯,并且不把女性当作色情的客体而是也当作色情的主体来赞美。”#9“色情”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当它成为一种话语方式,就具有极强的反讽功能,陈东东的《纯洁性》(199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书写了“色情”:
一架推土机催开花朵
正当火车上坡
挑衅滂沱大雨的春天
我在你蝴蝶图谱的空白处
书写:纯洁性
我在你纹刺着大海的小腹上
书写:纯洁性
色情和盐
当窗外大雨滂沱
一架推土机弯下了腰
我在你失眠的眼睑上
书写:纯洁性
纯洁性
火车正靠向你素馨的床沿$0
这首诗充满了对色情禁忌的嘲弄和反讽,“推土机催开花朵”“火车上坡”“我在你蝴蝶图谱的空白处/书写”“我在你纹刺着大海的小腹上/书写”“靠向你素馨的床沿”等诗句都与“色情”相关,诗人一边写“性”,一边重复着“纯洁性”,身体节奏和语言节奏统一在一起。诗人叛逆地将被现代文明视为禁忌的“色情”视作“纯洁”,似乎一个“魔咒”可以由此而解除。诗人将“色情”和“盐”并置意图明显,“色情”是人类文明压制下的产物,和“盐”一样也是文明的必需品,“滂沱大雨的春天”暗示着生命本能的昌盛,这种将“身体”的反叛性置入诗歌当中的写法在陈东东的诗歌中时常可见。再如《影像志》一诗,诗人以当代中国的电影放映场景为题材,将电影放映的历史事件和观看者的私人生活细节交叠在一起,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反讽和消解。
有意思的是,巴塔耶也是诗人,在诗学立场上,巴塔耶对逻辑语言、日常语言是不信任的,这也导致了其无比晦涩的语言风格,特别是他还将一些粗俗的词语引入诗歌,反叛性从形式贯穿到思想,它们都是“色情”得以存在的土壤。巴塔耶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之间有着很深的过隙,而陈东东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减少了早期超现实主义诗歌所包含的浪漫色彩,诗歌在语言风格上显得更加奇险诡谲,游戏和反讽的意味更加浓厚,这主要体现在他1990年代以后书写上海经验的诗歌中。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与很多中国诗人对乡土中国的“乡愁”不同,被称为“魔都”的“上海”作为现代化都市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它有繁荣、进步、现代的一面,也有物欲、喧嚣、实用的一面,陈东东对它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如果说他早期的诗歌主要是一种“远游的诗”——远离上海、朝向希腊文明,那么他1990年代以后的大量诗歌却回到了这座城市。“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牵引上海迷雾的夜/海关大楼迟疑着钟点/指针刺杀的寂静滴下了/钱币和雨/一声汽笛放宽江面”(《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我在街巷里迷失了我,想不起自己/究竟何物。十一月的上海更向往光荣/最后的塔尖上,夏天以阳光的方式/残存,一群雨燕更照耀人类”(《十一月》),“谁爱这死亡浇铸的剑/谁就在上海的失眠症深处”(《我在上海的失眠症深处》),这些诗句呈现了诗人对上海复杂的心理感受,有怀念和渴望,也有失望和无奈。
20世纪文学对都市生活迷恋的书写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兴盛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它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文学,呈现了物质化、感官化的现代都市风景。“新感觉派”笔下充满身体魅惑的“上海”是符号化的、表象化的,折射出新兴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普遍对都市既迷恋又恐惧的心态。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陈东东的诗歌对上海的书写更具有了包容性和普遍性,他将现实的上海和经验中的上海进行了区分,并将这种经验进行抽象和转换。他说:“这第二个上海才是我乐于亲近的上海,亲近的方式也几乎是肉体的,譬如在某个午后骑车上街去寻访旧踪、捕捉梦影、论证一次幻想的真实性。或许上海真的仅跟我的肉体有关,从肉体生长出来的精神跟上海已经没什么关系,我的语言、构成我诗篇的语言(它跟我平时所操的上海话也有着类似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也是与上海无关的。”$1虽然各种都市意象穿插在他的诗歌中,但都市没有成为一种符号和限制,诗人写都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明一种文化立场,而是可以自由地驰骋想象,陈东东的“上海诗”呈现的都市经验都因经过了艺术的转换和变形而变得抽象,这显然仍受益于超现实主义诗歌。
可以看到,陈东东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虽然有了现实元素,但“现实”在他的诗中仍然被抽象为了神话、幻想和梦境,“诗歌写作是诗人的一门手艺,是他的诗歌生涯切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大于诗人实际生存的寄儿之梦。诗人通过写作创造一件飞翔之物,一个梦,一首诗;而写作本身是有根的,是清醒的,这门手艺只能来自我们的现实。作为一个出发点,即使是一种必须被否决的世俗生活,也仍然至关重要,不容忽视和逃逸。诗人唯有一种命运,其写作的命运包含在他的尘世命运之中。那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写作由于对生活的放逐而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诗歌。诗歌毕竟是技艺的产物,而不关心生活的技艺并不存在”$2。经过超现实主义诗歌洗礼的诗人,他感兴趣的不会是绝对客观的现实,而多年的写作表明,陈东东是一个善于将客观经验经过语言变形转换为主观经验的诗人。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先驱,相对来说更具有海洋文化而不是内陆文化的特点,因而“海”不仅仅是这座城市的自然背景,也是它的文化背景,大海及其有关的自然景物激发了诗人无尽的诗意和想象。如果说陈东东早期诗歌中的“海”主要以希腊化的地中海为原型,1990年代以后的“海”逐渐成为诗人理想中的“上海”的化身,因而“海”的意象也大量出现在他的诗歌中。同时,通过用典,诗人也大量借助了与“海”有关的西方文学资源。在《海神的一夜》 (1992)中,诗人写道:
这正是他们尽欢的一夜
海神蓝色的裸体被裹在
港口的雾中
在霧中,一艘船驰向月亮
马蹄踏碎了青瓦
正好是这样一夜,海神的马尾
拂掠,一支三叉戟不慎遗失
他们能听到
屋顶上一片汽笛翻滚
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
当他们起身,唱着歌
掀开那床不眠的毛毯
雨雾仍装饰黎明的港口
海神,骑着马,想找回泄露他
夜生活无度的钢三叉戟$3
在希腊神话中,手执钢三叉戟的海神波塞冬,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安菲特里忒及其他的一些女性之间有许多香艳的故事。该诗以这一希腊神话为题材,神奇的想象、感官化的语言延续了诗人198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风格,“马蹄踏碎了青瓦”明显又是古典的韵味,中西杂糅,声色俱在。诗人仍然以“身体”的方式来施展想象,“肉体要更深地埋进对方”“掀开那床不眠的毛毯”,而“港口”“船”“汽笛”等城市的景物融进了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情色之欢”中,诗人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来去自如。可以看到,诗人将上海经验抽象化、审美化了,并不具有地域性诗歌通常以特定的自然风貌、人文风俗为书写对象的特点。
在對当代都市风景的书写中,陈东东善于通过想象和融入神话的方式将都市景观“身体化”,史蒂文斯曾说,“大地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个身体”$4,在陈东东的诗中,一个静止的“水泥森林”世界因为“身体”的跃动而得以表现。在《时代广场》(1998)中,“玻璃钢女神”这样的“人造物”正是高度现代化的都市的象征,诗人写道:
甚至夜晚也保持锃亮
晦暗是偶尔的时间裂缝
是时间裂缝里稍稍渗漏的
一丝厌倦,一丝微风
不足以清醒一个一跃
入海的猎艳者。他的对象是
锃亮的反面,短暂的雨,黝黑的
背部,有一横晒不到的娇人
白迹,像时间裂缝的肉体形态
或干脆称之为肉体时态
她差点被吹乱的发型之燕翼
几乎拂掠了历史和传奇$5
在整首诗的结构中,“时间的裂缝”和“玻璃钢”构成了一种张力,在密不透风的“玻璃钢”世界,只有在“时间的裂缝”中才会出现“一跃入海的猎艳者”,这个“猎艳者”显然不属于都市的时间,他拥有一种反叛和超越的姿态,即他的对象是“锃亮的反面”,诗人将这一抽象的思想诉诸一个具体可感的女性身体形象,因为“海”的存在,她只能是一个矫健的泳者,她跳跃、遨游的身姿全然不同于凝固的“玻璃钢女神”,因其属于“时间的裂缝”,诗人称其为“肉体时态”,“身体”于是从形式和表象的世界进入了时间:“她差点被吹乱的发型之燕翼/几乎拂掠了历史和传奇”,相对于“玻璃钢女神的燕式发型/被一队翅膀依次拂掠”,显然,前者主动,后者被动,也就是说,只有在主动创造中才能创造历史和传奇,这是“玻璃钢女神”所代表的机械、静止的世界所不具有的。
总之,“身体性”是陈东东诗歌中突出的语言现象,但陈东东诗歌中的“身体”并不具有个人经验性特征,无论表达题材出现怎样的变化,陈东东诗歌的“身体性”主要是在诗歌观念和语言方式的意义上呈现的,它一方面与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都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在释放诗人的想象力、构造新诗的现代品质上发挥着作用,同时,在文化的意义上,“身体”在陈东东的诗歌中也发挥了反讽的功能。
【注释】
ag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见王家新、孙文波编选:《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205页。
bflmnwy@9$1陈东东:《明净的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 225-226页、 237页、147页、 91页、 184页、227页、 166页、153-154页、228页。
c转引自[希腊]塞菲里斯、埃利蒂斯:《英雄挽歌》,李野光译, 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dhk[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188页、175页、123页。
e[法]马拉美:《白色的睡莲》,葛雷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i陈东东、木朵:《诗跟内心生活的水平同等高》,《诗选刊》2003年第10期。
j[法]雅克·郎西埃:《马拉美:塞壬的政治》,曹丹红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o#3[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裸体》,张婉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148页。
p[意]但丁:《神曲:天堂篇》,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
q[美]惠特曼:《草叶集》(上),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r[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s[法]安德烈·布勒东:《象征主义的最后圣火——安德烈·布勒东访谈录》,见[法]瓦雷里:《瓦雷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t#9[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扩充版),陈东飙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57页。
u陈东东:《词的变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0页。
v臧棣等:《打开禁地的方式——读陈东东的〈解禁书〉》,参见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314页。
x#0柏桦:《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演春与种梨:柏桦诗文集1979-2009》,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210页。
z陈东东:《黄昏》,《即景与杂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7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8陈东东、余弦:《二十四个书面问答》,《明净的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1陈东东:《大陆的鲁宾逊》,《我们时代的诗人》,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205页。
#2康正果:《风骚与艳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4姜涛:《“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见张桃洲、孙晓娅主编:《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5$0$3$5陈东东:《海神的一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239页、164页、163页、207-208页。
#6[法]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腐尸》,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7汪民安:《乔治·巴塔耶的神圣世界》,《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8[法]乔治·巴塔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胡继华译,见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2陈东东:《诗的写作》,《只言片语来自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67-168页。
$4[美]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飚、张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