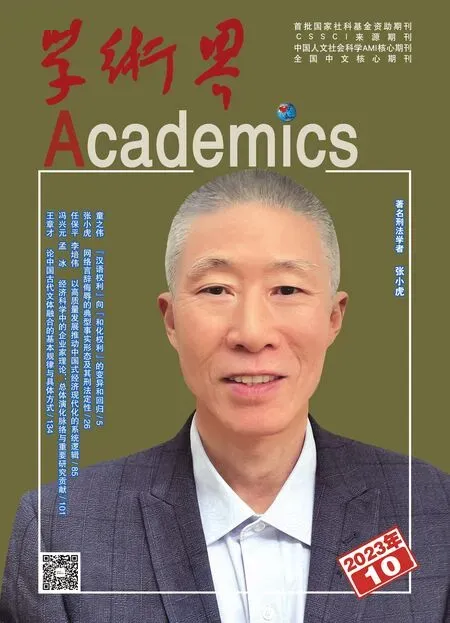近代俄(苏)在东北亚路港系统的衰变〔*〕
牛淑贞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受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尤其是日俄(苏)两国以经济活动主体的形式参与东北近代交通建设,使该区域的交通建设与交通运输问题与东北亚地区复杂的政治问题裹挟在了一起,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运输事业“不但为中国之关系,抑有国际之关系也”。〔1〕美国人雷麦称:“满洲外人投资的基础,不是通商口岸,而是铁路让与权。”〔2〕20世纪以来,“满洲之地,早已成为远东问题之焦点,日俄二国各以铁路为基本,竞扶植势力于满洲”,而中国则处于日俄(苏)两大势力之间。〔3〕因此,“东三省之运输事业不但为中国之关系,抑有国际之关系也”。〔4〕中日俄(苏)三国为了竞夺东北北部的腹地,努力为各自所控铁路—港口系统(以下简称路港系统)构筑可以深入东北北部的给养线。其中尤以日俄(苏)间的竞夺最为激烈,它们“施其灵活手腕,各走极端竞争,培养或修筑路线以图吸收货物,而便运输营业之发展焉”。〔5〕
目前,学界对近代东北地区的铁路、港口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从政治史、外交史等视角对俄(苏)、日等列强以及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铁路政策、铁路斗争及港口历史进行研究;〔6〕其二,从区域交通史、社会经济史及城市史、港口史等视角对铁路、港口的建设及其影响进行分析;〔7〕其三,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对铁路、港口在东北地区现代化空间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等内容进行探析。〔8〕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对日俄(苏)乃至中国路港系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竞争有所关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历史地理视角的研究对东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探讨,是以东北南部为核心展开的,导致其对三国竞夺的“主战场”——东北北部的关注不足,对三国所控路港系统对东北北部腹地的竞争状况及其影响的观照自然也不够,它们的“互动”对近代东北北部经济地理格局形塑的意义也无从感知;其他视角的研究,往往仅关注日俄(苏)之间或中日之间在某一时段就某一铁路的竞争状况,缺乏对三国路港系统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系统观照,失之粗疏、片断,而且大多没有把铁路与港口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考察。就俄(苏)的路港系统而言,日俄战后,它为什么会不断衰变?其衰变的历程是怎样的?中日路港系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俄(苏)为了保护其路港系统在东北北部的腹地作了哪些努力?既有研究成果难以清晰呈现近代俄(苏)所控路港系统衰变的复杂的过程脉络及其原因,当然也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东路—海参崴港系统的形成及俄(苏)为其构筑给养线的努力
近代俄国地处欧洲东北及亚洲的北部,其海军西不能出大西洋,南不能出印度洋,受制于英国。对俄国来说,破解之道只有经营远东以出太平洋。咸丰十年(1860),它利用《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沿海的地方后,“乃经营海参崴,建为军港,拟筑西伯利亚大铁道以联络之”。〔9〕自该军港建立后,俄国在远东的海军根据地遂由僻处北方的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移至海参崴,“俄在太平洋之海权,于是确立”。〔10〕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线本拟由西伯利亚东绕黑龙江左岸,即阿穆尔铁路,以接连乌苏里铁路,但是,自后贝加尔湖至哈巴罗夫克中间地势险要,招工集料十分困难,如果南下斜贯中国内陆以接乌苏里铁路,不但施工较易,且可节省五六百兆卢布费用,缩短548公里路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国通过《中俄密约》攫得了中东铁路的敷设权。〔11〕其干路,“西自江省之满洲里起,与西伯利亚及后贝加尔铁路衔接,东向至吉林之绥芬河,与乌苏里铁道枝线自双城子(今俄国乌苏里斯克)西来衔接”。〔12〕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又北接中东路干路的哈尔滨站,南至旅顺口、大连湾,修筑了支线。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中东路全线开通。〔13〕
在中国境内修中东铁路,且使其成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是俄国侵华、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重大战略部署。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称:俄国“必须用种种方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己手,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穿过满洲到海参崴的干线握在手中”。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以最短的线路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中国东北、黄海海岸及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会大大增加俄国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威信和影响;从经济方面来看,修筑该铁路,则海参崴会成为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俄国由此“就能在满洲及毗连满洲的中国省份坚固地站稳”。在修筑中东铁路干线以后,“短期间自然会由该线建筑支线到中国内地,并将促进后者与俄国间经济的密切接近”。〔14〕他还认为,西伯利亚铁路是广义的国家企业,沟通了欧洲与东亚以至太平洋,使欧洲与东亚间的交通条件发生了很大转变,它替俄国商业乃至世界商业开辟了新途径与新眼界。西伯利亚铁路能经过海参崴而参与太平洋上的经济斗争。在欧洲与东亚的商业贸易发展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俄国作为与东亚国家最接近的最大生产者与最大消费者,它要凭借西伯利亚铁路,成为西欧与东亚间的商业中介人,“在欧洲一切国家之前占着重要的优势”。〔15〕
尽管西伯利亚铁路为远东交通孔道,“若无东铁为之衔接,殊无以收指臂之效”。〔16〕俄国修筑中东铁路干线的目的,就是要将吉林省北部、黑龙江省全部的出入口货物以及西伯利亚的货物网罗于海参崴。但是,其南部支线(哈尔滨—大连)建成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位于南部支线南端的大连,常年不冻,且与中国其他沿海港口的距离较海参崴近许多,更便于“控制中国海及太平洋”。因此,南部支线修成后,中东路的出海口,“渐有疏远海参崴而惟大连是赖”,但其东干线仍由海参崴出入。〔17〕因此,从中东路开通到日俄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即俄国占据中国东北的全盛时期,它并没有全力营建海参崴港,而是全力建设大连港。至1903年,中东铁路公司已为大连港口、城市建设以及购置轮船投资近4000万卢布。〔18〕俄国对大连港—中东路系统的构建,因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夭折。战后,它将南部支线中长春以南的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两港割让给了日本,转而加强海参崴港的建设,“日俄在东省遂成对峙之势”,〔19〕尤以满铁与中东路在商业上的竞争最为激烈。〔20〕
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后,其势力不断向东北北部扩张。对俄国来说,海参崴在商务上为东亚贸易的吞吐口,在国防上为太平洋海军的根据地。它深恐由哈尔滨至海参崴的路线一旦为敌所断,海参崴将陷于孤危,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海参崴的经营,以保证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21〕海参崴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端,为俄国在东方唯一的大军港,以及在日本海上的重要商港。俄国自西伯利亚东来,若沿黑龙江、乌苏里江而至海参崴,则路远且不便,而通过中东路到海参崴,可缩短一半距离。因此,无论俄国国内政体如何,“此种利害关系,始终不变者也”。〔22〕
中东路南部支线修通后,就俄国而言,如果说大连港对海参崴港腹地范围的影响属于初步显现的“内部矛盾”的话,那么,日俄战后其对海参崴港的影响则是激烈的“敌我矛盾”。战后,俄国为了增强中东路—海参崴港的集货能力,以保证其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除了为中东路构筑给养铁路线外,还以中东路为根本,实行海参崴集中主义,阻止东北北部货物南运大连港。〔23〕俄国调整铁路运价吸引东北北部商货东行海参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为中东路构筑给养线的努力,却因中国与日本的反对等原因而收效甚微。以下试举几例以观察之。
1915年,洮南五路敷设权落入日本手中,俄国“援利益均沾之例起而攫北路之路权”,筹划在东北北部修筑滨黑(哈尔滨—黑河)与吉海(吉林—海林)两条铁路。滨黑路长约922公里,它以中东路的对青山站为起点,经呼兰、绥化、海伦折至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横贯墨尔根,沿黑龙江岸绕至巴彦,直趋齐齐哈尔,再由齐齐哈尔展至瑷珲,以达黑河与对岸俄境的阿穆尔铁路接轨。“呼、绥、海、巴系江省之绝大平原,江省之富源皆出于此,倘此线落成,则北满之命脉直落于俄人之掌握矣”。〔24〕滨黑铁路所经之地为东北北部的富庶之区,俄国人勘测时就拟将东北北部的名城巨镇尽划入该路线范围内,以掌握东北北部的命脉。美、日、法、俄都想借款给中国合筑此路,均被中国政府拒绝。〔25〕俄国之所以最终能够获得其建筑权,与袁世凯恐俄国反对其复辟帝制有关。该路名为借款自办,实则用人、购料一切大权全操控在俄国手中。受俄国十月革命等因素影响,该路一直未能修建。1918年,有传言俄国欲以滨黑铁路的敷设权作抵押,期限88年,向日本借款5000万。一方面,当时正处于俄国内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为战事所累,遂亦无暇及此矣”;〔26〕另一方面,因吉林当局和东北民众反对等原因,日俄瓜分滨黑路修筑权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27〕至1925年,苏联再次修筑滨黑等铁路的计划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吉海路全长约346~461公里,它以中东路海林站为起点,经宁安、额穆(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镇),沿额穆索斯河流域直达吉垣。其时因日本马上要动工修筑吉会铁路,“故俄国之筑此路,实急不容缓者也”。〔28〕修筑该路最大的军事意义在于使俄国驻远东的“海陆军可呼吸一气”,而中国军队却被该线截断。〔29〕
对中国来说,任由俄国在东北北部修筑这两条铁路,不仅该区域的经济权全被俄国操纵,就连军事上也“将为俄人驰骋”,“实不啻以北满全境奉献于俄人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自行修筑这两条铁路,但是,路线与长度有所变化。中国决定第一线以哈尔滨华界松花江对岸的马家船口为起点,先筑至海伦,即呼海铁路。因第二线双线(齐齐哈尔—瑷珲、锦县—齐齐哈尔)并修,需费浩大,筹款艰难,于是,东北地方政府致电中央政府,请求以东三省矿产作抵押贷款修建。对日本来说,俄国拟修的第二条铁路会与其拟修的吉会路线相冲突。最终,俄国因日本反对而计划改修齐瑷铁路(齐齐哈尔—瑷珲),与滨黑路相接。〔30〕
1925年,苏联为了抵制日本即将建成的洮齐铁路(洮南—齐齐哈尔)把东北北部农产吸收到南满铁路输出,再次筹划修筑滨黑等铁路。〔31〕它拟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至大黑河修筑一横断黑龙江的铁路(即滨黑铁路之一段),若该路修成,则黑龙江省丰富的特产均必由中东路搬运,“满铁虽包修洮齐,必无大宗特产可供满铁之吸收”。〔32〕因修筑该路需时费工,缓不济急,“惟有吸收蒙产由东铁运至嵗埠出口”为唯一的补救办法。苏联吸收蒙古地区特产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仅1925年1—8月,原由张家口经天津出口的蒙古皮毛改由中东路运至崴埠出口的约有3.28万吨。〔33〕1927年,中东铁路局决定投资2500万为中东路修三条支线:其一由乌珠河的一面坡间经同宾、方正两大特产区而达吉林依兰道的三姓,其二由其西线的安达站至拜泉县,其三由西线的满沟站到肇东县。它修筑这三条铁路的目的有两个:“一则近来日人要求满蒙五路之声浪日高”,为了与满蒙五路相抗衡,抑制黑齐(黑河—齐齐哈尔)与齐昂(齐齐哈尔—昂昂溪)路,进而使南满铁路的营业受到影响;一则截断中国洮昂铁路的货运,并吸收松花江流域的农产和木材。〔34〕
总之,日俄战后,俄(苏)筹议修筑的铁路多因中日两国的反对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革命的爆发等原因未能得到修建。截至1931年,由苏联所控铁路,除了中东路干线及南部支线外,仅有哈尔滨总站至道里江沿的4.27公里铁路及10多条运煤、运木材的专用铁路。〔35〕可见,它为中东路构筑给养线的努力“并无若何进展”。它虽建了札兰诺尔、穆棱两处运煤铁道及兴安岭的一面坡、鲁喀少窝、牙不力、横道河子等运输木材的轻便铁道,能够给中东铁路以“若干之给养”,但是,“皆无关于宏旨,尚未与吉黑二省若何之变化”。〔36〕
如表1所示,九一八事变前中东路的给养线共有16条,其中第1条为中东路南线,第6—16条为俄国所建运煤炭与木材的轻便铁路,第2—5条为中国所建,但第2条由日本人控制。

表1 中东铁路的给养线
该表所列齐克与洮昂两铁路原本可以为中东路提供给养,但因东北北部农产经齐克、洮昂路南运大连较经中东路西线至哈尔滨再南运大连节省运费,从而对其西线腹地造成很大切分。仅1930—1931年,其西线发运粮食被该路分流掉96万吨。〔37〕而中国自建的呼海铁路因与中东路实行联运,而变成其营养线。〔38〕
表1所列中东路干线的给养线近1700公里,其中尤以中东路南线对其贡献最大。但是,这条铁路与南满铁路相连,由它聚集的商货既可经中东路东线运往海参崴港,又可经南满路南运大连港,因此它既是中东路的给养线,也是南满路的给养线,日俄必然会围绕该路的货运展开激烈的争夺。
二、松花江与中东铁路联运对其给养线不足缺陷的弥补
东北北部的诸多河流,尤其是松花江与中东路实行联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给养线不足的缺陷。东北北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与中东铁路同为东北北部的交通大动脉。其中松花江贯穿黑吉二省腹地,自河口至哈尔滨可行大汽船,自哈尔滨至长春可行小汽船,“其航运效力在中东铁路以上,且水运较陆运低廉”。〔39〕
早在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8—1899)俄国修筑中东路时,“因运输材料、转运工人及供给工人食物等需要,就在渤海湾及辽河、黑龙江、松花江等处经营海上及内河运输事业,使这些水路运输衔接起来”。〔40〕松花江沿岸各地所产粮食向来“运至哈埠方分散于国内外”,“经济商业均赖以活动”。〔41〕东北北部的水运交通以哈尔滨为中心,沿松花江主航线及其支流,上游通吉林、齐齐哈尔,下游达三姓、佳木斯、富锦,进而利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通往布拉戈维申斯克、尼科里斯克、饶河、虎林、兴凯湖等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东北北部的航路已达4427公里。涨水期能够航行超过1000吨的轮船,表明水运在该区域交通经济中已占很重要的地位。〔42〕
松花江水路与中东铁路“相需为用,并行不悖,而成水陆两路与地方联络之形”。〔43〕在东北北部地区可先将货物由船运至哈尔滨,再经中东路运往海参崴港。松花江、黑龙江、嫩江等水路每年可运往中东路七八十万吨货物。〔44〕如吉林—陶赖昭间航路与哈尔滨—长春间铁路相连,由陶赖昭至松花江的同名埠头修筑了8公里的铁道运送客货。1910年,该航路所运货物达32万余吨。由哈尔滨至伯都讷查姆斯的航路在哈尔滨与中东路相连。1910年,其所运货物10万余吨。〔45〕
汇集在哈尔滨的大豆等农产,也可以经松花江、黑龙江两江水路直接运往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庙街等地,再经乌苏里铁路运往海参崴出口。通过这种水陆联运的方式,不但可避免哈埠商货南运大连港,且可不经中东铁路。由中东路至崴埠每吨运费2078.8科贝克(俄币名),自哈埠至松花江中段某点再至崴埠每吨运费为1643.5科贝克。这435.3科贝克运费的节省可以增加该路的出口量。哈埠有的出口商则将大豆由水路运至庙街换船装运至海外,“虽阿穆尔江口水量颇浅,但恒有船自丹麦来接载此项货品”。还有一路,即用帆船自哈巴洛斯克出发,上溯乌苏里江而达伊曼(今俄国达列涅列钦斯克),再装火车经258里铁路运至海参崴,“唯伊曼缺乏货栈码头等设置,不甚便利耳”。〔46〕这些路线尽管不经过中东路,但对俄(苏)与日本争夺东北北部腹地却是有利的。
1929年前,中东路在东北的腹地为黑龙江全省及吉林省北部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中东路的给养铁路线较少,但是,中东路是东北地区最长的铁路,也是东北北部铁路交通的重心,以及区域水运与铁路运输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短板,减缓了其路港系统衰变的速度。1933年,尽管满铁接收了哈尔滨与黑河的数座河运码头,但是,因这些码头与日本所控各铁路缺乏联系,苏联方面仍尽量利用本国所控铁路向海参崴运输货物,阻止哈尔滨货物南下,尽量避免这些码头与满铁干线联络。日本为了与此相对抗,于1934年5月在拉滨线(拉法—哈尔滨)的终点新建了三棵树码头,由此在哈尔滨建起了能够与日控铁路联络的码头。但是,1935年伪满购取中东铁路后,该码头的利用价值就降低了。〔47〕
三、俄(苏)所控路港系统的衰变
日俄战后,“日本得乘间插足于满洲之地,经营商业不遗余力,见俄人获得北满路权也,亦筑南满铁路。矿山也、森林也、豆也、麦也、盐也、茶也,一切商业上之大利,无一不思与俄人分享。俄人乃惕于日人经商手段之敏捷,而亦略变其计,以倾其全力于商业一方面,于是日俄两国经营商务之点始相接触,而权利竞争之关系益烈”。〔48〕海参崴是俄(苏)沿太平洋的主要商港及军港,且位于西伯利亚铁道东端,商业地位十分重要。〔49〕就东北北部货物输出海外而言,“海参崴地点尤较大连为优胜”,这是因为它“距北满之中心哈尔滨,既近而复有铁路直接相通,而旅客或货物之赴大连,则须绕道先运至长春,然后再行转运”。〔50〕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距崴埠路近而运费可省,商人自然会选择中东路东线运货。“若大连,则路远而运费昂,且长春—哈尔滨间与长春—大连间路轨之宽狭不同,往来必须在长春换车,转运甚为不便”。〔51〕哈尔滨至海参崴港794公里,运货仅需48小时即可抵达,连同办理报关、纳税等手续,也只需60个小时;而哈尔滨至大连944公里,仅运货就需64小时。〔52〕按说东北北部商货应以海参崴港作为其最主要的出海港,实际却因中日俄(苏)三国所控路港系统对东北北部腹地的争夺而不尽然。对于东北北部地区来说,选择大连、海参崴、罗津各港中的哪一个作为出海港,应该是对它们所关联的铁路系统的过货能力、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能力、运输时间、运输费用、稳定性、安全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后而进行的优选。但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日俄(苏)主导下的东北亚政治军事环境、日俄(苏)在东北亚所控铁路运费政策及其所控铁道网络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尤以铁路网络的变化对其影响最大。因此,各国努力为所控主干铁路构筑给养线。
但是,日俄战后,俄(苏)为中东路修建给养铁路支线,以扩充中东路—海参崴港系统的努力,因中日两国的反对等原因收效甚微。自日俄战争结束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为南满铁路构筑了更多给养线。其铁路系统以南满铁路为干线,以吉长(吉林—长春)、吉敦(吉林—敦化)、四洮(四平街—洮南)、洮昂(洮南—昂昂溪)及安奉(安东—奉天)五条铁路为进入吉黑及与朝鲜联络的主要支线。该铁路系统最为完整,“握住整个东北的交通”。〔53〕日苏路港系统在中东路南、西二线的沿线附近各地及哈尔滨一带展开激烈的腹地争夺,表面看,双方互有胜负,形成拉锯战的态势,其实是俄(苏)不断退却、日本不断向北扩张的态势。而日本铁路系统能够向北扩张,与一些中国铁路的助力有关。其实,中国的路港系统是为了抵御日俄(苏),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利权的侵夺而规划。中国铁路系统以北宁(北平—沈阳)路为干线,以沈海(沈阳—海龙)、吉海及打通(打虎山—通辽)三铁路为进入吉黑的主要支线。但是通辽以北的四洮、洮昂两铁路是用日本借款修的,管理权及财务权均在日本人手中,事实上与日本铁路无异,中国新修的齐克及呼海两铁路尚不能与北宁干线联络。〔54〕而且,中国铁路所赖以出口的优势终端港口——葫芦岛港的建设缓慢,导致其路港系统始终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因此,它只能以吞吐量不大的营口港河北码头为终端港,那它对苏控路港系统也形不成多大的直接冲击,甚至呼海铁路还因与中东路实行联运而成为其给养线,〔55〕但是,日本以借款关系使更多中国铁路变成南满路的给养线,使与东北北部农产输出关系密切的海参崴港,“得内地铁路之利益有限”,而大连港受惠于东北地区人口增加、物产开发、铁路延长等方面红利颇多。〔56〕
尽管苏控路港系统的腹地因一些伸入东北北部的中国自建铁路纳入日本所控路港系统,而使中东路西线货运受到齐克、洮昂等铁路的较大切分。但是,表2显示,1908—1928年,东北北部东行经中东路—海参崴港输出的货额与南行经南满路—大连港输出的货额,互有消长,处于拉锯战的状态。其势力仍不可小觑。

表2 1908—1928年东北北部地区经中东铁路向各铁路输出入货额
至1929年之前,中东路仍能以黑龙江全省及吉林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自己的腹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吉林和黑龙江设省。1929年前后,吉、黑二省所设县均为41个。吉林南部各县,如吉林、长春、伊通、濛江、长岭、舒兰、桦甸、磐石、双阳等9县,属于南满铁路的经济势力范围;吉林东部各县,如延吉、敦化、汪清、和龙、额穆、珲春等6县属吉敦、天图(天宝山—图们)等铁路的经济势力范围,“其余德惠、农安、双城、五常、榆树、扶余、滨江、宾县、同宾、方正、阿城、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苇河(今尚志市东南苇河镇)、依兰、勃利、同江、宝清、密山、虎林、绥远(今黑龙江省抚远市)、桦川、富锦、饶河、穆棱等24(应为26——引者注)县,皆直接、间接为中东路经济势力所支配”。黑龙江省除沿额尔古纳河的室韦(今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奇乾(今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二县及沿黑龙江南岸的漠河、呼玛、瑷珲、萝北4县被中东路经济势力间接支配外,其余龙江、嫩江、大赉、肇州、安达、林甸、克山、讷河、青冈、拜泉、肇东、呼伦(海拉尔)、胪滨、泰来、布西(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布西社区)、景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景星镇)、索伦、甘井、绥化、绥楞(今黑龙江省绥棱县)、呼兰、海伦、望奎、通北、巴彦、庆城(今黑龙江省庆安县)、兰西、木兰、通河、汤原、龙镇(今五大连池市龙镇镇)、铁力、绥东、明水、伊安等35县,“皆直接、间接受中东路经济势力所支配”。“综计吉、黑两省直接、间接受中东路经济势力支配者共为64(应为67——引者注)县”,在这67县中,位于中东路西线的,“尽属于黑龙江区域”;位于东线的,“半属黑龙江,半属吉林”;位于南线的,则全部属于吉林省。〔57〕一些当时属于吉林省的县,如滨江、五常、宾县、同宾、方正、阿城、珠河、苇河、依兰、勃利、同江、宝清、密山、虎林、桦川、富锦、饶河、穆棱等,今则属于黑龙江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南满铁路为根据,“由大连中心主义而进取南北满主义”,在前期已建铁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北部铁路网络与朝鲜北部罗津等港口的建设。以往东北北部的物产主要经中东路运往海参崴港出口,南满路不能与之争衡。吉会路(吉林—朝鲜会宁)—罗津港系统的建成,会使东北北部赖以向外输出商货的路港系统发生重大变化。〔58〕据统计,截至吉会路全线开通的次月(1933年5月),由海参崴港转向罗津港运送的大豆与豆油将近130万吨。〔59〕此后,日本还为吉会铁路修建了拉滨、图宁(图们—宁安)、延海(延吉—海林)等支线及其西延线——长大铁路,这些铁路使其新建的吉会路—罗津港系统更加完善。随着这些铁路的建成,中东路就不再握有东北北部的交通重心,〔60〕其腹地货源被大量分流。拉滨路与中东路南线走向一致,它们之间的竞争比南满路与中东路以往的竞争更加激烈。自从拉滨路开始营业以来,它早已压倒中东路南线,“吸引北满的货物运输并完成其本来的经济使命”。〔61〕1931年10月至1932年9月,东北北部大豆类农产的流通总量为248.7万吨;1934年8月拉滨路通车后,其中的173.7万吨改由拉滨路输送,占其总量的近70%。〔62〕至此,不仅中国自建铁路因缺乏自有出海港而以大连港为出海口,苏控路港系统也因中东路腹地的大量丧失而受到了致命打击。
在南满路—大连港系统与新建的会宁路—罗津港系统的合力打击下,苏控路港系统彻底失去了经济、军事价值。《申报》刊文称:“大连为南满铁路之吞吐港,黑龙江西部之产物,亦因洮昂、四洮两路之衔接而为大连所吸收。吉林农产,黑河流域谷仓,原为中东路开发之鹄的,吉会路完成,延吉与三姓线筑就后,则清津、雄基二港,势将包围海参崴,并劫制其海上的出路。于是,中东路仅有以西比利亚大铁道沟通欧亚两洲之单纯任务,在军事上亦将处于被动地位,而失其操纵之力。”〔63〕至1935年,苏联被迫将中东路卖给伪满洲国,这意味着俄(苏)与日本在东北亚路港系统竞夺中的完败。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承认苏联在保持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到海参崴和到大连不冻港的铁路过境运输方面的利益,“使苏联贸易得到经过满洲的不受阻碍的出海口”。〔64〕1945年,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及中苏相关协定重获大连港及中东路的管理权,并将中东路和南满路干线合并,改称为中长铁路。〔65〕随着1946年3月苏军撤离中国东北及1946年夏季解放战争爆发,中长铁路陷入无法正常运营状态,苏方员工撤退回国。〔66〕
四、结 语
近代,在东北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分别由中日俄(苏)三国控制的铁路—港口系统。它们在东北北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腹地竞夺战。对于东北北部地区来说,选择哪一个港口作为出海港,会受到日俄(苏)所控铁路运费政策及其所控铁路网络变化等因素的很大影响,尤以铁路网络变化对其影响更大。因此,各国努力为所控主干铁路构筑给养线。日俄战后,俄(苏)为中东路修建给养铁路支线的努力,因中日两国的反对等原因收效甚微,但是,松花江与中东路实行联运,以及中国自建的呼海铁路成为中东路给养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东路给养线不足的缺陷,减缓了俄(苏)路港系统衰变的速度。即使这样,九一八事变前,中东路西线腹地还是受到了数条因借款关系而变成南满路给养线的中国铁路的切分,对苏控路港系统形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中国增建铁路达2753公里,但因其中一些可伸入东北北部的铁路由日本控制,终端优势港口葫芦岛港迟迟无法建成,只能以营口港河北码头为终端港,导致其路港系统的竞争力始终处于最弱的状态,对俄(苏)路港系统形成的冲击很有限,其铁路甚至成为南满、中东二路的给养线,尤以南满路受益更大。九一八事变后,中东路东线与南线腹地又受到日本新建的会宁铁路—朝鲜北部诸港系统更严重的切分,对苏控路港系统形成致命打击。总之,中日路港系统的合力打击下,近代俄(苏)在东北亚地区的路港系统不断衰变,极大地改变了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政治经济格局。
注释:
〔1〕〔4〕《东三省之运输谈》,《申报》(上海)1923年10月13日第18187号。
〔2〕〔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论》,蒋学楷、赵康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3页。
〔3〕〔23〕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2号。
〔5〕〔32〕《东铁赞助改建齐昂之原因》,《申报》(上海)1925年8月28日第18856号。
〔6〕苏崇民:《满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任松:《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韩〕金志焕:《中东铁路出售的经济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等等。
〔7〕李书源、徐婷:《铁路与近代东北交通体系的重构(1898—1931)》,《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4期;易丙兰:《铁路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奉系自建铁路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等等。
〔8〕姚永超:《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9卷.东北近代经济地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
〔9〕〔11〕〔13〕徐曦:《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372-373页。
〔10〕方乐天撰述:《太平洋大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8页。
〔12〕〔40〕万福麟修、张伯英纂:《黑龙江志稿》卷42,1932年铅印本。
〔14〕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68-173页。
〔15〕〔俄〕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民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45页。
〔16〕〔52〕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印:《北满与东省铁路》,哈尔滨:哈尔滨中国印刷局,1927年,第283,219、223页。
〔17〕〔36〕〔38〕黄文涛:《中日俄竞争下之东北铁道网》,杨仁昌校,南京:南京书店,1932年,第177-178、177-179、171-172页。
〔18〕СЛaДКовCKИЙ M.н.,OЧepkИ ЭKOHOMИЧeCKИX OTHOШeHИЙ CCCP c KИTaeM.MОckBa,1957,с.142.
〔19〕〔26〕〔29〕《俄人转押我筑路权之传闻》,《申报》(上海)1918年8月13日第16340号。
〔20〕〔日〕高桥正雄:《满铁论》,《时事类编》1934年第2卷第10期。
〔21〕《俄人经营北满之野心如是》,《申报》(上海)1911年3月30日第13697号。
〔22〕朱偰编:《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4页。
〔24〕〔28〕《北满未来之俄国铁路》,《申报》(上海)1913年12月7日第14669号;《北满未来之俄国铁路(续)》,《申报》(上海)1913年12月8日第14670号。
〔25〕《苏俄有要求合办滨黑路说》,《申报》(上海)1924年3月11日第18329号。
〔27〕易丙兰:《多方角逐下的近代北满路权——以滨黑铁路为中心的讨论》,《兰台世界》2018年第3期。
〔30〕《民国路政之面面观》,《申报》(上海)1914年4月24日第14799号。
〔31〕〔33〕《东铁吸收蒙产之成绩》,《申报》(上海)1925年9月29日第18888号。
〔34〕王慕遽:《东三省铁路概况》,《交通管理学院院刊》1929年第2期。
〔35〕〔44〕南阳:《东三省铁路概况》,《中东经济月刊》1931年六周年纪念专号。
〔37〕哈尔滨满铁事务所编:《北满概观》,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144-145页。
〔39〕龚德柏:《揭破日本的阴谋》,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第154页。
〔41〕《苏俄收买大豆直接来船装运赴欧》,《申报》(上海)1931年3月25日第20823号;《苏俄贩运北满粮石》,《申报》(上海)1931年3月31日第20829号。
〔42〕〔日〕长谷川:《哈尔滨经济概观》,王绍灿、王金石译,哈尔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1990年,第15、25页。
〔43〕严躬:《北满之陆路交通》,《东省经济月刊》1926年第2卷第9期调查。
〔45〕《北满之经济状态与铁路》,《铁路协会会报》1916年第46期第5卷第7册。
〔46〕《日本在东三省之经营(再续)》,《申报》(上海)1923年4月19日第18011号。
〔47〕满史会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辽宁省营口县商标印刷厂印刷,1988年,第412页。
〔48〕《申报》(上海)1909年12月10日第13238号。
〔49〕《中国亟应醒觉之外论(续)》,《申报》(上海)1918年11月26日第16445号。
〔50〕《俄人力谋恢复海参崴商业》,《申报》(上海)1924年12月14日第18607号。
〔51〕《东路添设哈长双线之影响》,《申报》(上海)1922年2月23日第17599号。
〔53〕〔54〕〔60〕邝振翎等编:《中国经济概况》,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1930年,第381页。
〔55〕哈爾濱鐵路局北滿經濟調査所編:《滿洲事變竝北鐵接收後に於ける北滿主要都市の經濟的動向》,哈尔滨:北滿經濟調査所,1937年,第2、21页。
〔56〕祁仍溪:《葫芦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5页。
〔57〕雷殷:《中东路问题》,哈尔滨:国际协报馆,1929年,第169页。
〔58〕《吉会线の开通と内地四港(舞鹤、敦贺、大阪、神户)满鲜间の运输关系》上,《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第311号,1933年4月,第1-2页。
〔59〕《吉会线の开通と内地四港(舞鹤、敦贺、大阪、神户)满鲜间の运输关系》上,《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第312号,1933年,第36-38页。
〔61〕鐵路總局編:《日滿新交通路としての拉濱線》,沈阳:鐵路總局,1934年,第21页。
〔62〕《拉滨线の经济价值》,《满铁调查月报》1934年第14卷第2号。
〔63〕《日苏纠纷与苏联出卖中东路》,《申报》(上海)1933年5月10日第21578号。
〔6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2 v., v.II, Wash-ington,U.S., G.P.o., 1960, pp.1242-1243.
〔65〕АП РФ,ф.45,оп.1,д.322,л.32-33,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 шения,Т.IV.,Кн.2.,с.108;АП РФ,ф.45,оп.1,д.322,л.61,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Т. IV.,Кн.2.,с.129.
〔66〕С.Л.Тихвинский,Избранные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Кн.5,М.,Наука, 2006,с.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