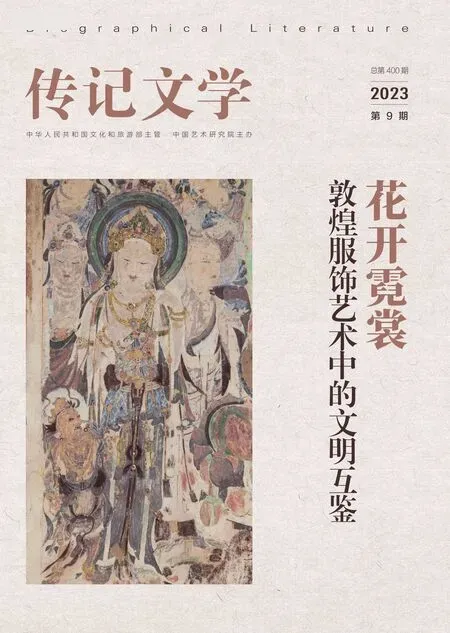一个“50 后”的学术自白
段崇轩

我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是所谓的“50 后”。这一代人被称为“特殊”群体,他们的每一个人生关口都遭遇了社会的重大变动,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复杂的社会精神和思潮。我是从乡村社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却选择了文学创作、研究与评论,这样一个狭窄而高难度的专业,兜兜转转、半个多世纪,每一步都蕴含着学术的诱惑与艰难。
乡村岁月“文学梦”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原平县,现已升级为县级市了。这是山西北中部一个东西为山、中间为平川的地域,素有“将军县”“文人县”之称。东晋高僧慧远,近现代抗日爱国将领兼诗人续范亭、翻译家余振、军旅作家西虹,当代作家杨茂林等,都是文化界的骄傲。我的故乡叫“南申村”,一个平平常常、不大不小、不富不穷的平原村落。北靠阳武河,东傍滹沱河。父亲经营的那个整洁而兴旺的小院,现在人去院空,渐渐颓圮,留下了永久的乡愁。
“50 后”一代人特别是乡村出身的,接受的学校教育大都是残缺不全的。我1960 年上小学,那时的教育已然正规,村里建了崭新的学校,教师绝大部分是公办,课本也很齐全、成熟。有几位语文老师喜欢读书、写作,我成为他们的“粉丝”,也跟着读和写,并悄悄给《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投稿。1966年,小学毕业的我和同学们去县城参加考试,不久收到原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在“文革”的风暴中,中学校门关闭了。这六年的小学生活,成为我一生学校教育的“黄金时代”。随后,我由一位小学生成为生产队的“半劳力”。村里办起了农业中学,我随大流也去上,但很不正规,只是拿到一纸中学毕业证。
1969 年秋天,县中学再度招生,我第二次考取原平中学。虽然课本是现编的,教师是刚“解放”的,规章制度是不健全的,但教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学校风气、秩序还好。我成为语文课代表,写作方面的特长受到了老师、学校的注意和鼓励。学校图书室“有限”开放,我以课代表的身份,借阅了鲁迅、茅盾、巴金以及赵树理、浩然、马烽等人的著作。我给班里办墙报、为学校办小报,还成为《原平通讯》小报和县广播站的通讯员,被采用了多篇稿子。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马炳光,北京人,山西大学毕业,对我偏爱有加。我常常找他请教写作问题,批改新写的文章,他总是不厌其烦。记得有一本吴调公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年出版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就是从马老师那里借到的。那是一本文学理论的基础读本,阐述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基本特征和创作规律,我读了很多遍,记住了其中的许多概念和作家。马老师见我喜欢,慨然相送。这本书至今还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是引导我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启蒙书”。

20 世纪70 年代末,本文作者与作家杨茂林(右)在太原合影
1971 年冬天,两年多的高中生活结束,我再次回到村里,成为返乡青年,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出身农家,但祖父、父亲两代人,并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做的是跟商业有关的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成为百货公司干部,没能把种地的传统、经验传给我,我更渴望的则是读书、写作,以及去到外面的世界。由于有写字、写作的特长,我常常为村里干点出板报、写文书的工作。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时代,这样的事项很多。我的特长被下乡的公社书记所发现、欣赏,他一个电话打到村里,我成为公社的专职文书。我一边为公社写公文、报告、通讯之类,在县、区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一边开启了自己的“文学梦”,骑自行车去县新华书店购买当时出版的各种文学作品集,并悄悄开始了文学创作,散文、小说、评论,什么都写。后来,我结识了作家杨茂林,他在忻县(今忻州市忻府区)工作,家就在公社所在的村庄。“文革”的批判浪潮也冲击到了他,他一度回本乡体验生活。我和一位朋友慕名拜访,老杨十分感动、兴奋,我们成为关系很“铁”的师生、朋友。他是一个朴实、健谈的人。常常骑车到公社、到村里,与我和朋友聚谈,谈社会、谈文学、谈小说,谈得热火朝天,并带走我刚写的几篇小说。这时地区成立文艺创作组,老杨成为负责人,他们要编一本《文学创作选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的一篇《同一块地里》的短篇小说,被老杨看中,他精心修改,收录在选集中,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这之后,我又在《原平文化》《忻县地区报》发表了二三篇小说,成为县、区重点年轻作者。回想当年,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能谈出、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小说呢?但我们却满怀信心、踌躇满志。其实在那些作品中,充满了虚妄的描写、议论,乃至说教。“50 后”的很多作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的文学、评论写作,就是从这时起步的。
由于我在文学上的一点成绩,1975 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通过选拔、推荐,我顺利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上学机会,认真读书、坚持写作,还当了三年写作课代表,同尊敬的老师们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老一辈先生姚奠中、姚青苗、马作楫,中一代老师曹玉梅、高捷、高仲章等,都给予我莫大的教诲与勉励。我在刚复刊的《汾水》与《太原日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评马烽小说的文学评论。1978 年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被安排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按照高捷老师开列的加长书单,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文学史到文学理论,囫囵吞枣读了不少书。但是,我对文学创作总是念念不忘,再加上一家两地分居难以解决,于是“弃教从文”,于1982 年调回忻县地区文联,在《春潮》文学刊物做了一名编辑。六年后的1988 年又调到山西省作协《山西文学》当编辑。编辑、写作,成为我大半辈子的主要职业。
山西评论家吴言曾经采访、评论过多位重要作家,如王安忆、张炜、范小青、徐小斌等,他说:“我忽然意识到,这些人都是五十年代生人,他们身上有着其他年代人身上没有的特质。在文坛他们显然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代人。作为一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引领。‘向五十年代致敬’,这个声音从我心底开始流涌。”[1]确实,她说的“50 后”作家,各领风骚、创造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而“50 后”的评论家学人,同样是出色的、有重要建树的。正如魏庆培所说:“‘50 后’学人作为一个学者群体,……他们分别在当代文学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料整理等‘历史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这里主要说的是文学史,整个文学评论亦然。譬如陈平原、陈思和、孟繁华、陈晓明、丁帆等。但我想说的是,这一代人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的、成熟的学校教育,致使他们的文化、文学功底不成体系。他们比之“40 后”学人就差了一截。“50 后”在思想构成上也是庞杂、矛盾的,缺乏定性,这在他们的文学著述中都有表现。他们的优势是有丰富曲折的社会人生认知与经验,有赤诚的人文情怀和使命意识。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他们后期补课、进取的结果。我作为“50 后”中的一员,深知这一代人的长项与短板。至于我个人,从高校落脚到作协,虽然获得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但也失去了诸多学术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是对是错?难说得清。
编辑、评论两不厌
从1982 年至2000 年,我做了18 年文学编辑。先是《春潮》6 年,后是《山西文学》12 年。在《山西文学》,从编辑直到主编。编辑是主业、评论是副业,我都喜欢。编辑与评论有时是矛盾的,但更是统一的。省作协的前辈老师就是榜样。如李国涛老师,长期担任《山西文学》主编,扶植“晋军”作家,推出他们的作品,同时写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为新时期山西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董大中老师,先做《山西文学》评论编辑、继而任副主编,后成为新办的《批评家》主编,着力发现、扶助山西的批评新人,他自己在山西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丰硕的建树。我同二位老师交往甚多,他们的编辑、评论实践,对我深有影响。
《山西文学》是一份“老字号”刊物,它的前身是《汾水》,再往前是《火花》,曾经有过几度兴盛。我主持刊物的时候已是20 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展开,文学渐渐滑向社会边缘。面对新的时代和文学,我采取了继承和发展刊物传统的思路和做法。一是继续推进和变革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山西文学在这方面有着强劲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而新的乡村小说创作也需要探索、变革。平时我注意推出乡村题材小说,到1996 年《山西文学》创刊四十周年之际,从第9 期至第11 期,连续推出“中国乡村小说特辑”,发表了本省作家张石山、王祥夫、谭文峰,外省作家田中禾、刘醒龙、关仁山等21 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开辟“乡村小说自由谈”理论栏目,推出了丁帆、张德祥、傅书华等14 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这一举措受到了全国文坛的关注与好评,当时山西作协焦祖尧、西戎等都给予赞赏和支持;二是扶持山西新一代作家,《山西文学》从最初创刊起,就很注重培养青年作家,我们秉承传统,把山西的第四、第五代作家团结在身边,推出作品、创办专辑、召开笔会,使新一代作家不断成长起来;三是把刊物的老式排版、印刷,转变为现代的排版、印刷,但由于技术、资金方面的限制,转型还不够理想。
我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小说家,但“文革”时形成的文学思想和写作套路,阻碍着我写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此外,我的逻辑思维强于感性思维,也使我的小说难以飞腾起来。虽然有长有短发表过六七篇小说,但自觉“此路不通”,有文友也坦率地指出我更适宜写评论,于是从80 年代中期起,我老老实实地转向了文学的研究与评论。
文学评论也是一个“大家族”,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乃至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研究,等等。我的文学评论是从研究山西文学起步,并逐步扩展到研究全国文学的。从两面入手,一个是宏观研究,对山西文学的历史、现状、问题的探讨,写过多篇长文;一个是微观研究,对山西当代作家中的重点作家及作品,一个一个进行阐释,写出数十篇综论。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本省刊物,多数发表在全国报刊。对全国文学的研究,重点在作家作品评论,如王安忆、何士光、谌容、田中禾、王文平、刘玉堂、聂鑫森、孙方友、郭文斌、关仁山、朱辉、李云雷等,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物上。不管是对山西作家,还是对全国作家,我都努力坚持客观、公正的“对话批评”方式,从思想艺术方面作出较全面的阐释与评判,得到了多数作家的认同与好评。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则重在对当下文学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作家论创作等的关注与探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了主体地位,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90 年代中期之后,我开始反思这一领域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文坛的关注。2005 年至2006 年,我发表了一组文章,阐述文学批评的“三分天下”现象,即由协会派、学院派、媒体派形成多元格局的观点,在批评界、作家和读者中引起反响和争论。2007年7 月19 日,《文艺报》以头版头条发表记者韩晓雪的综合报道《让文学批评形成合力》,论述了我的观点,采访了批评家吴秉杰、洪治纲、谢有顺、李美皆等,各自发表了不同观点和建设性意见。对作家论创作的研究,一直比较冷清,其实也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是个很有开拓空间的领域。2022 年前后,我陆续发表了《文学批评怎样“生成”文学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的互动共荣》《“绘画摄魂”——阎连科短篇小说散论》等文章,突出论述了作家论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旨在提升作家论创作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
名篇佳作的鉴赏和细读,也是我感兴趣的课题。早在2000 年,我和朋友傅书华,就在《中学语文教学通讯》开设专栏,两人同时解读一篇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名篇,坚持三年之久,受到众多教师、学生的欢迎,后集辑出版了《初中语文名篇双解》《高中语文名篇双解》两本书。我还在《名作欣赏》开专栏,用细读批评的方法,评述当下的短篇小说佳作,读者反响甚好。此外,我还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甚至有些批评文章,也有意识地散文、随笔化。2001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焦祖尧老师在序言中评价作者的散文“属于那种学者型、文人型散文”,“折射出他浓厚的文人心态,洋溢出一种‘淡泊、宁静’的书卷气”[3]。焦老师是“知我”的前辈、领导。
乡村小说研究是我倾注了很大心力的一个研究方向。乡村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主潮,山西文学更是几代作家耕耘在这方“沃土”之上。《山西文学》杂志则把发表、推动乡村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使命。置身在这样的潮流和环境中,我也把乡村小说研究放在重要位置。我的研究同样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切入的。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是对三十多位小说作家作了解读、综论,其中既有山西的,也有全国的,均为实力派作家。老一代山西作家研究,著有《赵树理传》(合作)、《马烽小说艺术论》;抽象的、宏观的研究,是对乡村小说的历史、现状、发展、问题等进行概括、提炼,然后写成较长的文章,譬如乡村小说的概念、题材、地域性、世界性、城乡之辨等。这些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受到了文坛和学界的注意,有多位学者在文章中引用了其中的观点。有的文章还获得了多个奖项。1999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专题性著作《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汇集我的阶段性成果。我本想就这一课题进一步开拓研究,向中国作协申报了《大地咏叹调——新时期以来乡村小说论稿》,被列入重点扶持项目。但由于我的研究方向调整,经费有限,而未能完成出版。我本应在这一课题上拿出一部丰富、严谨的学术著作来,但最终落空,让我深感抱愧!
执着文学评论四五十年,发表文章四五百篇,出版评论集《生命的河流》《永驻的厚土》《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小说中的大时代与小时代》《中国短篇小说十五家》六部。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这成果并不算多。
我的短篇小说“缘”
2000 年之交,全国的纯文学刊物普遍遭遇到生存危机。“断奶”“走市场”的声音在文学圈内外鼓噪。山西作协也被鼓动起来,讨论《山西文学》《黄河》的生存、出路问题,要求刊物数年内实现经济独立、自负盈亏。我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认为目前省一级纯文学刊物不可能进入市场,财政断奶几乎是“死路一条”,因此决定急流勇退,“趁机”转向我钟情的专业写作之路。我的请求得到领导的理解、同意,之后就转到山西文学院成为专业作家。二十余年过去,纯文学刊物突围无望,依然生存在体制的“羽翼”之下。
告别编辑岗位,开始专业写作。我的内心有一种轻松、自由、超然的感觉。我认真回顾、反思了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当代文学研究路子,梳理、分析了当下文学评论的现状与问题,深切意识到:我必须强化读书、补课,特别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美学等理论知识,以此填补我的“先天不足”,校正我在思想观念上的既有认知。我必须寻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课题,拿出几本扎扎实实的学术著作来。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4]当代文学评论,热热闹闹、鱼龙混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江湖”,说是显学,其实是俗学,学术含量稀薄。“50 后”一些学人,在其中如鱼得水,其实是在哄炒文学,贻误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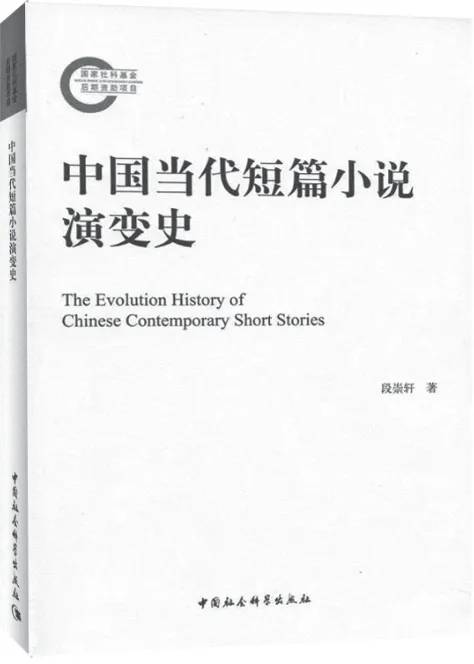
段崇轩:《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
我首先选择了短篇小说研究作为我一个阶段的学术课题,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从小喜欢阅读短篇小说,记得小学六年级时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谈小说创作》(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其中大都是著名作家如艾芜、杜鹏程、王汶石、王愿坚等谈短篇小说创作的文章,我读得爱不释手。中学毕业后,我回乡劳动,迷上短篇小说写作,竟发表数篇,虽然路子是错的,但也懂得了短篇小说的一些艺术特征和写法;二是我先后在两个文学刊物当编辑,担任的均是小说编辑,看了难以计数的稿件,熟悉了众多的小说作家;三是我的文学评论,很大一部分是以短篇小说作家为对象的,对作家作品、小说文体的认识不断深入。2005 年,我用较大的精力,写了一篇《消沉中的坚守与新变——1989 年以来的短篇小说》,投寄《文学评论》,得到责编董之林老师的赏识,在2006 年第1 期发表。这篇文章颇受关注,获得赵树理文学奖,进一步激发了我研究短篇小说的“宏大构想”。我向前看,一年一年评述年度短篇小说,从2006 年至2022 年已坚持十六年,有多篇选入《中国文学年鉴》;向后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十年的短篇小说作为一段历史,我用八年时间,写出一部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大半辈子与短篇小说不离不弃,这不是一种“缘分”吗?
短篇小说文体虽小,但分量很重,波及甚广,是“小说中的小说”。对小说“家族”乃至整个文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短篇小说不仅是文学的“风向标”,也是社会的“心电图”。短篇小说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不仅显示了文体本身的演变轨迹、内在规律,同时也折射了中国当代的时代更替、文化沉浮、人心流变。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可达“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的审美功效。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绪论”为总纲;第二章“一体化文学时期”论述了1949 年至1966 年短篇小说的发展;第三章“极‘左’、阴谋文学时期”概述了1966 年至1976 年短篇小说的“异化”;第四章“变革和创新文学时期”评论了1977 年至1989 年短篇小说的勃兴;第五章“多元化文学时期”讲述了1989 年至2009 年短篇小说的运演。有宏观、微观,有历史、文学,有审美、艺术,可算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的分体文学史。文稿分别刊登在全国各大报刊上。我曾把铁凝综论寄给作家本人,铁凝在回信中说:“谢谢您对拙作的评价。我的确喜欢短篇小说,只是觉得写好是太不容易了——初学时倒不这么看。这几年德国短篇小说突又勃兴,作家、读者均有好的兴致和热情,这值得研究。”还有评论家张炯、雷达、白烨、孟繁华、何绍俊、李敬泽等,对我的文章、课题,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指点,我很感谢他们!
2014 年,我把书稿打印成册,寄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出版中心郭晓鸿老师,她很快发来邮件,说书稿很有学术价值,提议由他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几个月后,书稿顺利入选、立项,获得资助,评审专家认为:“该成果从卷帙浩繁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抽取出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进行历史轨迹演变的研究,对短篇小说发展作出了系统的描述、分析和概括,探讨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变迁和发展变化规律,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相对完备的当代短篇小说创作史,填补了这一领域内多年来的一项空白。”评审专家还对书稿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修改意见,我用五个月时间,对书稿进行了仔细修改和补充。书稿于201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出版后,评论家贺仲明、张志忠、牛学智等发表评论,给予肯定和赞赏,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
“50 后”普遍学历残缺,但新时期之后有各种文学研修班可上。我就两次参加了这样的进修班。一次是1986 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文学评论高级研修班,学期一年;另一次是2005 年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评论高级研讨班,为期两个月。对我来说十分必要,收获颇多。
追根溯源“新文学”
2020 年春节前后,疫情突起,社会、民众恐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无可抗衡,最佳选择就是听从号令,足不出户,宅家做事。我找出陆续搜集、购买的书籍资料,一点一点开始了我的“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课题,走进百年前的历史和文学中。这真是一片广袤、神奇而荒凉的文学“矿床”,面对它,只觉得目不暇接。现实渐渐远去,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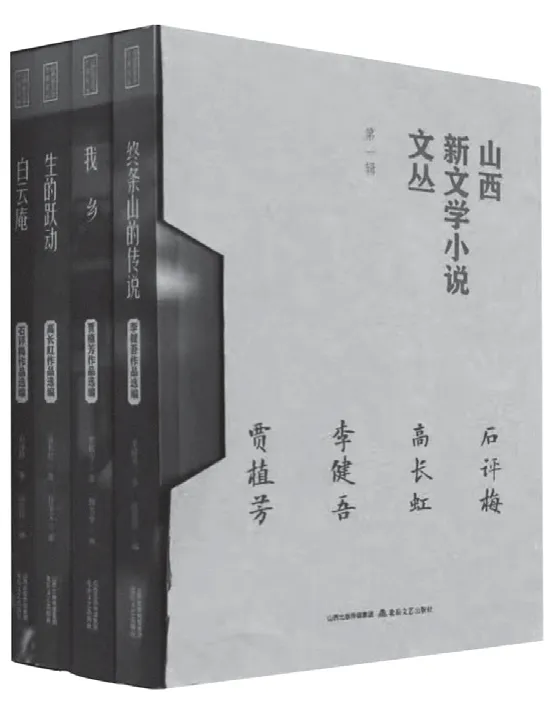
段崇轩主编:《山西新文学小说文丛》第一辑
我之所以转移阵地,从当代文学跨到现代文学领域,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2014 年由我牵头,邀集评论同仁杜学文、傅书华,草拟了一个《山西新文学小说文丛》编辑出版方案。在搜集、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深感山西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发生那么多重大事件,涌现那么多杰出作家作品,是百年山西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但后来我们有意无意淡忘、割断了那段文学,使人们误以为40 年代的根据地文学,就是山西现代文学的开端。“文丛”拟收集那一时期十多位作家的小说代表作、众多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合集,构成系列,分辑出版。直到2018 年省委宣传部批准方案,获得资助,2020 年出版第一辑。其次是我对现代文学可谓“情有所钟”,当年在山大中文系留校时,被安排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现代组,购买了大量史料、作品,并读过不少。后来当代文学师资缺乏,才把我强拨到当代组的,但我对现代文学始终念念不忘。读过数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再看山西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感觉亲近,看得也明白。再次是我对自己几十年的当代文学研究,再次作了审视、反省。虽然有所收获,但自己的学术创新在哪里?又有多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心中实在没底。坊间有传言:研究古典文学的看不上研究现代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看不上研究当代文学的。根源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门槛太低,缺乏学术含量。当代文学被有形无形的观念、戒律,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抑制、束缚、牵动着,很难有真正的独立、自由。那些有思想、学术、个性的研究成果,未必能得到学界、学人的认同与尊重;而有些迎合时势、八面玲珑的“短平快”制作,倒是大行其道。陈寅恪先生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5]而现在的当代文学研究,最匮乏的就是自由和独立的品格。我自知功力不逮,建树不多,但却实在看不上那种充满功利的“俗学”。退回文学历史,做一点纯粹的学术,正合我的意愿。
“诱惑”我转向新文学研究的,还有作协的老前辈董大中老师。在作协院里,很早就有“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个研究所”的说法。他数十年如一日,沉潜学术,从鲁迅研究开始,走向中国现代文学、山西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完成各种著述57 种,1430 多万字。2017 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董大中文集》。他最重要的是鲁迅研究、高长虹研究、赵树理研究,仅此三种就有23 本书。他以一己之力,建构了山西新文学的资料库、研究库。他的住宅里,书房有五六书柜书籍资料,三四十平方米的地下室堆满了层层叠叠的山西文化、文学史料。这些都是他从北京、山西的图书馆、档案馆及太原文物市场搜罗来的,也有从书店、网上淘来的。他从小听觉受损,跟人对话困难,于是浸润在丰富多彩的史料、学术世界中。几十年来,他不断出版著述,每出一本新著,就签名、钤印赠送我,我都珍藏起来,现在研究山西新文学,都派上了用场。
“开垦时代”,是鲁迅对山西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一个精辟概括。他在1933 年6 月20 日给太原一个叫“榴花艺社”文学社团的一封信函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6]短短四个字,表现了山西新文学的发展态势,体现了鲁迅对山西文学的谙熟和肯定。当时,在鲁迅身边,聚集了一批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青年作家,还有多位在北京上学、打工的文学青年,鲁迅对山西作家、山西文学是十分熟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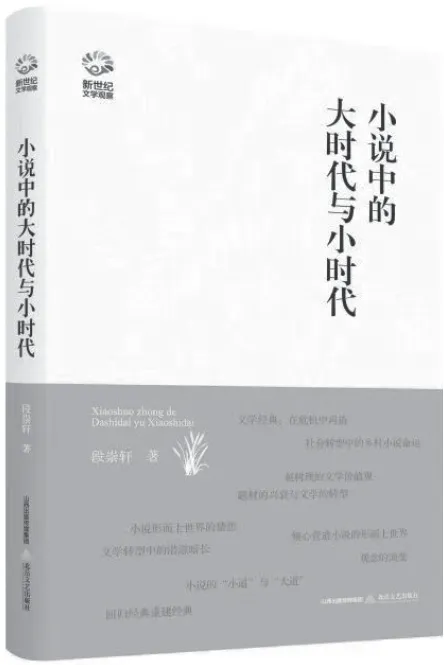
段崇轩:《小说中的大时代与小时代》
我对山西新文学的研究,是在中国新文学的大背景下观照的。山西文学同全国文学既是同步的,又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丰富、扩展了中国新文学。山西新文学在二三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诗歌、散文、小说、文论、戏剧文学等充满生机。在无序而长足的推进中,文学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我的研究兼顾诸体,但重在小说。因为绝大部分作家都写小说,而且成果卓著。小说成为后来几代作家的主要文体。我的研究集中在几个点上。一是“走向全国”的作家,如景梅九、高长虹、常燕生、石评梅、高歌、李健吾、贾植芳、关露;二是“守土开拓”的作家,如高沐鸿、赵树理、田景福、穗青、姚青苗、王中青;三是“历史回响”,侧重评述当时的重要文学现象、代表性作品,由此构成一个纵横交叉又有亮点的新文学史框架。这一课题由23 篇文章组成,近30 万字,分别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中国作家》《传记文学》《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使山西新文学走出历史、走向全国,展示出“庐山真面目”。
2023 年,疫情终于退却,生活回归常态,历时三年半之久的“中国新文学中的山西文学”阶段性竣工。但有关这一课题的新的题目不断产生,关于文学批评研究、关于作家论创作研究的新的构想也在成型。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无穷无尽、越陷越深。忽然想起董大中老师邮件中的一句话:“你还年轻,正是搞学问的时候……”他已88 岁高龄,还在笔耕,我岂能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