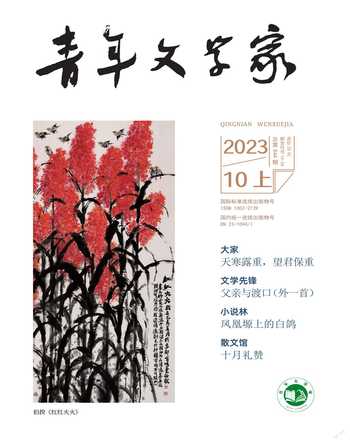父亲的背影
王尊广

倘若父亲在世的话,今年正好九十大寿。可是,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父亲走的那年六十六岁。按我们家乡的传统习俗,人到了六十六岁是要庆祝一下子的,俗称“过六十六”。为了让父亲高兴,我们做子女的邀请了亲朋好友,在饭店隆重地为父亲过了六十六岁大寿。那天,父亲看着晚辈都来给他敬酒,很高兴,几杯酒下肚脸色红扑扑的。
在我们鲁西南,盛传着“躲六十六”的说法,有些人本来到六十六岁,但他们直接称六十七岁。由此来说,人活着就是闯关夺隘,一生不知要经受多少关隘的磨砺。胜出者,无疑就是长寿者。从这方面说,我的父亲在六十六岁时罹遇不幸,成了生命长路的失败者。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在上班途中曾看到了父亲的背影,看他大步流星地走路,不知道他是去忙什么。就在那天中午,悲剧发生了—在我们村口的公路上,一个无德司机驾驶小汽车撞向了我的父亲,父亲不幸当场遇难。一切都无法挽回,我们作为父亲的子女,只有以泪洗面,痛哭失声。
父亲不幸遇难,使全村人都倍感痛心。因為父亲是全村公认的好人。在父亲当村干部的那几十年里,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对村民的各种要求总是不厌其烦地努力去做好。
对外面的事和他人的事,父亲倾注了无限心血;对自己家里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过多地让我娘去做。从读初中,我就开始住校了。后来,我又参军入伍,直到三十岁才回到了家乡。记得我回到家后,为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发。那天我下班后来到家,看到父亲端坐在院子里一把椅子上,脖子上围着一块塑料布。见此情景,我赶紧支起车子,跑到屋里找到那把理发推子,又拿了一把塑料梳子,煞有介事地给父亲理起发来,父亲的头发在我的手中慢慢变短。去当兵的时候,父亲的头发是黑的呀,并没有几根白的,可如今仅仅十多年过去,头发竟然白多黑少。我知道,我们成家立业了,父亲老了。我的眼前分明看见了幼年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清晰记忆。
在我十岁那年,家里要多困难有多困难。吃的也不行,尽是些玉米面窝头、玉米面饼子,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顿白面。那年腊月,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去辽宁抚顺我的姥姥家过年了。走之前一听不让我去,我十分不满,我的哥哥去过,现在两兄弟又去了,为啥不让我去?那时候我是没见过火车的,但我想象着火车拉着我的母亲、弟弟一路向东北的样子。那个冬天,我的棉袄外边天天套着母亲临去东北前给我做的一件军绿色的小褂,感觉像个军人,心里美着呢!
最难的要数过年了,平时吃啥都行,过年总得吃点好的吧!现在年轻人讲“仪式感”,在我们那时候无非就是过年整点儿年货,炸丸子、蒸年馍、包饺子。肉是不用买的,再困难的生产队年前都是要杀头猪的,不管大人、小孩儿,一人分上一斤、两斤的。家里没钱的窘况我是知道的,看得出来那些日子父亲的眉头是紧锁着的。家里只剩父亲、哥哥,还有我了,年货咋办呀?父亲每天出门了,我便蹲在门口望着他远去的高大背景,直到看不见。我想,父亲会有办法的,年一定能过好。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父亲回来,脸上有了笑容,他不光借着了钱,还借来了十五斤白面。第二天,父亲就开始蒸馍,虽然人家的年馍馍馅儿是用红小豆、红枣、甜地瓜做的,而我家的馍馍馅儿里只有地瓜和黄豆,但我们毕竟吃上了,而且过年时还吃上了白菜猪肉馅儿饺子。
而今,华发满头的我仍然时时想起我的父亲。每每想起,眼前便浮现父亲走出家门时的背影,可是,我再也看不到他回来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