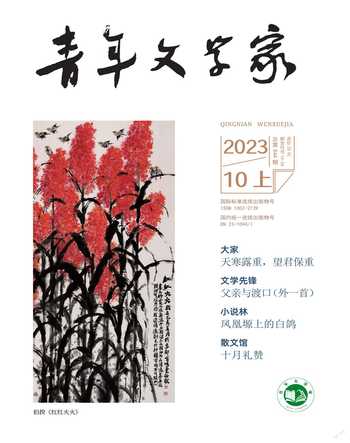你当像鸟,飞向自己的家
曹伟芳
有段时间特别忙,披星戴月进出家门,步履匆匆,却依然能感受到心底那一丝想驻足的留恋。有一天晚上,先生问我宝盖头下一个“女”是什么字,我说“安”。他说,房子里没有女人,心中不安。心下顿时明白他近来烦躁的缘由。
房子跟家不是一回事,当我把房子当成歇脚的旅舍,它就只是房子,而不是家。家里有时间,有丈夫、妻子、孩子、朋友的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那些能停留于这一方空间的时间便凝成了岁月;家里有烟火气,是衣物杂乱后的叠放,是灰尘污渍出现后的清扫,是寂寂夜色中的一窗灯火;家里有闲言碎语、胡言乱语、疯言疯语,有一句没一句,有上句没下句,随它去;在家里想说就说,不想说随时停止,即使被追问,一句“忘了”便可了结,不会探究是否别有深意,一会儿聊到其他事,不再记得刚才那半截子话。
但家与房子脱不了关系。
我的第一套房子在单位对面,小区老旧、杂乱。在旁人看来再傻不过,目光也太短浅,我却感到十足幸福。我那满屋子的书再也不用装编织袋里搬来搬去,它们在新做的书柜上找到了长久的位置,我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有来处,有去处,让人安心。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对房子的爱,窗帘、飘窗垫、绿植,喜欢的书画和摆件,只要我觉得房子需要便添置。曾经的我再喜欢一个房子也会保持距离,以免租约到期时房东赌你不愿搬离而借机涨价。从此,住在这里不再按年或月计算,这间老房子给予了我长久安定的拥有感。我还在每日便捷的上下班中体验到幸福,尤其是晚班结束,几步便能到家上床入梦的安适满足,不断强化着我对这所房子无所顾忌的喜欢。
入住后,渐渐发现杂乱的周边充满了生活气息。小区后面那排低矮的平房里居住着好几家外来务工人员,暮色降临时,辣椒与油烟味扑鼻,锅碗瓢盆与孩童的戏耍声盈耳……
我似乎从很高很高的塔楼里走下来,从漂泊不定的远方走到这里,走入这处老城区的小小角落敞开的暮色与烟火里。记得,最开始是楼下胖乎乎的邻居搬新家送我一份伴手礼,后来是楼上大姐嫁女儿送我的喜糖,我的孩子出生时婆婆给邻居们送去装着素面和蛋的红袋子,再后来住家阿姨会带孩子去前后栋邻居家串门,交换午餐最美味的那盘菜……
我不再是那个寄住于某户人家房子里的租户,而是安家在这里、长长久久住下去的街坊邻居,可以从容而又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的邻居,安心乐意地与他们交流美食或信息,我亦值得他们如此相待。
立秋后的一个深夜,看到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条房屋急售的信息,配图是朋友的房子。
我亲见她以一己之力买下这套房子,亲自设计、监工、添置家具、挑选软装,再到布置各类生机盎然的绿植、悬挂隐士朋友题字的牌匾。她厨艺极好,经常邀我去她家打牙祭,各种海鲜、时蔬总能让我的胃鲜活好一段时间。
我的孩子们幼年时都曾在她家那光洁的地板上攀爬打滚儿,承接着她温柔的照顾。孩子生气要离家出走,问他去哪儿,说到阿姨家去。中介发的图中,昏暗的客厅空空如也,浴室地上的毛巾黑灰蜷缩,无不暗示房子被遗弃的命运。我一直都知道她是这房子的精气神和顶梁柱,她走后房子必然破败,只是“灾难”来得如此快,受难如此之重,是我所不曾料到的。
飛云江风一阵接一阵地灌入书房,隔壁的鸽子已准时飞临窗台。它们胸脯饱满、羽毛光亮,在夜与晨的交界处飞翔、聚集,发出咕咕咕的声响。不知是受到江边夜风的惊扰,还是在向雌鸽求爱,或在向它的对手宣告自己的领地,而我更愿意将之视作它们在商量这一日的营生与游玩。隔壁房子已空置多年,每天清晨和傍晚,这群野鸽子聚集在那宽大有檐的窗台上,踱步、休憩、巡视周边,台面深深浅浅的鸟粪和翅膀时不时的扑棱声提醒着我—隔壁是鸽子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