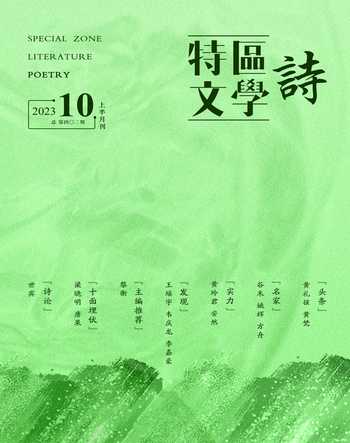穹顶之下
不是天空限制了我们
而是我们自觉有一个天空,
而且,我们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
诗人简介:
1988年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仁诗刊《北回归线》,1994年获《人民文学》建国四十五周年诗歌奖。2009年5月德国上海领事馆主办《梁晓明与汉斯·布赫——中德诗歌对话》。2014年上海民生美术馆主办《梁晓明诗歌朗读会》。2019年获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诗人。诗集《印迹——梁晓明组诗与长诗》《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分别入选“羊城晚报”花地文学全国十佳原创榜(2018、2019)。有作品于2021年第6期《收获》杂志“明亮的星”专栏推出。2022年5月获杨万里诗歌奖,2022年8月获第三届中国年度新诗奖“杰出创作成就奖”,2022年12月获得北京文艺网2021年度诗人奖。出版诗集《开篇》《披发赤足而行》《印迹——梁晓明组诗与长诗》《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忆长安——诗译唐诗集》,及散文集《诗,人与事》。
世 宾:天空是什么?
《穹顶之下》很短,只有三行。“天空”作为这首诗的关键词,“天空”是什么?诗人梁晓明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天空作为意象,我们的理解是高远、宽阔、无边无际,那是远方,是灵魂栖居的地方。诗歌开句“不是天空限制了我们”,这是一个现实的天空、物理的天空,这个天空限制不了我们,呼应了一句老话“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重要的是心,而不是现实。这看起来很潇洒,一副人定胜天的样子。但诗人笔锋一转,“而是我们自觉有一个天空”,这仿佛又不是人定胜天的意思,而是在说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牢笼。
天空还是个牢笼!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是的,诗人就是说天空就是个牢笼,而且是我们自己制作出来的。最后这一句更是加深了这个意思,“而且,我们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我们不仅制作了这个天空,而且时刻牢牢地放在心里。这就非常地悲剧了。天空广阔无边,本来是栖居的地方,而如今,我们把它制作出来,却成了限制自己的牢笼,成了“坐井观天”的那一片天。
我们为什么、凭什么制作了这个天空呢?无知和狂妄是我们制作这个所谓的天空的根源。我们的无知和狂妄既来自自身,也来自他者的洗劫,使我们在匮乏和不自觉中制作了自己的“天空”。我们在自己的天空下自以为是地活着,却不知道它是一个牢笼,世代相传,心安理得。
吴投文:用寥寥三行完成一首诗的厚度
见过诗人梁晓明几面,也读过他的不少诗,其人其诗都给我非常信任的感觉。他的这首《穹顶之下》倒是第一次读,感觉非常诧异,此诗应该算不上梁晓明的代表性作品,但反复细读之下,又觉得此诗深有意味,值得细细琢磨。
我的诧异在于,标题“穹顶之下”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诗却只有寥寥三行,这对我的阅读惯性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按照我固有的想法,这样的大题目需要充分展开才是,是该有一定长度的,在一个视野阔大的时空里展开想象。此诗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寥寥三行完成一首诗的厚度,把读者带入开阔的想象空间。
此诗的成功之处是对天空的象征性转换。我们头顶看得见的天空并不是诗人全神贯注的聚焦点,诗人的聚焦点是我们心里那个看不见的天空,这样,从自然的“天空”到象征的“天空”,在诗中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转换了。限制我们的并不是头顶的那个天空,而是我们心里所赋予意义的那个天空,或者说是一种心理习见,一种固化思维。自然的天空固然可以限制我们的视觉,却无法限制我们的想象;我们心里的那个天空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像一个人的固化思维一样板结,是极其不容易突破的。可怕的是,我们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心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狭隘的天空,这不正是我们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吗?
梁晓明的这首诗写得异常简洁,诗中也没有使用繁复的技巧,却在简洁中包含并不简单的意味。有人提倡“三行诗”的写作,梁晓明的这首三行短诗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典范。但一首诗的完整不在其短,而在诗意和结构的圆融上,否则就是一个片段而已。实际上,穹顶之下并无新鲜的事物,关键还是要找到恰当有效的表达方式,把一首诗的完整性体现在诗意叠加的厚度上。
向卫国:前科学时代的想象力对诗歌文化的有效性证明
这大约可算是一首极简主义的诗歌,此类诗歌的特点就是极尽最大可能地进行思维和思想聚焦,其聚焦点则可以有多种,一个真理、一个思想、一个瞬间的奇思或者感受,等等。这首《穹顶之下》可说是在现代科学知识的观照之下,对于人类的一个原始想象的还原,说是解构亦可。
前科学时代,大量的自然对象人类都无法解释,其中也包括了本诗涉及的“天”。“天” 之高远、广大、神秘、变幻等属性让人惊异,神往与恐惧并存,爱与恨相交织。直观上看,“天”永远在上方,与“地”对应,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关于“天”的想象,比如天圆地方等等;在想象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关于“天”的种种概念,天神、天公、天道、天理、天子,而作为一系列概念之“公因数”的“天”则愈益抽象,最终成为一个哲学范畴,尤其在中国哲学中,它还是最高范畴。中国思想大抵都出于对世界实体的感受,并没有(或者很弱)西式的形而上学之维,所以中国的道家之“道”、理学之“理”、心学之“心”,约略都等同于“天”,亦同于“自然”。
但是,科学早已告诉人类,古人关于“天”的想象是错误的,“天”也并不只是在上面,而是在四面八方。但人类的文化记忆却是顽固而坚韧的,即便我們知道没有那个神秘的“天”的存在,或者说“天”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天,我们仍然不会放弃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最初的想象,诗歌更不会——即使有了梁晓明的《穹顶之下》这首诗,也还是不会。
不仅如此,古代中国人讲“天”,现代中国人在明知“天”不存在,而且“天”所指的自然对象也并非“空”无一物的前提下,仍然相信它的“空”。所以在大多数具体的场合,再次发生了词语的转换,用“天空”(天—空,天而空也,类似那个生“有”之“无”或生“无”之“有”)一词取代了古代的“天”。可见,我们真的是“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
周瑟瑟:诗由心生,自我启蒙
南人北相,杭州人梁晓明有着粗犷的面相。有一年我与他来到鄂尔多斯响沙湾,坐在茫茫大漠下,天空压得很低。他宽阔的面部燃烧着一圈美髯,乌黑的头发卷起,浓眉亮眼,我想他的肝一定很好。他是一个心肠宽厚的男人。透过敞开的衬衣,隐隐约约可见胸膛的绒毛,总之此人雄性力比多旺盛。
我私下以为柔弱的人写阴柔的诗,阳刚气质浓烈的人写阳刚的诗。梁晓明在壮阔的雄性荷尔蒙中加入了心细如针的生命体验。
《穹顶之下》如一道闪电,短短三行直插入“心里”。“不是天空限制了我们/而是我们自觉有一个天空,/而且,我们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感性与理性是诗的双翼。梁晓明的诗首先来自感性的认识,诗诞生于感性,诗由心生,有一颗什么样的心至关重要。
《穹顶之下》无小事,梁晓明写出的是一首大诗。事关自我的解放,这是梁晓明给出的一个大命题。“不是天空限制了我们/而是我们自觉有一个天空”,终于发现我们虚构了一个天空来将自我囚禁,诗人揭示了人性的弱点。“而且,我们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这就是现实的局限,更是人性的荒诞。
梁晓明建立《穹顶之下》的自我的诗歌空间,如一件人类受虐的当代艺术。40多年来,当代诗歌与当代艺术同步更新自我的能力,强调自我启蒙的能力。
《穹顶之下》突破自我认知,试图进行自我启蒙,这是当代诗歌的任务。没有了古典诗歌与古典艺术那样的写实,当代诗歌回到了人类生活本身。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诗人是自在的,没有受到古典诗歌、现代诗歌的限制。这是一种心如止水的自由创作,无视诗歌的标准与边界。
当代性是诗歌本身的镜子,不是形式和边界的问题,而是获得打动心灵的力量。梁晓明建立了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仅仅三行,我认为他建筑了有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短小的形式去挑战一个巨型的“穹顶”。抛弃原有的权威,拆除诗歌的围墙,在创作过程中什么手段都可以选择运用。鄙视诗歌的流行趋势,让当代诗歌放松了自己,给诗歌松绑,回到“穹顶之下”。
内心的感受最为重要。感性如气流托起诗的重量,让诗飞起来。而理性让诗平稳着陆,激情不是诗必需的。理性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宫白云:对有限的确立和无限的打破
穹顶的意思是穹形的屋顶,中间隆起而四周下垂成拱形。它像天空又不是天空,天空无限,穹顶有限,它具有自身的限制。诗人梁晓明的这首《穹顶之下》把日常的一个“穹顶之下”的联想,神奇地与天空的抽象思考嫁接在一起,从中发现了无限与有限的哲学关系。虽然仅仅三行,容量却极其阔大深厚,意境深邃高远。该诗可阐释的东西很多,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思维与理解获得与自己相关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的诗可遇不可求。个人感觉此诗精妙地阐释了“穹顶”与“天空”,有限与无限,把“穹顶之下”的天空写得可以触摸到它的跳动,而诗歌的功效就是让读者能够真切地去感受。天空再大也超不出人们的视野,穹顶再小也有边界。边界之内才是“我们”那个更具体的自觉的天空,诗人以“穹顶”的意象为我们诠释了那个可以“放在了心里”的天空所在,它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像天空只能看,只能感知,却不能搭到它的邊界。如果把诗中的“天空”看作人生,那么穹顶之下其实就是对人生的一个截取,天空浩瀚无垠,人生短暂有限,能够截取到自我的天空并“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就是对人生最好的交代。虽然穹顶之外有更广阔、更不为人所知的天空,但穹顶之下才是真实可把握的现实世界,它见证着人世间的熙来攘往与百态人生。能够把握住“穹顶之下”那片自觉的天空,把自己渺小的人生实实在在度过,才是对有限的“自觉”的那个天空的确立和对亘古就存在的无限天空的打破。
赵目珍:单刀直入与破除惯性
这是一首以议论方式建构的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讲,议论性的写作容易陷入说教和讲道理的路数,使人产生厌恶心理。但是高明的写作者会以高明的方式弱化或者化掉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和宋诗的建构理路完全不同,然而宋诗之所以能够于唐诗之外另辟蹊径,自然有其“体格性分之殊”。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就明确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可见在诗歌写作上,以“筋骨思理”取胜也是一种常见的路数。梁晓明的这首诗即是以思理取胜。其实,自诗歌诞生以来,主情与主理的两种模式即已形成,此诗自然也不必说是沿着宋诗的路子来的。这是诗人建构诗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关于这一点,不再申述了。
虽是思理取胜,这首诗还贵在单刀直入,而不是迂回进入。与“文似看山喜不平”的心理模式相似,很多人认为诗歌也应该写得委婉,而不能直接裸露诗人的情思或者理性。当然,这样的议论也是老生常谈了。古今中外直接破题的经典诗歌也数不胜数,拘泥一隅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诗歌直接点题,宣示令人省思的道理,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写作路径。只要它能够击中阅读者的内心,其它都无足轻重。
不过,此诗虽是单刀直入,但仍有其打破惯常思维的一面。对于司空见惯的“穹顶(天空)”,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异样的思考。梁晓明却能够从日常事务中去发掘一些新异的东西,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遐想”。从正常的思维来讲,“天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支配着人类的存在,它的存在在无形中是限制了我们的。然而诗人不从这一惯常性的思维探入,而是直接进入“意识”的层面,做翻转思考。深入想想,这恰恰是一种本质性的或者说根本性的思考。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建立在人类现有的认知之上的。我们怎样认知这个世界,这个被认知的世界就怎样来限制我们,从而进一步构成人类意识的“牢笼”。而且你越是执着于此,这“牢笼”就对你束缚得越紧。梁晓明对“天空”的思考,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他的思考为我们重新认知“天空”,为我们探索人类如何更好地存在打开了一个豁口。它启示我们要摆脱现有认知的局限,去进行更为广阔的庄子式的精神逍遥之“游”。
张无为:哲思即天律
梁晓明《穹顶之下》只用一个半复句就高度梳理并确认出了某种天律。你可以说这是先验的,或是“唯心”抽象的,但不能否认此类设定的意义,因为人的判断标准大多如此。
这个复句结构是先并列,再递进,由此完成浓缩语言逻辑的诗意哲思。其核心是围绕人与天的关系,感悟出“时刻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的诗性判断。首句是对共识的有意再强调,这个“天(空)”一方面契合“天高任鸟飞”,另一方面又与 “无法无天”相对。次句基于天空的自在与空无,强调人的自为,即人的心中应自觉有这个自在的空无。“天空”这个词既悬在每个人的上面,又是比海更可包纳一切的空无。尾句用递进语气强调把这个天空放在了心里,既要“时时刻刻”又要“牢牢”。
诗意蕴藉微妙潜含,不只是出彩之处,更是哲思再发现、真理再确认。一、理性显示出自由自在发展的主题。大凡在穹顶之下,对每个人来说,天必然有,但并非是限制,也不能限制。二、强调人们必须从主观上依据逻辑性认同,将原本不限制我們的天空时刻牢牢放在心里。三、限定“天空”存在同样是假定的,一如康德确认的上帝。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也便于共识,容易体验。
高亚斌:一个被赋予的天空
梁晓明曾经是先锋诗歌的代表诗人,在《穹顶之下》一诗中,诗人没有过多地考量修辞和专注于诗歌情境或意象的建构(尽管“天空”在这首诗里是一个意象,但诗人更为倚重的并不在此),而是避开了不必要的饶舌和辩论,单刀直入地介入了诗歌的主题——是什么限制了人。
诗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揭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认知误区,甚至是一个思想盲区——我们头顶的这个“天空”(或是“穹顶”)并不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而是被赋予的:一代一代的人都接受了“天”这个存在,而无知或无视人们肉眼所看不到的更加浩大和黑暗的茫茫宇宙。一个天空所制造的宇宙的假象,覆盖和遮蔽了几千年来人们的认知,造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信息和认知茧房,这是多么令人为之惊讶的一件事!
在生活中,束缚和桎梏一个人的事物太多,时代、地域、家世……都可能成为我们思想的围栏。但归根结底,束缚一个人的是他自己,是一个人的知识、阅历和眼界,他的思想和各种观念构成了他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之下,每个人都成了井底之蛙,人的一切愚蠢的错误,都跟这个“天空”有关。于是,如何摆脱认知的阈限,来一个“无法无天”的大胆超越,成为自古以来挑战着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的所有发展进步,无不与此相关。
但反过来说,也许正是由于人们“把这个天空牢牢放在了心里”,我们才有了蔚蓝苍穹,才有了浮云千古,也才有了月明千里和遥远星空。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限制了我们的,同时也在成全着我们。对于井底之蛙来说,它的见识固然浅陋,但正是由于少了一个扰攘世界和烦恼人间,它才找到了一个自洽自足的精神空间,而不去艳羡井底之外更加目迷五色的花花世界,幸耶否耶,谁又能够说得清呢。
《穹顶之下》继承了现代诗歌诞生之初的“小诗”传统。小诗之小,在于能够以小见大,于尺幅之间展现千里。它如同冰心所说的“零碎的思想”,能够锐利地折射出世界的本质,因而,时至今日,“小诗”的传统不绝如缕。只是,任何一条路,如果走的人过多、过于拥挤,风景就会受到削弱,这是包括“小诗”创作在内的所有写作面临的一个瓶颈和困厄。
徐敬亚:不是小诗,而是大诗,而是发现
早在37年前的1986现代诗大展上,梁晓明那首《等待陶罐上一个姓梁的姿态出现》就令我为之一震。当年24岁的浙江青年亲切而玄秘的词语,几乎成为“大展”中最美妙的标题。之后的多年,中国陶罐上一直浮动着这位梁姓诗人的身影……而今天我们读到的《穹顶之下》,显然属于他的另类、沉稳的烧脑“姿态”。
假如人类有100种自我压抑功能,那么现在应该有90%都被发现了。在未被明确发现的阴影中,至少有一种自我制造虚假天空的“自我限制癖”应该属于梁晓明的专利,当然必须包括他使用了“天空”作为中介,也包括他使用了和柴静纪录片同样的标题:《穹顶之下》。
发现,不是一个小词儿。对于诗,创造很大。但对于整个人类,发现更大。
因此这首诗不是玩弄词句的人能写出来的。这是直面人生之诗、哲理之诗、痛切之诗。
这种发现之诗无法依靠修辞的手法推演出来,它的要害是精准。阅读的时候,我在每个文字中都感到了准确——这些词包括:限制、自觉、时刻、牢牢、放……它们并不优美,均非饱含诗意之语——但它们凭借着瘦瘦的、并不美妙的身段重新构建了另一个小号的天空——40个汉字、词语们共同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哲理发现——诗意突然涌了出来!
人类已经低着头思考了几千年,寿命只有百十年的人们,一生能有多少发现?
发现,那是超越诗意的巨型方程式,其中可以代入多少蒙昧、多少囿囚、多少自虐的屈辱……
霍俊明:如何面对一首“短诗”而不是夸夸其谈
梁晓明的三行诗《苍穹之下》几乎给所有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都知道,诗歌篇幅越小,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关键——而且二者之间尽量要呈现反比,无论是从诗歌技术还是思想载力来说都是如此。
在这首诗中诗人给出了一个选择,或者说是一种可能。“不是”与“而是”以及“而且”之间,诗人所强调的正是“心学”,强调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一首极短的诗歌,我想并不需要评论者给出长篇大论,只需要从关注的一点出发即可,可以不计其余。就梁晓明的这首诗,我们可以推而广之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从古典诗学到现代诗歌,诗人该如何在“限制”之内有效扩容,如何有效而完备地去完成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