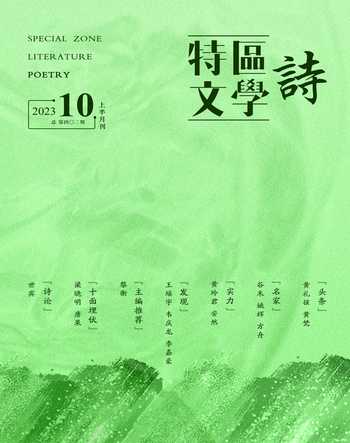构建诗歌新精神让日常事物闪烁人性之光
黄礼孩以诚实、美、热爱为三原色,
用拓扑等价原理重构诗歌精神,大大拓宽了现代汉诗的疆界。
诗集的不断出版缘于写作者与阅读者达成的某种不成文的约定,诗歌阅读成为诗人存在的范式。这么说来,黄礼孩出版诗集也是对诗歌不时的更换和穿行,就像多米尼加评论家乌雷尼亚说的:“现在我们踏上了通向那复杂的宫殿、通向我们文学渴求的令人疲倦的迷宫之旅的边界,寻求我们独特而纯粹的表达。”《我的地理的光明旅行》是一本穿越式的走出迷宫的诗选集,全书109首诗,除了一部分是新作外,大都选自《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我爱它的沉默无名》《一个人的好天气》《热情的玛祖卡》《抵押出去的激情》五本诗文集,涵盖了黄礼孩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7年之间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不但可以展现整体风貌,像阅兵一样检阅创作成果,还可以窥见他的创作嬗变过程。诗集的名字套用集里一首诗的题目,却也能体现他的创作调性——光明写作,甚至道出了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旅行。黄礼孩喜欢旅行,本诗集的行踪只是他游历过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御宅族咋舌。我按图索骥简单勾勒一下,国外(包括国家和城市)有波兰、挪威、爱沙尼亚、芬兰、朝鲜、缅甸、曼谷、新加坡、圣彼得堡、赫尔辛基、佛罗伦萨、威尼斯、都灵、布拉格、巴黎、汉堡、慕尼黑、卡塞尔、卡塔尔、里斯本、格拉纳达、马德里、巴塞罗那、直布罗陀、托斯卡纳、纽西兰、法罗岛、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欧洲之角;广东省外的国内地点有北京、澳门、西藏、稻城、陇南、喀纳斯、青藏高原、香山、甲乙村、石榴村;省内有沙面、水荫路、农林路、莲塘村、麓湖、逵园、东风公园、珠江新城、雷州半岛、西关、黄埔、花地湾、光孝寺,等等。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黄礼孩也保持了同样的谨慎,因为他清楚自己只是旅行,不是漂泊。旅行是有目的地的,有归期的;而漂泊不知道要去往哪里,无法预测归途,心态自然不同。他的旅行不再以观赏地理学的风景为中心,而是转向关注看不见的风景,具有精神与美学的双重启示性的意义。诗人作为精神王国的统治者,每一首诗都是他的一块领地,版图的大小取决于他的认知能力。如果说佩索阿是“乘坐身体或者命运的火车”“从一天去到另一天”,在时间世界里旅行,那么黄礼孩则是“道路在翻飞”“世界”“从我旁边侧身走过”,如果说旅行的地理是一个表意文字,那么黄礼孩让诗歌文本继续旅行,诗歌中的空间结构与内部心灵结构一起提供了隐喻,就连虚构也提供了新的想象维度。
黄礼孩认为,诗歌充满种种可能,修改诗歌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和发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本诗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有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许多作品做过修改,有些小改,有些大改,有些几乎是重写。《傍晚》原本是一首小长诗,后来只留下最后一则,变成一首只有八行的短诗,有点像徐志摩把《沙扬娜拉十八首》删去前十七首仅留最后一首的做法。《海》《纽西兰》《四月的另一半》等作品作了重写式的修改。在修改诗歌的态度上,有两派意见,一种是固化派,一种是生修派。固化派认为,一首诗的诞生犹如一个婴儿的诞生,一旦离开母体便完成了使命,写下即完成,不可改,不应改也無法改,好坏都已成为历史。生修派则认为,诗歌一经诞生便进入共生共长的世界,差诗会悄悄蔫掉,好诗会继续生长流传,必要即该修改,自己可以改,别人也可以改。庞德修改艾略特的《荒原》就是典范。李白的《将进酒》《静夜思》、张继的《枫桥夜泊》等诸多经典古诗,在流传过程中都留有后人修改过的痕迹。黄礼孩舍得忍痛割爱,敢于痛下狠手,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歌有苛严的要求,不见唯一之词绝不善罢甘休。诗人李白云说黄礼孩在诗歌里旧货翻新的能力强大,他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国内几乎无人能及。
我与黄礼孩的交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一路走来,看着黄礼孩成长为黄礼孩。如今,黄礼孩已是中国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研究他的文章已不胜枚举,尽管与他熟悉,他的文本让我清醒,但他是流动变化的。最近想为他写文章,在我有限的阅读里,该如何写呢?
我见过黄礼孩的身份证:1975出生。他的出生地是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徐闻小苏村,那是“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地方,就像他诗歌中写到的“里斯本”的寓意。在家乡“菠萝的海”,他度过了苦与乐、忧与喜、乖与顽、明与暗同在的童年。小时候,奶奶常常带他去教堂做礼拜,他似乎在懵懂中体会到最初的灵性。除夕夜,妈妈让兄弟姐妹们赤脚走在地上,感受地气,感恩大地,迎来新的一年。那段丰饶的童年时光是他一生解读不尽的往昔岁月。浩瀚的大海、威力无比的台风、起伏的菠萝地、小动物与野花同在的田野、高起来的教堂,都成为他的精神家园里无可替代的元素,乡土经验构成他精神成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湛江念完高二,他就提前考来广州上学了,毕业后又留在城里工作,三十年的都市生活令他的诗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歌成为他的志业。
哈代说:“将来总有一天,整个自然界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无华的卓越之处,才能和那些更有思想的人,在心情方面,绝对地和谐,这种时候即使还没有真正来到,却也好像并不很远了。”哈代的理念在黄礼孩的诗中是信仰般的存在,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大自然中发生在细小事物间的感人细节,以躬身向下的姿势获得超自然的爱和人性之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东西方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手法不尽相同,甚至有云泥之别。东西方都是把自然精神化的同时,又把精神自然化,以达到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自然的神秘蕴含着人类的想象与体验,在主客观上高度统一无法分离。但是,东方是以“伦理学”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西方则是以“数理学”为中心的“镜像关系”。东方讲究文以载道,西方讲究人本精神,中间隔着一道难于逾越的鸿沟。黄礼孩在《秋日边境》中写道“一朵花开出好天气”,看似平淡,实则天工自然,意味深长。看似写“花”,实际上是写“人”,看似聊“天气”,实际上在谈“心情”,一个“好”字,境界尽出。既是东方的“天人合一”,又显西方的“镜像关系”。黄礼孩经常通过改变词语的秩序去调整读者的心理结构,使审美产生陌生化的同时,又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他不写的部分。“树穿过阳光/叶子沾满光辉”(《飞扬》)“在海岸线漫步久了/身体里的日子也排列成波浪”(《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我认得出银杏/以及银杏背后的光芒/像多年前你眼中掩不住的喜悦”(《北京》),这既是诗人的语言态度,也是审美观念。
黄礼孩是被缪斯眷顾过的人,鲜衣少年时就有诗名,未及弱冠风神俊朗之年就有诗集问世,刚过而立之年就有诗歌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现在,他集诗人、诗歌行动家、编辑家、评论家、评奖家、装帧设计家、创意导师、客座教授、策展人、影评人、作词人、文化形象大使等众多衔头于一身,衔头多到估计他自己也一时难于搞清,在这个时代,像他这样用诗歌的力量去影响世界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当然,他最看重、最在意的还是诗人身份,他所有的力量几乎都与诗歌有关。他一直坚持主流与非主流并行不悖,文学杂志时不时以头条的方式批量推出他的作品,民刊也以推出他的作品为荣。三十多年来,他从未中断过诗歌写作,却不是高产诗人,平均每年也就只有二三十首,也许他用在艺术随笔上的时间多于诗歌创作的时间,编杂志也耗去他大量的精力。早期的黄礼孩,深受国内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影响的同时,也受国外聂鲁达、蒙塔莱等人的影响,与同时代的诗人一样,不可避免地依赖传统型的隐喻和象征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正如普鲁斯特受益于罗斯金,博尔赫斯受益于斯蒂文森,金斯伯格受益于惠特曼,九十年代末,黄礼孩受好友东荡子的影响,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之后又受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等人的影响,特别是在2014年前后,受忘年交扎加耶夫斯基的影响,他的创作理念再次发生方向性的改变。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虽说黄礼孩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但绝对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这个南方身材,阳光肤色,发型有艺术家气质的觉醒诗人,是个不烟不酒不牌的大忙人,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应不完的酬,总是脸带憨笑乐在其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将成为历史,70后诗人作为时间概念上的诗歌群体,已被时间推搡到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审美与精神还未被定义,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当代汉语诗歌,他们的诗歌都会契合时代的心灵。
从新诗的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黄礼孩写下《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时,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为了便于叙述,姑且称之为“改革纪元”,有慧眼的人把它选入大学教材,加速了其经典化进程。虽然“朦胧诗派”把诗歌从宣传工具纠回到人本艺术的轨道上来功不可没,但是,他们仍然深陷在时代的困局之中。第三代诗人虽然部分做到了奥登说的“避免读者像对待婴儿的安慰毯子一样,紧盯着共识和固化的意义,做到滑稽、精力充沛、不循规蹈矩,保持放肆的权利。保持愤怒,敦促读者清醒”,但他们的诗歌带给读者有多少丰沛的生活,却没那么乐观。对于第三代之后的“70后”,他们是最可塑的一代,因为他们写作的起步,前有基础,外有标兵,后有追兵,又遇上中西碰撞,壮怀激烈的时代。从赤贫到小康、从孤岛到大数据、从人工到AI,这些经历逼使他们无法自我膨胀,不敢自以为是,当然也不至于陷入绝望,他们在不卑不亢中觉醒,敢于直面未来。黄礼孩一首《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接过朦胧诗一代的火炬,当意识到“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时,敢用“我要活出贫穷”的勇气打破时代的闷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的姿态,奔跑在“丛林在飞”的路上,全诗生机勃勃充满力量,大气磅礴地体现出一代人的精气神,写出一个时代的情绪特征,成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文本。“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芥川龙之介一句自带嘲酷却又让人无法抗拒的话,让很多人记住了他们两个人。其实,有时候,一个意象也能让很多人记住一个诗人,就像“坛子”之于史蒂文斯、“风声”之于勃莱、“麦地”之于海子、“漂木”之于洛夫一样,“闪电”也让很多人记住了黄礼孩。当然,从诗歌艺术成就层面来看,《谁跑得比闪电还快》不是黄礼孩最好的诗,正如入选课本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乡愁》这些诗歌,肯定不是西川、海子、余光中最好的诗一样,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征候,具有春风化雨可润心田的教化意义。
从诗学意义的层面来看,黄礼孩把普世精神以本土化的方式带入现代诗学,有望成为新传统。我国诗学自古以来都是以儒家精神为基石,唐时的李白和王维分别把道家精神和佛家精神带入诗学,丰盈了古典汉诗的精神传统。我这里所说的是诗歌,千万不要误解为宗教。佛教在我国本土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六祖慧能,跟王维没有任何关系。以禅入诗,王维肯定不是第一个,但是别人只是把禅写进诗歌,只有王维把禅带入诗学,成为诗歌的新传统。由于诗与禅在精神与形式上高度契合,诗人与僧人又常常诗禅双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往往诗偈难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閑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的这些句子,是诗不是偈子,是充满禅意的诗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慧开), “终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无尽藏),这些句子,是偈子不是诗,是充满诗意的偈子。这是宗教与诗歌的区别,是从能指与所指的维度进行辨认,是以“说了什么”而不是以“说什么”“怎么说”进行区分。施奈德把寒山的《人问寒山道》等24首诗译成英文诗,深深影响了美国垮掉的一代,成为精神导师。我认为,不是寒山的诗影响了他们,而是诗中的“禅”影响了他们。
普世精神由来已久,并非新鲜事,以宗教原式进入我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以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方式进入我国少说也有上百年,以本土化诗学的方式进入汉诗却是新近的事。把创世纪、失乐园、复乐园等元素或者意象写进现代汉诗表达普世精神的早就大有人在,黄礼孩肯定不是第一个,但是别人只是带入诗歌,黄礼孩却把它带入诗学。黄礼孩以虔诚、仁慈、美善、眷恋、感恩等方式来获得内心安宁,寻找世俗的欢欣和超自然的安慰。
面对现实,黄礼孩保持一份宽容的清醒,做绝望世界里爱的使者,让爱在众声指责过后回到人间。叶赛宁说:“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那么,这一生怎么过才值得?阿德勒认为:“没有一个人住在客观世界里,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各自赋予其意义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一个诗人展示给读者的世界,并非诗人生活过的世界,而是诗人审美过的世界。黄礼孩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拥抱世界,用希望去治愈绝望,通过生活中光亮的细节来展示人性之美和力量。他善于以朴素胜高明,以柔软胜刚强。他的《没有人把鱼放回大海》,让我想起美国诗人毕肖普那首著名的篇幅有点长的《鱼》,该诗从“我捉到一条很大的鱼”开头,到出人意料地“我放了那条鱼”结束,一个闭合式的结构,一个思想情感的变化过程,但她的目光始终聚焦于那条鱼身上,不曾游离在这条“鱼”之外,以散文化的手法在细致入微的描述中升华感情,从而产生巨大的张力。黄礼孩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选择一个截面而不是一个变化过程,把目光放在“鱼”之外,说东言西,在平静客观中揭露人性之恶,悲悯而不刻薄,闪烁着人性之光。
现代诗人都喜欢写光,主要是出于对抗黑暗的需要,但几乎都是从词语到词语,而不是内心拥有光明,所以读者感觉不到光亮。那些光是无源之光、虚幻之光,无法唤醒读者内心的人性与尊严。黄礼孩说:“写作是采集光的过程,我用光照亮自己。”因为他内心有光,或许源自大自然,或许源自内心激发出来的信仰能力,所以读他的诗会让人觉得温暖、温馨、充满爱。“窗子被阳光突然撞响/多么干脆的阳光呀”(《窗下》),“词语中的灯塔重新亮出强烈的信号”(《灯塔》),“一地的叶子/多么奢侈的阳光”(《北京》),“世上还有另一个地方/离你不远不近/恰好是一片月光的距离”(《距离》),“我听到大海/被火焰不断传唱/呵,是什么让我变得如此激动”(《传唱》)。黄礼孩诗歌存在的光,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一样,他尝试在已知事物、未知世界及新灵性事物之间做转化与融合,感受人类灵魂微妙的震颤,去填补灵晕中心的空洞,将灵魂引向纯化。
谈黄礼孩的诗歌创作,就不能不提完整性写作。大概在2003年前后,针对当时盛行策略性写作和功利化写作的情况,黄礼孩、東荡子、世宾等人提出了完整性写作,得到蓝蓝、陈超、代薇、浪子、安石榴、梦亦非、黄金明、沈苇、古马、哑石、张执浩等众多诗人的响应。完整性写作不是一种流派主义,而是一种诗学主张,是把尊严和良知再神圣化的写作,是不断消除黑暗的光明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保守现代主义者,是对激进者进行盲目扩张的批判,是对远离人本价值的一次纠偏。这里所说的“保守”并非贬义词,而是与保守自由主义的“保守”一词同义。他们一方面要求诗人觉醒,作品要具有现代性意识;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的写作划定界线,不至于偏离传统的神圣价值太远。世宾是理论阐释者,东荡子是境界开拓者,黄礼孩是美学传播者,他们三人也被称为完整性写作的“三剑侠”。在黄礼孩看来,万物有灵,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都有它自己的美学。他把激情与时间倾注在喜悦的事物之上,再通过诗歌把审美呈现出来。他编办《诗歌与人》、举办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策划广州新年诗会,无不显扬完整性写作的美学主张。黄礼孩按照自己的审美方式进行判断筛选,以“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为媒介,把当下心仪的大师的诗歌整体介绍到中国来,并想方设法邀请他们到中国来访问交流。丽塔·达夫、扎加耶夫斯基、西尔泰什、阿多尼斯等人的到访引发不小的旋风,这令人忆起当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一起陪伴的场面。黄礼孩试图通过与不同语种之间的巅峰交流,把新思想带入汉诗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汉诗的新成果。不可否认,近二十年来,诗歌界的翻译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前的单向输入翻译到现在的双向互译,我国有不少诗人的作品译成不同语言输出到世界各地,译作数量庞大,但是反响平平。我们应当自省,中国诗歌作为世界诗歌的结构性的他者存在,中国诗人能为世界输出什么样的诗歌精神和诗歌美学,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爱伦堡曾感叹:“写诗的人很多,诗人很少。”他说的也是我们,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黄礼孩以诚实、美、热爱为三原色,用拓扑等价原理重构诗歌精神,大大拓宽了现代汉诗的疆界。他以在场者的身份做精神边缘的观察,通过自己的诗歌实践不断定义诗歌之于生活的含义,让诗歌展开未被发现的丰富性,去消解时代的仇恨,宽容世界的不完美。他用活性的语言处理当代生活中的纷乱、嘈杂、异化、荒谬,写出陌生、神秘、美妙的作品,用充盈的审美让日常事物闪烁着人性之光,向生活提供意义。
温志峰,笔名老骞,广东紫金人,写诗,兼事译诗,著有诗集《如此固执地爱着》(合集)《谁的语言打碎桌上的杯子》,译有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集《使命》,庇山耶的诗集《滴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