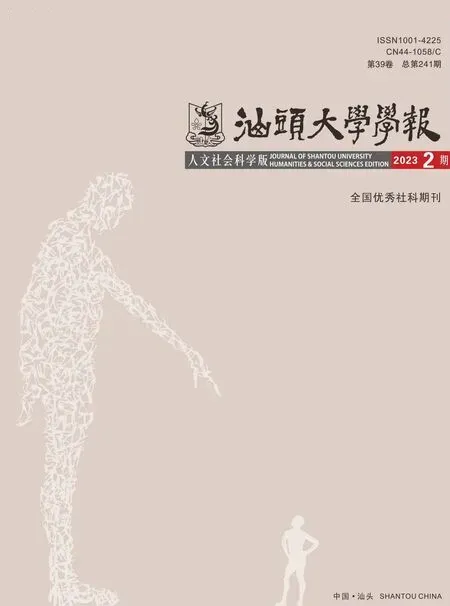以朱子论“中”观其“万物一体”
魏子钦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陈荣捷以“中字六说”认定“中”居于儒家哲学的核心地位,不仅依此判定“三代以前‘中’字为思想热烈讨论之点”,也认定“中”字“贯乎(儒家)经籍之中,可谓盛矣”[1]。从儒家哲学发展史看,作为“集孔子以下集学术思想之大成”[2]23者,朱子对“中”字也有鞭辟入里之发挥。关于学界对于朱子论“中”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方向。一是概念解析,陈来先生以朱子理学的“已发未发”[3]阐明“中”背后的朱子心性论;二是经典诠释,张立文先生以朱子经典诠释为内容,提出“伦理道德”[4]234的理学思考;刘学智先生也从经典诠释入手,讨论朱子与洛学及“关学关系”[5]的学脉继承问题。从上述研究看,朱子对“中”的理学诠释,主要集中在朱子心性论、朱子理学的传承问题,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对“中”的理学阐释,主要是从诠释方法、诠释内容、诠释视角进行展开,目的是通过对“中”的阐释落实“万物一体”的圣人之境。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朱子对“中”做出的概念界定、言语表征及其命题判断的理学诠释,透视由朱子论“中”展开的理学语言图景,揭示朱子对儒家之“中”的理学分析,期以展现朱子论“中”背后的理学境界。
一、以“跨越汉学”论“中”
“中”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集理学之大成”[2]23的朱子也曾论“中”。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6]19
从汉学角度分析,朱子对“中”的理解,并未借鉴汉唐经学的学术成果。在汉学的训诂中,汉唐经学家是以“大本”注“中”。例如《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郑玄注曰:“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7]1422孔颖达疏曰:“言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7]1424汉唐经学家对“中”的注释主要落实在人性、情欲上,认为“中”是“礼与政教生发与制作的根据”[8],是从礼由心生的角度进而解释王道教化的礼乐政治问题。
从郑玄到朱子,尽管可以说朱子接受汉唐经学家以“大本”注“中”的讲法,但也可以说朱子是从《中庸》本身思考以“大本”释“中”的诠释。而且,就算说朱子是借鉴汉唐经学家注“中”的学术成果,但是朱子也改变汉唐经学家的诠释向度。一方面,朱子以“未发”阐释“中”,认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6]20。另一方面,朱子指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6]20“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6]21朱子对“中”的阐释,并未采取汉唐经学家对“中”的训诂,也未专意于郑玄等经学家的王道教化问题,而是转向未己未发、天命之性、道体等理学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朱子在阐释“中”时采取“跨越汉学”的方式,是因为朱子不满汉唐经学家对《中庸》的注释。
“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中庸》)所传之要,以着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9]3639朱子认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因“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9]3639。所以,到了汉唐学者那里,《中庸》或是被用作思想比附,或是仅作通释考义。董仲舒、郑玄等“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9]3639,唐代“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中庸》),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9]3639所以,朱子认为真正得《中庸》之义是周敦颐、二程兄弟。从“道统”而论,朱子将孟子之后的汉唐学者对《中庸》注释与阐释之贡献加以剔除,以此确立濂溪、二程在儒家道统的正统位置,绘制一条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的理学道统谱系。
从学术继承看,朱子论“中”的理学阐释,主要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程颐说:“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中。”[10]160(《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颢也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10]122(《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对此,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6]17面对二程先生的学术思想,朱子并未紧跟先生之旨而亦步亦趋,而是认为“不偏不倚”“不过不及”与二程“不偏不易”稍异,即“以‘平常之理’(朱子)较‘正道定理’(二程)规模大。”[4]237不仅如此,朱子也吸收吕大临对“中”的认识,即“无过不及”和“不倚之谓中”。吕大临说:“圣人之学,以中为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也。”又说:“不倚之谓中,不杂之谓和”[10]608(《河南程氏遗书》卷九《与吕大临论中书》)。可见,朱子对“中”的阐释跨越汉唐经学的思想成果,在二程子、吕大临的理学建树上推进一步。可以说,“中”在朱子的理学阐释下也获得新发展。朱子曾说:
“中,一名而有二义。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9]548(《朱子全书·第六册·中庸或问》)
朱子认为程子论“中”有“在中之义”(未发)与“中之道”(已发)二义,是根据程子此说加以推进,认为“不偏不倚”即是未发之前的在中状态;“无过不及”是已发之后的中之道。在《朱子语类》中,朱子曾用“未发之中”与“随时之中”解释过“中”之二义。“至之问:中含二义,有未发之中,有随时之中。”曰:“《中庸》一书,本只是说随时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随时之中,缘是有那未发之中,后面方说时中去。”又言:“时中,便是那无过不及之中。”[11]1584朱子认为“未发之中”是“不偏不倚”、“随时之中”是“无过不及”。
从“未发之中”看“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是指不偏向任何一方,表示中立、公正。朱子曾言:“喜怒哀乐之未发,不偏不倚。”[11]1614从修养论出发,“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6]82“不偏不倚”代表一种内在平衡之“中”,可将其理解为“喜怒哀乐之未发”“不偏不倚”的状态,强调人不断修养而逐渐丰满内在之“中”,看做是一个内在于人心的且趋于无限的空间。
从“已发之中”看“无过不及”,“无过不及”是指做事情做的不过头,不会超过也不会不如,恰到好处。“学者要学得不偏,如所谓无过不及之类,只要讲明学问。”[11]245从文质论看,“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6]62从为学立场看,“若谓之中,则无过不及,无非礼之礼,乃节文恰好处也。”[11]2556可见,“无过不及”代表一种外在平衡之“中”,这在文质关系上强调既不能侧重繁琐之文,也不能偏向淳朴之质,而是要追求文质彬彬,恰到好处。
朱子对“中”的概念界定,不仅跨越以郑玄为重的经学高峰,也立足以二程为首的理学立场,在拓宽儒家论“中”诠释向度同时,肯定周敦颐、程颢、程颐在儒家道统地位,依此重建儒家道统谱系,完成对朱子理学合法性的确立与讨论。
二、以“理一分殊”论“中”
朱子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由于朱子弟子未能理解《中庸》之旨,朱子曾在《朱子语类》中,以“中”对《中庸》展开细致解释。
问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云云。
曰:“如何说晓得一理了,万事都在里面?天下万事万物都要你逐一理会过,方得。所谓‘中散为万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龟山之论,便是如此,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11]1594
“一理”散则包含万事,合则汇聚“一理”。“散”只是“一理”运动变化的中间过程,其最终目标是为实现“合”的豁然贯通。从运动过程看,“一理”的运动形式以“散”与“合”的形式呈现,它既可在万事万物中分化显现,又可在万事万物汇聚后合为“一理”。从学术继承看,朱子对《中庸》的阐释继承程颢的思想。《朱子语类》指出,明道谓:“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子语)“虽曰‘合为一理’,然自然有万事在。”[11]1713朱子在程颢、杨时基础上推进一步,以“理一分殊”完善“散为万事,合为一理”。故而,朱子得出以“中”为核心的语言表征:中行、中正、中和、中庸、中道。
“中”从外在礼仪看,存在“中行”的语言表征。“中行”出自《论语·公冶长》,主要指行为举止。朱子认为,由于孔子推行天下大道的愿望未能实现,便将此愿寄于后世,“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6]80在朱子看来,“狂士”的言行并不符合“中”,尽管志向高远,但容易超越“中”而沦为异端,无法顺利完成传道天下的大命。换言之,只有言行举止,才能守住“中”。只有做到“中行”的无所偏失,士君子才能顺利地得道传道。
“中”从内心存养看,存在“中正”的语言表征。“中正”主要指为行为规范,属于道德问题。朱子言:“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6]53朱子强调“中正”,即礼义规范要符合“中”,主张将“中正”之理应真切地应用在礼义,使其作为礼义的内在要求。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言圣人礼义之中正,过之者伤于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沦于污贱而可耻。”[6]252中正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规范,想要符合礼,就必须做到严谨且从容,和谐而有节制,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过或者达不到都是不符合礼的,否则就会失去中正,偏向一方。
“中”从未己未发看,存在“中和”的语言表征。“中和”讨论性情的问题,属于心性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6]20朱子认为心之“未发”则性,心之“未发”谓之中,若“未己未发”都合规则,便是端正,无所违背,便可顺天地之正气,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另外,朱子也认为“中和”是就内在性情而言的,但朱子谈“中和”多指圣人孔子,“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6]91“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6]98,“中和”这种看似轻松平常的愉悦状态,如孔子圣人才能精微体察。
“中”从不学不虑看,存在“中道”的语言表征。“中道”是指思想与行为相协调的内外状态,《中庸》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1]2996。朱子进曰:“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6]32朱子以天理阐释中道,认为中道是圣人气象的真实流露,并认为若欲实现“中道”,以学思并举通向成圣之路。朱子还指出,“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6]138,圣人教人学思并重就是以“中道”为内容,只是掣肘于现实,只能退而求其次,与时偕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6]120
“中”从涵养心性看,存在“中庸”的语言表征。“中庸”主要指礼义德行层面的问题。《四书章句集注》指出,“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6]21可见,“中和”偏内在性情,“中庸”言心性德行,故“中和”内在于“中庸”。朱子言:“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6]21可见,欲见“中庸”需回人伦日常之间,“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6]24
在《中庸》中,“中”散为万事,分化出中行、中正、中和、中庸、中道的理学言语表征,但这些理学言语表征又可复合为一理,其同一性归纳即为“诚”。首先,关于“诚”的内涵,朱子曾作解释:“诚,实也。”[7]19“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6]34其中,诚也有天理的含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6]32其次,朱子在揭示“诚”的同时,也展开对“实理”之诚与“中和”“中庸”之中的关系讨论。朱子言:“中和云者,所以状此实理之体用也。天地位,万物育,则所以极此实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实理之适可而平常者也。过与不及,不见实理而妄行者也。”[9]594朱子认为把握“实理”之“诚”是践行“中庸”“中和”的关键问题。“中和”是“诚”这一实理的体用义描述,“中庸”是“诚”这一实理的平常义运用,“天地位,万物育”则是发挥“诚”这一实理的境界展现形态。相较之下,朱子认为“过与不及”的两种状态,便是没有真切地认识“实理”的体用义、平常义与境界展现,反向突出“中”“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理学内涵。
从“诚”与“中”的关系看,朱子言:“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11]1588从内外关系出发,“‘诚’是‘中’的根本,而‘中’是‘诚’的外在显发”[12]的道理。在《朱子语类》中,也曾记载朱子与其弟子曾对话:“中庸既曰‘中’,又曰‘诚’,何如?”朱子答:“此古诗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也。”[11]1588可见,“中”与“诚”不仅体现内外关系,也是不同视角转折的一体两面,即以“理本体”为核心对“诚”与“中”予以阐释。所以,朱子从“理一分殊”论“中”,即揭示“中”散为“中正、中行、中和、中庸、中道”的理学言语表征,复合可为“天理之本然”的运动过程。
三、以“通权达变”论“中”
为指明“中”字之重要,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颐之语:
“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6]334
按朱子之义,欲真同情之理解儒家之“中”,须是注意“默识心通”。从空间位置看,中可以是指厅之中央,但从家看,厅之中便不再是中,中是以堂为中,而在国而论,中又有了变化。所以,程朱理学指出“中”的灵活性与变动性,表明“中”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故而需要“默识心通”,即通过求诸自我内在,以心领神会的方式获得“中”之义理。
从厅堂之喻看,之所以朱子强调“默识心通”,在于朱子十分注重儒家的“经权时变”。自儒家创始以来,就提出“与时偕行”“因时损益””等儒家经权观。从“经”的概念界定看,“经”在《说文解字》中:“经,织,从丝也。”段玉裁注曰:“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13]644朱子指出:“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6]39“经”就是常道、常则及大经大法。从权的概念界定看,“权”在《说文解字》中:“权,黄华木。从木雚声。一曰反常。”段玉裁注曰:“《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13]246朱子言“权”:“程子曰:‘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6]110可见,“权”是指权衡,即符合于“义”的衡量轻重、权衡利弊。最后,从经与权的关系看,
问:“经、权不同,而程子云:‘权即经也。’”(朱子)曰:“固是不同: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朱子)又曰:“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11]1061
朱子否定程子对经权关系的判定,认为经、权不同。“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11]1061不仅如此,朱子以道贯经权的同时,也对践行经权的主体做出说明。“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11]1064“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于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11]1061即“权”乃为圣贤方可行之、用之,朱子突出践行“权”的难度与高度。所以,“权”作为千变万化之法,朱子强调只有做到“默识心通”,才能把握“时中”,践行圣人之言,明晓变通,不为迂阔。总之,正因朱子领会儒家“通权达变”,所以在解释“中”字时,强调切不可流于文字表面,须“默识心通”,如比寻一厅、堂、国之“中”,须随时而论,亦如《孟子》言: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淳于髡)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6]265
孟子以权变回应淳于髡的诘难,认为男女不亲手递送东西是礼法,即经也。但若是此女子为嫂子,嫂子溺水不去救,便是枉为人;伸手去救助溺水的嫂子,是对“男女授受不亲之经”的变通。对此,朱子在孟子论证“权”的立场上,提出“权而得中”的说法,认为“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权而得中,是乃礼也”[6]265。换句话说,朱子认为“嫂溺援之以手”的说法,体现孟子“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的权变道理,即以“通权达变”论“中”。所以,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朱子以“盖权而得中,则不离于正矣”[6]268阐释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6]268。
紧接着,朱子在借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以“通权达变”论“中”的同时,又深化孟子所批评之“子莫执中”,确定“中”的诠释区间。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6]334
朱子判定“此章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一方面,朱子言:“杨墨之失中也,故度于二者之闲而执其中。”[6]334又言:“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6]334又引程子曰:“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着则不中矣。”[6]334朱子主张“权而得中”,这是指对“中”不应执一,而是应以权应事,从情境意识出发,强调根据具体情景做出符合“中”的选择。另一方面,朱子认为“不得中”“执中”遮蔽“时中”,有碍“中”的真意。“为我害仁,兼爱害义,执中者害于时中,皆举一而废百者也。”[6]334朱子认为杨墨二者因为不得中而皆失“中”、子莫执中而偏离“中”。杨朱“为我”过于利己而执于自身;墨子“兼爱”则是不分厚薄与亲疏,两者都没有在权变思想上践行“中”。子莫看似“中”,实则此“中”无“权”,此三者看似求“中”实则害“中”。《朱子语类》言“时中”:
问:“杨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讨个中执之。”(朱子)曰:“子莫见杨墨皆偏在一处,要就二者之中而执之,正是安排寻讨也。……”道夫云:“常记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义。这个中,要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异,与时中之中同。’”(朱子)曰:“然。”[11]1550
从“已发”看“时中”,“天地之中,是未发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时中。”[11]442另外,朱子对“时中”也有界定,“时中”是指“无过不及”,“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那无过不及之‘中’。”[11]904在此基础上,朱子指出“‘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若推其中,则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为‘时中’之‘中’。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11]1584朱子认为“中庸”之“中”是在“已发”范围的“无过不及”,其大旨核心在“时中”。“时中”内部包含的“中”,是指“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是“未发”之中。从体用关系看,“时中”内部包含的“中”是本体,即性情之中、未发之中;“时中”的这个“中”字是发用,即德行之中,已发之中。对此,朱子指出“时中”之“中”字也包含“未发之中”,即兼具内外,容纳“中和”。
朱子以“通权达变”锁定“中”的诠释区间,认为“不得中”、“执中”,皆是离“中”、害“中”。若想识得“中”字,须是“默识心通”“权而得中”,但是朱子也强调践行“权”的难度与高度,认为“权”乃圣贤方可行之、用之。所以,若能以“时中”随时应事,便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境。
结语
问“时中”。(朱子)曰:“自古来圣贤讲学,只是要寻讨这个物事。”[11]1629
“时中”,即“中”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朱子认为“时中”乃圣贤讲学之所在,故弟子欲学此圣贤道,须以“默识心通”儒家之“中”字,随时取中,“便无所用力,自是圣人教化如此。”不过,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弟子曾提出“致”是偏离“时中”的疑问。
问:“中有二义:不偏不倚,在中之义也;无过不及,随时取中也。无所偏倚,则无所用力矣。如吕氏之所谓‘执’,杨氏之所谓‘验’、所谓‘体’,欲致力于不偏不倚之时,故先生于或问中辨之最详。然而经文所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之一字,岂全无所用其力耶?”
曰:“致者,推至其极之谓。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学之‘致知’,论语‘学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贴者,有中垛者,有中红心之边晕者,皆是未致。须是到那中心,方始为致。致和亦然,更无毫厘丝忽不尽,如何便不用力得!”[11]1625
朱子弟子认为朱子强调“中”的“无所用力”。所以,朱子在其或问中,批评吕氏之执,杨氏之验与体,认为这些人皆是致力偏倚,是不得中、失中、害中。只是,从儒家经文看,弟子不解的是,为何《中庸》要讲“致中和”,要强调“致”之用力工夫。对此,朱子从极致境界解释“致”字,认为“推至其极”谓“致”,“致中”如同射箭射中靶心。“致和”如同无缝罅,盛水不漏。亦如朱子所言之“‘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11]1624。又言之“‘致中和’,须兼表里而言。致中,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缪,而又能无适不然”[11]1624。所以,“致中和”之“致”,并非是指工夫之极致,而是境界之极致,如此之“中”便是无所用力,故圣人以“时中”契入此道,深谙此理。可见,朱子以极致之境界解释“致”字,解开弟子对“致中和”是偏离“时中”的疑惑。
针对践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有位者而言,有朱子弟子曾问:“‘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11]1627可见,朱子对“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有位者的理解,不是以政治视角看待,而是以儒家仁学目光加以审视。《朱子语类》载:
元思问:“‘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朱子)曰:“孔子已到此地位。”[11]1627
朱子以有德者居之的“圣人之身”认定“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为位者,否定弟子以“政治上位”认定“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为位者,认为孔子以“圣人之身”实现“致中和”之效:即“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11]1626。孔子也以“圣人之身”实现“万物育”之效:即“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6]20由此,朱子进言“万物一体”。朱子曰:“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6]20朱子认为“万物一体”并未向外做功夫进以求取最高境界,而是复其己性之初。换言之,因万物均气而同体,故我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是以“时中”践行“为己”,在己之位行己之事,实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验效“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学,敞开“万物一体”的圣人之境。
朱子站在二程与吕大临的理学基础上论“中”,给出不同汉代经学对“中”的界定,认为“中”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与此同时,从“道统”而论,朱子以“跨越汉学”论“中”,朱子剔除孟子之后的汉唐学者对《中庸》注释与阐释,依周敦颐、二程论《中庸》重建儒家道统,呈现一条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的道统谱系。另外,朱子以“理一分殊”论“中”,生成出一系列以“中”为核心的理学言语表征,呈现出散为“中正、中行、中和、中庸、中道”之万事,复合为“诚”之一理的运动过程。其中,“诚”与“中”的关系是一山之两景,用朱子的话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诠释观念看,朱子以“通权达变”论“中”,强调“默识心通”,以“权是时中”批判杨墨“失中”子莫“执中”。按朱子之意,只有把握“时中”,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效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圣人之学,以“圣人之身”践行“天地万物自然安泰”的圣人之教,依此敞开“万物一体”的圣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