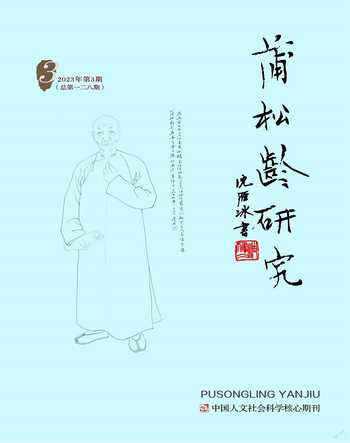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画”叙述
朱嘉璇
摘要:琴棋书画是明清时期文人游艺的主要方式,因而深得小说家的偏爱,成为明清小说中重要的叙述内容。《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凝聚了蒲松龄毕生的心血,他以超凡的文学功力与精深的艺术修养,借助“书画”叙述,构建出一个精妙绝伦的文本世界。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中“书画”叙述的特点与功能进行探究。首先,作为一门技艺,“书画”能够为读书人带来金钱、名利与富贵;其次,“书画”是文人适情娱志的主要手段,起到了沟通情感、增进情愫的作用;最后,“书画”的“传神性”特点,使其成为沟通虚实、连接画境与人境的媒介。
关键词:《聊斋志异》;书画;现实谋求;传情媒介;虚实相通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志码:A
明清时期,琴棋书画是文人游艺的主要内容,据嘉靖《昆山县志》记载:“(明初)士大夫游艺,当审轻重,谓学文胜学诗,学诗胜学书,学书胜学图画,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后。若琴弈,犹不失为清士,舍此则末技矣。” ① 古代文人长期浸润于儒家正统思想之中,治世理想往往通过承载着“道”的诗文来实现,因此,书法的地位自然要比诗文低一等,绘画、弈棋、抚琴更是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但不得不说,琴棋书画终究属于高雅的兴趣,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清小说家们多擅长琴棋书画,或以之治生谋食,或借其娱志适情,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游艺途径,如钟惺、祝允明、蒲松龄、曹雪芹、李汝珍等,他们小说中有关琴棋书画的叙事,便反映了这样的时代风气。
本文拟选取《聊斋志异》作为研究文本,将视点聚焦到“琴棋书画”中的“书画”这一点上,着重分析“书画”这一叙述对象在文本中的叙事特征与功能。《聊斋志异》中涉及“书画”的内容颇多,或作为主人公娱志适情的工具,或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甚或仅仅是一笔带过的描写,都无不体现出留仙先生精深的文学造诣和高雅的生活意趣。蒲松龄借助“书画”叙述,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情节性与审美效果,构造出一个光怪陆离而又精妙绝伦的“书画”世界。
一、“书画”叙述基于现实谋求
古代的读书人喜用书画、诗文互酬赠答,贫寒之士常卖文鬻畫以谋生计。毋庸置疑,书画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带来金钱、名声与富贵。明代杜琼《自题山水》写道:“纷纷画债未能偿,日日挥毫不下堂。郭外有山闲自在,也应怜我为人忙。” [1]48足以看出当时社会用书画作品充当礼物、商品的风气十分兴盛。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年轻时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前往扬州卖画,后来在写给从弟的信中回忆当时的心境:“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稼穑;实救困贫,托名风雅。” [2]118然而,无论少时臧否如何,写字作画终究作为一项谋生手段,帮助郑板桥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成就了他经久不衰的盛名。
《聊斋志异》中描写的多是人鬼、人狐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通常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只能依靠卖字卖画来谋求生计。《侠女》中的金陵顾生,“博于材艺,而家綦贫”,又因母亲年迈,不忍外出谋生,“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此篇中的“书画”除了显示出顾生的“材艺”,为其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外,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某日,有少年狐妖上门求画,“姿容甚美,意颇儇佻”,并且“三两日辄一至”,渐渐成为了顾生的“娈童”。狐妖因“求画”而与顾生相识、相知、相恋,最终却因屡次轻薄侠女而“身首异处”。“书画”作为一个重要线索,既开宗明义地点出了男主人公的身份与才学,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可谓妙笔。
《聊斋志异·聂小倩》篇中,鬼女聂小倩嫁与宁采臣后,凭借贤良的品性与高超的画技赢得了认可与尊重,“女善画兰梅,辄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之什袭以为荣” [3]167。聂小倩所画之兰、梅,本就是风雅之物,以画酬客更是风雅之举,以至于戚党“反不疑为鬼,疑为仙”,可见擅长书画确实能收获不错的声名。无独有偶,将“书画”作为礼物酬谢宾客,又见于《瑞云》篇。杭州名妓瑞云“色艺无双”,求见她的客人必须奉上厚礼,“贽厚者,接一弈,酬一画;薄者,留一茶而已” [3]1387,冯镇峦在此处评曰:“名妓身份几与名士等。” [3]1387的确,名妓不以色相取悦于人,而是与客弈棋、作画、品茶,这般情趣与追求颇有名士之风,难怪富商贵介们会“接踵于门”。后来瑞云赠诗于穷书生,将芳心暗许,甚至欲与之“图一宵之聚”,也着实配得上那“风流”二字。
自古以来,凭借一技之长得到当权者赏识而荣登仕进、坐享荣华的例子不在少数。《吴门画工》就记述了一名画工因痴迷于绘吕洞宾像,最终遇到吕祖真身,获得富贵的故事。吴门画工对吕祖有着极致的热爱,常幻想有朝一日能与其相见。某天,他在一群乞丐中看到酷似吕祖之人,便捉臂相认,伏地跪拜;吕祖念其虔诚,约定梦中相见。吕祖认为画工“志虑专凝”,但“骨气贪吝,不能为仙”,便让他牢牢记下董娘娘的相貌。画工虽不明所以,但谨记吕祖教诲,醒后将梦中之人绘成了画图。几年后,皇帝的宠妃去世,宫廷诸工皆不能准确画出董妃之像,于是画工便将自己所藏画像呈于皇帝,“宫中传览,俱谓神肖”。皇帝大悦,赐其万金。从此以后,画工名声大噪,皇亲贵戚纷纷携重金求其为先人传影,结果他每次只需凭空想象一番,所画之像便“无不曲肖”,数十天内又收获了万金。据《吕祖本传》载,吕祖得道升仙后尝称:“人若能忠于国,孝友于家,信于交友,仁于待下,不慢自心,不欺暗室,以方便济物,以阴骘格天,人爱之,鬼神敬之。即此一念,已与吾同,虽不见吾,犹见吾也。” [4]11这似乎是吕祖劝导世人向善的说辞,画工也并未表现出“忠于国,孝于家,信于友”的崇高道德,但他却凭着一腔热忱得见吕祖真身,获其赐福。其实,画工的成功除了归结于他“虔结在念,靡刻不存”的诚心,还要得益于他高超的画技,正因为他常年画吕祖,所以对吕洞宾的外貌、神态和气质都了然于胸,才能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对方。此外,所谓“熟能生巧”,丰富的人物画经验与技巧令他能够将仅有一面之缘的董妃描摹得惟妙惟肖,此等绘画功力也着实令人钦佩。
《促织》篇讲述了因皇帝喜好斗蟋蟀而致百姓倾家荡产、民间生灵涂炭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成名也因为一幅画获得了荣华富贵。成名被迫担任里正,负责征收促织,但又不忍勒索百姓,以致自家“薄产累尽”。无奈之下,他只能亲自去林间搜觅促织,结果捉来的都是劣品,被县宰杖打数百。绝望之际,村里来了一个驼背女巫,自称能预卜凶吉。成妻便前往诣问,随后从帘内飘出一片纸,“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跳舞” [3]485。成名按照画中的景象去搜寻,果然捕到一只俊健的青项金翅促织,解了燃眉之急。但明伦在“食顷”句后评曰:“即神亦怜之,惟神乃怜之。” [3]485认为是上天怜惜成名的悲惨遭遇,所以才会赐给他那幅带有预言性质的画。事实上,这幅“书画”确实成为改变成名及其家族命运的关键,虽然后来这只“青项金翅”被他的儿子失手弄死,但成子由此契机化身为“轻捷善斗”的促织,令皇帝大为满意,使得呈献促织的诸人无一不受到丰厚赏赐。不出一年,成名家已经“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 [3]489。这则小说中,女巫之“画”是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也是成名谋求现实利益的重要途径——由此不难看出,书画作品对于现实人生有着巨大作用。
二、“书画”叙述成为男女传情媒介
自古以来,写字作画都是文人才子们所钟爱的陶冶情操、抒发情志的重要方式。北宋郭熙《林泉高致》指出:“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画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5]64文人们热衷于借助书法和绘画宣泄自己心中炽热的情感,因此,“书画”也常常成为小说中主人公之间寄托情思、沟通情感的桥梁。
《小翠》篇讲述了狐女小翠为报恩而嫁入王太常家,还帮他的傻儿子王元丰治好傻病的故事。小翠虽然举止怪异、行为疯癫,但多次帮助王家躲避灾祸,而当她失手打碎价值千两的花瓶时却遭到公婆的严厉诟骂,于是她盛气而出,与王家不再往来。王元丰在小翠的陪伴下度过了多年快乐时光,更是在她的治疗下“痴颠皆不复作” [3]1005,此后婚姻生活愈加幸福,可谓“琴瑟静好如形影” [3]1005。面对小翠的离去,王元丰“恸哭欲死”“寝食不甘” [3]1005,无奈之下,“惟求良工画小翠像,日夜浇祷其下,几二年” [3]1006。后来元丰偶然路过自家的村外亭园时,闻得内有两女子嬉笑,“听其声,酷类小翠” [3]1006,便“疾呼之” [3]1006,继而红衣人走上前来,居然真是小翠,两人终于久别重逢,再续前缘。
小翠画像为“良工”所作,自然逼真传神,元丰的日夜祈祷或许也感动了上天,这才令他们得以破镜重圆,正如但明伦评“一红衣者”句所云:“浇祷有灵,画像活现。” [3]1006此处,小翠的画像充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元丰将自己对小翠深沉的思念与执着的爱恋寄托于画像之中,使得画像显灵;而小翠本是狐妖,自然有超乎常人的感知力,她感受到了元丰对自己的爱意,知道对方因为思念自己而“骨瘦一把矣” [3]1006,不忍其再受相思之苦,所以自愿现身,以慰君心。中国画论自古强调“写形传神”,惟妙惟肖的画像或许真有几分难以言说的灵力,能够沟通天人,寄寓情思。但明伦在回后批中评道:“小像尚存,郎心未死,二年来一把瘦骨,差可以修目前之因耳。岂浇祷有灵,遂不嫌被人驱逐之羞,而为此邂逅耶?……若小翠者,其仙而多情者耶?抑多情而仙者耶?” [3]1008小翠的“仙而多情”自然溫婉动人,元丰的“日夜浇祷” [3]1006也不可或缺,而小翠的画像更是在两人的情感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画之“传情”效果可见一斑。
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宦娘》篇中,女鬼宦娘为温如春的琴声所感,却因人鬼殊途,无法与之结成连理,便暗中助成温如春与葛良工的婚姻,告别时,宦娘给温如春留下一幅画像,对他说:“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当悬之卧室,快意时焚香一炷,对鼓一曲,则儿身受之矣。” [3]989-990画像本是无生命的物件,此处却似乎具有了魔力,能令画像中的人(鬼)于千里之外领受到祷祝之人的焚香之情。但明伦在文末评曰:“高山流水,知音只在黄泉;逸响新声,绝调复传尘世。以受业之高弟,转为传钵之名师,绘以小像,供以瓣香,可以摅铭心之感,可以结再世之缘矣。” [3]990宦娘与温生那有花无果的爱情,通过人与画的交流实现了延续与升华。事实上,中国民间向来有祭拜神像、祖先像的传统,祭祀之人只要秉持虔诚之心,便可与画像中的神灵沟通,此处正是这一民间传统信仰的变异,“这实质上是亲人之间企图超越生死界限进行交流的愿望,它以祭祀的形式来体现,既是无奈,也是自欺,支撑这种祭祀的实质力量来源于感情” [6]139。所谓的“画像显灵”,大抵只会出现在《聊斋志异》这类志怪小说之中,但“以画传情”却灌注了人世间最真挚、最热烈的情感,所以《小翠》《宦娘》这类故事读来便分外感人。
《聊斋志异·小谢》篇中,书画活动与男女主人公日常生活紧密融合,是他们增进情感、表达爱意的主要方式,也是维系“双美”模式的一个重要纽带。狂生陶望三独居姜部郎废第,被女鬼秋容、小谢戏弄,但他正气凛然、坐怀不乱,赢得二女鬼的尊敬,他们的感情也在读书习字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一天,陶生抄书未卒而出,“返则小谢伏案头,操管代录” [3]774,小谢看到陶生突然返回,惟“掷笔睨笑”,尽显调皮憨态。陶生细看小谢所作,“虽劣不成书,而行列疏整” [3]774,连赞小谢“雅人”,“乃拥诸怀,把腕而教之画” [3]774,手把手教其写字。不料这时秋容突然自外入,见两人如此亲密,“色乍变,意似妒” [3]774。小谢连忙解释,结果越描越黑,秋容依旧“不语”。陶生看出这两人争风吃醋,便将秋容“抱而授以笔,曰:‘我视卿能此否?” [3]774当秋容写完,生大赞“秋娘大好笔力” [3]774,秋容这才转妒为喜。从此,小谢、秋容临摹习字,陶生另一灯夜读,彼此各得其乐。但由于秋容以前没读过书,以致“涂鸦不可辨认”,所以常常“自顾不如小谢,有惭色” [3]775,但陶生总是鼓励安慰她,直到她“颜霁”为止。“二女由此师事生,坐为抓背,卧为按股,不惟不敢侮,争媚之” [3]775。从此以后,他们三人的关系更进一层,除了情人般的爱意,更增添了对老师般的敬意。过了月余,小谢的书法功力越发深厚,陶生不禁赞赏了一番,却不料又被秋容撞见,“秋容大惭,粉黛淫淫,泪痕如线” [3]775,自尊心受到打击,醋意又占了上风,最后“生百端慰解之乃已” [3]775。秋容之所以屡次争风吃醋,正是因为她深爱着陶生,不甘落后于小谢,足以看出一个女子在爱情中的敏感与痴情,也可见她的自尊与要强。
众所周知,书法是古代读书人的必修课。从现存于辽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上半部手稿可以看出,蒲松龄本人也十分擅长书法,且风格苍劲古朴,运笔挥洒自如。蒲松龄天性嗜书,常常手不释卷,亲手抄录过许多典籍,有些是诗文,有些则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此举意在“补益身心,取资日用”,故他于书法可以避俗求雅,运笔如风。蒲松龄在《与赵晋石》中有对书家性情的论述,曰:“又得沾墨沈之余,一豁俗抱,篆结如何也!无声之诗,妙足通灵。” [7]144足以看出蒲松龄对书法的功用评价极高。这样的爱好与追求诉诸小说创作,便有了《小谢》中二女鬼通过学习书法而与男主人公互通情愫的情节。陶生将小谢“拥诸怀”“把腕教之画” [3]774,将秋容“抱而授以笔” [3]774,都是非常亲密的举动,但陶生却未起淫欲,未动邪心,秉持着自己“坚拒不乱”的作风,用自己的才学与修养打动了两位女鬼,这也为后文二女鬼拼死营救陶生埋下了伏笔。
三、“书画”叙述对虚实相通境界的营造
《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8]2即是说,宇宙的本体“道”既有“无”的性质,又有“有”的属性;“无”是形成天地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这种对“有无”“虚实”的思考与追问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之中。“虚实”观念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处事之道。中国传统山水画中“虚实相生”境界的构成,也几乎都遵循和体现了老庄的“道”论。清代笪重光《画筌》认为:“山之厚处即深处,水之静时即动时。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清光何处著笔?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9]18中国山水画所追求的“虚实相生”境界,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之道的追问,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探寻。
中国古代小说也不乏对“虚实”关系的探讨,清代章学诚便认为,《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然而,长期以来,小说理论界对“虚实”的研究重点都在于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比较,侧重分析文学文本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度,很少关注到文本内部“虚境”与“实境”的互涉,而《聊斋志异》中有关“书画”的叙事则生动地展现了这种特殊的“虚实”关系。
《画壁》篇讲述了朱孝廉被古寺壁画吸引而进入“画境”之事,可谓是演绎“虚实相通”故事的典范之作。朱生与友人孟龙潭同游古刹,见壁上“图绘精妙,人物如生” [3]14,内有一垂髫少女“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 [3]14,注目良久后,不由得神摇意夺,“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 [3]14。但明伦在此处以“幻境”二字批注,冯镇峦则评曰:“因思结想,因幻成真,实境非梦境。” [3]16两位杰出的评点家都对《画壁》的“虚”与“实”进行了思考与阐发。具体来说,小说以壁画为界,建构了双重空间——第一重空间是以现实世界为参照的寺庙,即是“真”;第二重空间是壁画世界,即是“幻”。朱生通过壁画进入到一个封闭的“异空间”,这一空间以某种完整的、区别于现实世界的形态而呈现,正如朱生所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 [3]14。初入画境时,朱生的意识并不清醒,而是处于神游状态,呆立在老僧面前听其说法。反倒是散花天女表现得异常主动,先是“暗牵其裾” [3]14,然后“冁然竟去” [3]14;进入房舍后,朱生逡巡不敢靠近,天女连连招手唤其进入,于是两人遂相狎好。据《维摩诘经·观众生品》载,维摩诘室中有一位天女,当菩萨们聆听佛说法时,她就将天花撒到各位菩萨身上,以检验他们的道心是否坚定。凡俗之心已尽者,花不着身;凡俗之心未尽者,花着身不落。[10]110然而,《画壁》中的天女非但不以这种高高在上、纤尘不染的圣女形象出现,反而像凡间女子一般大胆热烈地追求爱情。从这个角度看来,画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壁画世界中的人物具备了鲜明的人间特征,甚至比现实中的人更富有人性,显得更加真实。
再回到小说文本,朱生正与天女卿卿我我之际,同行友人转瞬不见朱生人影,疑而问僧,老僧于是以指弹壁呼唤朱生,“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 [3]16。至此,人境与画境不再是彼此分割的独立世界,也不再是简单的“虚实”关系,现实世界通过壁画与图画世界实现了交流,现实中的人可以通过“神游”亲身进入画境,画中的人也可听、可感现实中的一切。朱生听到呼唤,“飘忽自壁而下”,仍然是“灰心木立,目瞪足软” [3]16,延续着他在画中的心理与情绪。而当他们回首再看彼时“拈花人”时,早已“螺髻翘然,不复垂髫矣” [3]16。朱生于是惊拜老僧而问其故,老僧只以“幻由人生”四字作解。篇末“异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3]17此言颇具佛家意味,要求世人不可生发“淫心”“亵心”,洋溢着对人生的感悟与反思。但是回到文本自身,摒去文末的宗教说教,全文不过是“借奇幻以写实”的笔法,借用朱孝廉进入画境的奇妙想象,写青年男女一见钟情,并完成一段仙凡之恋的故事。
再看《单道士》篇,同样是表现画壁之奇异,此处则借道士之手,以幻术的形式呈现。单道士因擅长变戏法而成为韩公子的座上宾,公子爱其术,“欲传其法” [3]338,单执意不肯。公子因此怀恨在心,以细灰破了道士的隐身术,将其乱揍了一顿。道士意识到韩家非久居之地,便从袖中变出美酒珍肴答谢自己的仆人,公子听闻此事大惊,又令其表演戏法。道士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挝,城门顿辟” [3]338,将行囊衣物“悉掷门内” [3]339,大喊一声“我去矣” [3]339,随后跃身入城,结果“城门遂合,道士顿杳” [3]339。道士明知将法术传给心术不正之人是“济恶宣淫”之举,但还是四处显摆自己的本领,以致受到小人的嫉妒陷害,正如何守奇所评:“道士自亵其术,故取辱。” [3]339此处姑且不论道士的品行如何,单看他“画壁为城”的道术,却着实令人咋舌。道士于壁上所绘之“画”,本应是画家用笔墨、丹彩在画卷(此处为墙壁)上所描绘的图景,但却因为道士施加的法术,成为沟通人境与“异境”的桥梁。他利用壁画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实现了现实世界中不同空间的“转移”,而在整个过程之中,“画”并不是作为独立的“宇宙”而存在,仅仅是沟通两重空间的“中介”,起到了类似于“钥匙”的作用,这又显然是有别于《画壁》的。
上文讨论的是由“人境”进入“画境”的情况,而《聊斋志异》中讲述画中人物进入现实世界的故事也不少,《画皮》便是其中的典型。太原王生与陌生女郎“寝合”,被一位道士说身上“邪气萦绕” [3]119,便将信将疑地回家偷窥女郎的行为,结果大吃一惊:“(生)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3]120本文中的女鬼并非利用于纸张或者布帛,而是在人皮上作画。蒲松龄以绝妙的创造力与高超的想象力创作了这篇小说,流露出对“真”与“幻”的思考。女鬼凭借一张人皮,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她在人皮上所画的定是一幅精妙绝伦的人物画,大有《牡丹亭》中杜丽娘所遗画像的美貌与神韵,因此才会惹得王生神魂颠倒。画上的人物本是“虚无”的,欣赏者可以观察到她的神态外貌,甚至感受到她的风姿气度,但却不可能触摸到她的实体。读者对于艺术的欣赏,依赖的是以视听等感官为基础的创造性想象,而这篇小说中的女鬼将画皮披在身上便能幻化成画中女子的形象,将“虚”的画像转变为“实”的人形,确是聊斋先生的妙笔。但明伦评曰:“明明丽人也,而乃翠面锯齿,徒披采绘之人皮者乎?世之以妖冶惑人者,固日日铺人皮,执采笔而绘者也。吁!可畏矣!” [3]120诚然,女鬼以画皮“换形”非常可怖,却仍能被道行高深之人轻易识破,但人心之“画皮”却不易参透,甚至更令人悚然,正如何守奇所評:“然魅之为魅可畏,非魅之魅仍可畏,是故君子慎之。” [3]123-124
《画马》篇亦讲述了画中形象进入现实世界的故事。山东临清的崔生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自家门口躺着一匹马,把它赶走后晚上又来。有天,崔生急着投奔山西好友,苦于没有交通工具,就骑着那匹马去了。“既就途,马骛驶,瞬息百里” [3]1027,即使晚上不吃粮草,第二天依然健步如飞,很快抵达了山西。晋王听说了这件奇事,重金购来此马。后来晋王有急务,派校尉骑着这匹马赴临清,谁知马跑到崔生的邻居家就不见了。进门一看,才发现墙上挂着陈子昂的画马,只见“内一匹毛色浑似,尾处为香炷所烧” [3]1027-1028,正呼应了文章开头崔生所见马的形象——“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断者” [3]1027,这时才明白过来那匹马原来是“画妖”。陈子昂的《画马图》如今虽已不复得见,但仅从蒲松龄的叙述中便可看出,陈子昂画马的技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所画之马不仅栩栩如生,甚至还化身为妖,具备了人间态的实体。这不禁令人想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画龙点睛”一事:“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不点睛。每曰:‘点之即飞去。人以为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皆在。” [11]120陈子昂画马与张僧繇画龙有异曲同工之妙,画中的景象本是“虚”的,却因画家的笔力而拥有了“实”的生命,充满了传奇色彩。文末但明伦评曰:“今子昂画马,赝帧颇多,岂惟不能妖,抑且不似马。” [3]1027诚然,世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临摹前人佳作,或是趋利而往,或是附庸风雅,其实不过是贻笑大方。
概而言之,在上述各类故事中,“虚”与“实”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实”是指现实存在、人们生存其间的世界,而“虚”则指某种虚无缥缈、难以触及的境界。然而,现实中的人能够以某种途径进入幻境,虚幻世界中的人和物也能以某种方式进入现实——在《聊斋志异》中,这种“虚实相通”的实现依靠的便是栩栩如生的“书画”。
结语
蒲松龄以其高深的艺术素养与精诣的文字功底,借助独具魅力的“书画”叙述,为读者创构出一个光怪陆离的文本世界。不管是以“书画”为主要叙述对象,还是以画喻人,又或是构建出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者总能从阅读体验中获得艺术的熏陶、文学的滋养与心灵的震荡。《聊斋志异》作为凝结了蒲松龄毕生心血的旷世奇作,其中储备的“琴棋书画”文化底蕴,依然值得我们深入品读领悟。
参考文献:
[1]吴企明,史创新,注评.历代题画绝句评鉴(第二册)[M].合肥:黄山书社,2018.
[2]王庆德.郑板桥诗文集注[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3][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唐]吕洞宾.吕洞宾全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5]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G].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刘晔原,郑惠坚.中国古代的祭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清]笪重光.画筌[M].关和璋,译解.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10]赖永海,主编.维摩诘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Discussion on the Narra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in Liaozhai Zhiyi
ZHU Jia-xuan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Qin,chess,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e the main means of literary recre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thus are deeply favored by novelists,becoming an important narrative content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Liaozhai Zhiyi,as the final volume of Chinese short stories in the literary language,is the life's work of Pu Songling. With his extraordinary literary skills and profound artistic cultivation,Pu Songling creates an exquisite textual world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rratives in Liaozhai Zhiyi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as a skill,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an bring money,fame and wealth to the literati;secondly,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e the main means of amusement for the literati,playing the role of communicating emotions and enhancing sentiments;Finally,the “evocative” character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makes it a medium to communicate fiction and reality and connect the realm of painting with the realm of people.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Painting and calligraphy;Realistic seeking;Medium for conveying emotions;Realism and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