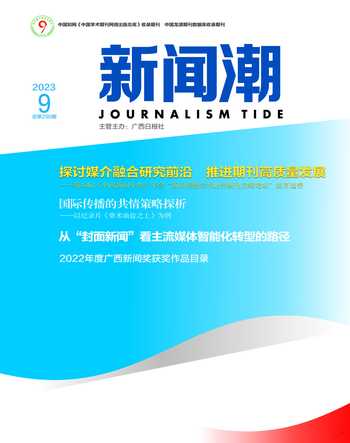智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特征与转向
姚一娴
【摘 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策略应随媒介生态的改变而相应调整。以马克思媒介技术观来观照“对AI言说”的时代表征,从真需要与伪需要之争、数字力与引领力之争、圈层化与大众化之争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特征,从源头、动力和进路三大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需要转向、主体转向和媒介转向,进而培根固本、成风化人,凝聚起中国式现代化的Z世代力量。
【关键词】智媒互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AIGC
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政党的精神旗帜,并通过媒介这个中介,在大众的精神世界构造理想信仰和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策略应随媒介生态的改变而相应调整。人工智能涌现与规模化普及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张力系统的动态演进。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对人的生活的无边界延伸?如何化解人工智能对人脑的不断挑战?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以提升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领力、凝聚力来应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具有时代性、复杂性、长期性、隐蔽性。
一、智媒互联时代“对AI言说”的时代表征
(一)内容多模态化
视觉符号优先。《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数据显示,我国网络视听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短视频和直播成为2022年泛网络视听产业的市场规模中最大的增量。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時长超过2.5个小时。[1]“截至2022年底,国内主流媒体开设并运维740个活跃视频号,在抖音共产生2915条点赞超百万作品、在快手共产生3671条播放量超千万作品。”[2]主流、主要、重大传播越来越重视网络视频生态的参与,大小屏、横竖屏互动越来越深入,主流媒体短视频化传播激发越来越大的舆论引导效能。Web3.0灰箱中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内容生产与人类实践生活无缝衔接,并且涵盖了所有样态的传播符号。“短视频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映射,生成式AI技术的参与本质上是数字化的空间再次被延展,更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世界,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参与生产、参与互动的实践场所。”[3]
柔性话语流行。出于缓解情绪、释放压力的目的,不少青年人习惯于回避硬新闻,青睐“软”新闻。在网络传播中,硬灌与说教更容易招致抵触与不信任,情绪是最大的传播动力。简单直白的煽情话语极易唤起直接情绪,“萌式表达”、戏谑、反讽等更易被接受、聚变和社交,在弹幕等互动式狂欢行为的加持下,情绪实现了放大、叠加、渲染、宣扬。
人机协同生产内容。Web3.0时代“人+人工智能”共生,AIGC与人生产的各种信息共存,构成了无边界生产,可以无限复制、无限保存、无限链接、无限共享的传播场域。“元宇宙作为媒介高度融合的参与式媒介,其对虚拟空间的探索也深刻反映出了媒介进化的趋势,人们在不断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去全方位调动人的感觉官能,试图在虚拟空间以数字方式重构人们在现实世界的体验。”[4]技术赋能、赋权和赋魂重新构建的媒介情境中,人的感官体验、组织身份、价值认知都实现了延伸,现实和虚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二)主体多元化
机器具备了主体性地位。人类的传播从“对空言说”进入了“对AI言说”的模式。机器和人获得了一样的主体性地位,而且在生产速度、生产数量、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方面比人更胜一筹。“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5]
价值隐喻化与多元化。不同思潮通过不同媒介的多模态符号,转换为日常的文化消费品,进而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内容的趣味化带来泛娱乐化、后真相、泛道德化的网络空间。审美观、消费观、自由观等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在隐喻化的符号、游戏化的逻辑、互动式的传播行为中受媒介改写,“窥视”心理驱动下审美异质、精神消费异化,治愈系文化、佛系文化、丧文化等亚文化弥漫。
(三)关系平权化
传播层级缩小。当用户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信息的传播层级会缩小,恰如喻国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中所言,结构转向是“洋葱式”到“海星式”,方式转向是层层扩散到绝大多数节点直接与枢纽相连。智媒互联时代,信息传播层级的缩小弥合了人的能力沟。“‘能力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间巨大不公平的根源,而Chat GPT能够帮助普通人成功突破专业能力方面的局限,使他们的能力达到社会平均线之上,这就极大增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对话能力和对话资质。”[6]
重塑社会生活模式。人工智能促进了知识的快速普及、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和交流,通过重塑人的主体性来重塑社会生活模式。“随着这些有益产品对更多社会阶层的个人变为可得之物,它们所携带的训诫就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7]信息传播层级的缩小导致连接功能替代了根据资源、知识、认知的占有、支配地位所划分的阶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大众在内容创新、传播表达以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与分布式社会的权力构造相匹配,是传播权利作为第一权利的‘先行一步”,[8]这说明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共处方式。
(四)智媒互联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要素重构
根据寇清杰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提升》的论述,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需具备三个条件:有解释力和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有亲和力和令人理解的表达方式,有公信力和令人支持的传播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媒介生态的嬗变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网络传播的要素也随之发展为时长、主体(主观能动力)、主题(价值力)、意识形态隐喻(内核力)、背景(场景力)、情绪 (驱动力)、符号(表现力)、密度(强力),越来越呈现出动态、开放、互动的特征。
二、智媒互联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困境
(一)真需要与伪需要之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稀释
本质之争: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复杂斗争仍然存在。互联网舆论场共同体单级聚化、群体极化,各类网络趣缘社群中的圈际之间、圈层内部冲突,叠加“塔西佗效应”、蝴蝶效应,多元的价值评判体系让受众无所适从,极易带来舆论场失焦、失衡、失序。“‘主流‘网络‘境外三个舆论场的冲突与融合,使得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被瓦解、消弭乃至失灵。”[9]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介的可供性催生了“处处皆传播”的情境。作为传播主体的人随时、随地可以触发传播,即时化传播带来了UGC(用户生产内容)信息过载,导致受众的注意力稀缺,涌现越来越多“标题刺客”、眼球新闻,内涵表意流于浅表化、口号化,价值意义悬浮于故事人物之外,思想认知依然游离于叙事和情感之外,只限于煽情,却并无共鸣、悟化的效果,虚假短暂的伪需要极易让受众价值观失焦。
信任之争:虚拟时空构建的对现实的不信任感仍然存在。“后真相”时代,互联网的舆论能量衍变出正向与负向两个方面,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撕裂。然而,互联网感性化的传播机制使负面情绪更易病毒式传播,社会热点倾向性传播“平权化”,社会事件流变性传播“快餐化”,在某种情况下会加速或抑制信息、思想、行为的传播。意识形态符号的柔化、游戏化的互动逻辑与严密的逻辑说明力之间难以破局,网络传播生态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遭遇多重困境,价值让位于情绪,内容让位于流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稀释,权威受到挑战。
(二)数字力与引领力之争:人与机器谁的价值观为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人工智能和穿戴媒介作为新闻生产链的延伸,不可避免地会被少部分人恶意使用,制造虚假信息、恶意传播并扰乱舆论场,面临道德伦理、隐私和安全问题。
技术权力和人的边界之争。智媒与人自动化产生的内容虽然含有一定的思辨能力,但人与机的内容谁主要谁次要?以谁的价值观为主?价值观如何研判正误?如何体现国家意志的独特性?人工智能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权力界限如何区分?要科学审视技术权力和人的边界,对技术与工具不能过于依赖也不能回避。
(三)圈层化与大众化之争: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如何融合
公域传播和私域定制之争。人机协同的内容个性化,属于量身定做的私域作品。但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面向普罗大众进行大众化传播,属于公域的产品。技术赋权、赋能、赋魂带来了普罗大众的认同危机。
趣缘认同与国族认同之争。虚拟身份认同下的圈层文化仍然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壁垒。群体极化中“粉丝怎样像爱爱豆一样爱国”依然值得深思。身份定制、兴趣定制带来了交流定制和认同小众化。圈层外的信息较难破壁。“信息茧房”的喂养造成了在宣传传播路径、社会话语体系、叙事风格、舆论演化规律等方面引起结构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动态流通的壁垒随着“信息茧房”而加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碎片化,话语权式微。
三、智媒互联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情境转向
(一)需要转向:源头
根据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人的发展要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步,需要也具备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技术革新的工具性价值要同国家社会的目的性价值相统一。
(二)主体转向:动力
传播主体能力转向。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质量与匹配度,取决于人描述问题的精确度。Web3.0时代用户在信息池获取知识的能力转向提示工程能力。人之间的信息竞争转向了认知竞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人的争夺,是认知的争夺。由于“把关人”的素养差异,存在解码的弱化,由于主体教育水平、思想觉悟、领悟解读等方面的差异,存在内化程度不同。在智能化生存的时代,主体的自主阐释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亟须提升。
主体作用转向。教师的角色偏向辅导和引导,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扮演学生人生道路上“引路人”的角色。而随着知识价值习得、技能机械操作的作用稀释,学生知识教育的学习模式会更倾向于“公域的信息聚合学习+私域的个性内容生产”。
(三)媒介转向:进路
媒介作用转向。决定媒介传播效果的已经不单是内容本身,更多的是内容的链接。专业媒介机构的作用由TO C模式转向TO B模式,即由Web2.0时代的直接面向受众,转向Web 3.0时代的内容生产者。
表达方式转向。为消解娱乐的传播吸引力与理论的逻辑论证力之争,重量级事件的报道要向轻量化、年轻态、直播态的表达转向,巧用隔屏共情,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Z世代中的有效传播和最大传播。
传播关系转向。Web3.0时代的传播关系不仅局限于人,而是人—物、物—人、物—物。
四、结语
深刻认识智媒互联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境、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规律是坚守网络阵地的前提。人们从人工智能知识媒介获取信息的深度需求、长远需求仍然是追求获得感和认同感。利用媒介景观深度激活受众内心对真善美的需要,引导人们识别真需要和伪需要,进而深度激活人们内心对国家、政治、文化、社会认同感的需要,引导人们将“短视”转向“远视”,知识体系转向信仰体系,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边钰.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N].四川日报,2023-03-30(A04).
[2]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J/OL].[2023-03-29],https://mp.weixin.qq.com/s/a2uhYTrCVPDfqxff9HOD2Q.
[3]喻国明,滕文强.生成式AI对短视频的生态赋能与价值迭代[J].学术探索,2023(7):43-48.
[4]门泽宽.未来媒介图景“元宇宙”:从人的再延伸到价值反哺[J].青年记者,2022(14):27-29.
[5]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5):81-90.
[6]揭晓.视覺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6(1):68-74.
[7]喻国明.ChatGPT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重构[J].探索与争鸣,2023(3):9-12.
[8]江先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图像化传播的表征、危害及其应对策略[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48-55.
[9]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5):81-90.
[10]陈先红,宋发枝.互联网新技术背景下的舆论传播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