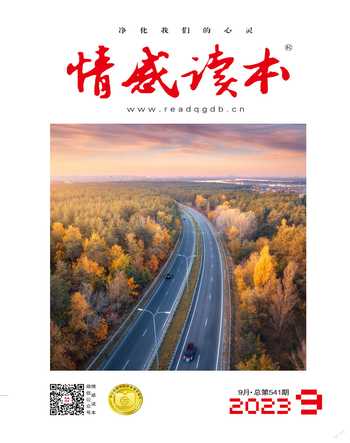那个送我回家的男孩
崔茂晶
有一种感情,它无关爱情,也不像友情,而是温情。我想人是无法长期生活在太强烈的感情中的,那些余下的平凡日子,正是需要被这种淡淡的温情来支撑的啊。
在剑桥读书时,我每天都迷路,也跟寄宿家庭闹了点矛盾,索性就用“回家的路太复杂”这个理由上报学校,希望能换一个家庭寄宿。没想到,老师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还安排了一个和我顺路的男同学每天送我回家。
那个从没和我说过话的男孩——菲利普,与我并排坐在办公室里,一字一句听着老师的安排。他乖巧地点头答应,我也只好答应,在心里嘀咕:“偷鸡不成蚀把米”。
菲利普来自中国澳门,这个大我两岁的天蝎座男孩,不到迫不得已,绝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和女生交际,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的动作至少比正常人放慢了一倍,水要一口一口地喝,桌子上的东西要一件一件地放进包里。他转身走到我面前,问一声:“要走了吗?”之后,掏出一双黑色的皮手套戴上,就出门了。我把桌上的纸和笔一把塞进袋子,心不甘、情不愿地跟他走出校门。
英国已进入深秋,下午三点多太陽就落山了。“往这边吗?”他指着路问我。“好像是吧。”“还是那边?”“应该也可以。”“是从这里走吧?”“不知道。”菲利普拿出地图对照着他标出的一条曲折的黑线,坚持说:“这才是最近的一条路。”我无奈地跟在他身后,在他说的近路上绕来绕去。天越来越黑,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只有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但我受不了跟陌生人之间的沉默,于是积极找话聊。
“你是从哪里来的?”“家里住哪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你去过云南吗?”“你喜欢英国吗?”菲利普的普通话很差,一句话同时夹杂英语、粤语还有极其不标准的普通话,我居然都听懂了。我接着问,他接着答;我不问,他就不说话。要么突然停下来,说:“等等,你别说话,我要找到路了……”终于到家,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跟菲利普一起回家,就像做作业一样,我提前一天想好话题,可上了一天的课又给忘了,话堵在喉咙里什么都说不出,心里喊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人啊!”“你说什么?”他突然停下来问我。“我没说话呀!”我顾左右而言他。
刚开始一个人走夜路,因为神经紧绷,我没有多余的心力去记路。后来和菲利普一起走了一个星期,我就完全记熟了,不再随身带着地图,还盘算着找个机会和他说以后不再送我了。
又是一天放学后,我和菲利普走在路上。他停下来把手伸进包里一摸,像是忘带什么东西了,说要回学校一趟,接着就骑上车往回赶。我站在路边等,风呼呼地吹,比起害怕,我更觉得冷。我站在两个大垃圾桶后面躲风,一滴雨砸到我头上,接着是两滴、三滴……雨哗啦啦地下起来。我捂住头跑着找避雨的地方,谁知在雨里一阵乱跑,居然就到了家门口。
洗了澡,换了睡衣,我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用力跳着。下那么大的雨,他应该已经回去了吧?刚要吹头发,寄宿家庭的妈妈敲了敲门。“有人找你。”她指了指楼下说。我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风衣,跟她走下楼。冷风吹进裤管,想到那个唯一会找上门来的人,我的每一步都变得沉重。
菲利普扶着自行车站在门口,头发和衣服都湿了。他看到我,跑上前问:“那你刚才走的是我说的那条路吗?”“可能是的……”我说。“可是我根本没看到你呀!”我从来没听过菲利普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他两颊红红的,明显是急坏了。
见我不语,他只好“唉”了一声,说:“你安全到家了就好。”然后摆摆手,把自行车调转了个方向就走了。看着他和他的车消失在黑暗的小路上,想到他和我一样,年少远离家人故土,承受着身为外来者的压力,我觉得自己对他实在太冷漠了。
第二天,菲利普没有来上学。看着那个空着的座位,我的心被内疚感浸透。到了第三天,我注视着同一个方向——他还是没有来。生病了?生气了?心灰意冷?我开始一遍遍地在心里哀求:“菲利普呀,求你明天一定来上学吧!只要你没事,我保证,以后每天都乖乖让你送我回家!”
第四天,他终于来了,看上去一点儿事也没有,只说是得了流感,放学后还是和我一起回家。我跟他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走在路上,反而觉得很安心。我观察到他思考的时候会抿嘴唇,半蹲着开自行车锁的动作像拿着一根丝绸的针,缓慢而温和。我边和他走着,边感受着心里微妙的变化,再也没有迷路。
从那天开始,寄宿家庭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像在说:“才来几天就交到男朋友了啊!”可是我该怎么让他们明白菲利普带给我的那种无关爱情的小小触动呢?他们不说破,弄得我连解释的机会也没有。
过了寒假,学校就不再让菲利普送我回家了。他恢复了一个人骑自行车上学、放学的生活,我们却比以前来往得更频繁了。
三月初,一个朋友过生日,请了很多中国同学去一家叫“小上海”的中餐厅吃饭。我叫了菲利普,他背了一个大背包姗姗来迟。吃饭吃到一半,他打开包,拿出一把吉他,说要唱一首歌作为生日礼物。
菲利普抱起吉他,餐厅里所有人都停下筷子,准备鼓掌。他把手放在弦上摸索,找准位置,开始弹。他弹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弹完了我也没听出来是哪首歌。在场所有人用掌声掩盖笑声。“还是有点儿好听的。”有人这么说。
吃完饭,我们在餐厅门口分别,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即便入春了,天也黑得很早。我拉上外套的拉链,一个人走在路上,墨黑色的天空挂着几颗星星,我幻想自己就是其中一颗。那些固定在旁边的星星是家人,那些在路上遇到的人是流星,他们短暂划过我的天空,带来一瞬间的光亮,我也许会错愕,但不会对这样的交错有所期盼。如果可以这么看待的话,面对聚散我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儿了。那些来来去去的人,无所谓缘深缘浅,也不一定是遗憾,而是在看一场流星雨。
在国内,我总是爱恨分明,要好的时候总把一辈子挂在嘴边,吵架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后来才慢慢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维度有很多。有一种感情,它无关爱情,也不像友情,而是温情。我想人是无法长期生活在太强烈的感情中的,那些余下的平凡日子,正是需要被这种淡淡的温情来支撑的啊。
就是这种慢慢发现到处可寻的平淡温情,让我开始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感兴趣。我对着镜子,模仿菲利普说话的样子。一想到他,我就会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这种牵挂,不要对与人交往失去信心。然后又不得不陷入一种黯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从没问过他的中文名字。
张泽林摘自《时代青年·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