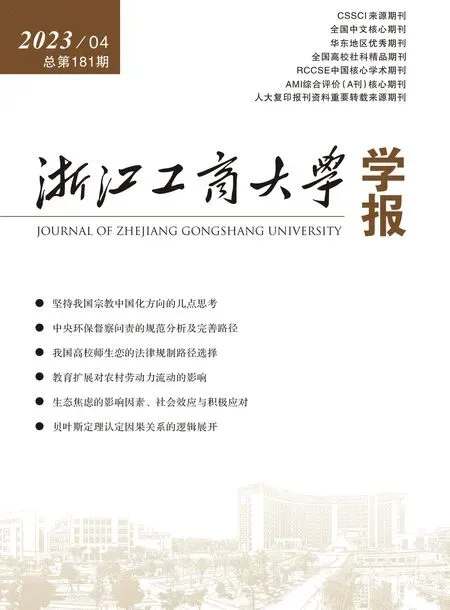全球化视域下的伊斯兰教中国化
李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 作为方法的全球化
(一) 全球化与宗教中国化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断交流互鉴充分说明,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过程中,除了应重视“本土性”与“时代性”,还应看到宗教中国化具有“全球性”与“国际性”,也就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历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三大世界宗教传入与扎根中国就发生在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历史背景下。就伊斯兰教而言,杭州的凤凰寺,泉州的清净寺、灵山圣墓与陈埭丁氏祠堂以及广州的怀圣寺与光塔等我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古迹,便是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明证。以往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多从中国史与中国化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全球史与全球化的一面。如能将中国伊斯兰教放在全球史、全球化的视角下解读,那些熟悉的材料与事件将呈现与以往不同的面貌与意义。本文的目的是从“全球化”与“全球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与解读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整体历史,特别是我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以探索与呈现宗教中国化的“全球性”与“国际性”内涵。
(二) “全球化”的实与虚
在对“全球化”这个概念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全球化”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作出说明。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汗牛充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全球史导论》一书中,作者S.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提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网络化和互联化”[1]12。这个定义将重点放在了“全球化”互联互通上,但没有说明“全球化”具体指哪些方面的互联互通。本文综合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界定“全球化”的具体含义。
第一,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互联互通,还包括政治秩序与文明范式。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现代世界实现互联与整合的关键在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也就是依靠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传播以及市场和资本积累的经济体系的建立[1]148。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近期在一次讲座中提道:“‘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全球化,全球化是由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两部分构成,中国接受了经济全球化,拒绝了政治民主化。”中外两位学者都认为现代世界或者说冷战后的全球化包括两重内涵,即经济互通与政治秩序。作为“冷战后全球化”的亲历者,当代人容易受到最近一轮全球化的影响,将全球化理解为经济的互联互通,而忽略了全球化还可能包括经济以外的内容,如特定的政治秩序与文明范式。比如,明代建立的朝贡体系是前现代时期一次典型的全球化,本文称为“朝贡全球化”。“朝贡全球化”不仅包括一套由明王朝官方主导的经济交换的网络,也意味着一套以明王朝为中心、统摄周边国家权威的政治秩序与教化体系。
第二,全球化具有实指和虚指两个方面。“实指的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的阶段性或局部现实。“虚指的全球化”是指全球化可以构成一种解读方法与分析工具,帮助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本文的主题是“全球化视域下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也就是以“全球化”为视角和分析工具,将我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乃至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整体历史放在“全球化”与“全球史”的视域下进行重新解读。
第三,与全球化相对的概念有“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等。(1)所谓“反全球化”指出于经济利益、民族主义、国家安全等理由,反对全球化的局部弊端甚至整体网络,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用地方化对冲全球化。(2)“反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区别在于:“反全球化”是民间的、个案的,“去全球化”则是由国家等政治实体有意识进行的去除全球化的过程,历史上一些帝国乃至现代民族国家都曾具有“去全球化”的动机与经过。(3)“逆全球化”则是指在众多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实体的联合推动下,促使全球化互联互通解体,转向强调地方化、国家化。
(三) 狭义全球化与广义全球化
第一,为什么要区分“狭义全球化”与“广义全球化”?全球化是否只出现于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规模生产、通信与交通等为全球互联互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但全球化并非仅属于现代社会。以往一些观点认为,直到20世纪晚期才实现全球化,其具体过程被描述如下:在18世纪,世界仍是一个区域性的世界,到了19世纪末,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也就是出现了全球化的萌芽,而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化到1990年达到了高峰。本文主张,在理解全球化时,需要突破西方的认知模式,认识到并非只有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才叫“全球化”。为了打破这种思维惯性,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区分“狭义全球化”与“广义全球化”。
第二,“狭义全球化”。“冷战”结束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或者说20世纪晚期达到高峰的这一轮全球化,只是“狭义的全球化”。在它之前和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始终存在,并出现过多次典型阶段,前现代时期几个全球化高峰都与中国有关。“冷战”以来的这轮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从20世纪晚期到现在反而进入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经济全球化在解体,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意识与举措也在逐步明显。
第三,“广义全球化”。“广义全球化”将全球化理解为多元现象与常态过程,强调复数形态的“全球化”,包括历史上的几次典型全球化过程。跨地区、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并不是只发生在过去的三四十年,而是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在前现代时期曾出现一些重要的全球化浪潮,其中由中国参与和主导的典型全球化阶段包括: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蒙元时期的“贸易全球化”以及明清时期的“朝贡全球化”。当时与中国互联互通的主要伙伴是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中国伊斯兰教就产生于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互联互通过程中。不幸的是,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全球化”的兴起,传统的贸易线路被打破、秩序规则被改写,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被打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被强行卷入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才重新实现了独立自主。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由盛转衰。2022年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共构中阿命运共同体,由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以及相关国家共同构建的新一轮全球化可能再现于世界舞台。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几次全球互联互通中,来华穆斯林以及后来的华化穆斯林都是重要参与者。参照中国伊斯兰教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便可找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几次重要的全球化高峰。熟悉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人都知道,伊斯兰教自唐代入华以来,经历了以下五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唐宋时期(618—1279年)、第二阶段蒙元时期(1279—1368年)、第三阶段明清时期(1368—1911年)、第四阶段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第五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至今)。
相应地,可将以中国—阿拉伯世界为主导的、环印度洋区域的早期全球化分为以下三个标志性时期:(1)公元8—10世纪与10—12世纪,即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2)公元13世纪,蒙元时期的贸易全球化;(3)公元14—20世纪,明清时期的朝贡全球化。此外,再加上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两次全球化浪潮:(1)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殖民全球化。(2)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期的全球化,即我们熟知的狭义全球化。这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化,其覆盖范围前所未有,甚至有西方学者因此宣告“历史的终结”,但这轮全球化正在解体。(3)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化,本文称为“区域全球化”。在这一轮全球化里,中国将成为全球化的引擎和中心。本文将按照这几个阶段划分,从全球化与全球史的视角解读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重大事件。
二、 从全球化视角重新解读中国伊斯兰教史
(一) 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
1.“市舶全球化”。“市舶全球化”指唐宋时期,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为轴心的国际化互联互通,其特点是:第一,以跨国经济贸易为主体,不涉及构建政治秩序;第二,以环印度洋为主要范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是唐宋时期市舶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中国政府设立以“市舶司”为代表的官方机构,致力于推动当时的贸易全球化。
唐代的“蕃坊”仅指蕃客所居之所,而非政府设置的机构。到了宋代中期,“蕃坊”则演变为政府正式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域,并专设司属官衙“蕃长司”管辖。北宋朱彧在《萍州可谈》中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2]据此可知,蕃长职责有二:第一,“管勾蕃坊公事”,掌管坊内宗教事务,解决民事纠纷和治安案件;第二,“专切招邀蕃商入贡”,招引海外商旅来华贸易,增加朝廷市舶收入。在蕃长的两个职责中,第二项“专切招邀蕃商入贡”显然更重要。因为必须先有蕃商,并且达到一定数量,才谈得上“管勾蕃坊公事”,管理蕃客是为市舶贸易服务的。

图1 侯赛因·本·穆罕默德石墓碑(今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照片来源网络)
泉州是唐宋时期市舶贸易的重要港口。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正式开放泉州港。从此,商船可以直接从泉州出海贸易,而无须通过明州或广州市舶司审批,外国商船也可以直航泉州进行贸易活动。泉州不仅比未设市舶司的福州港优越,甚至可同设有市舶司的广州、杭州、明州平起平坐。南宋赵汝适提举福建市舶司,所著《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其中,有“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3]89此时,泉州港已是最远可达大食并可与广州港并驾齐驱的国际化大港口。到北宋后期,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赶上或超过了明州,仅次于广州。相关文献和文物证明了当时泉州海上贸易的繁荣。苏轼记载“泉州多有海舶”[4],对外贸易的船只称“海舶”,来华贸易的称“番舶”。吴澄记载,“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贾巨商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5]299。《梦粱录》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6]《泉州古回回教寺考》记载,泉州是“蕃客密居之地”。
泉州现存大量伊斯兰教墓葬建筑石刻。这些墓碑的主人来自阿拉伯和波斯各地,反映了宋元时期市舶全球化贸易涉及范围之广。碑文记载了各地穆斯林的来源,有来自也门(Yemez)、哈姆丹(Hamdan)、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Al-malaq)、亚美尼亚的哈拉提(Khalat)、波斯的施拉夫(Siraf)、设拉子(Shiraz)、贾杰智姆(Jajarm)、布哈拉(Bukhara)、花刺子模(Khorazm)、霍拉桑(Khurasan)、伊斯法罕(Isfahan)、大不里士(Tabriz)、吉兰尼(Jilan)等地。其中,经波斯来华者,人数最多。在墓碑中年代最早的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这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哈拉提的坟墓。真主怜悯他。卒于(伊斯兰教历)567年4月(1171年12月,南宋乾道七年,辛卯)。”[7]15

图2 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哈拉提石墓碑(今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林摄于2023年5月)

图3 潘总领塔式墓盖顶碑石(今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李林摄于2023年5月)
2.市舶全球化推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泉州历史上至少存在过六七座清真寺。元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在《重立清净寺碑》中记载:“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而兹寺之废复兴,虽遭时数年,名公大人硕力赞赞,亦摄思广、益绵之有其人也。”[3]9泉州最著名的清真寺是建于伊斯兰历400年(1009—1010年)的艾苏哈卜清真寺(今习惯称“清净寺”),寺门楼甬道后北墙所嵌阿拉伯文石刻记载:
此地人们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这座最古老、悠久、吉祥的礼拜寺,名称“艾苏哈卜寺”,建于(伊斯兰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三百年后,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斯,即设拉子著名的鲁克伯哈只,建筑了高悬的穹顶,加阔了甬道,重修了高贵的寺门并翻新了窗户,于(伊斯兰历)710年(公元1310—1311年)竣工。此举为赢得至高无上真主的喜悦,愿真主宽恕他……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7]2-3。

图4 泉州清净寺(艾苏哈卜清真寺)(李林摄于2023年5月)
市舶全球化推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外来穆斯林来华定居、繁衍后代,并终老于斯。今天,泉州等地仍可以看到这些来华穆斯林生活的遗迹(包括清真寺和坟墓)以及他们的后代。《重立清净寺记》记载,宋绍兴元年(1131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自撒那威(今伊朗西拉夫)从商船来泉州,在城南建立一所清真寺:
至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寔航海至广,方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刱兹寺于泉州之南城。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土田房屋以给众[7]9。
《诸蕃志》记载:“元祐(1086—1094年)、开禧(1205—1207年)间,各遣使入贡。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3]这些来华穆斯林的后裔,定居泉州等地,逐渐华化。灵山圣墓群的部分碑文表明,穆斯林的后裔留居于泉州附近,繁衍至今。这些来华穆斯林后裔中,人数最多的要推丁、郭两姓,分别聚居于陈埭与百奇两地。
3.市舶全球化的受益者。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除了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还出现了以蒲寿庚、佛莲为代表的一批市舶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从事甚至垄断海外贸易,逐渐发展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势力集团。《宋史》卷四十七记载:“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8]942《闽书》卷一百五二记载:“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9]4496除了蒲寿庚,他的子孙女婿,也受其荫蔽而获益。《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记载:“泉南(泉州城南)有巨贾回回佛莲者,蒲氏(蒲寿庚)之壻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10]193《闽书》卷一五二记载:“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数十余年,元亡乃已。”[9]4496
4.“反市舶全球化”与伊斯兰教的中国处境。第一个案例是《宋史》卷四百记载汪大猷知泉州时发生的事情:“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8]12145中国伊斯兰教史相关著作中经常可见到这则史料。以往多从宋代政府管理外国人司法角度解读,也有人认为此争论具有“华夷之辨”的意味。本文提出,此案亦可放在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以及伴随出现的个别反全球化声音这个背景下来解读。当时,蕃商已久居中国,与当地人发生纠纷,如不涉及严重刑事犯罪,往往以牛折价,作为赎罪补偿,当地百姓多乐于接受这样的调解方案,乃至形成惯例。这种以牛赎罪补偿的方式,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反映了蕃商多从市舶全球化中受益,经济实力比本地人雄厚。市舶贸易多为官方垄断,本土百姓不易从中收益,故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乐于接受以牛赎罪的经济补偿。汪大猷等文人士大夫却从夷夏之辨的角度,反对这种早已被蕃、土双方接受的调解方式。这或可说明,当时部分士大夫非市舶全球化的受益者,考虑的角度不是经济而是礼教文化,强调中国不能用岛夷习俗。可见,在唐宋市舶全球化的背景下,泉州等地出现了反对市舶全球化及其受益者的迹象,甚至将中华礼教与外来穆斯林文化的区分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来维护礼教秩序与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案例是《朱子全集》卷九十八《朝奉大夫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傅公行状》记载的一事:
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士子以为病,言于郡。贾赀钜万,上下俱受赂,莫肯谁何。乃群诉于部使者,请以属公。使者为下其书。公曰:“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后以当撤报[11]。
有胡商欲建高楼,其址恰在府学之前,遭到士子剧烈反对,群起告官,但胡商上下打点,无人受理。此事转至通判傅自得,他以“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为由,勒令终止建楼,事态方得以平息。《唐律疏议》《宋刑统》似无明令规定“化外之人,法不当城居”。从胡商建楼一事的前因后果看,更像是傅自得为了化解危机而制造的借口。真实原因还是“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士子以为病”,维护礼教秩序。胡商能够“赀钜万”,说明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从市舶全球化贸易中收益颇丰,其财力是儒生士子无法抗衡的。但胡商以钱欺人这种做法也将自己推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对立面,引起朱熹、傅自得等儒家士大夫的抵制。唐宋以后,随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程度的加深,这种与儒家对立的做法消失。中国伊斯兰教不仅“不主动攻击儒家”,甚至通过援儒附儒、会通伊儒等方式被中国社会接纳。
(二) 蒙元时期的贸易全球化

元代海外贸易较之宋代有了很大发展。《永乐大典》残本中所存《南海志》载海外通商香国与地名147个。元代广州市舶司把海外诸番分为几个区域。一是南海西岸至暹罗湾,以交趾、占城、真腊、暹国等国为首。二是小东洋,指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以佛坭国(今文菜)为首。三是大东洋,分为两部分,其东部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东南海域,以单重布罗国为首;其西部指爪哇和小巽他群岛一带,以爪哇国为首。四是小西洋,指今马来半岛顶端和苏门答腊岛一带。五是西方诸国,包括今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之地。元初广州港的通商范围东起麻里芦(今菲律宾),西迄茶弼沙(Jabulsa),即大食诸国中极西之地,今西班牙一带、马格里布(今摩洛哥),囊括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及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和拜占庭帝国。
这些外来穆斯林从全球化中受益,富有财力,在中国资助建立清真寺。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纳只卜·穆兹喜鲁丁在泉州城南初建清净寺。后因继任者没塔完里阿合昧失职,管理不善,“凡供天给众具窜易无孑遗。寺因废坏,不治其徒”。到了至正九年(1349年),伊斯兰教长老即摄思廉不鲁罕丁(Shaikh al-Islam Burhan al-Din)命谢里夫即舍剌甫丁哈悌卜(Sharif al-Din Hatib)向闽海宪佥赫德尔(Hedar)申诉,得到受理。在达鲁花赤高昌偰玉立(Qi Yuli)支持下,坊民金阿里出资重修清真寺[7]9。元至正十年(1350年)吴鉴在《重立清净寺碑》记叙其事。

图5 《重立清净寺碑》(右)今存于泉州清净寺(李林摄于2023年5月)
元代来华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屡屡述及,旅途中经过的刺桐城(泉州)、汗沙城(杭州)等城市都有穆斯林法官和谢赫,并称:“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13]
元末明初,伴随着这轮贸易全球化的退潮,在泉州等地出现了反全球化迹象,这从对蒲寿庚及其家族的污名化与打压中可见一斑。《金氏族谱传赞》中的《元武略将军一庵公传赞》和《丽史》篇章对蒲寿庚家族的丑化、妖魔化最具代表性。比如,《丽史》记载了在至正甲午(1354年)的一场蒲化家族与福州兵的战争中,福州军“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民间秋毫无所犯……福州军至,发蒲贼诸塚,得诸宝货无计。寿庚长子师文,性残忍,杀宋宗子。皆决其于圹,中宝物之多。圹志玛瑙石为之……盛称元君恩宠,及归功寿宬文学智谋云。大抵犬戎叛乱,出其天性,而奸诡饰诬,或目文学所济,亦有之。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伊櫹蒲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肉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洪武七年,高皇帝大赦天下,圣旨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监其祸也。”此外,清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卷十八引录明代无名氏之《樵书》载:“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读书入仕。与衢州留梦炎子赴考者,责令画一结,曰并非梦炎子孙,方准入考。”《丽史》等书所载明太祖下诏蒲氏子孙“悉配戎伍”、不得读书入仕等说法,不见于正史。李兴华认为,对蒲寿庚家族丑化和妖魔化的背景是元末和明初泉州先后发生过两次“排外运动”。本文认为,对蒲寿庚家族污名化,可放在元末明初的贸易全球化退潮背景下进行解读。这些对蒲氏家族污名化理由有两个特点。第一,并非针对蒲寿庚个人,而是针对其整个家族。就连蒲寿庚之兄、有“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美誉的蒲寿宬,也难逃被污名化的命运。“洪桐县里无好人”,明显不符合事实。第二,打压多以政治伦理、忠孝节义为理由,但颇为牵强。明朝与南宋无直接承袭关系,明太祖为蒲寿庚背叛南宋而惩治蒲氏子孙,于常理不合。真实情况恐怕还是与蒲氏家族“熏炎泉州数十年”有关。蒲寿庚家族经历宋元,三代皆出平章,地位显赫,加之长年垄断海舶,操控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元末明初的乱局中,某些地方势力趁乱而起,以排外运动为由,洗劫当地色目与回回富商。在明初海禁的背景下,明政权也有意打压以蒲寿庚及其家族为代表的海商势力集团。
(三) 明清时期的朝贡全球化
1.明代的朝贡全球化。明代永乐(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两朝,对内招揽朝贡、羁縻诸藩,对外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建立了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全球化政治秩序与经济网络,成为前现代时期规模最大的全球化体系。在此过程中,擅长航海、贸易、语言的大批中外穆斯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西域诸国多聘回回人来明朝朝贡,就连郑和本人及其多位重要助手也皆为穆斯林。
自洪武初至天启末年(1370—1627年),回回与明朝通好朝贡,就《明实录》所记共923次,代表39国。蒙古地区回回朝贡者,自永乐五年至嘉靖三十五年(1407—1556年)共有55次,其他地区亦有回回朝贡者。明朝统治者对周边各国的朝贡屡次遣使,广事招徕。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二月丙午,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借有司之力,以营其私。”这里,礼科给事中黄骥控诉西域使客的不端行为,不是来华朝贡,而是私下贸易。也就是说,当时的朝贡体系之下,由明朝廷掌握着以“朝贡”为名的对外贸易,具有官方垄断的性质。西域使客与民间的私下贸易获利更丰,所以不惜冒险。而明朝政府明知朝贡者有私下贸易的弊端,但为了维护朝贡体系,破例规定回回朝贡者,明朝政府“例许稍挟私货”“来京贸易”。
2.维系朝贡全球化与保护伊斯兰教。明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十一日,明成祖朱棣颁发保护伊斯兰教文告,通常称为《米里哈只敕谕》:“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7]7明清以来,这道敕谕被视为保护伊斯兰教的著名文字,在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体中广为流传,但如果仅从保护伊斯兰教出发,恐无法了解这道敕谕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用意。

图6 《米里哈只敕谕》今存于泉州清净寺(李林摄于2023年5月)
“米里哈只”一词,陈达生认为是所有清真寺掌教的泛称,李兴华认为可能专指一位身份特殊的宗教人士并推测为乌马儿的七世孙赛哈智。北京大学陈彬彬最新研究认为,“米里哈只”是一种头衔,在14世纪早期扬州一带就存在带有“米里哈只”头衔的穆斯林,包括苏州砂皮巷惠敏清真寺的伊玛目“米里闪思丁”、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伊玛目“赛亦的哈马鲁丁”等[14]。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经麻喏八歇国、三佛齐等地;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米里哈只敕谕》下达时间恰好是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归来之时。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中有明确记载:“永乐十一年暌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领宝船往西洋诸国开读赏赐,余以通读番书,亦被使末。”[15]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哈三、费信、马欢等是郑和专门聘请的助手。显然,明成祖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之际颁布《米里哈只敕谕》并非偶然,而是为了褒奖与笼络郑和及其多位穆斯林助手,乃至对沿线伊斯兰国家示好。可以说,《米里哈只敕谕》的内容是保护伊斯兰教,但出发点是为了维系对大明王朝至关重要的朝贡全球化体系。

图7 “郑和下西洋行香碑”现存于泉州灵山圣墓(李林摄于2023年5月)
此外,明王朝在对外建立朝贡体系的过程中,也希冀从宗教上得到伊斯兰教圣贤的庇佑。郑和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之前,曾亲自到灵山圣墓祈求庇佑。“郑和下西洋行香碑”竖立于灵山圣墓柱廊的西侧,碑面阴刻五竖行汉文,其文字为:“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
3.西方殖民全球化的兴起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一书提出,明代以后,由于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即逐步走向衰落[16]。到了清代中叶,泉州港已经从宋元时期的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沦为我国地区性的一般港口。李兴华认为,“泉州港的这种衰落,直接关系着泉州伊斯兰教发展的命脉,因为泉州从陆上远离西域,几百年来传入伊斯兰教主要依赖海上交通”。还有人从亦思巴奚之乱来解读泉州港的衰落。
笔者认为,泉州港衰落的时间,从明朝嘉靖、万历朝以后开始,其主要原因不在中国内部,而是由于“大航海”以后进入了西方殖民者主导的殖民全球化阶段。这一时期,全球贸易的主要路线发生了改变,主动权也从中国与阿拉伯手中逐步转移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先后崛起的西方殖民者手中。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迪亚兹(Bartholomeu Diaz)到达非洲南端,因遇风暴,而名之日“暴风角”。后葡王约翰三世下令更名为“好望角”。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葡国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好望角东行到达非洲东岸,在一位阿拉伯航海家的帮助下,横渡阿拉伯海抵印度西海岸之马拉巴尔(Malabar)。这一重要发现使东西交通线发生重大变化。1557年,葡萄牙窃据我国澳门后,传统的“华南—南海—东南亚—印度洋”环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被“澳门—满刺加—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新航线取代[17]。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新兴西方殖民国家先后崛起,为西方殖民全球化时代拉开序幕。西方殖民全球化兴起与国际贸易航线变化决定了泉州港的衰退不可避免。先是澳门成为国际贸易的中转枢纽,后有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公平参与全球贸易的地位,沦为西方殖民全球化中的受剥削者与产品倾销地。
三、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模式比较
范可《泉州回民宗族与伊斯兰文化——一个历史与人类学的案例》一文分析了陈埭丁氏、百奇郭氏构建宗族身份的背景与过程。至迟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年),丁姓建立了祖坟、祠堂、族谱三大要素完备的宗族组织,族人内部形成了士绅集团,这是伊斯兰信仰在这一期间迅速废弛的重要因素。明嘉靖年间,陕西人胡登洲(1522—1592年)有感于“维吾教之流于中国者,远处东极,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开创了经堂教育体系,更新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承方式与操作系统。几乎同一时期,陕西伊斯兰教与福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出现了不同的转向:在陕西,以经堂教育来克服传承危机;在福建,则以宗族化来适应当地社会。此后不久,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第三种模式,即汉文译著。比较不同地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走向,对我们深入探究伊斯兰教中国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一) 儒士化与回儒化之分
《泉州宗教石刻》记载,明末清初,泉州回族的丁姓、李姓出了不少进士、举人、拔贡[18]。丁姓族人在明清两代共出有进士16人、举人21人、拔贡15人。而在16名进士中,有明一代者为9名,文人著述有30种。

图8 福建陈埭丁氏宗祠(李林摄于2023年5月)
回族李姓的李贽、林奇材(林李同宗)都为著名的明末进士。从这些回族进士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有振兴伊斯兰教和回族的记述。李兴华认为,元末明清至民国时期,泉州地区伊斯兰教普遍衰落,而南京、苏州一带伊斯兰教并未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泉州没有像南京、苏州那样,出现将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恰当地结合起来的知识阶层。即便是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这样的文人撰述,也不同于汉文译著,“与王岱舆、刘智等在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所阐发的伊斯兰教教理有质的不同。一个是没有了骨头或没有了灵魂的伊斯兰教教义教理阐释,另一个则是有骨头、有灵魂即有伊斯兰教特质的伊斯兰教教义教理阐释。基于此,我们将李光缙碑所阐发的教义教理称之为儒化和易化了的伊斯兰教教义教理”[19]。
(二) 宗族化与宗教化之别
中国穆斯林社会身份的中国化进入深入阶段时,分散在各地的穆斯林群体需要通过某种集体身份立足当地社会,其身份选择有二:一为宗族,二为寺坊。一般认为,东南地区的穆斯林受到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影响更大,而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更易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在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南方地区,宗族势力往往较大,宗族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身份。受此影响,当地穆斯林群体也注重通过修族谱、建祠堂等行为,构建自身的宗族身份。而在西部一些地区,宗族的影响较小,故当地穆斯林群体参照系不是南方的宗族,而是西北社会较常见的基层单位“里坊”,故将宗教认同与地方社会融为一体,构建了以“寺坊”为标志的社会身份[12]。
泉州等地在宗族化的过程中,是否遵从伊斯兰教,成为当地宗族的构成和演变一个重要因素。泉州《荣山李氏族谱》中所载林奇材撰《睦斋公圹志》,描述了林氏家族在七世族之时,因航海至忽鲁谟斯等地而信仰伊斯兰教,导致林氏家族分为林、李两支,各遵其俗,各奉其教:
始祖睦斋公之长子也,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卒年四十六。吾宗七世以上,犹葬用椁,其祖谐此乎。然而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矣。
(三)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模式比较与原因探寻
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各地呈现不同特征。明代嘉靖中期,陕西出现了经堂教育;大约同一时期,福建走向了宗族化与儒士化;在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了汉文译著。在此,不妨比较不同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探究为什么福建陈埭等地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没有像江南地区那样走向汉文译著,或是像陕西那样产生经堂教育,而是走向了宗族化与儒士化。
丁氏族谱中记载伊斯兰教信仰在陈埭丁氏家族如何变迁的文献,当数《祖教说》和《感纪旧闻》两篇文字最详,其中《陈埭丁氏回族宗谱·祖教说》记载丁氏第十二世孙丁衍夏记载亲身经历:
吾家自节斋公而上,其迁所自出,俱不得而详也。由其教而观之,敦乎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如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裹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荐神惟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楮帛。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夏稚年习见如此。厥后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裹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矣,牲务肥腯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棉帛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犹故也。今则祀先有焚棉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裹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余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食有以豚者。虽渐变以合于礼,而于非礼之所自者有之,于明洁之尚,吾见其皆莫之省也。
这段文字通过丁衍夏等一生三个阶段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明朝中期以后丁氏由信仰伊斯兰教、遵从伊斯兰习俗转而接受儒家礼教与当地习俗的影响。陈埭丁氏、百奇郭氏、荣山李氏等泉州本土代表性回回家族,为何既没有出现以胡登洲为代表的本土化经师,也没有出现王岱舆、刘智那样的汉文译著家,而是走向了宗族化和儒士化?
王柯在《社会移动与国家认同——晋江陈埭丁氏从“穆斯林”到“中国人”的“本土化”过程》一文中认为,陈埭丁氏走向“宗族化”与“科举化”,与丁氏族人在第七世祖时期经历的“撒氏戍卒之诬告”以及第八世祖时期经历的“祖先墓地遭蚕食”有关[13]。“撒氏戍卒之诬告”使丁氏宗族强调自己是明朝的子民,而非来自中亚出身的元朝驻屯兵,“祖先墓地遭蚕食”使丁氏宗族意识到参与科举对于个人和宗族的重大意义。伴随着陈埭丁氏本土化的加深,伊斯兰教的历史痕迹仍在,但不再作为宗教信仰,而是演变为一种宗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本文认为,陈埭丁氏的特殊经历,恐不足以作为解释福建等地穆斯林走向宗族化和儒士化的充分原因。一方面,距离陈埭不远的惠安百奇郭氏未必具备和陈埭丁氏一样的经历,但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宗族化和儒士化。另一方面,在西北、江南等地,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选择通过科举而向政治权力靠拢的道路,而是走上了以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为标志的中国化道路,出现了大批阿訇经师与汉文译著家。
或许仍可以回到全球化来寻找答案。在福建陈埭、百奇等地,穆斯林依赖“宗族化”与“科举化”的“单一路径”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应与当时的全球化转型有关。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在宣德八年(1433年),到了明代嘉万年间,郑和航海建立的“朝贡全球化”体系已然衰退。而大航海以后,西方殖民全球化初露头角。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葡萄牙窃据澳门等迹象说明,当时的明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全球化的冲击,转入以防守为主的局面。洪武十七年(1384年)泉州林氏家族还有人随郑和下西洋。到了嘉靖年间,明朝廷则从主动下西洋,转为被动防御。泉州地方史多有“嘉靖倭患”记载。明嘉靖年间,倭寇袭扰东南沿海,给地方民众生活带来很大冲击。陈埭于1560年遭受倭寇袭击,倭寇上岸后并未立即离去,而是逗留了相当时日。从族谱记载可知,这一事件几乎使丁氏社区解体。倭寇将房屋尽毁,大部分族人为避祸逃到泉州城。根据丁衍夏在族谱中的记载,社区在倭患之后陷入了危机,日常生活处于失序状态,更别提一息尚存的伊斯兰教仪式生活。郭姓族谱也记载,在万历年间,郭姓亦遭“兵燹之灾”并因此而“出教”。传统的贸易路线断绝,又兼逢战乱,陈埭丁氏、百奇郭氏等泉州当地穆斯林家族由从商转为务农、以宗族强化凝聚力、以科举向政权靠拢等转变,都不失为明智之举。此外,泉州穆斯林家族与海外联系渠道断绝也是他们单一依靠“宗族化”与“科举化”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些家族之内,既未有人能像前辈一样“发航西洋”,传递与更新原有的伊斯兰信仰;也无法像西北、江南地区穆斯林那样,保持着与伊斯兰世界以及国内其他穆斯林社区的人员往来与信息交换,不断获得新的宗教典籍,更新宗教观念和仪式,为本土化的伊斯兰教注入、激发新的活力。
四、 结 语
第一,要将全球化当作视角和分析方法,而不要局限于特定现实。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固有观念,发现现实中的全球化并不局限于今天所谓的“狭义全球化”,而是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其中,中国参与和主导的全球化阶段包括:唐宋时期的“市舶全球化”、蒙元时期的“贸易全球化”以及明代的“朝贡全球化”。这几轮全球化不仅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秩序与贸易合作,也带来了文化与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深度中国化以及几种典型中国化模式的出现都与全球化有关。
第二,宗教中国化不仅不应局限于空间概念上的中国,而且需要将宗教中国化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伊斯兰教产生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互联互通过程中。应打破囿于中国史写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做法,转而从全球史和全球化的视角重新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撰写一部新的“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伊斯兰教”,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学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为主要参与者的新一轮全球化“区域全球化”呼之欲出,将再现唐宋时期市舶全球化、蒙元时期贸易全球化与明代朝贡全球化的繁盛。在此过程中,我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乃至中国伊斯兰教应有所作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