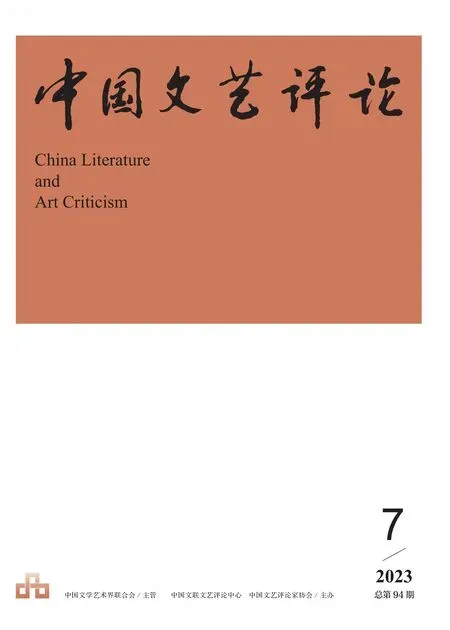互证与阐发:关于中国现代美学方法论的一种理解
■ 杜 卫
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的突出特点和贡献之一是以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材料,由此构建起中国的美学以及美学史。这种方法就如陈寅恪所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陈寅恪:《海宁王静安遗书序》,房鑫亮、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杨周翰先生指出,“用从西洋输入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化和文学”,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因为它是真正做出成绩来的潮流”。这种阐发研究的途径“应当算作‘中国学派’的一个特点”。[2]杨周翰:《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镜子和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正是由于一些前辈学者的阐发式研究,激活了我国悠久而丰厚的美学思想,中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开始建立,同时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阐发实际上也促成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美学史。因此,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实际上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融汇的背景下,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美学阐发过程中开始被建构起来的。对这种美学传统的理解必然要涉及当时中国本土问题、西方美学(内含对西方美学的中国式理解)、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含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解读)等要素。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美学传统这种“互证”和“阐发”的方法论,不仅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美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我们建设当代中国美学也具有启示意义。
一
首先,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在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意义上具有美学的开端。它的确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是,基本问题来自中国现代思想和社会现实,其核心价值是中国的,并形成了一系列本土化的美学话语。从本土问题出发和核心价值的中国化是中国现代美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王国维发表于1903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向我们展示了在急需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历史时期,美学这种“无用之学”之所以在中国诞生的历史原因。在此文开头,王国维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生而有欲,欲总得不到满足,使人受制于利害得失的计较,由此便生出人生和社会问题:“于是内之发于人心也,则为苦痛;外之见于社会也,则为罪恶。”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国维给出的方案是用“美”来消除个人过分的私欲,使人超越利害得失的计较:“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人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最后,他提出了审美和美育的价值就是“无用之用”的著名论断。[1]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18页。而这个来自《庄子》的词语也成为了穿越百余年的中国美学话语,他所创立的“审美功利主义”也成为了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影响直至今日。
蔡元培美育观念的核心也是消除过分私欲,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参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盖美之超绝实际也。”[2]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0—61页。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返回绍兴前在天津车站有一个谈话,他说道:“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我自民国元年以来,常举以告人。”[3]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0页。蔡元培倡导美育的逻辑是:审美具有消除过分私欲的作用,可以拿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提升国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增强民族凝聚力。朱光潜在《谈美》的开篇就写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页。朱光潜主张人生艺术化的逻辑是:要拯救只追求温饱和功名利禄的人心就应该从情感入手,从人生美化做起,这就需要美学。朱光潜的这个逻辑和蔡元培倡导美育的逻辑是相一致的,而源头则可以说是在王国维的“无用之用”说。
那么,为什么把“欲”作为重要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呢?这是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重要传统。从先秦开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把克服过分私欲作为修身养性的关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要害就在于去除个人过分的私欲。楼宇烈曾指出,“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提升”,“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诱惑和腐蚀”。要想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也就是“君子”,那就必须“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他把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描述成“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2]楼宇烈:《以人为本——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1—52页。儒家如此,道家亦如此;先秦如此,明清亦如此;古代中国如此,20世纪的中国亦如此。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们都还记得。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观念使得王国维等前辈学人选择了美学,并倡导美育,因为美学里面有一个“审美无利害性”命题,因为他们把这个命题理解为审美具有消除个人过分私欲的功能。[3]当然,夏夫兹博里、康德等欧洲学者所讲的“无利害性”只是指一种知觉方式,至于把无利害性作为审美所具有的消除人心私欲的功能,那是王国维等人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理论误读的结果。详见杜卫:《“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中国化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第57—61页、第74页。由此可见,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需要,诞生于从“修身”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任务出发对西学的选择。
审视我国当下的美学研究,是否还具有现代美学那种强烈的现实感和本土问题意识?这是值得反思的。
二
中国现代美学面对本土问题,采用打通古今中外之方法,试图解决当下问题。在此过程中,采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发中国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建构的基本方法。笔者曾在一本书里写道,王国维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主要不是由他的一系列美学观点奠定的,而是由于他确立了中国美学的形而上观念以及人学意义,从而实现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4]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他倡导学术和艺术独立,主张“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正因为有此观念,王国维创造了打通古今中外的中国现代美学格局。他的美学和文学研究从哲学和美学观念来分析和概括《红楼梦》的悲剧性,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形而上研究方法,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点评式”“感悟式”方法,把中国美学研究提高到形而上的理论境界。这是王国维的历史性贡献,也是中国现代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基点所在。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写道:“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2]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页。他从孔子的诗教、乐教以及引导学生游历自然之美等来阐发孔子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美育,是成就叔本华所谓的“无欲之我”、席勒所谓的“美丽之心”的美育。而且在这个阐发过程中,王国维引证了夏夫兹博里、哈奇森、康德、席勒、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孔子、荀子、邵雍等人的论述以及陶诗苏词等诸多诗文相互印证,显示出糅合中西学术的美学研究格局。[3]参见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从论旨上讲,王国维此文属于美学理论的建构,他试图建立一种美学或美育理论来解决当时中国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西哲学和美学观念以及诗文的相互印证过程中,实际上还利用西方学术阐发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美学思想,开始了中国美学史的建构。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和美育实践,但是,在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和理论加以阐发之前,这些都是潜在的,也从未被冠以“美学”“美育”之名。他对于孔子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那句断语(“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成为了对儒家美学思想和对中国美育思想的经典性总结,从此,诗教乐教就是美学的、更是美育的中国传统。
朱光潜是在国外系统学习心理学和美学的,应该对西方学术十分熟悉而且深受影响。然而,在他的论著中,即使是在介绍西方新近的美学理论时,也总是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思想和艺术的相互印证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新阐发。例如,他在国外写成的《文艺心理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化的现代美学著作,书中第一章是“美感经验的分析(一):形象的直觉”,开头介绍美感经验研究在近代美学里居于首位,接着他写道:
什么叫做美感经验呢?这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比如在风和日暖的时节,眼前尽是娇红嫩绿,你对着这灿烂浓郁的世界,心旷神怡,忘怀一切,时而觉得某一株花在向阳带笑,时而注意到某一个鸟的歌声特别清脆,心中恍然如有所悟。有时夕阳还未西下,你躺在海滨一个崖石上,看着海面上金黄色的落晖被微风荡漾成无数细鳞,在那里悠悠蠕动。对面的青山在蜿蜒起伏,仿佛也和你一样在领略晚兴。一阵凉风掠过,才把你猛然从梦境惊醒。“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你只要有闲功夫,竹韵、松涛、虫声、鸟语、无垠的沙漠、飘忽的雷电风雨,甚至于断垣破屋,本来呆板的静物,都能变成赏心悦目的对象。不仅是自然造化,人的工作也可发生同样的快感。有时你整日为俗事奔走,偶然间偷得一刻余闲,翻翻名画家的册页,或是在案头抽出一卷诗、一部小说或是一本戏曲来消遣,一转瞬间你就跟着作者到另一世界里去。你陪着王维领略“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的滋味。武松过冈杀虎时,你提心吊胆地挂念他的结局;他成功了,你也和他感到同样的快慰。秦舞阳见着秦始皇变色时,你心里和荆柯一样焦急;秦始皇绕柱而走时,你心里又和他一样失望。人世的悲欢得失都是一场热闹戏。[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这里说的几乎全是中国人的美感经验,而且还信手拈来几句古诗,把它们作为美感经验的直观呈现。这其实也是一种阐发,即用西方美学观念把中国人的某种经验命名为“美感的”,把中国传统的一些诗文解释成美感经验的表现。
接着,朱光潜介绍了一些西方关于美感经验的理论,分析了美感经验的直觉性特征,行文中又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句: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句话很可以应用到美感经验上去。学是经验知识,道是直觉形象本身的可能性。对于一件事物所知的愈多,愈不易专注在它的形象本身,愈难直觉它,愈难引起真正纯粹的美感。美感的态度就是损学而益道的态度。……梅花对于科学家和实用人都倚赖旁的事物而得价值,所以它的价值是“外在的”(extrinsic),对于审美者则独立自足,别无倚赖,所以它的价值是“内在的”(intrinsic)。[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在讲到康德的美学理论中的“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时,朱光潜和王国维一样也采用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把它翻译为“无所为而为的观赏”。[3]参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7页。这个翻译本身其实也是用西方学术来阐发中国传统思想,把道家的观念纳入到中国的美学传统中来,把古汉语所表达的思想也转换到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形态中。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除了介绍西方美学之外,还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直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而且他年轻时期讲西方美学和诗学比较多,到了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他在1941年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此文中,宗白华直接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念与方法来阐发《世说新语》,讲述晋人的审美观念,把中国美学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这一点与王国维相似,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对中国美学的阐发过程中,宗白华很少直接引用西方的理论,而是把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作为一种“前理解”的观念和方法来阐发中国美学材料。
在文章的开头,他满怀热情地写道: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这段话是对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历史性判断,评价很高:“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他作出这种评价的根据却是西方美学的基本观念:艺术独立和自由。这一点在文章具体分析《世说新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的过程中清晰可见。例如他指出,“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这种评价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却隐含着一种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和美学的观念,那就是心灵的自由是审美和艺术的至境。他还写道,“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人玄境”;“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里说的是晋人的审美情怀,然而阐发晋人审美情怀的观念却是自然作为心灵象征的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宗白华还概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标准:“雅”“绝俗”,并称之为“唯美的人生态度”,甚至把晋人的这种生活定性为“唯美生活的典型”。他写道:“当时美的标准树立得很严格,这标准也就一直是后来中国文艺批评的标准:‘雅’、‘绝俗’。”“这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于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的价值的体味和创造。”“二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2]此段所引详见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8—279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西美学的相互印证中,中国美学获得了现代意义,获得了潜在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追求“雅”的境界,拒斥“俗”的营生。而这种现代的、现实的意义,与前面所述“去除个人过分私欲”这个中国现代美学创建的初心是完全一致的。
从上述例举我们可以发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引进西方某些哲学和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发中国古代以来就有的思想,由此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美学理论。中国现代美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种美学既包含了今天我们所讲的美学原理,还包含了对西学的介绍,更可贵的是,这其中隐含着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建构,并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用现代汉语的形态加以表达,使得我国古代优秀的美学思想观念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这些成就是在没有明确学科细分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美学的“史”和“论”都是糅合在一起的,也只有糅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打通古今中外的美学研究格局。
三
中国现代美学所创立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是中国美学的宝贵财富,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美学的知识生产也具有深刻启示。
首先,这种现代美学传统包含着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本土问题意识。20世纪初,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是怀着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使命学习西方理论的。这种初心使得他们做学问总是眼睛盯着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突出的本土问题意识。美学本来就是“无用之学”,但正因为无用而生发出有用的作用,那就是可以部分消除国民过分的私欲,所以,王国维把审美和艺术的价值说成是“无用之用”。正是看中了这种特殊的功用,一些大学问家、大教育家才选择了美学,并大力倡导美育。朱光潜在《谈美》的开头就讲:“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1]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页。这番话很清楚地表明:人有出世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为了做好入世的事业,由此引申开去,谈无用之美也就是为了使人具有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胸襟和理想,做成伟大的事业。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使中国现代的美学传统总体上具有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从而具备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创的学术性的有机融合,这是中国现代美学留给我们十分可贵的方法论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其次,这种现代美学传统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作了有益尝试,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受过系统的传统经学教育,具备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他们又怀有强烈的社会介入和本土问题意识,所以,他们所创立的美学传统是与古代学术相贯通的。[2]关于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传承关系,详见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杜卫等:《心性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关系研究》等论著。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论著是写给国人看的,所以,列举一些传统的思想也有助于国人理解美学这门新学问。作为一个反例,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是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当时是写给外国人读的,所以全文几乎找不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明显踪迹。这同他写给国人读的论著形成鲜明对照。在中西美学思想的相互印证过程中,中国现代美学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学术,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激活,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美学传统。这项工作的另一个原创性成果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这些传统思想被转换到了现代汉语的语境之中,一方面具有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形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把古代美学思想与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连接,真正实现了古代美学的现代转换。这在当时可能并不是全然有意识的创造,但现在看来却是为我们从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转换提供了深刻启示和方法论借鉴。这里的要点是: 第一,语言表达方式的转换;第二,问题意识的转换;第三,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实现转换。这里就引发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美学思想的当代转换是不是必须原汁原味?首先,从文本研究的角度讲,对古代美学文本的理解应该尽可能在训诂学意义上做到准确,对思想意义的阐释也要进入当时语境,尽可能体会文本的原本意义。其次,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都不可能摆脱阐释者个人的、主观的制约,因为任何个人都被置身于历史的、传统的认知框架之中。对此,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都作过清晰论述。事实是,由于“前理解”的制约,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对传统的阐释都会不尽相同。而且,任何对传统的阐释都是当下的,也就不可能也没必要非得原汁原味。我们需要的是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而中国现代美学正是这样做的,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方法论典范。
从上述两点启示出发,反观当下的中国美学,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学科过于细分所带来的问题。这一届中华美学学会已经设置了多个二级专委会,学科性质的有中国美学、外国美学、文艺美学、审美文化、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设计美学、美育等。但是,从中国目前从事美学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看,上述学科划分意义不是很大,因为相互之间重叠很多。真正比较真实的学科划分是中国美学和外国美学,在这两个领域不仅集中了不少优秀学者,而且也产生了突出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美学和外国美学的学科分类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起到了诸多积极作用,但是,美学内部的学科细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外美学的相对隔离。当前,中国美学界出现了一大批专心研究西方美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他们有的是从国外学成归来,有的是在国内博士生阶段专注于西方美学。他们或对于西方美学的一些新出现的理论比较敏感,或对于西方经典美学论著有精深研究。这些学者的论著显示了作者较好的外语功底(和国内人文学者相比)以及对西方美学的强烈兴趣。了解和研究西方美学是很有必要的,研究西方美学的内部构成和发展轨迹也是有价值的,至少对于中国其他领域的美学研究具有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作用,对于中国美学界的国际交流也有助益。但是,这些论著多数脱离中国人当下的审美经验,缺乏本土问题意识,知识压过思想,这一点,与我们的前辈存有很大差异。这些年,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产出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中国美学的古代传统正在被建构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成绩。然而,中国古代美学如何融入当代美学学术话语和当代生活,也就是古代美学的当代转换,这个问题讨论了多年,还不断被作为研讨会的话题,实际上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关键还是外国美学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需要基于当下中国人的审美经验,需要当代社会介入意识和本土问题意识,需要中西美学相互印证和阐释。这就是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给我们的启示。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是没有明确的学科细分的,只有美学;我们今天分出来那么多学科分支,恰恰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域:美学基本理论。现在谈论中国美学理论总脱不开“美学大讨论”“美学热”和“实践美学”等话题,讨论美学理论基本构成总脱不开美、美感和艺术这个大框架。问题在于,这样的美学与我们切身的审美经验是否有真实的连接?与我们所研究的外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在学术上是否能兼容?再拓宽一点视野,我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取得了不小进展,我们的美学理论是否真正有意同当下的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分享一些共同的本土问题并展开对话?反观中国现代美学,那是贯通古今中外的美学,也是参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重建的美学。例如,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反复强调“审美无利害性”命题,并肯定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与此同时在科学界,生物学家竺可桢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话题,他甚至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求是非,不计利害”,认为中国需要培育产生真正科学的社会文化。[1]参见竺可桢:《利害与是非》,《科学》1935年第19卷第11期,第1701—1704页。这显示出与当时美学界相似的对急功近利社会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将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发展美学理论,在打通古今中外美学的大格局中,继续建构中国美学理论,作出美学应该有的思想和学术贡献。
当然,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系统的美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也是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草创期,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对于西方现代美学的现代性认识不足,对西方美学和中国古代美学的系统研究不够,甚至存在诸多误解,等等,这些都是时代、学理等局限所致。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变化,我们可以在反思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给我们的启示中,结合当下思想文化和审美经验,把美学研究推向深入,做出既能体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又能参与国际交流的中国美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