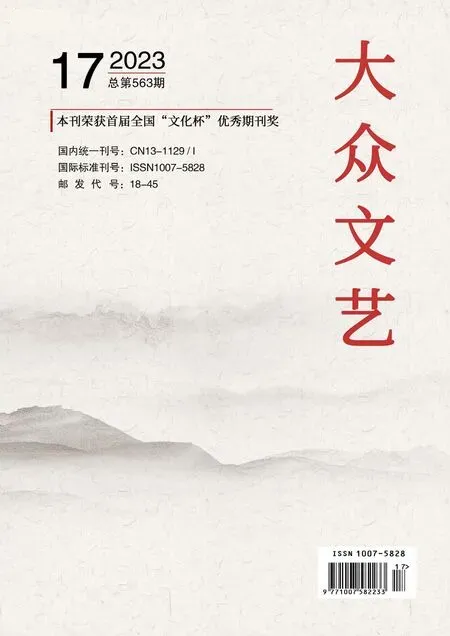数字技术下光晕再造的实现路径
孔雅琪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把艺术作品的生产时代划分为“手工复制时代”与“机械复制时代”。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大批量的复制艺术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大大增加了艺术品的展示机会,导致了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原真性与光晕都随之消失。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本雅明的时代相比又有所不同,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我们迎来了数字技术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AI等技术纷纷与艺术作品相融合,不仅拓宽了艺术作品的传播渠道,也推动了艺术作品光晕的再造。
一、光晕的原初概念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从光晕消失的角度批判了复制艺术品。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那些复制艺术品,那些大批量走技术化路线生产出的美学作品,一些直接借鉴甚至复制艺术作品、艺术风格的东西,从外观上看的确是美的也很和谐,但都缺少了光晕。光晕是本雅明独创的理论概念,数次出现在本雅明的文章当中。因此,要理解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思想、分析光晕消失的原因以及找寻光晕再造的实现路径,明确理解光晕原初概念至关重要。
光晕一词最早出自德语Aura,被译为(一个人特殊的)光芒、气息、影响作用,同时也是指教堂中圣像画上围绕着圣人头上的一抹光。例如:圣母、耶稣头顶都有一抹光晕,这便是光晕的出处。光晕在德语、英语、拉丁语中的解释都是大同小异的,无一例外地与“光”相联系,这些都在彰显着光晕中掺杂着神学的韵味。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便不难理解本雅明所说的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也正是来源于此[1]。
本雅明认为,光晕这一概念是传统艺术与机械复制艺术的根本性区别,也是传统艺术的魂之所在。本雅明初次提及光晕是在他的《摄影小史》中“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知道“此时此刻”成为显现的一部分——这就是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光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将光晕表述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切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2]本雅明指出,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根植于神学,同时独一无二性也成了光晕的本质特征。基于此,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光晕的原初概念以及光晕的本质特征“独一无二性”。20世纪开始,机械复制技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发达资本主义时期机械可以将人的手解放出来,用机器替代对艺术品进行大规模标准化复制生产,复制艺术品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最终造成了艺术作品的危机—光晕的消失。
二、光晕的消失
本雅明对于光晕消失的态度是矛盾且复杂的,在他为艺术品逝去的光晕感到惋惜的同时,也惊喜于机械复制技术带给社会的巨大变化,不仅在规模上制造了数量颇丰的艺术品,更是对人的感知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通过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关于原真性、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的论述,可以分析出光晕消失的原因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原真性的丧失
原真性是指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艺术作品只有借助的独一无二性才能够构成历史,这也是机械复制的艺术品不能实现的,复制艺术品无法再判断艺术品实际存在时间与长短,这导致了复制艺术品的历史证据难以确定,消解了艺术品内在的历史感,在此基础上,该艺术品的权威性也难以确定。本雅明认为,即便是最完美的艺术品,也无法具备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独一无二性,这是艺术品原真性的根本属性,也是光晕的本质特征,而那些机械复制技术的东西根本无法分清它的即时即地性,它随处可见,因此消解了原作的原真性。好比说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些艺术品它们都有很多的复制品,可以出现在公众建筑、走廊、书本、广告中,但是哪怕是最精细的仿制品也无法将原作的原真性复制出来,只有我们到了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卢浮宫,即时即地看到原作时,才能感受到艺术品的原真性。因此,机械复制时代的复制艺术品,他们丧失掉了即时即地性、独一无二性,也失去了独一无二性中蕴含的历史感与权威性,消解掉了艺术品的原真性,最终导致了光晕的消失[4]。
(二)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
本雅明指出“一件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是与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关联相一致的。”“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某种礼仪——起初是巫术礼仪,再后来是宗教礼仪。”[2]而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也就是光晕的价值是通过膜拜价值展现出来的,因此很容易理解膜拜价值是与神学、礼仪、传统相关的。例如中世纪大教堂的圣母像,正是为了受教徒顶礼膜拜所产生的。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对艺术品的观赏不再局限于该艺术品所在地,人们可以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去参观这些复制艺术品,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膜拜解放出来,其产品便增加了展示机会,大大地提高了艺术品的可展示性,同时艺术品丧失了即时即地性,它的膜拜价值也被推向了展示价值的一端。膜拜价值作为光晕价值的展现,在膜拜价值滑向展示价值的过程中,光晕也随之消失了。[5]但是本雅明并不认为艺术品在礼仪中被解放是一件坏事,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一件艺术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的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2]
艺术品之所以具有膜拜价值,是因为艺术品及其技术只能与当时的社会、礼仪相融合才能使艺术品存活下来,与传统相关联才能展示其光晕。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进步,艺术品技术与社会结构、传统逐渐对立起来,艺术品从膜拜价值转变为了展示价值,光晕也随之消失。因此,如何引导艺术品及其技术的发展,如何实现艺术品光晕的再造以及膜拜价值的回归,这都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三、数字技术下光晕再造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尝试通过将艺术品及其技术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找到光晕在数字时代的再造的实现路径。
(一)虚拟空间的塑造
数字技术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可以使观众穿梭在“过去与未来、感性与理性”不同逻辑的时空维度里。过去的无论是艺术品原作还是复制艺术,采取的参观方式都是直接参观的方式,但这种参观方式具有很大的时空局限性。塑造虚拟空间,应将数字技术融入艺术品中,突破艺术品原有的时空界限、拓宽艺术品参观渠道,为沉浸式交互体验奠定环境基础。例如“发现•养心殿”体验展,将高精度扫描技术应用于97件艺术品上,实现了数字复制。同时借助VR眼镜等虚拟现实设备,在虚拟空间中,观众不仅可以身临其境的观赏、挑选心仪的作品,还可以全面体验艺术品的制作过程,感受来自古代艺术作品的光晕与魅力,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体验感,增强了传播效益。除此之外,还可以将LED、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画展,打造出全方位立体环绕的艺术效果,能够使观众好似处于艺术家创作艺术品的时代或是无尽贴近艺术品、艺术场所,见证伟大艺术作品的诞生,感受来自艺术品的光晕。在这种由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空间中,观众仿佛置身于数字技术为艺术品带来的神秘光晕中。因此,艺术品可以在虚拟空间的塑造的过程中实现光晕再造。
(二)沉浸式交互体验的营造
1.感官交互体验
人类感知与认识外界事物的桥梁是感觉器官,人们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形成对事物的初步认知。以“发现•养心殿”体验展为例,该展将博物馆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突破以往展览以视觉为核心的展示方式[3]。目前,博物馆的数字文化展览,更多采用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相结合的多感官交互体验模式。
首先,在艺术作品数字化的视觉体验方面,设计师们更多将视野放在造型与色彩上。展示空间造型的复杂多变可以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新奇感与美感,此外,色彩是视觉交互设计的灵魂,会影响观众的内心感受与参观行为。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以红色作为展内的主色调,大面积的红色给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会营造出浓厚的革命文化氛围,使观众们会不自觉地将自身代入其中被革命精神所震撼。
第二,在艺术作品数字化的听觉体验方面,设计师往往会用听觉去弥补视觉艺术无法到达之境,视觉与听觉的结合为观众带来更为震撼的视听交互体验。设计师不仅可以通过对艺术品的解说增强观众对于艺术品的理解与印象,还可以运用合乎主题的背景音乐渲染气氛。例如裸眼VR《清明上河图》的设计就很好地运用了背景音乐及声音,通过声音来传达专属于北宋的时代特点与人文风格,使人身临其境。
第三,在艺术作品数字化的嗅觉体验方面,无论是回忆或是艺术作品对于观众来说都是有特定味道的。例如,当观众们闻到檀香的味道会想起故宫或是博物馆,闻到向日葵的味道会想到凡•高的《向日葵》作品等。因此,近年来设计师将嗅觉体验加入交互体验中,使观众不仅可以通过视听交互体验了解感知艺术品,更可以通过嗅觉进而唤醒埋藏在观众心底的记忆。
第四,在艺术作品数字化的触觉体验方面,这是一种作为直接的交互体验模式,能够直接影响人的感受与心理活动。在以往以参观为核心的艺术品展览中,往往放置着请勿触摸的牌子,使观众们只可远观,但触觉体验的加入大大弥补了这一处的空白。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使观众在虚拟空间中任意触摸、拿取,实现观众与艺术品之间的“0距离”,打破了观众与艺术品现实的隔阂。同时,将触屏设备应用于艺术作品或博物馆,运用信息技术的储藏功能,观众可以通过滑动触摸屏更为直观且快速地了解他所欣赏艺术品的相关信息。
2.行为交互体验
行为交互体验更加注重通过身体的互动来实现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这种交互设计在增强展示空间趣味性和娱乐性的同时还能保证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在趣味性强的行为交互设计中,可以获得全方位的身心体验,例如VR皮影戏《田忌赛马》通过趣味性行为交互设计与艺术作品相结合使观众们实现更为深层次的体验,进一步提升观众的沉浸感,更好地满足了观众对于艺术品的生理以及心理需求。
(三)膜拜价值的回归
1.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过,机械复制时代之前是艺术作品是以膜拜价值为主的,膜拜价值起源于巫术礼仪、宗教礼仪并伴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复制艺术品从礼仪中解放出来且不断增加展示机会,最终导致了膜拜价值转向了展示价值[2]。例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太多的仿制品了,人们去参观或是拥有这些复制艺术品其目的也不是单单的膜拜了,复制艺术品更多起到展览、装饰的作用。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膜拜价值的再次回归,由此实现光晕再造的可能。
2.膜拜价值的回归
首先,数字技术的巨大进步,例如全息投影、VR的应用,不仅为观众营造了感官与行为的交互体验增强其沉浸感,也会使观众叹服于数字技术的强大魅力。其次,艺术作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例如,“发现•养心殿”体验展更能提供给观众家国情怀等情绪价值,促进中华文化的推陈出新,增强观众的文化崇拜与文化认同。借助数字技术可以使观众肆意穿梭在过去与未来[3]。通过在虚拟空间的交互体验,不仅使观众们叹服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更可以增强观众对艺术品的崇拜,这些都可以推动膜拜价值的回归并赋予膜拜价值新的时代内涵。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使观众超越时空的界限,也推动了艺术品收获了教育价值、社会价值等附加价值,实现多元价值共振,加速了艺术作品与数字技术与时代相融合,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助力艺术作品光晕的再造。
结语
本雅明认为,每一个艺术品都有其独一无二性,都有其光晕,不过是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以及膜拜价值转向展示价值的过程中,艺术品的光晕消失了。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依旧希望艺术品再次散发其光彩,实现光晕再造。在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将技术与艺术作品融合,通过塑造虚拟空间、营造交互体验与推动膜拜价值回归都会让本身被展示价值所掩盖的艺术作品的光晕再现。与此同时,重建艺术作品的光晕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任务,事关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