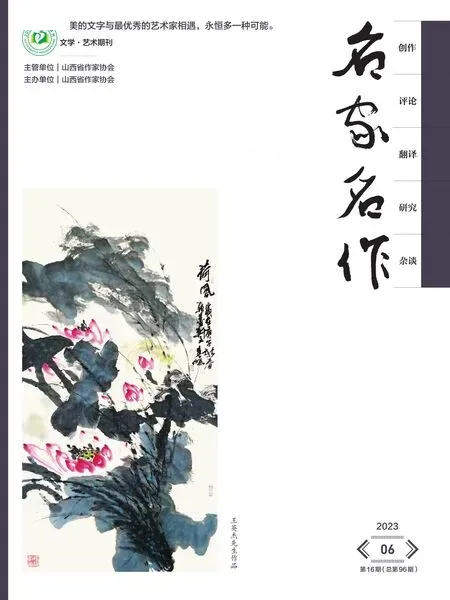新生代马华小说中马来本土语境下“中国性”的呈现
陈瑶琼
在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中,“中国性”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性’本身是弥漫权力的话语,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意义建构”[1],“中国性”决定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中国性指的是中国特质、特色与特性,“主要是指向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中国的哲思,如儒、释、道思想”[2]。“它强调的是它在文化想象上的‘纯粹性’。因为中国性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能动客体,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其大部分特质得以保存。然而,在马华的想象中中国性更显出了其纯粹性。”[3]“中国性”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中国文化,朱崇科教授把中国文化分成三个维度,第一重是相对古典的中华文化;第二重是 20 世纪以来(或现代)的中华文化;第三重是指中华文化在不同区域变异后仍然具有较强中国性的本土中国性文化。[4]
1995 年,以黄锦树为代表的新生代马华作家发起“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的论争。黄锦树指出,“中国性”一直以来是马华文学的重要创作灵感源泉,但另一个方面也成了马华文学的负担和桎梏,让文学具有了“表演”性质。[5]如何处理“中国性”与马华文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开拓马华文学本身的主体性,是新生代马华作家在写作实践中不断探索的方向,他们调动“原乡想象”,将“中国性”融入离散书写中,再现了马来西亚华人离散漂泊经验与原乡文化无法切断的关联。
一、马来本土语境中的中国意象
黄锦树是旅台马华新生代代表小说家,他试图打破陈规,努力将马华文学由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雨》是黄锦树继《死在南方》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短篇小说集。小说集由16 个短篇故事组成,围绕南洋橡胶林中一个马来华人家庭展开,每个故事独立成篇,又共享着相似的背景、人物和情节。小说集的主人公是一名叫“辛”的小男孩,他的一家人生活在胶林深处,以割胶为生。胶林潮湿多雨,充斥着各种恐怖意象和难以言说的秘密,失踪与死亡贯穿整个小说集,小说集中的故事和人物时刻被包裹在死亡和失踪的阴影之下。黄锦树对“死亡”和“失踪”的痴迷其实是在暗指马来西亚华人的“失语”和“失根”状态。1942 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全境,直至1945 年日本投降,马来西亚才脱离日军控制。战争结束后,马来西亚的国家政策使马来西亚华人很难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而重返故土的愿望也几近幻灭。马来华人处境十分艰难,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依靠苦力谋生。《雨》中所呈现的华人家庭都是支离破碎的,父亲离奇失踪或死亡,年幼兄妹离奇夭折,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惨生存处境。他们背井离乡,漂泊异乡,无法获得本土认同,又与母国切断联系。小说集中“父亲”的失踪,在某种程度上暗指马来华人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小说中反复书写的“父亲失踪”象征着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丢失的焦虑和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黄锦树虽然倡导“去中国性”,但是用中文写作就无法逃脱中国文化的浸润,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象不时出现在黄锦树的小说中。在《雨》这一短篇小说集中,“鱼形舟”这一意象反复出现,“鱼形舟”让读者联想到“神舟”,“神舟”与“中国”可以作为互涉的文化隐喻,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想象空间。在《老虎,老虎》中,辛的父亲在沼泽深处偶然发现了一只独木舟;在《树顶》中,父亲乘坐单薄的鱼形舟离家,消失于茫茫大雨中,父亲离奇失踪后,鱼形舟被发现倒挂在一棵枯树上;《水窟边》中的鱼形舟随着死去的人一起神秘消失;《另一边》中的鱼形舟成为兄妹二人在茫茫大雨中出逃的“诺亚方舟”;《土糜胿》中描述了一条自父亲死后被白蚁啃食的鱼形舟,形态可怕怪异。在这些对“舟”的描述中,其共同点是“舟”都是残破不堪,无法正常使用的。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舟”不仅仅是通往故国的一种交通工具,更指代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记忆,鱼形舟的破损与消失象征着马来华人重返家园的愿望的渺茫。
第一代和第二代马来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执念,而第三代马来华人则呈现出一种试图拆解和颠覆原乡情怀的倾向。新生代马华作家黄锦树也试图用鱼形舟的残破来解构“中国性”。《归来》这一故事中,二舅和二舅妈因为孩子夭折,便用一艘中国古沉船的废木雕塑成一个婴孩形象,以慰藉他们的丧子之痛,满足他们对得子的期待,而文中“我”和“妹妹”却将这一木雕扔进火堆中付之一炬,这一情节意味着对以“我”和“妹妹”为代表的第三代华人而言,原乡记忆几近空白,原乡想象也已失效,他们所有的只是关于橡胶林的片片回忆。
黄锦树的另一短篇小说《鱼骸》也呈现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意象。小说主要有两条叙事主线:一是对哥哥的死的追忆,二是主人公“我”的成长历程。小说通过展现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显示了对中国原乡文化既向往又抗拒的矛盾情感。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龟,“龟”及“甲骨”一共在小说中出现23 次,贯穿整部小说。“龟”这一意象带有明显的“中国性”。作为四灵之一,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古代,每当遇到祭祀或其他重大活动时,人们会依靠龟甲燃烧后的裂纹来预测吉凶。到了现代,龟往往有长寿的寓意,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自保、长寿、智慧、防御、神秘、生殖崇拜等诸多意义,这一意象本身就散发着浓厚的“中国性”。
小说开篇便引出有关龟甲的几段中国古文,这一意象本身就极具中国文化意味,且“龟”与“归”同音,让读者不禁联想到“归属”“回归”或“归途”等,小说开篇就暗示了浓厚的乡愁情怀。小说主人公自小跟随哥哥一起长大,对哥哥十分崇拜。从小,哥哥就多次告诉他有关中国的故事,表达出回归中国的热切渴望。哥哥因意外丧生后,主人公在哥哥的遗体旁找到了一堆龟甲。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龟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大的生物,能灵活往返于陆地与水域之间,甚至被赋予穿越的神秘能力。哥哥死后,他的骸骨与龟壳堆积在一起,这其实在暗示哥哥最后的归属,哥哥的心魂早已借助龟的灵力飞越南洋这片土地,飞往他向往已久的神州大地了,只留下一堆躯壳在沼泽地里。
龟骨及其上面的文字符号是典型的中国意象,主人公对龟骨的痴迷其实在暗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主人公在潜意识里埋藏着对千里之外的中国的无限向往与着迷。主人公在高中时代,哥哥的同学“长白山”曾经给他看过一本破旧的记载着中国甲骨文的书,告诉他这些珍贵的甲骨文已经被帝国主义者掠夺。从那时起,主人公便对甲骨文萌生热爱,立志要研究这一中国古老文字。主人公在异乡研究室发现残破的甲骨碎片得以保存时欣喜若狂,他对研究甲骨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废寝忘食。对龟骨的痴迷亦是他的精神支柱,每当彷徨不安时,抚摸龟骨及其上面的文字便能给他带来安宁和慰藉。主人公埋头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中,不问世事,当同乡问他为什么不返回家乡为家乡做贡献时,他内心深处充满矛盾。主人公就像龟一样,虽然成长于南洋,原乡却在中国,他的命运就像龟壳分离后无法还原一样,无法回头。
这篇小说是黄锦树对“中国性”的矛盾态度的写照——拒绝中国性,却又无法脱离它。马华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和束缚,黄锦树认为只有“去中国性”才能让马华文学焕发新的生机。黄锦树生长于马来西亚,之后求学并定居于台湾,“‘文化原乡’‘地缘故乡’与‘流寓异乡’的三乡纠葛造就了在台马华作家身份的复杂性和独特性”[6]。三重离散情境使黄锦树对马华文学始终保持清醒和谨慎的态度,他对马华文学中的“中国性”始终保持警惕,意识到马华文学在“中国性”的包裹之下可能会产生的主体性缺失。黄锦树努力寻求一种重建马华文学的写作策略,试图用离散经验和离散情境,结合原乡想象,将“中国性”拆解并融合进离散书写中。在《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黄锦树把“橡胶林”和“鱼形舟”等极具“中国性”的意象融入离散书写,营造出“雨林乡愁”的氛围。由此看来,“中国性”既是阻碍马华文学自身主体性发展的巨大障碍,又是文学创作中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这一矛盾也体现在众多新生代马华小说家的创作过程中。“中国性”与马华文学的“本土性”和“现代性”永远不可能割裂开来,“中国性”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镶嵌在马华文学中,与其“本土性”和“现代性”并肩而行。
二、本土立场下的中国原乡书写
在华文小说中,“原乡”一般指“中国”。“原乡书写”一般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书写者必定是离开故乡的,对故乡有一种距离感;二是作家的书写风格呈现出记忆、缅怀及伤感的充满乡愁的基调。[7]马华新生代作家中很多都有离开故土、外出求学或旅居欧美的经历。他们离开马来西亚后,书写主题依旧离不开大马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这种远距离地对故乡进行书写造就了他们想象与真实故乡的差距。而作为马来华人,他们的血液中始终涌动着中华文化的因子。他们自小在马来西亚长大,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祖辈父辈口中的遥远故事,他们对中国只留有模糊的、碎片式的概念,因此他们的书写中也经常会出现对中国原乡的想象式的书写。因受到大马本土情结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原乡书写在全球华文书写中显得新奇又独特。
新生代马华作家很多在我国台湾接受高等教育,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下文以三位作家为例来阐述新生代马华小说的中国原乡书写。李永平的原乡书写更偏向于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文化观。李永平对汉字的使用有着深深的迷恋,他对汉字的使用往往要经过精心提炼,喜爱使用繁体字和生僻字,而他对汉字的着迷其实是源自童年时代殖民地时期西方殖民者对汉字的侮辱和贬低。他回忆说,儿时在南洋读书,西方殖民者对中华文学和汉字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和轻蔑,这让年少的李永平印象深刻,学校的神父和修女称汉字是“撒旦的符号”,教育孩子们要“远离那方块字的诱惑”[8]。日后写小说的过程中,李永平总是设法用特殊的汉字来传达中华文化,他的作品犹如一座座文字迷宫,一个个汉字在他的精心堆砌之下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感。
潘雨桐的原乡书写侧重中国文化的古典韵味。在《纽约春寒》《烟锁重楼》等作品中,潘雨桐描述了留学生的生活日常和情感生活,表达了他们在不同文化撞击下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的思考。潘雨桐受琼瑶小说的影响很大,他的小说《天凉好个秋》是一部仿写琼瑶《一帘幽梦》的小说,有着琼瑶式的纯情叙事,然而小说情节却不像琼瑶小说那么浪漫梦幻。作者讲述了一名留美女硕士在生活重压之下的情感故事。主人公坚强独立,不能接受西方社会视结婚离婚如儿戏的价值观,然而又不能坚守自己与男友的爱情,理想中的爱情最终也没有到来。因为父亲重病急需一大笔医疗费,她被迫接受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酒店老板的追求,心中对现实残酷无限感慨。这部小说把中华文化中的婉约意境和传统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塑造了鲜明而现实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来折射他对中国原乡的想象和情感。
张贵兴的原乡书写侧重“寻根”,他擅长在文本中想象和重构华人的南洋历史。他的代表作《顽皮家族》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蛮荒的婆罗洲,整部小说将各种离奇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浓厚的幻魔现实主义色彩。身怀武林绝技的父亲、与父母亲结怨的海盗、顽龙的五禽形意术、雨林抗日的传奇经历、家族内部的爱恨情仇,这些都写得肆意奇特,读完犹如置身于一座奇幻迷宫之中。
综上所述,新生代马华作家由于缺少直接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概念都是模糊和碎片式的,当他们离开故乡马来西亚来到我国台湾,感受到更多的中华文化,但他们对中国原乡书写的现实层面始终保持谨慎的状态,而在文化层面上想象丰富,取得了很高成就。新生代马华作家对中国和汉语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们被华文文学中的“中国性”和“现代性”所吸引,而台湾经验对于他们而言,其深刻程度和影响力始终不及他们在马来故乡的本土生命经验,因此,新生代马华作家的作品中将中国性、本土性和现代性完美融合在其作品中。他们的中国原乡书写表现出突出的马华式特征,新生代马华小说中呈现的“中国性”是基于马来本土情境下的“中国性”,而这也是让马华小说在众多其他区域华文小说中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